#人形芝居 風流蝶花形
Text

人形芝居 風流蝶花形
アトリエ ジュサブロー
写真・海老沢一郎、題字・飯塚康行、レイアウト・安彦勝博
監修・辻村ジュサブロー
原作=泉鏡花、脚本・演出=辻村ジュサブロー、語り阿部寿美子
#人形芝居 風流蝶花形#風流蝶花形#jusaburo tsujimura#辻村ジュサブロー#海老沢一郎#飯塚康行#安彦勝博#kyoka izumi#泉鏡花#anamon#古本屋あなもん#あなもん#pamphlet#パンフレット
62 notes
·
View notes
Text
小點心,雞尾酒會
外燴
外燴
如果您需要聖克勞德及周邊地區的餐飲服務,請隨時聯繫我們。 您也可以點擊下方查看我們的菜單和價格。 這些俗氣的棒子在兒童和成人中很受歡迎,尤其是與番茄湯射手搭配使用時。 這道簡單的開胃菜在聚會上很受歡迎,只需要一些主食。 另外,把蝦做成蝴蝶狀給人的印像是一道花哨而昂貴的菜。 無論您使用自製肉丸還是冷凍肉丸,這道開胃菜都是一種易於上菜、適合大型聚會的開胃菜。
請記住,這些僅供參考,始終備有充足的瓶裝水,為所有人營造安全舒適的環境。 Sweetwater Catering 以實惠的價格為您提供酒吧、調酒和茶點套餐,供您舉辦假日活動。 “如果沒有 Serendipity 的能幹、出色的員工,我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無論是為客人再喝一杯雞尾酒,還是準備額外的開胃菜,無論需要做什麼。 廚房總是比他們發現時打掃得更好,該區域放回了他們來時的位置!
炸丸子是由土豆泥和培根製成的油炸丸子,裡面夾有融化的奶酪。 說到罪惡款待,他們絕對名列前茅。 這些伏特加果凍味道鮮美,會給您的客人帶來恰到好處的嗡嗡聲! 它們肯定會為任何聚會增添更多色彩和刺激。 您只需將帕瑪森芝士塗抹在抹了油的烤盤上,在上面放上切半的小土豆,然後放入烤箱。 你基本上只是把所有的配料倒在切成薄片的土豆上,讓烤箱發揮它的魔力。
無論您是舉辦小型午餐會、親朋好友大型派對、迎嬰派對還是公司活動,這些開胃菜一定會給您的客人留下深刻印象。 蘸醬三重奏——包括鷹嘴豆泥、酸奶黃瓜、烤紅辣椒蘸醬、皮塔餅片、芹菜條 亞洲雞肉餃子 - 嫩餃子,裡面塞滿蔬菜和雞肉,用平底鍋輕輕煎炸,佐以亞洲蘸醬。 它很容易準備,做三明治味道很好,而且通常很適合自助餐。 與土豆沙拉、玉米棒子或其他令人垂涎欲滴的燒烤配菜之一一起食用。
婚禮、家庭餐飲
我們可以製作一系列相互補充的獨特菜單,並在整個過程中與單一供應商合作帶來無縫便利。 如果婚禮上有客人不希望看到的景象,那很可能是餐車。 雖然近年來這種趨勢越來越流行,但流動餐車仍在挑戰極限,為您的婚禮增添獨特魅力。 讓得梅因堡酒店富有創意的餐飲團隊為您的活動和特殊場合提供卓越的當地美食。 在愛荷華州得梅因市中心舉辦令人難忘的婚禮、招待會、宴會和派對。
事實上,他們激發了對我們公司的信任,以至於我們幾乎只使用 Tidewater Catering 的服務。 以您的文化為靈感的婚禮美食將傳統提升到一個全新的水平,例如這款由 Chef Chai 製作的色彩繽紛的夏威夷風格水煮梨沙拉。 走狂歡節風格,用紙筒裝大蒜味的炸薯條呈現給您的客人。 試試定制的煎蛋捲吧,就像這個由 Hamby Catering 製作的吧,您所愛的人可以用他們最喜歡的食材定制。 迷你奶昔搭配巧克力曲奇蘸醬,將在您重要的一天結束時滿足每個人的甜食需求。 Fernbrook Farms 的旅館為這對夫婦和他們的客人提供這些甜點,讓他們盡情享受舞池。
我們的最新成員 The Oak Room 非常適合舉辦更私密的招待會或彩排晚宴,同時我們還可以在戶外空間舉辦更大型的婚禮。 大理石牆壁和精美的拱形窗戶是您舉辦歷史性活動的完美背景。 在婚禮上展示您的個性的一個好方法是提供招牌飲品。 快餐車,尤其是與更傳統的餐飲選擇相比,往往極具成本效益。 根據 The Knot 的數據,餐車人均成本通常為每人 10 至 20 美元,而傳統餐飲平均每人 70 美元。 因此,將自助餐或坐式餐飲換成快餐車選項時,可以節省大量資金。
因此,儘早計劃以確保您能夠安排該地區的頂級餐飲公司。 通過提早計劃,您將能夠提前發出邀請。 客人會喜歡這個,因為他們將能夠在這個繁忙的季節做出相應的計劃。 活動規模越大、越複雜,東道主就應該越早開始這個過程。 即使沒有計劃假期派對,假期有時也會讓人不知所措!
派對食物介紹
必須計劃菜單,使其與 F 的主題相得益彰 提前製作您的播放列表並選擇您喜歡的歌曲——畢竟這是關於歡迎客人進入您的領域——只要它們會讓您和您的客人感到快樂和放鬆。 提供一些不同的選擇是很好的,這樣客人就可以玩 D.J.如果音樂不適合晚上。 想像一下您正在召集的小組,並考慮如何將他們安排在一起。 如果您找不到適合您的任何客人的鄰居,請考慮將他們從名單中刪除或邀請其他人成為他們的好同桌。
你的應該反映你晚上的審美和你希望交流的正式程度。 如果您正在籌劃更正式的晚宴,請發送打印或手寫的邀請函。 對於更隨意的活動,可以使用電子郵件或電子邀請。 盡快發送邀請——你給客人的通知越多,他們來的可能性就越大。
該文件包含詳細的總賬信息,還可以盡可能頻繁地重新導出以捕獲對 Caterease 事件所做的更改。 令人驚嘆的房間選擇嚮導甚至可以讓 Caterease 為您選擇最合適的房間——甚至關心您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寶貴的空間。 縱觀歷史,飲食一直被視為一種社交活動。 一家人圍坐在餐桌旁分享故事,同時享用精心準備的飯菜。 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我們吃的東西變得更加公開。
我們專注於提供完美的活動和無可挑剔的服務,每個細節都得到無縫執行。 使用最新鮮的食材烹製美味的高品質食物;床單很乾淨,佈置也很細緻。 我們的使命是提供多樣化的菜單選擇,創造精緻、平易近人、融合精緻風味、呈現令人眼花繚亂的食物。 如果您計劃舉辦小型活動,則不太可能需要食物雕塑、冰雕或更精緻的展示。

可堆肥外賣容器
您可以通過聊天功能或電子郵件提交查詢,並查找有關批量訂單和交貨時間的詳細信息。 查看其他客戶的想法並聯繫批發供應商,以了解有關定制和其他業務選項的更多信息。 當您在 Alibaba.com 購物時,一切皆有可能,而且價格低廉,交貨快捷。
您的食品包裝向客戶展示您關心什麼,進而向客戶展示您不關心什麼。 這意味著您的外賣包裝在設計時需要考慮到便利性。 它應該重量輕、易於攜帶且���重新密封(因此不需要一次吃完)。 漢堡王是最早接受這種簡約美學的大型餐廳品牌之一,通過用更現代、簡約的設計重新包裝其外賣包裝。
尋找簡單而時尚的展示和包裝的普通白紙和卡片餐廳包裝用品,或選擇與您的企業品牌相協調的彩色盒子。 當您也有零售業務時,為高端產品提供紙巾、絲帶和標籤時,盒子的效果非常好。 或者,如果您正在尋找儲物箱和移動箱,厚卡片箱可能是您的首選,尤其是那些可折疊和可堆疊的卡片箱。 Karat 食品容器以綠色、白色和粉色出售,並有多種尺寸可供選擇。 紙質食品容器非常適合盛放冷熱物質;但是,不建議將其用於煮熱湯或飲料——最高溫度 a hundred ninety °F (88 °C)。
餐飲職位描述樣本
似乎正在發生更大的專業化,餐飲服務商在美食和產品方面更加謹慎地選擇他們的領土。 在準備好所有餐桌、餐位佈置、服務區和食品並且客人準備好用餐後,可能需要餐飲人員提供食物。 在大多數正式活動中,都會提供餐桌服務,餐飲服務員會逐道將餐點直接送到餐桌上,同時在兩道菜之間清理丟棄的盤子。 在提供自助式餐點的休閒活動中,可能會要求服務員為在食品服務站排隊的客人提供某些食物。
建議更新此職業職位以反映您組織的獨特情況和餐飲服務商的職責。 遵循行業慣例以確保食品可以安全食用,包括了解適當的食品處理技術、了解適當的溫度等。 查找餐飲服務商職位描述示例,您可以重複使用這些示例以加快招聘速度,或者使用我們的模板創建您自己的模板。 餐飲服務商的薪水取決於他們的教育水平和經驗、他們承辦的活動類型以及活動地點。 與廚師/餐飲業的平均工資相比,助理廚師職業的收入通常較低。
這可能包括通過他們的州和縣獲得適當的許可、獲得任何必要的許可、應收賬款和應付賬款、處理稅收和管理客戶文書工作。 個體經營的餐飲服務商執行行政職責的時間與準備食物的時間一樣多。 根據州的指導方針,雇主可能需要食品處理人員的證書。
廢物管理
通過向食物銀行、流動廚房或庇護所捐贈食物來幫助您的社區。 盡量減少您購買的食物數量或減少菜單上的項目數量。 是食物浪費的一大來源,客戶越來越多地尋找能夠證明 ESG 資質的酒店。 土地在農業中的利用方式造成了大規模的食物浪費。 用於種植未食用穀物的耕地造成了每個地區 4-15% 的食物浪費。
許多區域必須每天徹底清潔,而其他區域則需要定期維護。 必須每天對廚房、咖啡區或任何食用食物的空間進行消毒。 EPA 報告稱,室內空氣質量是美國人類健康面臨的前五大風險之一。 該機構發布的研究表明,室內空氣中的污染物含量通常高於室外空氣中的污染物含量。 即使是經營得最好的企業也可能存在隱藏的室內空氣質量問題,從而導致生產力下降。 眾所周知,受污染的空氣對人類健康構成威脅,但許多企業主可能沒有意識到不健康的室內空氣的重大影響。
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現在禁止每週扔掉超過一噸的食品垃圾。 因此,餐廳正在尋求其他解決方案,例如首先減少浪費和加強食物捐贈。 Winnow 開始使用 AI 實現食物垃圾管理自動化。
辦公室的 20 個公司午餐餐飲創意
Saint Germain Catering 的首要任務是確保我們的客戶吃得健康並始終保持健康。 我們可以提供無麩質或無素食或素食或其他特色菜單,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為您和您的家人準備的美味節日大餐。 在您與家人放鬆的同時,讓聖日耳曼為您做飯並送來節日大餐。
如果你真的想讓你的團隊說“法國萬歲! ”只需添加一些經典的炸薯條和加入香草的蛋黃醬即可。 米娜一直想擴大她的業務並確保它保持領先地位。 早在 1999 年,Saint Germain Catering 就開始經營企業餐飲,如今它提供全方位服務的餐飲。 增長歸功於 Mina 致力於讓業務每天都變得更好。 Mina 通過參加有關美食、裝飾和設計的專業研討會來了解最新動態,以保持業務的相關性。
如果您的辦公室定期參加週末 5Ks 和慈善跑,甜甜圈是周一早上等待的完美公司午餐創意。 它會給你們當中那些特別積極的人一種應得的待遇,更重要的是,會讓那些不太積極的人覺得他們做了一些值得的事情。 我們不會撒謊——素食並不是那種容易推銷的辦公室餐飲理念——即使你的辦公室裡到處都是優秀的銷售人員。 我們不需要指出甜點作為現場含糖零食的好處來保持相機轉動。
1 note
·
View note
Text
22/6 fav Movies

6月はあんまり映画見なかったしな…とダラダラしてたら早速遅れてきたお気に入り映画まとめ。(多分梅雨で死んでいたんだと思う)
最近は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チックだったり、現実味の強い作品ばかり選んでしまっているので、この夏はファンタジー感強い何かに包まれたい気分です。
▼22/6のラインナップ
チェン・カイコー 『さらば、わが愛/覇王別姫』
早川 千絵 『PLAN 75』
ホン・サンス 『あなた自身とあなたのこと』

1.チェン・カイコー 『さらば、わが愛/覇王別姫』
レスリー・チャンが放つ、心労がにじむ美しさみたいなものが大好きで、初めて観た時からこの作品の虜です。
私が持ってるDVDはおそらくデジタルリマスター版で、Bunkamuraで35mmフィルムで上映するとのことなのでせっかくなら行こうと思ったのですが、びっくりするくらいチケットが取れず!
チケット購入が解禁される0時を待って取らないと無理で、まるでどこぞの有名ブランドの福袋状態でした。
当日映画館に行ってみると、場内から聞こえる会話の半分以上が中国語もしくは英語という感じで、謎が解けた…レスリー・チャンの人気はやはり凄まじいのね。
上映後拍手が起こったのも、一体感があって…なんかとてもよかった。(ね、よかったよね、って言葉がわからなくても呼応した感じ)
ストーリーとしては、京劇の古典作品「覇王別姫」を演じる2人の愛憎の人生を描いた作品なのだけれど、今回改めて鑑賞して、女役であるレスリー・チャンが男役であるチャン・フォンイーに向ける激しい執着/愛(どこか歪んだ)は近年の作品だとあまり描かれない類のものだな…と感じたりした。
レスリー・チャンが演じる程蝶衣は、幼い頃に母親に劇団に捨てられて、劇団でも激しい体罰を伴う稽古を受けながらスター役者へと成長する。そんな幼少期の心の支えだったのが、チャン・フォンイー演じる段小楼で、「覇王別姫」の物語にリンクするような形で、彼に深く愛するようになるという感じなのだけれど。
不遇の幼少期を過ごすことで、どこか依存するような形で人を愛するようになり、その人自身の成長というよりは、愛憎劇にスポットライトを当てた作品って、最近だとあまりないよな、と。(実際に程蝶衣は「覇王別姫」の物語と激しい愛に囚われたままラストを迎えま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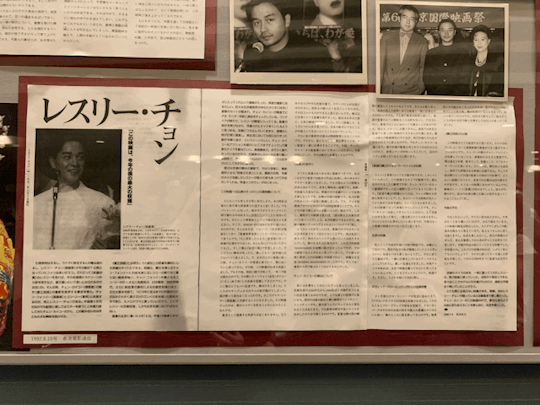
レスリー・"チョン"!
なんか最近の作品って「自己との向き合い方」「(恋愛ではない)唯一無二の人との関わり方」みたいなものが主題として取り上げられることが多くない?(私が好き好んでそういう作品ばかり見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
過去を乗り越えて自分が成長していく、ヘルシーになっていく感じ。(もちろん、そこには他者から差し伸べられた手があったりする)
自分ひとりでヘルシーに立っていられる人と人が作る愛というのは、面が滑らかで、玉みたいで、ぶつかったりこすれたりしても、せいぜいさざなみのようなイメージなんだけれど。
「さらば、わが愛/覇王別姫」で描かれる渇望するような愛は、まさに"愛憎"で、ゴツゴツとした荒々しい何か。でも何かの拍子にカチッと凸凹がはまったときに途轍もないエネルギーが生まれたりするもののように思えるのです。
私は自己を内省するみたいな映画も好きですが、切実で顔をくしゃくしゃにして泣くような愛が描かれた映画も好き。(そして最近は供給が少ないので見られてよかったなあ…という話です)
そして、レスリー・チャンには愛憎/切実/影という言葉が似合うので…!影のある愛を渇望する人間を演じたら右に出る者はいないと思います。顔の表情ひとつから指先の動きまで計算されていて、緊張感があって、存在自体が美しさそのもの。
「さらば、わが愛/覇王別姫」は日本での上映権が切れてしまったみたいで、サブスクにも今はないみたいなのですが、同じくレスリー・チャン主演、チェン・カイコーが撮影した「花の影」もとても美しいお話なので、見てみてください…(どこかのサブスクにあるはず!)
🔽2023/8/30に4Kで再鑑賞しました🤱
「(蝶衣は)芝居と現実、男と女の区別がついていない」by那。京劇の客層は変わっていく、初めは熱狂的な市井の人から日本軍になり、中国軍になった。小楼も変わっていく、自信家で覇王のように尊大だった彼はコンリーという守るべきものができたり次第に堕落し、時代の流れを仕方ないと受け入れて順応した。コンリーも変わった。初めは高飛車な女郎だった彼女は小楼を愛し、彼を立て、どこか女将のような貫禄も感じ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蝶衣だけが変わらない、ずっと変わらない。まず日常/舞台の様子をとってもそう。女形?が染みついているのか、普段から手は前で柔らかく重ねていることが多く、指先の動きまでしなやか。小楼を見る時も一旦下を向いて見上げたりする(少し伏目がちになる仕草が色っぽい)。あと、客席からの妨害があっても演技を辞めない様子は、舞台と客席で断絶が起きてるみたいだった。主に京劇絶世期?の193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の1960年代までとかなり長い年月を駆けていく作品だけど、蝶衣のアイラインの角度はいつも正確だった。蝶衣は小楼に「永遠の話をしてるんだ」って言ったけど。何か新しいエッセンスを加えない限り京劇においては同じ演目が繰り返され、「伝統、変わらないこと」がその真価である。変わらないことが正しい京劇(少なくとも蝶衣の中では)と、変わらない、変われない蝶衣は表裏一体。京劇の芸術性も虞姫として覇王を愛する気持ちも小楼への執着に似た何か…も永遠のうちに閉じ込めた蝶衣は京劇そのものだった。

2.早川 千絵 『PLAN 75』
少子高齢化がより一層進んだ日本で、75歳以上の高齢者に生死の選択権が与えられる法案、通称「PLAN 75」が可決・施行された社会を描いた作品。参院選前に見たこともあり、鑑賞後は結構ぐったりしました。
公園の炊き出しの隣に「PLAN 75」のブースが設置されていたり(しかも「住民票がなくても利用できる」なんて言葉が書いてある!生きるためのセーフネットからは漏れてしまうことが多いのに…)、生活保護への相談ブースの隣に「PLAN 75」の相談窓口があったり。職員の笑顔の裏に"国のエラい人々"の真意が透けて見えていて、気持ち悪いと感じざるを得なかった。今の日本社会を静観している人ならではの着想だな…と感じたし、虚構と現実味が巧妙に共存している。
「あなたも苦し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私も苦しい」と口を開けば言ってしまいそうになる。そんな心境の中で「こいつよりは上、こいつよりは自分のほうが生きる価値がある」とか…誰かを貶めることで自分を正当化したくなる。「PLAN 75」が施行された世界の根っこにも今の日本の根っこにもそういう感情があって、そういう蔑みはおそらく誰が誰に面と向かって語ることもなく育っていくものだと思う。(誰もオフラインでは言わないから、ネットに垂れ流されて)
今不遇だと感じることは決して弱者の存在のせいじゃないから、ということを忘れず、理性を持っていたい。
3.ホン・サンス 『あなた自身とあなたのこと』
JAIHOでホン・サンスの日本未公開作品が特集されていたので、見てみたうちのひとつ。
しがない画家のヨンスが、恋人のミンジョンが男と深酒をしていたという噂を耳にし、問い詰めて喧嘩になったことでミンジョンは姿をくらましてしまう。一方、ヨンスが住む延南洞では、ミンジョンと瓜二つの女性がミンジョンを知る男たちに声を掛けられ酒を飲み、口説かれていた。しかしそのミンジョンにそっくりの女性は自分はミンジョンではないと言い張る。ヨンスもミンジョンにそっくりの女性と街で出会うが、やはり自分はミンジョンではないと言い張る、という感じのストーリー。
「あなたとお互いを知る前に戻って出会い直す」っていうファンタジーにどこか憧れがあるので、結構珍妙なストーリーではあったんだけど、好きでした。私は死にたいと思うことはないんだけれど(なぜなら痛みを伴うから)、「これまで出会ってきた人の記憶から一旦消えたい(=それは死?)」と思うことはあるから。
あと、主演のミンジョンを演じているイ・ユヨンさんが魅力的すぎます…ホン・サンス作品といえば、キム・ミニだけれど、お二人ともうちに秘めたる色気が半端じゃありません。
ホン・サンスの映画って、ウォン・カーウァイの作品と似て、なんか集めて回ってみたくなる感覚がある気がします。新作の「イントロダクション」と「あなたの顔の前に」は劇場では見られなさそう…!どこかのサブスクにやってきてくれると嬉しいけど。前作?の「逃げた女」はとてもとても好きでした。
暑いしコロナの感染拡大が続いているので、私は今年の夏もおとなしく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りそうです。あなたはどうでしょう!
読んでいる人が多くないと思うから言うけれど今は実家に帰ってきていて、しばらくこちらにいるつもりです。東京を離れると夏がより夏らしく、風がより風らしく吹いていきます。あと、サブスクでいよいよ曲をリリースできそうで、楽しみというより心がザワザワしています。
❤︎me→https://lit.link/asaiii
0 notes
Text
MAGIC HOUR with Eiji Akaso & Keita Machida 2021/2/27②
ーーまだまだ足りないと思いますので、ぜひ色々コメントしてください。次のコーナーに参りましょう「フォトストーリー!」(Photo Story)イエー!
赤「イエー!」【両腕上げて】
町「いぇー。ははははっ」
ーー撮影中のオフショットの写真を見ながら、その時のエピソードを聞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赤「はい」
ーー最初の写真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メリーゴーラウンドで二人並んで座ってる写真
赤・町「ああ~~(笑)」
町「メリーゴーランド」
ーーこちら何の時の写真なんですか?エピソードがあれば教えてください。
町「これ遊園地デート…の話があった回があ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ーーデートの練習ですね。
町「デートの練習の方ですね。黒沢が、安達に「行こうよ」って言って連れ出して」
ーーその時何に乗ってるとか覚えてますか?後ろに馬とかあるんですけど。
赤「これは、普通に椅子ですよね。コップ?」
町「これはね、これは普通にあのーメリーゴーランド。後ろにもたぶん乗り物が見えてる���思うんですけど、本編では安達がカバ?」
赤「カバ。カバ乗りました」
町「僕は馬、乗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あの、本番撮って終わった後に、飽き足らず二人でそこに座って記念撮影を、はい」
赤「すごく照れくさい写真ですね(笑)」
ーーこれは実際には放送では使ってないってことですね。
町「使ってない、完全にたぶん二人でその…」
ーーオフショット。
町「オフショットですね。時間はい」
赤「見てください、この町田くん。カメラを持って、もうそっちに集中してしまって」
ーーセルフィーですね。
赤「はい、オフショットに、気づいてないっていう写真ですねこれは」
町「これは撮られたの僕気づいてないですからね」
赤「あはは」
町「今初めて知りました。あの、僕が撮った方からの写真だったらあるの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
ーーあーなるほどですね。
町「あ、こういう風に撮られてたんだ」
ーーじゃあこれが町田さんが撮ったっていうことは、自分の携帯で撮った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よね。
町「これは黒沢の携帯。あの、お芝居で、劇中で使っていた携帯なんですけど」
ーーそのあとは自分の携帯に写真を転送しましたか。
町「あの、転送してないですね」
ーー残念ですねー。
町「そうなんですよ。あの●●で」(※MCの言葉と被ってどうしても聞き取れない)
ーー保存して欲しいです。
町「(笑)」
ーー続いての写真はこちらです。
☆10話の黒沢妄想内レストランでの写真
ーーおしゃれー。
赤「おしゃれですね」
ーーこちらの写真はどの時なんですか。
赤「これは…10話?の、黒沢の妄想のシーンです」
ーーどうですかその時の印象。
町「これ実は、あの、安達蝶ネクタイをしてるんですけど」
赤「はい」
町「これ、あの、衣装さんに聞かれたですよね。ネクタイ?これ蝶ネクタイ?どっちがいいと思う?って。聞かれて」
赤「はい」
町「蝶ネクタイでしょ」
ーー町田さんが選んだ。
町「僕もそうだし、「だよねー」ってみんななっていて。やっぱりそ��、ねぇ、蝶ネクタイ姿の安達は、黒沢見た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か」
ーーなるほどですねー。
町「はい」
赤「そんなことあったんですね」
町「そうなんです。だからたぶん、赤楚くん…には、決定権がたぶんなかった。勝手にもう決まってたと思います」
赤「僕は、色だけどれがいい?っていう」
ーー蝶ネクタイを持ってこられて、どれがいいって?
赤「2つその色のどっちか、って言って、こっちって言って」
ーーちなみにどっちの色とどっちの色ですか?
赤「なんかこの色ともう1個派手な方があって。派手すぎるとちょっと違うなってなって「こっち」(黒)って言ったんですけど」
ーー3枚目の写真はこちらです。
☆「花」のオブジェの前の肩組んでる写真
赤・町「おお~~」
ーーこちらはいつのどの写真なんですか。
町「懐かしい、これ。何個かあったんだよねこのシーン撮ったのって」
赤「何個かありました。でもこれを撮ったのは、前半の方ですよね」
町「たぶんそうだね」
赤「だから、告白ではなかったと」
町「うん。じゃなかったと思う、確か」
赤「そうなんですよ。告白じゃなくて」
町「うん」
赤「たぶん帰り道」
町「なんか…あの二人のその、6話があって7話で安達が告白してくれて、その帰り道だったと思うん
だよね」
赤「その帰り道の方が先に撮ったんですよね」
町「かな。その帰り道のシーンを先に撮ったので。そこの、時だよねたぶん撮ったの」
赤「そうですね。で、その、「花」の、この下の漢字とちょっと合わせてみて、ああいうポーズになりました」
ーーなるほどですね~。ちなみにお二人が好きな花は何ですか?
町「好き?あー僕はあの、水仙てご存じですかね」
ーースイセン。
赤「おー」
町「地元の、その出身地が、日本の群馬県って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そこの、あの、ある一部の地域の出身なんですけど(笑)。そこの町の花なんですよ確か」
赤「へぇー」
町「だから子供の頃からすごいよく見てて。もうそこら中いっぱい咲いてたんですよ」
ーー水仙ですね。
町「はい」
ーー赤楚さんはどうですか。
赤「僕が好きな花はチューリップですね」
ーーチューリップですね。
赤「はい。何故なら、僕は幼稚園の時にチューリップ組に入ってたからです」
ーー素敵ですね。いろんな思い出があったってことですね。続きましてこちらの写真です。
☆お揃いのジェラピケ着てチェリまほポーズの写真
赤「ああ~」
ーーこちらですね、ペアルックって感じなんですかね。
赤「はい」
ーーやってるポーズって何ですか?
赤「これは、6話の妄想のシーンの」
町「うん」
赤「あの、これは「チェリまほポーズ」って言って、チェリまほ。その、衣装さんのその、白石さんっていう方が発案したポーズなんですけど。この手を2つ合わせることによってサクランボになるっていう」
ーーシライシさんが?
町「(笑)そう白石さんが」
赤「(笑)白石さんが」
ーー結構皆さんで流行ってるってことですかね。
町「なんか現場でね」
赤「現場ではめちゃくちゃ」
町「やってたので、あの、皆さんもしかしたら真似してくださってるの、かも、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赤「で、大事なのは、白石さんは言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こうポーズをとった時に、あの、腰を入れる」【立ち上がってポーズをとる】
赤「ここの腰はすごく大事だって言ってたので、ぜひ皆さんも真似してください」
ーー画面を通してみんなポーズやってると思います。町田さんもぜひ一緒に。
赤「あっはは」
町「いや、僕知らなかったですよ。そんなアレあったんですね」
赤「僕こそっと言われました」
ーー赤楚さん教えてあげてください。
赤「はい」
町【立ち上がり】「まずポーズとって」
赤「はい」
ーー大事なのは?
赤「せーの、ちぇりまほ~」【腰を入れたチェリまほポーズ】
町「腰を入れるの?」
赤「腰入れるんです」
ーーみんなキャーキャーキャーキャーしてると思いますよ。こちら見るだけでもうほっぺたがサクランボのように赤くなってるぐらいですよ。
町「上手ですね~」
ーーこのポーズで山形県のサクランボをぜひ宣伝出来たら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赤・町「あはははは」
ーーサクランボ、タイ人も大好きなので。
町「あ、そうなんですね」
ーータイはサクランボあまり咲いてないんですよ。じゃあ最後の写真はこちらです。
☆クランクアップ時の花束もって肩組んでる写真
ーーお二人ですね、大きい花束を抱えてる写真なんですが。
赤「これは」
赤「クランクアップの」
町「クランクアップですね」(同時)
ーー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すって言われた時に、どんな感じの思い出が残ってますか。
赤「あぁ、でも、まずは、終わった喜び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感じてて、その、ただ嬉しいっていうん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こういうご時世だからこそ、ほんとに無事にちゃんとやりぬいて、みんな誰も、いなくなることなく、ちゃんとみんなで一緒に終われたっていうことが、ホントに嬉しくて。っていうやり切った喜びと、あと、やっぱその、車での帰り道で、僕はとても寂しい気持ちになりました」
ーー町田さん知ってましたか。
町「え?なんですか?」
ーー寂しかったんですって。
町「あ、でもさみしいさみしいって言うのは結構、その、これが終わった後にみんな言っていて。赤楚くんもそうだし。で、あの、スタッフさんたちもみんなそういう風に言ってくれていて。で、帰りちょっと話してたら、あの、みんな結構ちょっとテンションが高ぶってしまって、スタッフさんの中にはちょっと涙目になって、(笑)はい。あの、なってる方もいたりとか。本当になんかこうやっぱ温かいチームだったなぁってやっぱ思いますよね」
#MagicHourEijiKeita#Magic hour Eiji Keita#cherry magic#cherrymaho#eiji akaso#keita machida#30歳まで童貞だと魔法使いになれるらしい
21 notes
·
View notes
Text
各地句会報
花鳥誌 令和3年10月号

坊城俊樹選
栗林圭魚選 岡田順子選
………………………………………………………………
令和3年7月1日
うづら三日の月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ちらちらと風になびくや小判草 喜代子
月涼し越し人生を返り見る 同
堤防の舗装工事に夏深む 英子
大夕焼茜に染まる遊びの子 都
誰が化身蛍火となり闇を舞ふ 同
訳有りの香水今は琥珀色 同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3年7月3日
零の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吸殻はサルビアの雨に崩れて 和子
色悪の血まみれとなる夏芝居 要
柏手も汗も小言も楽屋口 荘吉
歌舞伎座の江戸むらさきの涼しさよ いづみ
通り抜けても青梅雨の銀座かな 要
辯松へ思ひありしか梅雨の蝶 三郎
歌舞伎座の裏店にある水羊羹 いづみ
木挽町の色を正して濃あぢさゐ 和子
風鈴や木挽町しか知らぬ風 順子
三つ編みをほどき蛍をとほくする 光子
岡田順子選 特選句
やうやくに楽屋貰ひて夏暖簾 佑天
高楼に埋もるる梅雨の小料理屋 小鳥
緑蔭にレノン形見の喫茶店 いづみ
三越の獅子にまたがる父の朱夏 俊樹
緞帳の街を治める朝曇 三郎
一センチほどの薔薇咲く木挽町 小鳥
垢抜けぬ頰で見にゆく夏芝居 光子
紅薔薇を傘もささずに買ふ男 きみよ
吸殻はサルビアの雨に崩れて 和子
夏深し妾の店の連子窓 光子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3年7月7日
立待花鳥俳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手の窪に水の匂へる蛍かな 世詩明
梅雨ごもりポストは音を待つてをり 清女
魚の店は蝿取りリボンぶら下がる 誠
雲の峰海へと続く行者道 同
潮浴びの乾きし肌に白き塩 同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3年7月10日
花鳥さゞれ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栄枯知る一乗谷の大夏木 かづを
老鴬に耳遊ばせてゐる故山 同
山日和老鴬機嫌よく啼けり 同
夏潮の香を浴び渡る神の島 同
海に向く茶房の窓や夏の潮 匠
縁側は親のぬくもり端居せる 同
夏潮の三国河口に女佇つ 和子
棟梁で寡黙な男哥川の忌 同
泰山木花の大いさその白さ 天空
夏潮に護られるごと句碑三基 同
丸ごとのこれぞ西瓜と云ふ西瓜 雪
夏潮を佐渡へ蝦夷へと旅せし日 清女
なんとなく撫でてあげたい西瓜かな 笑
美しき娘を残し夏の月 千代子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3年7月10日
札幌花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とび降りる水待つ滝の流れかな 独舟
ドア開けて人を待つかに水中花 清
客一人静かさにある水中花 同
手も足も尻も出てゐる夏蒲団 晶子
口癖も日焼けもまさに親子なり 同
蜘蛛の囲に雨粒光り蜘蛛は留守 寛子
一滴のブランデーなりし夜の秋 岬月
鳶職の足場を雲の峰に組む 同
ボート漕ぐピアスとピアス光り合ふ 雅春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3年7月10日
ますかた句会
栗林圭魚選 特選句
月見草闇押し退ける力あり 秋尚
枕辺に老舗の名刺うなぎの日 多美女
リハビリを終へギヤマンの氷菓子 同
月見草夕靄濃ゆき無人駅 ゆう子
空蟬や古寺の砌に横たはり 幸風
けさの雨白く飛沫きぬ原爆忌 ゆう子
母の言ふ忘られぬ空原爆忌 多美女
女坂木々の重なり寺涼し 瑞枝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3年7月12日
武生花鳥俳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料亭の盛り塩に梅雨しとどなる 清女
剥落の蔵の上なる雲の峰 上嶋昭子
時鳥行幸の山鳴き交はす みす枝
一枚の朴の落葉にある孤独 ただし
気に入らぬ日射しひまはり北を向く 時江
梅雨豪雨猛獣の群れ襲ふごと みす枝
木蔭には木蔭の色の額の花 信子
朝曇世の盛衰の見えかくれ 時江
喉飴をがりがり噛んで梅雨籠 清女
アマリリス弱気の兄を背に庇ひ 上嶋昭子
鬱憤を噴き出す如くソーダ水 みす枝
夏雲の一つ一つに獣住む 世詩明
青簾一枚外は日本海 ただし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3年7月12日
鳥取花鳥会
岡田順子選 特選句
海に果つ誘導灯や月見草 美智子
博物館枡に咲かせる古代蓮 悦子
雷鳴に引き摺られ行く雨の音 佐代子
短夜や寝返り毎に白みをり 宇太郎
幽妙な香となる風蘭の夜風 悦子
雷雨去り砂丘稜線みづみづし 都
沙羅散るや禅語の数と思ふ程 益恵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3年7月12日
なかみち句会
栗林圭魚選 特選句
虹立ちてひと刷り濃かり空の碧 秋尚
捨て切れぬ夢まだありぬ雲の峰 同
神職の袴は浅葱雲の峰 美貴
たこ焼きのたこはみ出して雲の峰 有有
入道雲目指して彼方定期船 史空
片脚を天城嶺に置き朝の虹 怜
横寝する父の跣足や縒れる爪 聰
雲の峰青空少しづつ食みて 三無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3年7月13日
萩花鳥句会
遠き日や開聞岳の夾竹桃 祐子
砂山の一つ残りて晩夏かな 美恵子
子窓開け直ぐ二度寝入る風晩夏 健雄
山津波救命急ぐ汗汗汗 陽子
月涼し今日も安堵の日でありき ゆかり
広島の空の青さよ夾竹桃 克弘
………………………………………………………………
令和3年7月14日
さくら花鳥会
岡田順子選 特選句
八日目のバナナ甘美をまとひたる 登美子
テーブルにぽつんとバナナ夜を明かす あけみ
歳月に吾と琥珀色増す梅酒 みえこ
半夏生物忌みの日と畏みぬ 同
開け放す御堂鶯老を鳴く 令子
疫病を祓ふ茅の輪をくぐりけり 同
行く人も来る人も居てかき氷 裕子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3年7月16日
伊藤柏翠俳句記念館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雨蛙いつ迄其処にゐるつもり 雪
百年に滅びし栄華夏の草 同
修羅場秘め密かに待てる蟻地獄 みす枝
伝達はちよつと一ト言蟻の列 同
稲光どつと天地を翻へす 玲子
形代を流せる指の皺深し ただし
一山のみどり明りの中を来し かづを
雲の峰見上げて君を待ちをりし 高畑和子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3年7月18日
風月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蟬の穴覗きて闇の深からず 三無
草いきれ甘く重たき風となる 和子
アイスキャンディー食ふ子とそれを見てゐる子 千種
しつかりと姉の手握り雲の峰 斉
炎帝や年尾の句碑の揺るぎなく 亜栄子
絵日傘をたたみ閼伽桶汲む女 芙佐子
少年へ機関車聳ゆ日の盛 千種
組む足で裾さばきをりサンドレス 和子
栗林圭魚選 特選句
草影の一枚はがれ夏の蝶 和子
炎天へかひな開けり母の塔 千種
背に誰か並ぶ気配や夏の果 和子
両手拡げ風となる子や夏野原 三無
菩提樹といふ仏性が蟬集め 同
這ひ上り仏足石に迷ふ蟻 芙佐子
少年へ機関車聳ゆ日の盛 千種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3年7月21日
福井花鳥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雲の峰仰ぐ男の子の目の青さ 和子
ナース行く七夕竹にすれすれに 昭子
半夏生ほどの化粧や母在さば 同
父の日や兄に残りし父の顔 令子
福井空襲夏休待つ前日だつた 同
洗ひ髪彼の世此の世の人を恋ひ 雪
猫であることを忘れて猫昼寝 同
青葉木菟明智軍記を蔵す寺 同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3年7月21日
鯖江花鳥俳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夕べ啼きをりし蛙は殿様か 雪
母に別れ蚊帳に別れし昭和かな 上嶋昭子
思案中らしき男の白扇子 同
水中花の水替ふ君の留守の部屋 同
蛍篭明りに本を読みし日も 洋子
仏壇にもつとも古りし水うちは 同
曇天にほのかな明り合歓の花 紀代美
御住職までもあやめり水鉄砲 一涓
青天を背にし三人ラムネ飲む ただし
炎天下裸婦像ことに裾からげ 世詩明
山を割る男瀧の水の白きかな 同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九州花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釘の錆風鈴を吊る指先に 睦子
行水の音たばしらせ若き父 同
炎昼や人みな影としか見えず 同
白刃のごとく立ちたり滝行者 ���子
風鈴の吊しままなる売家かな 久美子
人形の動かぬ瞳水中花 ひとみ
行けど行けど夏鶯の浦の径 由紀子
花海桐煌めいてゐる忘れ潮 さえこ
夏の夜のあやかし君とゐるスナック ひとみ
七夕や園児は時を駆けてをり 勝利
落蟬の足動きつつ曳かれ行く 志津子
噴水のあざとき色を噴き上げぬ 伸子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1 note
·
View note
Text
【劇評】夢幻的光景のなかで提示されるリアリズムのねじれ
リ���ャール・ブリュネル演出『海を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女もいた』(ジュリー・オオツカ『屋根裏の仏さま』より)@アヴィニョン演劇祭
片山 幹生

〔Certaines n'avaient jamais vu la mer © Christophe Raynaud de Lage〕
1.日系アメリカ女性移民の叙事詩的文学の舞台化
日系アメリカ人女性作家のジュリー・オオツカの小説『屋根裏の仏さま』が、フランスで演劇化され、今年のアヴィニョン演劇祭で上演された。
20世紀初頭にアメリカに「写真花嫁」として移住した日本人女性たちの苦難を叙述したこの小説は、2011年にアメリカで公刊された翌年にフランス訳が出版され、フランスではフェミナ賞外国小説賞を受賞している。ちなみに日本語訳は新潮社から2016年に刊行されている。
フランス語版のタイトルは『海を見たかったことがなかった女もいた』(Certaines n'avaient jamais vu la mer)で、舞台版の翻案・演出を行ったのは南仏の都市ヴァランスの国立センター、コメディ・ド・ヴァランスの芸術監督、リシャール・ビュルネルだ。この作品はビュルネルにとっては、はじめてのアヴィニョン演劇祭の公式招聘作品(「イン」と呼ばれる)となった。
『海を見たかったことがなかった女もいた』には12人の俳優が出演するが、その中には別稿でインタビューを掲載している二人の日本人女優、外間結香と竹中香子が含まれている。日本人女優がフランスの国立劇場制作の作品のキャストに選抜され、アヴィニョン演劇祭のインの演目に出演するというのは、画期的な事件ではないだろうか。作品は修道院教会の回廊であるカルム回廊中庭で上演され、多くの現地メディアから絶賛された。
本稿では、この作品のアヴィニョン演劇祭公演について、現地評を参照しつつ、記述していきたい。

〔Certaines n'avaient jamais vu la mer © Christophe Raynaud de Lage〕
2.コロス的演劇、流動性の高い美しい夢幻的スペクタクル
『ル・モンド』、『フィガロ』などフランスを代表する一般紙に掲載された劇評を含め、16の劇評を私は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た。私が参照した16の評のうち、否定的な評は一つだけで、残りの評は概ね肯定的な評価だった。アヴィニョン演劇祭での『海を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女もいた』の公演は、現地の批評家、観客たちから支持されたとみていいだろう。
『海を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女もいた』はほぼ原作小説の構成を蹈襲している。「写真花嫁」たちが経験したいくつかの主題・出来事にもとづく複数の断片的証言が「わたしたち」という主語とともに提示される。特権的な主人公はいない。多数の無名の女たちの語りは、「わたしたち」を主語とする文章で並列され、一つの総合的な語りへと集約されている。語られるのは個別的で具体的なエピソードでありながら、その一人称複数による文体の無名性と多数性ゆえに、原作小説の叙述は高い抽象性・象徴性を持つ叙事詩的次元に到達している。
まず厳しい評から紹介しよう。マルティニークの文芸批評マガジン、Mandinin'artのセリム・ランダーは、『海を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女もいた』の舞台は原作小説の「単なる説明の段階を超えるものではなく、原著の読書がもたらした衝撃にははるかに及ばない」、「原文に含まれる暴力も優しさも満足いくような表現に到達していない」と否定的な評価を下している。
「わたしたち」によって語られる単一性と集合性を舞台上に移し替えるために、演出のブリュネルはギリシア悲劇のコロス的手法を用いた。このコロスの用い方を高く評価する評は多かった。『ル・モンド』紙のファビエンヌ・ダルジュの評から引用しておこう。演出家のブリュネルの演出は「原作の持っていたあらゆる感情的な次元と繊細さを演劇的なかたちで見事に再構築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ており、「コロスという形式が、痛ましい響きの朗唱のなかで、女たちの声の複数性を聞かせてくれる」。
批評サイト、L'Insenséの評者アルノー・マイゼッティ は、さまざまな主題が拡散していくなかで、この舞台は「個別性を乗り越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なコロスを作り上げることで、個人的な体験から共有されうるものを立ち上げようとする意志を感じと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記している。

〔Certaines n'avaient jamais vu la mer © Christophe Raynaud de Lage〕
舞台の視覚的美しさについては多くの評が言及し、絶賛していた。薄くて白い布のカーテンが舞台の周囲でゆらめき、そのなかには実に多くのオブジェが入れ替わり立ち替わり現れる。背景のカーテンや移動する白い「衝立」はスクリーンとなり、そこには「写真花嫁」たちのポートレートをはじめ、さまざまな感覚的な映像が映し出される。その映像表現は舞台上の女たちの不安や恐怖を敏感に映し出す。
舞台上で語られるのは断片的なエピソードだ。その断片とともに舞台上の風景が次々と変容し、移り変わっていく。滑らかな流動性が視覚に与える快感はこの舞台の特筆すべき美点の一つだ。エピソードの羅列がもたらす単調さと反復は、演者たちの優雅で舞踊的な動きと結びつくことによって、視覚的な詩を作り出していた。CULTUREBOX に掲載された評の一節を引用しておこう。
「変化する舞台装置、素晴らしい衣装、俳優たちのダンス。さまざまオブジェが舞台上を滑り移動する。経過する時代にふさわしい場面が現れ、この苛酷なドラマに豊かさをもたらしている」。『テアトラル・マガジン』は「断片的な語りで構成された形式は、Anouk Dell'Aieraによって制御された舞台美術とバレエによってダイナミックな活力を獲得していた」と評している。
フランスの文化芸術の批評サイトNONFICTIONの記述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とても美しい舞台美術は、自然主義的の要素が強い。衣装と装飾品はできるだけ考証をふまえたものが用いられていた。移民たちが働くテンサイ畑、織物工場、アメリカのブルジョワ家庭の屋内についてもそうだ。しかしこれらの自然主義的要素は、多彩な照明、古い肖像写真やビデオ映像のポートレイトが映し出されるスクリーン、裸の空間のあいだの舞台全体に散りばめられた実物の小道具の数々によって、緩和されていた」。

〔Certaines n'avaient jamais vu la mer © Christophe Raynaud de Lage〕
「写真花嫁」の歴史と物語は20世紀初頭にはじまり、太平洋戦争開戦とともに終わる。長きにわたる苦難の連続のあとようやくアメリカ社会に居場所を確保しようとしていた日系移民たちは、日米開戦とともに生活の場を追われ、収容所に入れられてしまう。
『海を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女もいた』の舞台の構成は原作小説と同じく二部にはっきり分かれていて、最後の1/4の部分は日本人がいなくなった町で消えた日本人について語るアメリカ人ブルジョワ婦人の一人語りに託される。それまでは7人の女優と4人の男性俳優によってコロスのかたちで場面が展開していくのだが、最後の場面はナタリー・デセーのモノローグとなる。
デセーはその優れた歌唱力のみならず、卓越した演技力でも知られた世界的なオペラ歌手だったが、数年前にオペラ歌手を引退し、俳優として活動を始めている。『海を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女もいた』はデセーが俳優として本格的な舞台に出演することでも注目されていた。
集団的コロスによる舞踊的演出が行われていた前半とデセーのモノローグ劇となる後半は、どちらも「わたしたち」という一人称複数によって語られるとはいえ、表現として際だったコントラストをなしていた。この表現上の対照は、物語の内容にも対応した優れたアイディアだ。デセーはごく短い歌を一回歌うだけで、抑制された静かな芝居を行う。オペラの演出を変えてしまったと言われるぐらいオペラ歌手としてのデセーの作品解釈と演技は優れたものであるが、そのセンスのよさは今回のような語りの芝居でも発揮されていた。
私が見た7/20(金)の公演では、このデセーの出演場面が始まる頃から空に雷光がきらめき、強い風で舞台をとり囲む白い布が激しくゆれ動いた。時間が進むにつれ、ごろごろと不穏な雷鳴がとどろきはじめ、終演直前には雨が降り始めた。そしてカーテンコールのあとに、土砂降りとなった。
こうした予想外の天候の急変は、日本人が去った町の不安と空虚さを語るモノローグの内容に呼応する不穏な雰囲気を作りだし、結果的に見事な演劇的な時空を作り出した。しかし劇全体から考えると、デセーのモノローグ劇の時間は長く取られすぎてバランスが悪い。大スターであるデセーを起用する以上、それにふさわしい場を用意する必要があ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が、この芝居ではデセーのキャスティングは中途半端で、せっかくの大スターを無駄遣いしている感があった。

〔Certaines n'avaient jamais vu la mer © Christophe Raynaud de Lage〕
3.フランスの舞台作品で、フランス語によって日本人が演じられることへの違和感
別稿のインタビュー記事のなかで出演者の竹中香子が話していることだが、このプロダクションの画期的なところの一つは、これまでフランスの舞台ではあまり活躍の場がなかったアジア系の俳優が多数出演していることだ。移民問題は現在のヨーロッパ演劇では重要なテーマであり、フランスの演劇界でも民族多様性が問われるようなっていると言う。結果的には、日本人俳優は竹中香子と外間結香の二人で、他は中国系、ヴェトナム系、韓国系といったアジア系俳優以外に、白人の俳優もキャスティングされた混成的編成となった。
原作は英語で書かれているが、ブリュネルの舞台用翻案では台詞は当然フランス語がベースになっている。しかしフランス語だけが舞台言語として使用され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映像には日本語が映し出されるし、劇中で歌われる歌の歌詞は日本語だ。俳優が話す台詞にも時折日本語と英語が混じる。
『海を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女もいた』のキャストの多民族性、舞台言語の多言語性は、フランスの批評家や観客は違和感を覚えることがなく、むしろ肯定的に捉えていた感がある。L'Insenséの評者は次のように記している。この作品で、観客は様々な出自の俳優の身体と言語を受け取る。作品は「複数の異なる言語、異なる訛り、そして異なる抑揚を聞く機会でもあった。こうした機会はフランスの舞台ではほとんどない」。
『ラ・クロワ』紙の評は、「日本人、韓国人、中国人、フランス人の女優たちはいずれもすばらしい。それぞれが自分の特性を示しながら、同時に一つに溶け合っていく。彼女たちの長台詞は、それぞれの生の複数性を伝えながら、共通の運命を描き出す」と記している。『レ・ゼコー』紙では「繊細でときおり過剰に思えるほど抑制された雰囲気のなかで、日本、韓国、中国、フランスの8人の女優たちは、共同の建造物を作るために、それぞれが持っている石を積み上げた」とあった。
竹中香子と外間結香はいずれも、この作品に参加するにあたって、自分の日本人性を特に意識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とインタビューで語っている。そして竹中が言うように、私がこの舞台を見て感じた違和感やねじれは、私が日本人観客であることに起因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
『海を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女もいた』はコロス的演出、舞踊的表現の導入、そして流動性の高い舞台装置によって幻想的な舞台空間を創り出す一方、個々の俳優の表現のディテイルにはリアリズム表現へのこだわりがあった。またキャストのなかになまじ日本人女優が2名入っているから余計に、他の日本人ではない俳優の非日本人的なアクセントや動きがノイズとしてひっか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のもあるだろう。

〔Certaines n'avaient jamais vu la mer ©Jean-Louis Fernandez〕
原作はフィクションとはいえ、20世紀初めの現実の歴史を取材したものであり、そこではアメリカ移民女性の悲痛な体験が生々しく語られている。『蝶々夫人』ならば、そこで描き出される「日本」がどれほど異様なデフォルメをされていても、西洋のジャポニスムのなかで生成・発展したファンタジーとしての「日本」として私は受けとめることが可能だが、「写真花嫁」の悲壮な運命を叙事詩的に描くこの作品では、彼女たちの「日本人性」から離れて彼女たちと向き合うことは難しい。アジア系移民あるいは移民の象徴的存在として彼女たちを認識するには、彼女たちの歴史・物語は私にとってはあまりにも生々しく感じられ、日本人以外の俳優がフランス語で演じる日本人女性に違和感を覚えてしまったのだ。この違和感は、生身の人間が目の前で他の人間を表象するという舞台芸術の特性によって強調された。フランス語で書かれた劇評には、私が感じたこうした抵抗感について言及しているものは一つも無かった。
私が読んだもののなかでは、アメリカの媒体であるBROADWAY WORLDに掲載されたウェスリー・ドゥセットの評は、キャストの多民族性がもたらす問題について言及した唯一の劇評だった。彼は「文化的盗用」と言うわけではないが、身体の政治性、とりわけ日本人という身体の持つ政治性が問題になっているこの作品に白人俳優を入れることは、当時の社会的現実の認識を歪め、作品の持つ政治的意図を損なう危険性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重要な指摘をしている。ただしドゥセットも白人の俳優だけを問題にしているわけで、アジア系俳優についてはひとかたまりに同じ属性の身体を持つものと見ている点では、フランスの批評家、観客と変わりはない。
ドゥセットの指摘は私が『海を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女もいた』を見たときに感じた居心地の悪さの本質的理由を説明するものだ。少なくともジュリー・オオツカの原作では、彼女たちが「日本人女性である」という属性が重要である。移民が一般的に抱えうる普遍的な苦難も語られてはいるのだけれど、物語の最後で彼女たちが町から消えてしまったのは、ドゥセットの書くように、彼女たちの身体の政治性が問題になったからである。日本人俳優を含む混成的キャストでは、その特異性がぼやけてしまう。
『ル・モンド』紙の評者は、「日本人のほか、朝鮮人、中国人、フランス人がいたが、アジアとの強い絆を保持していた」と書いているが、果たしてわれわれ東アジアの人間が、ヨーロッパ人のように、あるいはアフリカ人のように、アジア人としての共通の歴史や感性を共有していると言うことはできるだろうか。東アジアを一つの文化圏としてまとめて捉えることが可能だという考え方自体が、ヨーロッパのごう慢と無知であり、粗雑な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いうべきものではないか。そうした西洋のナイーブな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を、われわれが内面化して受け入れることは問題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日系アメリカ人によって英語で書かれた日本人女性についての物語を、フランスの劇場と演出家が取り上げ、多民族キャストがフランス語で、フランス人の観客の前で演じる。『海を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女もいた』公演が内包する複合的なねじれは、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について私が抱えている問題意識を刺激するものになった。
●片山 幹生(かたやま・みきお)1967年生まれ。兵庫県神戸市出身、東京都練馬区在住。WLスタッフ。フランス語教員、中世フランス文学、フランス演劇研究者。古典戯曲を読む会@東京の世話人。
公演情報:『海を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女もいた』Certaines n’avaient jamais vu la mer
URL :http://www.festival-avignon.com/fr/spectacles/2018/certaines-n-avaient-jamais-vu-la-mer
出演:Simon Alopé, Mélanie Bourgeois, Youjin Choi, Natalie Dessay, Yuika Hokama, Mike Nguyen, Ely Penh, Linh-Dan Pham, Chloé Réjon, Alyzée Soudet, Kyoko Takenaka, Haïni Wang
原作:Julie Otsuka, Certaines n'avaient jamais vu la mer
翻訳:Traduction Carine Chichereau
翻案・演出:Richard Brunel
ドラマトゥルク:Catherine Ailloud-Nicolas
舞台美術: Anouk Dell'Aiera
衣装:Benjamin Moreau
音響:Antoine Richard
照明:Laurent Castaingt
映像:Jérémie Scheidler
演出助手:Pauline Ringeade
上演会場:アヴィニョン、Cloître des Carmes
上演日時:2018/07/19(木)〜24(水)22時より(22は休演)
上演時間:2時間
1 note
·
View note
Text
2021/5/22
朝、Nからの連絡で目が覚める。その内容に飛び起きてガッツポーズ! 大慌てで支度をして、心のアンテナを調律しながら向かいます!
ちょっと胸の高鳴りが止まらないんだけれど、鈴の音を聴きながら歩いていたら落ち着いてくる。ぴょこっとした黄緑色のコケみたいのがかわいらしくて、しゃがんで写真をとる。12時ぴったりに駅に到着。改札前にはほかにも大勢のひとたちが個々に待ち合わせをしていて、人とひとが再会するところどころにぴこっと笑顔の花が咲く。改札から出てきた女のひとがお友達を見つける、とっても嬉しそうにおたがい駆け寄って、控えめながら抱き合っている。男の子たちの集団にさいごのひとりが遅れて到着する、男の子たちはまるでホームランを打ってベンチに帰ってくるチームメイトを迎え入れるように、うぇーいってさいごのひとりに肩をぶつける。そんな再会の様子を眺めていたら、泣いてしまいそうになって、上を向く。
5分になって、階段からまた大勢のひとたちが下りてくる。その中からNとKさんの姿を探す。あれれ、おかしいな、遠くからでもすぐにわかるはずなのに、と思ったら、下りてくるひとだかりの中から一本の手が挙がる。だけども、そのすぐ近くにいるはずのKさんの姿がいまだに見出せなくて、あのラピュタのパズーみたいなひとがKさん? いつもと雰囲気のちがうNの髪型と服装がチャイナかわいくて胸の♡に矢がズキュンと突き刺さる。そしてKさんと衝撃のご対面、経験的にこういうときにはそこに「関係」のような何かが発生して、居心地の悪さといったら大げさだけど、くすぐったさのようなものを感じる。それはぜんぜん悪いことではなくて、いい予感のほうがはるかに多いくらいなんだけど、Kさんの目をひとめみたとき、そこに関係のような何かがまるで発生しなくて、へぇ~って言いながらこっちを眺める生身のKさんがそこにいる。おたがいに初めましてって挨拶を交わしながら、え、これはいったいどういうことって思う。対面してひとのことを見ようとすると、そこに何かしらの機微を感じるっていうか、何かしらの関係のような何かが生じる。だけど、Kさんにはそれがまるでなくて、すんなりKさんのことを見ているし、Kさんにも見られていると感じている。え、なんだろう、あいだに関係みたいな何かがないから、おたがいにすれ違っているんだけど、それだけに相手をちゃんと見据えている? Mさんとはじめてふたりで会ったとき、Nとはじめてふたりで会ったとき、関係していくなかで喋っているじぶんの声が生身にきこえるとき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ている。ふだんは関係みたいな何かの渦にからめとらて、わけがわからなくなって、その渦の流れにのまれるままに喋っているから、それは喋らせられている感じにも似ていて、じぶんでも何を言っているのかよくわからなくなる。だけども、ふたりと喋っているときは、不思議とじぶんの声が録音の声をきいているみたいにはっきりきこえていて、これと似たようなことが視線を介するだけで起きているような感じがする。じぶんの声がきこえるように、じぶんの投げ掛けている視線が見えるような。
NとKさんが今朝のことを相性抜群の夫婦漫才みたいにたっくさん話してくれて大笑いの連続! コッちゃんのこと、より子のこと、カラスのこと、不審な警備員さんのこと、お友達の野田さんのこと、Kさんの壮絶な部屋のこと。Kさんはコッちゃんはカラスをお友達と思ったんだよって言い、Nは怯えていたと思うって言う。不審な警備員さんに対して態度を豹変させるKさんのNの物真似がおもしろすぎる。それから、Kさんの部屋に入ろうとしたときのNの再現も!
Oさんの魚介カリー。三人で来たものだからOさんびっくりしている。Kさんは端がいいんだよね、とNがKさんを優しく気遣う。席についたとき、Kさんとふっと目が合って、涙がうるみそうになる。注文を済ませるまえからKさんのマシンガントークが止まらない! ポン、ポン、ポーンとどんどんはなしが飛躍する。生まれ故郷の島のはなしをしていたと思ったらビールをゼリーにしてみたはなしになっていて、そのふたつのはなしを繋いだのは船の回転するスクリューが起こした泡だったりする。お友達の野田さんのはなしが何度か浮上する。Kさんはけっこうズケズケと野田さんを批判したり、もう会わないようにしようと思ったとか言う。それでもKさんは今朝も野田さんに挨拶をしていたらしくて、批判は批判としてあるんだけれど、それとはすれ違って野田さんのことをありのままに見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なって思う。Kさんのマイスプーン、すっごく小さくて掬えるご飯が少ないうえに、大盛りだし、ずっとずっと喋っているから食べるのが誰よりも遅い。Nとふたり、Kさんの食べ終わるのを待つんだけれど、Kさんがまたベラベラ喋りはじめて、これだから食べるの遅いんだよねってじぶんでツッコんでいる。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公園に向けて歩きながら、Kさんのこと一瞬で好きになっちゃいましたって伝える。Kさん、首筋に冷たい風のよぎったみたいに、きらいにならないでねって言う。野生のルンバ。Kさんは色んなものを見たり触ったりしながら歩く。まるでそのひとつびとつに挨拶をしているみたいで、じっさいに通りがかったひとにもこんにちはって挨拶をする。行きにかわいいなって思って写真を撮ったのと同じ種類らしき黄緑色のコケみたいなのにも触れる。これと同じかなって写真を見せる、うれしいな。墓場道、いい感じの葉っぱの下に赤い実が落ちている。しゃがんでその実を見ていたら、目のピントがだんだんと密かに蠢くそれに合ってきて、すぐ近くにアリさんたちの大行列ができている。
公園に帰ってくる。Nが大きくなったカモの赤ちゃんに大驚き! Kさんがいつもルリコンゴウインコのいる樹とすっと一体になる。長年この公園のことを見てきて、この樹と戯れているのはルリコンゴウインコとKさん以外知らない。かと思ったらKさん、雨も降っていないのに雨が降ったらこの池の水面に波紋ができるのかなって。まさに雨の波紋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た矢先だったから、いきなりそんなことを口走るKさんはやっぱり超能力者なの? 雨の降っていないときでもアメンボがいれば波紋が見られるけど、いまはカモの赤ちゃんがぜんぶ食べちゃっていないって伝える。Kさんはコイたちに熱心な視線を注いでいる。Nが水面に浮かぶ赤い実みたいのをコイが食べては吐き出していることに気がつく、ベェーってすぐに吐き出しちゃう。えさをもらえ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か、コイたちがどんどん集まってくる。コイからはこっちのことがどんなふうに見えているんだろう。Kさんはひらっと泳いだり、飛び跳ねたりするコイたちをみて、色んな芸があるって言う。
小学校のニワトリを見にいこうとするけれど、ニワトリ小屋のところには入れなくて、Kさんはよれよれの草花を持ち帰る。信号を渡って、100均とファミマ。メモ、こんど信号待ちのときみんなと足で踊るやつやりたい。念願のゴザがあって、ゴザを買う。青と黄色と緑。そういえばかよこさん、青の時計みつかったらください! Nに促されてボールも買う。ニンマリ。ボールも買う。Kさん造花を触りながら足に良さそうだと言う。え、どういうことって思って造花を触ってみると、たしかに足で踏んづけたら気持ちよさそう。お茶をひとつ選ぶのにもNのKさんことを想う真心みたいなのがポロっと出ていて涙がうるむ。買い物を済まして横断歩道で信号待ち。メモ、こんど信号待ちのときみんなと足で踊るやつやりたい。空の雲がどす黒い色をしていて、おおッ、きたなって気持ちが盛り上がってくる。さっそく雨が降りはじめる、Nが傘をひろげる。入る? (雨に打たれるの好きだから)まだだいじょうぶ。
屋根のあるベンチで雨宿り。大勢のひとが集まっている。何だったか忘れたけど、子どもが面白いことを言ってクスッと笑う。雨はすぐに弱まって、屋根のなかが少しずつ空いてくる。そこへTがひらひら手を振りながら登場する。(駅で雨宿りしてるってもっと早くに気づけたらな、傘あったから迎えに行きたかったな)大あくびを連発するKさんはコクッと一瞬寝かけている。Tとの挨拶がひとしきり済んで、KさんにTを紹介するときには、Kさんはまたずうっと喋りっぱなしのモードにもどっていて、Nといっしょにこれまでのいきさつをひと通りおさらいする。Nの物真似とか再現がなんど見聞きしても面白くって、面白くって大笑いするたびにKさんもいっしょに大笑いしてくれる。Kさんも気ままに笑っているのだから、いっしょに大笑いしてくれるっていう言い方も変なんだけれど、なんだか「いっしょに笑っている」という感じがして心がぽかぽかする。Kさんはわりと頻繁に、いつもこの時間なにしてる? って質問をする。じぶんのときはOさんのところにいるときだったから、ここにいるよって応えたけども、何かもっと言い方が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まになって思う。いつしかKさんの視線が一点に固定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その視線の先にはTの目がある。KさんがTの真っ直ぐな眼差しを褒める、そう! そう! そうなの! って全力で同調する! じぶんのことのように嬉しいなぁ。と思ったら、きみはひとのはなしをよく聞けるね、おおらかだね、土地柄なのか、家族の影響なのかってKさんに褒められる。それで何故だか咄嗟に思い出したのがお母さんの家出のはなし。真夜中、お父さんと喧嘩をして激怒していても、一枚、二枚、三枚と、台所のお皿をゆっくりと丁寧に床に落として割っていく。そして、じぶんと弟を引き連れて高速道路で実家に帰る。Kさんはすごいな! そういう表現方法もあるんだなって、お母さんのことも褒める。音と形で、いちど壊れたものは直らないってことを伝える教育だったのかも、とまで。すごいなぁ、そんなこと考えたこともなかった。この家出のはなしはお母さんとの思い出のなかでもとくに好きなはなしで、いつも車に乗るときは弟と後部座席に乗っていたんだけれど、弟は爆睡しているし、子供心ながらなんかじぶんはお母さんの隣に座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ような気がして、そのときはじめて助手席に座って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めた。お母さんは一言も喋らずに脇見もせずに高速道路をひたすら運転して、くるりの『ばらの花』とか、フラワーカンパニーズの『深夜高速』を繰り返し大音量で流した。じぶんは音楽やその歌詞に耳を傾けながら、色んな光の過ぎてゆく高速道路の夜景をじっと眺めていた。我ながらいい思い出である。
みんなの出会いのはなしになったりして、ツイッターのはなしになったりして、そのKさんの言い回しがどうしても思い出せないんだけれど、ツイッターが歯車のようにうんぬんでみんなを結びつけてくれたんだね、とっても感動的なことを言ってくれて、Nを筆頭にわわわわわ~ってなる。Mさん、それからRとNちゃんもこっちに向かっているらしい。そしたらKさんがいきなり「Nちゃんはやれることちゃんとやっててえらいね!」ってNの肩をガシッと後ろから抱く。わああああっと泣きそうになっちゃう。巨乳になって小5と中2と高2の男の子にお願いしておっぱい触ってもらう夢みた。夢のはなしになって、毎晩眠りに就くとき、いい夢見れますようにってお祈りしていることをはなしたら、Kさんがそうだよね、お祈りって大事だよねって。その一言がとてもうれしい。
Kさんのはなしどれもテープレコーダーに録音しておきたいくらいいいはなしなんだけども、あとで思い起こそうとしても、その言葉の数々はびっくりするくらいあたまを通り抜けていて、なんとなくの印象だけは残っていても、不思議とその言い回しを思い出すことができない。Kさんのはなしには主に二種類あって、ひとつはこういうことがあったっていうある特定のエピソード、こっちのことはまだ思い出せるんだけれど、もうひとつの個別のエピソードに付随する人と人との関係性や繋がりの抽象的なはなしについては、そのどれもに深く共感しているのにも関わらず、具体的になにを言っていたのかはイマイチ思い出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にかく大量の言葉を発しているからというのがひとつ、南方熊楠みたいにキーワードひとつではなしがどこかに飛躍して、いつかの絵しりとりのように文脈が途切れているというのがひとつ、でも、それだけではないような気がする。とにかく大量の言葉を発しているのに言葉はいらないんだ、とも言う。それでも言葉を発し続けるKさんのはなしをどうにか汲みたいと思って、とりとめもない全体像を思い浮かべる。ところどころのはなしに散りばめられた「挨拶」ってキーワード。もっとシンプルに声掛け? というか一歩その対象にこちらから素直な気持ちで歩み寄ろうとすること? そんなような何か。さいしょはKさんのことをとらえどころのない不思議なひとだなって思っていたけれど、だんだんとこのひとは、ものすごく小さくて細やかな信念みたいものをひとつびとつ丁寧に丹念に、いまにも崩れ落ちてしまいそうな積木みたいに、どうにか積み重ねようとし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ことを思う。やれることやっててえらいね! って言葉に、言葉はいらないと言いながら、それでも周囲の発する機微のひとつびとつを言葉にして掬わないと気が済まないKさんの律儀な性根。Kさんにいきなり歯並びきれいだねって褒められる。ほら、私もきれいなんだよって前歯を見せるKさん。そんなこと大昔に恋人に言われたっきりだから照れちゃう。
そんなこんなで雨上がり、芝生にゴザを敷いて、念願のキャッチボール! 楽しいなぁ、ほんとうに楽しいなぁ! 四人でぐるぐるボールを回し合う。そこにお待ちかねのRとNちゃんが池の石橋をてくてく渡ってくる。R髪の毛のびたね、いつものジャージだね。Nちゃんはじめまして。このあいだ思いがけずケンカの火種をつくってしまってごめんね。なんかぐるっと芝生の上で円になっていて、どっちが先に言ったか忘れたけれど、Nちゃんって呼びかけていて、Nちゃんも名前をただ呼びかけてくれる。そのたったの一言から、何でも知ってるよ、何でもわかってるよ、何にも知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し、何にもわか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だいじょうぶ、ぜんぶ何でも受け入れられるよって感じのすごい大きな朗らかな気持ちが伝わってきて、いい子だなって思う。Nちゃんは一人称がじぶんの名前で、それがとっても似合っている。なんとなくAさんのことを思い出す、Aさんも一人称がじぶんの名前で、いつも朗らかで、スクッとまっすぐ地面に立っていて、面倒見がよくて、良くないと思うことはちゃんと良くないよって言ってくれる。Nが「ね、みんないい子でしょ」って宝物を見せるように言うのがとてもうれしいね。Mさんから、美容室の予約があって、来てもすぐに帰ることになっちゃうから今日はやめとくって旨の連絡がくる。そのことをきいたKさんが「いいね、予約してあるから来られないってことちゃんと伝えてくれるのがいいよね」って旨のことを言う。次々とあたまを通り抜けてゆくKさんの言葉のなかで、このことはあたまにはっきりと残っている。あまりにも当たり前のことを当たり前に褒めているから、かえって耳に残ってしまったらしい。もしかするとKさんの名言の数々がすっぽりあたまを通り抜けてしまうのは、あまりにも当たり前のことを当たり前に肯定してくれているからな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そんなことを思う。その当たり前のことは人と人とが関係していくうえで、うやむやに、曖昧に、何となくそこらじゅうの人に身についていたり、おろそかにされても大して気にもされないような些細なものかもしれなくて、でも、Kさんにとってのそれらは当たり前なんだけれど当たり前じゃない、当たり前じゃないんだけど当たり前なそんな些細のことを草の根の運動のようにひとつびとつ積み上げようとしているようなそんなような気概を感じる。お昼にはじめてKさんと出会ったときの不思議な感覚の謎が解けていくような感じがする。もしかしたら、あのときKさんとのあいだに感じた関係の途切れのような何かは、うやむやに関係の渦に巻き込まれるまえに、まず相手のことを関係されてしまうまえのありのままの生身の姿で見ようとする意志の表れだ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ことを思う。ひとでも動物でも植物でもものでも、ありとあらゆるこの宇宙のものは個々にそれぞれにそれらだけの固有の光を発しているって思う。そう思っている。ナイーブに言えば、そういうものものと関係していくことは、そのひとつだけの、それだけでひとつの膨大な宇宙のようなものから、じぶん都合のものだけをつまみ食いするようなふうになってしまう。たとえば、掃除機をゴミを吸い込むための道具をみなすように。必ずしもそれが悪いことだとは思わない。人と人でも、人とものでも、関係してなんぼだと思う。関係していくなかで(たとえば、じぶんに固有の光を誰かにわかってもらえないとかして)傷ついたりすることも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れど、ちょっとずつ、ちょっとずつでも、ひとつずつ、ひとつずつでも、完璧な関係なんてものは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れど、よりよい関係にしようとやっていきたい、そのための草の根の第一歩として、まずは関係するまえのありのままの姿を見ようとする、そんなようなKさんの気概が、ある道具をそれに求められている用途とはまるでちがう仕方で使おうとすることに表れ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こんなことを書き連ねるじぶん自身も、Kさんやみんなをじぶん都合のものに落とし込め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この日記を書きはじめた当初、その日の空がきれいだなって思ってそのことを書こうとしたんだけれど、きれいって書いたらそれ以外の何かが欠落してしまうような気がして、そのことを書けないって書いたことををよく憶えている。それからはどう思ったとか、こう思った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書くのをなるべく差し控えて、みたものをそのままに書くようにしていたように思う。自然のこととか、じぶんとは直接あんまり関係のないひとのこと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だけども、みんなと出会った頃からこの日記のあり方も変わってきた。じぶんと直接的に関係のあるものごとについても、その関係の渦中から書い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た。きっかけは大好きなみんなのことを書き残しておきたいっていう素朴な理由なんだけれど、それは関係の渦中からしか書けなくて、いままでのようにはいかなくて、どう書いたらいいんだろうってことの以前に、どう関係したらいいんだろうってことがまるでわからなくて、そんなわからなさにさいしょのヒントをくれたのがHさんのからだを張ったさよならの仕方だった。それがものすごくうれしくって、みんなのことよくわかるような気もするし、ちょびっとしか知らないけれど、それでも、それでも、ちょっとだけでも、思っていることや感じていることを言葉やからだで表に出して伝えられたらなって思う。
友達が少ないってはなしをしたらRが意外だという。Kさんも友達が少ないらしい。でも、いまはこんなに友達できたよ! 円になってしばらく立ちばなしをしていたら肌寒くなってきて、円をひろげて6人でキャッチボールを再開する。ぐるぐる、ぐるぐる、隣から隣へボールを投げる。Kさんのボールをキャッチして、Rにボールを投げる。RはNちゃんに近距離にもかかわらずけっこうな速球を投げる。Nちゃん、ちゃんとキャッチしていてすごい! だんだんと野球部の練習みたいに捕っては投げ、捕っては投げが速くなる。逆回転、Rがイノシシみたいな怖い顔で剛速球を投げつけてくる。しかも、ためて、ためて、ためて、いきなり投げつけてくる。捕れたときは手のひらがジーーーン。捕れなくて池ポチャ、ボールが思ったよりも水を吸い込んで、水を切っていると、誰かがラーメン屋の湯切りみたいって、みんなラーメン屋の湯切りの真似をしている。なんて愉快なんだぁ! Kさんの胸をめがけて軽く抜いたボールを投げる、Kさんが捕り損ねると胸ポケットの小銭がチャリンと心地よい音を鳴らす。Kさんの投げ方はドカベンの殿馬みたい。このあいだTと投げ合ったときには容赦ない力の込められたボールがきたものだけど、Nに投げるときはとても捕りやすそうに投げている。またRが怖い顔で凄んでくる、顔が怖いよ~って言うと、Rはサイコパスみたいなヤバイ笑顔になり、それがもっと怖くて笑ってしまう。からだが温まるというか暑いくらいになってきて、みんなゴザのところに集まり、Rを誘って二人で投げ合おうよ。ちゃんと距離をとって投げ合う。Rにフォームがきれいって言われる。エッヘン! 真っ直ぐがいい感じにRの胸に届く。ためしにスライダーを投げたらくくっと曲がる。フォークを投げようとしたら指から抜けなくてワンバンになっちゃう、走らせてごめん!
お腹痛いのをおして来ていたTがひと足先にバイバイ。ひらひらと遠ざかって姿が小さくなってゆく。恐竜みたいとも思ういっぽう、名前のとおり蝶々みたいだなぁとも思う。またね!
ゴザに寝転がって主にKさんのはなしをきく。数時間まえからNが頻りに「Kさん今日はたくさん喋って疲れたねえ」ってKさんの背中を撫でながら優しく労わるんだけれど、Kさんのマシンガントークはいっこうにおさまる気配なし、それどころかより加速さえしているような……。ここでもNの物真似と再現が炸裂して、何度見ても大笑いしちゃう。それから今回がはじめてになる神社に参拝したときのKさんの物真似「きょうも元気で楽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Nが、私はお願いごとばっかしてたのにKさんはって。ううぅって、とうとう感動して泣いてしまう。それから話題は主にNちゃんとRのことに。Nちゃんがじぶんで「Nは男気あるからな」って言う。その自信にあふれた強い一言にとても好感をもてる。Rが軽くKさんに説教されるようなかたちになって、ニヤニヤしちゃう。ここでもKさんはごめんね、とか、ありがとう、とか、些細なあいさつのことを言っている。でも、きみは素直だな、飾らないところがいいよって説教しながらもRのことを褒める。同棲のはなしから、じぶんにも同棲生活が長くあったはなし、それから、頑張り屋さん、もがいているひと、あがいているひと、悪あがきしているひとが好きってはなし。たぶん、それはじぶん自身も悪あがき好きで、悪あがいているときに生き生きとしているからな���だと思う。なんでいっしょに暮らそうと思うんですかってRからの質問に、だって好きだったらずっといっしょに居たいと思うでしょって。それはそうだけどKさんが言うと不思議な感じってR。なんだかその一言が引っかかっていて、こんどどういう意味なのかきいてみたい。
重ねがさねにトイレ、Kさんの姿がふいに見えなくなってちょっと不安になる。まあ、だいじょうぶだろうと思いながらもKさんが帰ってきていないことをNに伝える。Nはとぼとぼ広場のほうに歩いてゆき、小さくなったNがぽつんと広場の片隅に立っている。空はもう暗くて、そのぽつねんとした後ろ姿を見ていたら何となく胸騒ぎがしてきて、そういえばKさんが空のペットボトルをわざわざ持っていったことが急に気がかりになってきて、じぶんもKさんを探しにいく。どこにもいないねってNと合流、星に帰ったのかな、公園を半周して元いた場所にもどってくるとKさんはふつうにそこにいる。かるく迷子になっていただけだったみたい。よかった! 信じられなかったことがちょっと悔しい!
さよならの時間、どぎまぎしながら駅に向かって歩く。それぞれに方向も状況もなにもかもちがう。Rが来たばっかりなのにもう帰るのかって。その素直な気持ちがうれしくて、それだったらうちに寄ってく? って言いたいんだけれど、早朝の朝5時から活動しているKさんとNのことを考えると口ども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ときにも素直に思っていることを伝えて、これこれこう思うんだけどどうってことをうやむやな関係に流されずに伝えていけたらって思う。そういうときいつも矢面に立って、どうにかしようと頑張ってくれているのがNだ。その姿勢を見習っていきたい!
まずNちゃんとRを見送る。電光掲示板の数字のことからNちゃんに、ひとよりちょっと目のいいことが唯一のとりえだよって自虐的に伝えてしまったけれど、そのことはけっこう本気で自慢に思っているよ。電車が走りだして、窓枠からNちゃんの顔が見えなくなったとき、Nちゃんがひゅっと顔を覗かせて、また(^^)/を見せてくれたとき、すごいうれしかった。階段を渡ってNとKさんも見送る。すぐに電車きて、ふたり乗る、向かい合う、いい表情、目がとってもいい、走る。
Kさんのようになりたいなって本気で思う。ちょうど10歳差、10年後、Kさんのようになれたら、いや、なってやるぞって強い決意をかためる。かためさん。
0 notes
Text
沒有劇荒的恐懼:Netflix 10 月份片單整合,每部都值得花時間一看!

Netflix 今個月帶給觀眾們不少驚喜吧?9 月份上的劇集和電影都是討論度極高,特別是幾部原創的電影和劇集,包括Millie Bobby Brown 主演的《天才少女福爾摩斯》(Enola Holmes)、 Tom Holland 主演的《神棄之地》(The Devil All The Time)及 Tom Holland 主演的《神棄之地》(The Devil All The Time),已經讓觀眾們非常興奮!相信不少忠實的觀眾已經把這幾部劇集和電影看完了吧?若然你擔心陷入劇荒的話,那麼不用擔心,事關 10 月 Netflix 仍然有多不少超強電影、劇集出爐!
Netflix 10 月的片單仍然非常豐富,有一眾時尚迷非常期待的《艾蜜莉在巴黎》(Emily in Paris),劇集找來 Lily Collins當女主角兼製作人,加上本劇為《色慾城市》皇牌製作人 Darren Star,以及找來《穿 Prada 的惡魔》的當代時尚教母 Patricia Field 親自操刀全劇造型,單是預告已經換上 20 個造型,難怪會成為大家期待的劇集;另外,由 Lily James 和 Armie Hammer 當男女主角的電影《Rebecca》(蝴蝶夢)亦是討論度非常高的電影,全因其演員班底吸引外,更加被指比《失蹤罪》更出色,馬上讓它成為近期備受矚目的驚悚懸疑電影;還有就是集一眾男神級演員於一身的《芝加哥七人案:驚世審判》(The Trial of the Chicago 7),由奧斯卡金獎編劇 Aaron Sorkin 自編自導,故事取材於真實歷史事件,由《超能計劃》Joseph Gordon-Levitt、《丹麥女孩》Eddie Redmayne、《鳥人》Michael Keaton 等實力派演員主演,單是演員班底已經讓女生們非常期待。不少得的當然是非常愛歡迎的恐佈劇集《陰宅異事》的第 2 季《陰宅怪事》(The Haunting of Bly Manor),還有關於超強 K-POP 女團 BLACKPINK 的紀錄片《BLACKPINK: Light Up the Sky》和韓劇《私生活》,絕對不會讓觀眾有喘息的空間!
《Rebecca 蝴蝶夢》:10 月 21 日
youtube
新婚的年輕女子抵達丈夫雄偉的家族大宅,宅邸位於大風侵襲的英國海岸,而她發現自己竟得對抗丈夫第一任妻子蕾蓓卡所留下的陰影,那名妻子雖然仙逝多年,精神卻仍長存在這棟宅邸中。
以《仙履奇緣》走紅的女星 Lily James,與《以你的名字呼喚我》性感男神 Armie Hammer 飾演片中羨煞旁人、郎才女貌的夫妻。故事改編自曾獲封英國爵士的傳奇女作家 Daphne du Maurier 同名小說,由奧斯卡獲獎片《黑暗對峙》、《愛.誘.罪》製作團隊打造,並找來英國影壇最具前瞻性的鬼才導演 Ben Wheatley 執導。
(延伸閱讀:「所有婚姻裡都有秘密…」被指比《失蹤罪》更出色,驚悚迷不能錯過 Netflix 這部全新作品!)
《Emily in Paris 艾蜜莉在巴黎》:10 月 2 日
youtube
芝加哥行銷主管艾蜜莉正處於二十幾歲的事業博殺期,她意外得到在巴黎的夢想工作。新生活充滿醉人冒險和驚人挑戰,看她如何努力兼顧職場、友誼和戀情。本劇為《色慾城市》皇牌製作人 Darren Star 全新力作,全劇造型交由《穿著 Prada 的惡魔》當代時尚教母 Patricia Field 親自操刀,Lily Collins 則擔任女主角兼製作人。
(延伸閱讀:屬於時尚女生的劇集:Lily Collins 主演的《Emily in Paris》單是預告已經換上 20 套服裝!)
《The Trial of the Chicago 7 芝加哥七人案:驚世審判》:10 月 16 日
youtube
在 1968 年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生的一場示威抗議,原應和平進行,卻演變成群眾與警察及國民兵的暴力衝突。主導這場社運的「芝加哥七人」隨後遭聯邦政府控以各式罪名,展開美國司法史上惡名昭彰的驚世審判。
奧斯卡金獎編劇 Aaron Sorkin 自編自導,故事取材於真實歷史事件,由《超能計劃》Joseph Gordon-Levitt、《丹麥女孩》Eddie Redmayne、《鳥人》Michael Keaton 等實力派演員主演。
《The Haunting of Bly Manor 陰宅怪事》:10 月 9 日
youtube
在歷經一場變故之後,亨利雇用年輕的美國保姆來照顧變成孤兒的姪子和姪女,和廚師、管理員和管家一同居住在莊園中。在一片戰慄的哥德式氛圍中,隱藏數世紀的暗恨情仇及暗黑秘密等待被發掘,在這裡,死亡並不代表消失。《陰宅異事》編導 Mike Flanagan 及製作人 Trevor Macy 聯手打造續作《陰宅怪事》,改編 1898年恐怖小說《碧廬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aw),前作演員都將回歸演出。
(延伸閱讀:Netflix 最佳恐怖劇集:《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第 2 季預告正式出爐!)
《The Queen’s Gambit 后翼棄兵》:10 月 23 日
《后翼棄兵》改編 Walter Davis 同名小說,故事設定在 1950 年代肯塔基州的一間孤兒院,有位年輕女孩發現自己擁有驚人的國際棋天賦,卻也同時辛苦對付藥物成癮,以及伴隨天賦而來的種種煎熬。
兩次榮獲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提名、《無神之境》主創 Scott Frank 擔綱編導及監製,由影壇新星 Anya Taylor-Joy 演出劇中陰鬱古怪的天才棋手貝絲,其他演員包括《哈利波特》Harry Melling、《權力遊戲》Thomas Sangster、《小丑》Bill Camp。
《Hubie Halloween 萬聖節救星修比》:10 月 7 日
儘管修比對家鄉麻省塞勒姆(以及鎮上著名的萬聖節慶祝活動)鞠躬盡瘁,鎮上的大人小孩仍然以取笑他為樂。不過今年萬聖節,晚上卻真的傳出恐怖的動靜,鎮上出現逃犯和一位神秘的新鄰居,當鎮民開始神秘失蹤後,修比挺身而出,試圖說服警察怪事背後的真相,拯救萬聖節的大任就落在修比的肩上了。
Adam Sandler 帶來全新喜劇作品,除了飾演電影中的怪咖主角修比,同時參與編劇和製作,《摩登家族》茱莉鮑溫、《四海好傢伙》雷李歐塔也加入演出。
《Over the Moon 飛奔去月球》:10 月 23 日
一個聰敏過人、熱愛科學的小女孩懷著滿腔熱誠,為了升上月球探個究竟而建造了一艘火箭船。她要向大家證明,月亮女神並不是傳說,而是確實存在的,一場冒險就此意外展開,住滿各種奇幻生物的奇異世界也正等著她。
《飛奔去月球》由奧斯卡得獎導演兼動畫師 Glen Keane 執導,Gennie Rim 及周佩鈴
(Peiling Chou) 監製,聲演陣容包括 Cathy Ang、Phillipa Soo、Robert G. Chiu、Ken Jeong、周約翰 (John Cho)、Ruthie Ann Miles、趙牡丹 (Margaret Cho)、Kimiko Glenn、Artt Butler、諸慧荷 (Irene Tsu)、Clem Cheung、Conrad Ricamora 及吳珊卓(Sandra Oh)。
《The Alienist: Angel of Darkness 沉默的天使:第 2 季》:10 月 22 日

一年後,莎拉開了自己的偵探社,並受雇尋找西班牙領事尚在襁褓中卻遭人綁架的女兒。《沈默的天使》續作,第一季中的三大主演 Daniel Brühl、Luke Evans、Dakota Fanning 將再度搭擋破案。
《Unsolved Mysteries: Volume 2 懸疑未決:第 2 輯》:10 月 19 日
掀起廣泛熱議的犯罪紀錄影集《懸疑未決》將推出第二輯,由原班創作團隊和《怪奇物語》製作公司聯手合作,將延續第一輯的風格調性,帶來在 12 宗愛人因故身亡或離奇失蹤的案件,讓劇迷沈浸在辦案推理的懸疑氛圍中。
(延伸閱讀:Netflix 全新紀錄片《未解之謎》,讓你跟團隊一同解開全球各種懸案!)
《Social Distance 社交距離》:10 月 1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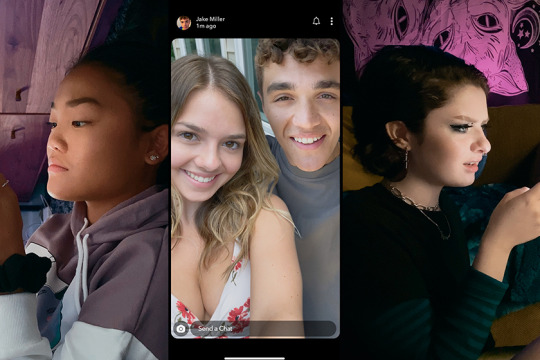
《Social Distance》是一部因應疫情期間而生的遠距拍攝計畫,由《勁爆女子監獄》團隊策劃,影集包含 8 集各自獨立的故事,描繪受疫情影響的人們,在被迫削弱的人際交流、必須實行社交距離的生活中,所面臨的個人情緒和經歷。
《Dick Johnson Is Dead 老豆已死》:10 月 2 日
Kirsten Johnson 多年投入紀錄片製作,對攝影機呈現真實的力量深信不疑。這次她決定用上過往所學的電影知識,拍攝她 86歲的年邁父親走向人生終點的模樣,希望父親的形象得以長存。
監製 Kirsten Johnson 是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第四公民》(Citizenfour)攝影師,本片是她寫給父親的一封溫暖情書,巧妙結合虛實並交織歡笑和淚水,今年更拿下日舞影展評審特別獎。
《BLACKPINK: Light Up the Sky》:10 月 14 日

BLACKPINK 出道至今堪稱「紀錄製造機」,2019年更成為首組登上科切拉音樂節(Coachella)舞台表演的韓國流行音樂女子團體,紀錄片除了收錄與團員 JISOO、JENNIE、ROSÉ 和 LISA 的獨家訪談外,還穿插從未曝光過的畫面,並搶先揭露新專輯的錄製過程,讓全世界的粉絲們都能一窺 BLACKPINK 從練習生迅速崛起為超級巨星的歷程。
(延伸閱讀:Netflix 為 BLACKPINK 推出紀錄片,讓觀眾看到她們迅速崛起的歷程!)
《私生活》:10 月 7 日

眼前世界數據資料已不再具任何隱私性,一群詐騙高手並肩合作,要揭發政府和貪婪企業串謀主導的一樁監控計畫。本劇由「少女時代」徐玄、《請回答1998》高庚杓及人氣配角(《夫妻的世界》、《愛的迫降》)金永敏、金孝珍主演。
《Do Do Sol Sol La La Sol》:10 月 7 日
youtube
透過《阿爾罕布拉宮的回憶》出道的李宰旭在不夠兩年就以實力成為男主角,與女神女神高雅羅在新劇《Do Do Sol Sol La La Sol》中上演浪漫愛情故事。可愛的鋼琴家具蘿蘿正值人生低潮,卻在此時遇見神秘又難相處的鮮于俊。鮮于俊能否讓具蘿蘿重拾生命的意義?
《Start Up:我的新創時代》:待定
徐達美(裴秀智 飾)夢想成為韓版喬布斯,為了賺錢而選擇退學,她以為南道山(南柱赫 飾)是數學天才,於是要兩人一起開創公司。另外,她還將南道山錯認是自己的初戀,而南道山為了追求達美,決定努力工作出人頭地。
延伸閱讀:
>重磅猛片全上架:Netflix 九月份片單整合,每部都值得期待!
>Netflix 最佳恐怖劇集:《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第 2 季預告正式出爐!
>「所有婚姻裡都有秘密…」被指比《失蹤罪》更出色,驚悚迷不能錯過 Netflix 這部全新作品!
>人氣電影系列一口氣上架:劇荒別怕!為你整理 Netflix 八月份必看精彩片單!
Follow us on Facebook: fb.com/POPBEE
Follow us on Instagram: Instagram.com/POPBEE
#POPBEE#Netflix#Drama#Movie#BLACKPINK#EMILY IN PARIS#REBECCA#THE HAUNTING OF BLY MANOR#THE TRIAL OF THE CHICAGO 7
0 notes
Text
ひとみに映る影 第三話「安徳森の怪人屋敷」
☆プロトタイプ版☆
こちらは無料公開のプロトタイプ版となります。
段落とか誤字とか色々とグッチャグチャなのでご了承下さい。
書籍版では戦闘シーンとかゴアシーンとかマシマシで挿絵も書いたから買ってえええぇぇ!!!
→→→☆ここから買おう☆←←←
(あらすじ)
私は紅一美。影を操る不思議な力を持った、ちょっと霊感の強いファッションモデルだ。
ある事件で殺された人の霊を探していたら……犯人と私の過去が繋がっていた!?
暗躍する謎の怪異、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く真実、失われた記憶。
このままでは地獄の怨霊達が世界に放たれてしまう!
命を弄ぶ邪道を倒すため、いま憤怒の炎が覚醒する!
(※全部内容は一緒です。)
pixiv版
◆◆◆
1989年十月、フロリダ州の小さな農村で営業していた時の事だ。
あの村で唯一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近代的施設、タイタンマート。
グロサリーを買いこむ巨人の看板でお馴染みのその大型ショッピングセンター前で、俺はポップコーン屋台付き三輪バギーを駐車した。
エプロンを巻き、屋台の顔ポップ・ガイのスイッチを入れ、同じツラのマスクを被り、
「エー、エー、アーアー。ポップコーン、ポップコーンダヨ」
…スピーカーから間の抜けたボイスチェンジャー声が出ることを確認したら、俺の今日の仕事が始まる。
積載電源でトウモロコシを爆ぜていると、いつもならその音や匂いに誘われて買い物客が集まってくる。
だがその日は駐車場の車が少なく、やけに閑散としていた。
ひょっとして午後から臨時閉店か?俺は背後のマート出入口に張り紙でも貼っていないか、様子を見に行った。
一歩、二歩、三歩。屋台から目を離したのは、たった三歩の間だけだった。
ガコッ!ガコガコガシャン!突然背後から乱暴な金属音がして俺は振り返った。
そこには、一体どこから湧いて出たのか、五~六人の村人が俺の屋台バギーを取り囲んでいた。
奴らはポップ・ガイの顎を強引にこじ開けた。
ガラスケース内のポップコーンが紙箱受けになだれ込む。それを男も女も、思い思いにポリ袋やキャップ帽などを使って奪い合う。
「あぁー!!?何しやがるクソッタレ!!!」
俺はマスクを脱ぎ捨て、クソ村人共を押しのけようとした。その時。
サクッ。…背後で地面にスコップを突き立てたような音がした。
振り返るとそこには、タイタンマートのエプロンを着た店員と…空中に浮く、木の棒?
いや、違う。それは…俺の背中に刺さった、鉈か鎌か何かの柄だ。
俺は自分の置かれた状況が理解出来なかった。背中を刺されたという事実以外は。
ただ、脳が痛覚を遮断していたのか、痛みはなかった。異物感と恐怖心だけがあった。
目の前では相棒が、俺のポップ・ガイが、農村の狂った土人共にぶちのめされている。
奴らはガラスケースを割り、焼けた調理器に手を突っ込んでガラスの破片とポップコーンを頬張り、爆裂前のトウモロコシ粒まで奪い合いながら、「オヤツクレ」「オカシ」「カシヲクレ」などとわけのわからない事を叫んでいやがる。
そのうち俺を刺しやがったあのクソ店員が、俺のジーンズからバギーのキーを引ったくり、屋台を奪って急発進させた。
ゾンビめいた土人共がそれにしがみつく。何人かは既に血まみれだ。
すると駐車場の方からライフルを抱えたクソが増えた。
ターン、ターン、ターン。タイヤを撃たれたバギーが横転する。ノーブラで部屋着みてぇなブタババアが射殺される。俺の足に流れ弾が当たる…痛ぇな、畜生!
ともかく逃げないとヤバい。こいつらきっとハッパでもキメてやがるんだ。
それにしても、俺の脳のポンコツめ。背中の痛みはないのに、なんで足はこんなに痛いんだクソッタレ!
「コヒュッ…コヒュッ…」息ができない。傷口が熱い。体が寒い。全身の血が偏ってきていやがる。
もはや立ち上がれない俺は匍匐前進でマートの死角まで這って逃げた。
そこには大量のイタチと、中心に中坊ぐらいのニヤついたガキが立っていた。
そいつは口元が左右非対称に歪んでいて、ギンギンに目の充血した、見るからに性根の腐っていそうな奴だった。
作業ツナギの中にエド・ゲインみてえな悪趣味なツギハギのTシャツを着て、右手にニッパーを、左手にカラフルな砂か何かの入った汚ねえビニール袋を持っていた。
「おっさん、魚みてえだな」…あ?
「背中にヒレ生えてるぜ。それに口パクパクさせながら地面をクネクネ這いずり回ってさ。
ここは山ばっかだから見た事ねえが、沖に打ち上げられたイルカってこんな感じなのかな」
何言ってやがる…このガキもキチガイかよ。それにイルカは哺乳類だ。どうでもいいがな。
「気に入ったぜ。おっさん、俺が解剖してやるよ」…は??
「心配するな。川でナマズを捌いた事がある。おいお前ら、オヤツタイムだぜ!」
おいジーザス、いい加減にしろ!あのクソガキは俺にキチガイじみた虹色の砂をブチまけてきやがった!
鼻にツンとくるクソ甘ったるい匂い。そうか、こいつはパフェによくかかっているカラースプレーだ。しかもよく見ると、細けえキャンディやチョコレートやクッキーまで混じってい���がる。
ファック!このガキ、俺をデコレーションケーキか何かと勘違いしてんじゃねえのか!?
「あんたのポップコーン、いつも親が買ってたぜ。油っこくて美味かった。
だからあんたの魂は俺達の仲間に入れてやるよ…」
なんでなんでなんで。なんで俺の生皮がいかれたガキのニッパーで引き裂かれてやがる。なんで俺の身体が汚ねえイタチ共に食い荒らされてやがる!
カラースプレーが目に入った。痛え。だからなんで背中以外は痛えんだってえの。
俺が何をしたっていうんだジーザス。みんなの人気者のポップ・ガイがなんの罪を犯したっていうんだ。
やだよ。こんな所で死にたくねぇよ。
こんなシケた田舎のタイタンマートなんかで…おいクソ巨人、お前の事だ!クソタイタンマートのクソ時代遅れなクソ看板野郎!なに見てやがる!
「Get everything you want(何でも揃う)」じゃねえよとっととこのクソガキを踏み殺せ!!
こんなに苦しんで死ななきゃならねぇならせめてハッパでもキメときゃ良かった!死にたくねぇよ!ア!ア!ア!アー!
そうだ。こんな物はただの夢だ。クソッタレ悪夢だ。もうハッパキメてたっけ?
まあいい。こんな時は首筋をつねるんだ。俺は首筋をつねれば大概のバッドトリップからは目覚める事ができるんだ。
そう、こんな風に―
◆◆◆
「あいててててて痛え!!!」
ジャックさんは首筋をつねる動作をした瞬間、オリベちゃんのサイコキネシスを受けて悶絶した。
磐梯熱海温泉の民宿に集った私達一同は、二台繋げたローテーブルを囲い、タルパの半魚人ジャック・ラーセンさんが殺害された経緯を聴取していた。
「そんなに細かく話すな!イジワル!!」
涙目のイナちゃんが、私のモヘアニットのチュニックを固く握りしめたまま怒鳴った。
彼の話に「ライフルを持ったクソ」が出てきたあたりから、彼女はずっと私にしがみついてチワワのように震え続けている。
おかげで買ってまだSNSにも投稿していないチュニックが、ヨレヨレに伸びきってしまっていた。
<あんたあのね、女子高生の前でクソとかハッパとか、言葉を選びなさいよ!>
ローテーブルの対面で、オリベちゃんがジャックさんを叱責する。
「まあまあ。そんで死んだ後はどうなったん…なるべく綺麗な言葉で説明してくれよ」
一方譲司さんは既に、ポメラニアンのポメラー子ちゃんのブラッシングを終え、何故か次はオリベちゃんのブラッシングをさせられている。
「まあ、その後はだな。要するに、お前達のお友達人形にされてたってわけさ」
ジャックさん、オリベちゃん、譲司さん。三人のNICキッズルーム出身者の過去が繋がった。
イナちゃんがこれから行くキッズルームは、バリ島院以外にも世界各支部に存在する。
アジア支部のバリ島院、EU支部のマルセイユ院…オリベちゃんと譲司さんが子供時代を過ごした中東支部キッズルームは、テルアビブ院だった。
(アラブ人ハーフの譲司さんは、十歳まで中東で暮らしていたんだ。)
その当時テルアビブ院には、魂を持つ不思議な人形と、それを操って動かす黒子の少年がいた。
少年は人形と同じ顔のマスクを被っていて、少年自身の意思を持っていなかった。
でもある日突然、少年は人形を捨て、冷酷な本性を剥き出しにしてNIC職員や子供達を惨殺して回ったという。
つまり、少年…生き物の魂を奪って怪物を作る殺人鬼、サミュエル・ミラーは、人形のジャックさんという仮面を被ってNICに近づき、油断した脳力者の魂を収穫したんだ。
「その辺の話は、俺よりお前ら自身の方が嫌でも覚えてるだろ。
あいつがわざわざ変装用の魂をこしらえたのは、オリベ…お前みたいに人の心を覗ける奴が、NICにはわんさかいるからだろうな。
俺は自分が自分の黒子に殺された事なんざ忘れちまってたし、
用済みになった後も奴の脳内に格納されて、長い眠りについていたようだ。
友達や先生方の死に面を拝まずに済んだ事だけは、あのクソサイコ野郎に感謝だな」
ジャックさんがニヒルに笑う。殺人鬼の隠れ蓑にされていたとはいえ、彼とオリベちゃん達の間の友情は本物だったんだろう。
仮面役に彼が選ばれたのは、生前の彼が子供達に愛されるポップコーン売りだったからだと私は推測した。
サミュエルは殺人に、怪物タルパを取り憑かせたイタチを使うらしい。
人間のお菓子や人肉を食べるように調教されたイタチは人間を襲い、イタチに噛まれた人間は怪物タルパに取り憑かれる。
取り憑かれた人間は別の人間を襲う。その人間も怪物に心を支配され、別の人間を襲う。
そうしてゾンビパニック映画のように、怪物に操られた人間がねずみ算式に増えていく。
サミュエルはこのようにして、自ら手を下さずに集団殺し合いパニックを引き起こすんだ。
1990年。二十年前のNIC中東支部を襲った惨劇も、この方式で引き起こされた。
幼い頃のオリベちゃんはその時、怪物タルパとイタチを一掃するために無茶なサイコキネシスを放った後遺症で構音障害になった。そして…
「なあジャック」譲司さんが口を開く。
「アッシュ兄ちゃんって、覚えとるか?
弱虫でチビやった俺を、一番気にかけてくれとった」
「ん、ああ。勿論覚えてるさ。
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の種をペンダントにしていた、サイコメトリーの脳力児。あいつがどうかしたのか」
ジャックさんが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という単語を口にした瞬間、譲司さんは無意識に頭に手を当て、
「ハァー、…フーッ」肺の空気を入れ替えるダウザー特有の呼吸をした。そして、
「…アッシュ兄ちゃんは。俺の目の前で、サミュエルに殺された。
その時…兄ちゃんの魂は胸の種に宿って、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になったんや」胸元に手を当てて言った。
「なんてこった…!」
ジャックさんは目元を強ばらせる。
話を理解できなかったイナちゃんが、私のチュニックをクイクイと引っ張った。
「ええとね…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っていうのは、簡単に言えば動物の霊魂を宿して心を持つ事ができる霊草の事なの。
譲司さんの幼馴染のアッシュさんは、殺された時、その種を持っていたおかげで怪物に魂を取られずに済んだけど、代わりに植物の精霊になっちゃったんだ」
「そなんだ…。ヘラガモ先生、今も幼馴染さんいるですか?」
「ああ。種はもう花を咲かせてなくなっとるけど、兄ちゃんは俺と完全に溶け合って、二人合わさった。
せやから、アッシュ兄ちゃんは今俺の中におる」
「すまねえ…あいつの事を思い出せなくて、お前らみたいなガキ共を巻き込んじまって。本当にすまねえ」
ジャックさんがオリベちゃんと譲司さん、そして譲司さんと一つになったというアッシュさんをまっすぐに見つめる。
一方、当のオリベちゃん達は、ジャックさんが謝罪する謂れはないとでも言いたげに、彼に優しい微笑みを向けていた。
「ヒトミちゃん」
しんみりとしたムードの中、イナちゃんが芝居がかった仕草で私のチュニックを掴んだ。
「ごめんなさい、チュニック、伸ばしちゃたヨ。
お詫びにあげたい物あります。お着替え行こ」
「え?」
「ポメラーコちゃんにも!」
「わぅ?」
私はポメちゃんを抱えたイナちゃんに誘導され、別室に移動した。
◆◆◆
「へえ、韓国娘。あんた粋なことするじゃないの」
高天井の二階大部屋。剥き出しの梁の上では人間体のリナが、うつ伏せで頬杖をついたまま私達を見下ろしていた。
その時イナちゃんが着ていたのが水色のパフスリーブワンピースだった事も相まって、まるで不思議の国のアリスとチェシャ猫みたいな構図だ。
二階に上がったのは私とイナちゃん、ポメラー子ちゃんにリナ。階下に残ったのは中東キッズルーム出身の三人のみ。
そういう事か。
「『後は若い人達に任せましょう』。私が好きな日本のことわざだモン」
胸を張ってイナちゃんが得意気に言う。それ、ことわざだったっけ…?
イナちゃんは中身を詰めすぎて膨らんだスーツケースの天板を押さえながら、布を噛んだファスナーを力任せに引いて開けた。
ミチミチの服と服の間から、哀れにも角がひしゃげたユニコーン型化粧ポーチを引き抜くと、何かを探すように中身を床に取り出していく。
「ボタニカル・ボタニカル」のオールインワン下地、「リトルマインド」のリップと化粧筆一式、「安徳森(アンダーソン)」の特大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
うーん、錚々たるラインナップ!中華系プチプラブランドの安徳森以外、どのコスメも道具も、高校生のお小遣いでは手を出し難い高級品だ。
蝶よ花よと育てられた、いい家のお嬢様なのかもしれない。
「あったヨ!」
ユニコーンポーチの底からイナちゃんが引き抜いたのは、二重丸の形をした金色のペンダント。
「ここをこうしてネ…ペンダントと、チャームなるの」
二重丸の中心をイナちゃんが押し上げると、チリチリとくぐもった金属音を立てて内側の円形が外れた。それは留め具付きの丸い鈴だった。
『링』
『종』
中央が空洞化してリング型になったペンダントと鈴の双方に、それぞれ異なる小さなハングル文字が一文字ずつ刻印されている。
それを持ったイナちゃんの両手も、珍しく左右で手相が全然違う模様なのが印象的だった。
左は生命線からアルファベットのE字状に三本線が伸びていて、右は中央に大きな十文字。手相には詳しくないから占いはできないけど。
イナちゃんはE字手相の左手でペンダントを私の首にかけ、右手の鈴はポメちゃんの首輪に括りつけた。
金属のずっしりとした重量感。これも高価な物なんだろうと察せる。
「イナちゃん、これ貰っちゃっていいの?まさか金じゃないよね?」私は恐る恐る聞いた。
「『キム』じゃないヨ。それは、『링(リン)』と読みます。リングだからネ。
キーホルダーは『종(チョン)』、ベルを意味ですヨ」
「い、いやいや、ハングルの読み方を聞いたんじゃなくて」チャリンチャリンチャリン!「ワンワンっ!」
私のツッコミは鈴の音を気に入って飛び跳ねるポメちゃんに遮られた。
「ウフッ、ジョークジョーク。わかてますヨ、ただのメッキだヨ」
「な…なんだ、良かった。それでもありがとうね」
貰ったペンダントを改めて見ていると、伸びたチュニックが一層貧相に見えてきた。
この後私達はお蕎麦屋さんに夕食を予約している。さすがにモデルとして、こんな格好で外を出歩く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折角貰ったいいペンダントに合わせて、私は手持ちで一番フォーマルな服に着替える事にした。
切り絵風赤黒グラデーションカラーのオフショルワンピースだ。
「アハ!まるで不思議の国のアリスとトランプの女王だわ」
梁から降りたイナが、私とイナちゃんが並んだ様子を比喩する。
「そういうリナはさっきまで樹上のチェシャ猫だったじゃない」
「じゃあその真っ白いワンコが時計ウサギね」
私達は冗談を重ね合ってくすくす笑う。こんな会話も久しぶりだな。
そこにイナちゃんも加わる。
「ヒトミちゃん、ジョオ様はアイシャドウもっと濃いヨ」
さっき床に散らかしたコスメの中から、チップと安徳森の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を持って、イナちゃんはいたずらに笑った。
安徳森、アンダーソンか…。そういえば…
「私…磐梯熱海で、アンダーソンって名前の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の精霊と会ったことがあるな」
私はたった今思い出した事を独り言のように呟いていた。
イナちゃんの目が好奇心に光る。
「さっき話しした霊草の魂ですか?ここにいるですか!」
「うーん、もう3年前の事だけどね…」
それは私が上京する直前のこと。
ヒーローショーの悪役という、一年間の長期スパンの仕事を受ける事になった私は、地元猪苗代を発つ前にここ磐梯熱海温泉に立ち寄った。
和尚様と萩姫様にご挨拶をするためだ。
するとその日は、駅を出るとそこらじゅうに紫色の花が咲いていた。
私は合流した萩姫様に伺い、それが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の花だと教わった。
そしてケヤキの森で、それらの親花である魂を持つ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アンダーソン氏を紹介して頂いた。
アンダーソン氏は腐りかけの人脳から発芽したせいで、ほとんど盲目で、生前の記憶もかなり欠落していた。
ただ一つ、自分の名前がアンダーソンだという事だけ辛うじて覚えていたという。
とはいえ、元警察官の友達から聞いた話では、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は麻薬の原料にもなり日本では栽培を許可されていないらしい。
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には類似種の『マンドラゴラ・オータムナリス』というよく似た花があるから、駅に咲いていたものに関しては、オータムナリスだ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
「改めて今熱海町に来たら、もう駅前の花はなくなってるし、さっきケヤキの森を通った時もアンダーソンさんはいなかったの。
もう枯れちゃったかな…魂はどこかにいるかも」
「だといいネ。私も見てみたいです。
そ��お花さんに因みな物あれば、私スリスリマスリして呼び出せるですけど」
「え、すごいね!イナちゃん降霊術もできるんだ…」
スタタタタ!…私達が話している途中から、誰かがものすごい勢いで階段を駆け上がる音がした。
二階部屋の襖がターン!と豪快に開き、現れたのはオリベちゃん。
<その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よ!今すぐ案内して頂戴!!>
「オモナっ!」驚いたイナちゃんが顔の前で手を合わす。
「え!?ど、どういう事ですか?」
<サミュエルは最後に逃亡する直前、ジャパニーズマフィアの薬物ブローカーだったの。そして麻薬の原料として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の種子を入手していた。
だからそれを発芽させるために、ブローカー仲間の女子大生を殺害して、その人の肉や脳を肥料に与えていたというのよ>
「ああ…女子大生バラバラ殺人の事ですね。指名手配のポスターで有名な」
物騒な話題にイナちゃんは顔を引きつらせる。またストレスで悪霊を呼び寄せないように、すかさずリナは彼女の体を抱き寄せて頭を撫でた。
イナちゃんは知らないだろうけど、実はサミュエルの通名、水家曽良という名は日本では有名だ。
彼は広域指定暴力団の薬物ブローカーで、ブローカー仲間だった女子大生を殺害した罪で指名手配されている。
だから駅や交番のポスターには、彼の名前と似顔絵がよく貼ってあるんだ。
<その女子大生から生まれたと思しき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がね…なんと、眠っていたジャックを呼び覚まして助けた張本人らしいのよ!>
「そうなんですか!」
オリベちゃんに続き、そろそろとジャックさんと譲司さんも二階に上がってきた。
ただ譲司さんは、興奮気味のオリベちゃんとは裏腹に煮え切らない顔をしている。
「いや、せやけどなオリベ。殺された女子大生は『トクモリ・アン』って名前やろ。
ジャックが言っとった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は『アンダーソン』って名乗っとったらしいし…『アン』しか合っとらんやん」
トクモリアン?ああ、はい。
私とイナちゃんとリナは三人同時に察して、ニヤリと顔を見合わせた。
「ダウザーさん、その被害者の名前の漢字、当ててあげようか」挑発的にリナが譲司さんに微笑む。
リナが目配せすると、イナちゃんはあの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を譲司さんの前に持っていった。
「あん、とくもり…安徳森!何で?」
「そです。でもちがうヨ!中国語それ『アンダーソン』て読みます」
「なるほど!」
「そういう事だったのか」
<え…ど、どういう事ですって?>
譲司さんとジャックさんが納得した一方、ユダヤ人のオリベちゃんだけは頭にはてなマークを浮かべた。
私はパレットの漢字を指さしながら、非アジア人の彼女に中国語と日本語の漢字の読み方を解説した。
<じゃあ、中国語でそれはアンダーソンになって、日本語ではアン・トクモリになるの!面白いカラクリだわ。>
「ファティマンドラ化した徳森安は生前の記憶を殆ど失っている。
その文字列が印象に残っていても、自分の名前じゃなくて有名な化粧品ブランドの読み方をしちまったのかもな。
あれでも女子大生だったし」ジャックさんが補足する。
<となるとやっぱり、殺された女子大生で間違いないようね。
ジャックを蘇らせてくれたお礼と、サミュエルに関しての情報も聞きたいわ。
どうにかして彼女と会えないかしら?>
「ケヤキの森にいないなら…怪人屋敷に行けば何かわかるかもしれねえな。
まだあいつが成仏していなければ、だが」
ジャックさんが親指に当たるヒレをクイクイと動かす。その方角は石筵を指していた。
「怪人屋敷って、石筵の有名な心霊スポットですよね?山にある廃工場の。
実際はこの辺りで生まれたタルパとか式神達の溜まり場で、それを見た人間が『人間とも動物とも違う幽霊がいっぱいいる!』と思って怪人屋敷って呼び始めた…」
「何よ、じゃあ私も人間にとっては怪人だっていうの?失礼しちゃうわ!」
リナがイナちゃんを撫でながらプリプリと怒る。
「怪人屋敷なら俺が場所を案内できる。かつてのサミュエルの潜伏地点だ」
「そうか。よし、夕食までまだ時間がある。車で行ってみよう」
◆◆◆
日が沈みかけていた。
私達を乗せたミニバンは西日に横面を照らされながら、石筵の霊山へ北上する。
運転してくれたのは、譲司さんに半身取り憑いたジャックさんだ。
生前は移動販売をしていただけあって、私達の中で一番運転が上手い。同乗していて、坂道やカーブでも全くGを感じない。
譲司さんも彼のハンドルテクに、時折感嘆のため息を漏らしていた。
故人の意識にハンドルを任せたのはギリギリ無免許運転かもしれないけど、警察にそれを咎められる人はいないだろう。
廃工場の怪人屋敷か。私が観音寺に住んでいた頃は、そんな噂があ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
でも行ったことは何度もある。
あそこには沢山の式神、精霊、タルパ、妖怪がいた。みんな幼い私と遊んでくれたいい人達だ。
人に害をなす魂がいなかったのは、すぐ近くに和尚様が住んでいらしたから、だったのかも。
私はリナと共に影絵を交えながら、そんな思い出話をイナちゃんやオリベちゃんに語った。
「ジャックさんは、会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和尚様。
怪人屋敷のすぐそばの観音寺です」
私はバックミラー越しにジャックさんを見ながら話題を振った。
「残念だが、俺があの屋敷にいた時は、サミュエル本体に色々あって夢うつつだったんだ。
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の幻覚と現実の狭間をずっと彷徨ってた感じだ。
けど、少なくともその世界には神も仏もいなかったぜ」
「そうなんですか…。後でちょっと寄らせて下さい。紹介したいです」
「ああ、俺も知り合っておきたい。本場チベット仕込みのタルパ使いなんだろ、その坊さん。
だったらあのクソに作られた俺みてえな怪物も、いざという時に救って下さるかもしれねえよな」
「そんなこと言わないで下さい、ジャックさんいい人ヨ」
イナちゃんが身を乗り出して反論した。
ジャックさんは目線をフロントガラスに向けたまま、小さく口角を上げた。
カッチ、カッチ、カッチ。リズミカルなウィンカー音を鳴らしながら、ミニバンは車道から舗装されていない砂利道に入る。
安達太良山の麓にそびえ立つ石筵霊山の、殆ど窓のない無機質な廃工場が見えてきた。
多彩な霊魂が行き交い、一部の界隈では魔都と呼ばれるこの郡山市でも、ここは一際邪悪な心霊スポットとして有名な場所だ。
そんな噂が蔓延しだしたのはいつ頃の事だっただろうか。
少なくとも私の知っている廃工場は、そこまで物々しい場所じゃなかったのに…。
ジャックさんが工場脇の搬入口にミニバンを駐車している間、私は和尚様の近況を案じた。
その不安感が現実になったかのように、ミニバンを開けた瞬間何かを察知して顔を引きつらせたのは、意外にも譲司さんではなくオリベちゃんだった。
<あの二階、何かある。何だかわからないけどとんでもない物があるわ!>
テレパシーやサイコキネシスを操る彼女だけが、その有り余るシックスセンスで異変を察知したんだ。
オリベちゃんが指さした工場の二階には窓があるけど、中は暗くて見えない。
私やリナ、イナちゃん、ジャックさんには遠すぎて霊感が届かないし…、
「すまん、オリベ。あの窓はめ殺しで開かんやつやから、俺にはわからん」
空気や気圧でダウジングする譲司さんには尚更読み難い状況だ。
「それより、あっちに…」
譲司さんが言いかけた事を同時に反応したのは、ポメラー子ちゃんだった。
ポメちゃんは鈴を鳴らしながら譲司さんの脇をすり抜け、バイク駐輪場らしきスペースに駆けていき、
「わうわお!」こっちやで!とでも言っているような鳴き声で私達を誘導した。
そこにあった物は…
◆◆◆
「うぷッ」
条件反射的に私の胸がえずく。直後に頭痛を催すような強烈な悪臭を感じた。
隣でオリベちゃんが咄嗟に鼻をつまみ、リナはイナちゃんの目を隠す。
既に察していた譲司さんは冷静に口にミニタオルを当てていた。
そこにあったのは、腐敗した汚泥をなみなみと湛えた青い掃除用バケツ。
ハエがたかる焦茶色の液体の中には、枯葉に覆われて辛うじて形を保った、チンゲン菜のような植物の残骸が見える。
花瓶に雨水が入って腐ったお墓の仏花を想起させるそれは…明らかに、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の残骸だった。
「アンダーソン」ジャックさんが歩み寄る。
「もう、いないのか?あいつを待ちくたびれて、くたばっちまったんだな」
ジャックさんは汚泥にヒレをかざしたり、大胆にも顔を突っ込んだりしながら故人の霊魂を探した。
でも、かつて女子大生の脳肉だった花と汚泥が、彼の問いかけに脳波を返す事はなかった。
するうちリナの腕をほどいてイナちゃんが割って入る。
また彼女の精神がショックを受けて、悪霊を呼び出さないかと心配になったけど、
驚く事に彼女は腐った花に触れ、「スリスリマスリ…スリスリマスリ…」と追悼の祈りを捧げた。
「い…イナちゃん、大丈夫なの?」私達は訝しみながら彼女の顔色を覗きこむ。
しかしイナちゃんは涼しい顔で振り返った。
「安徳森さん、ジャックさんのオンジン。だたら私のオンジンヨ。
この人天国に行ってますように、そこにいつかジャックさんも行けますように。
スリスリマスリ、私お祈りするますね」
イナちゃんが微笑む。その瞬間、悪臭と死に満ちた廃工場の空気が澄み渡った気がした。
譲司さんは前に出て、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をイナちゃんの手からそっと取り、目を閉じる。
「オモナ…ヘラガモ先生?」
「サイコメトリーっていってな。触れた物の残留思念、つまり思い出をちょっとだけ見ることが出来るんや。
死んだ兄ちゃんがくれた脳力なんよ…」目を閉じたまま譲司さんが答えた。
そのまま数秒集中し、彼は見えたヴィジョンをオリベちゃんに送信する。
それをオリベちゃんがテレパシーで全員に拡散した。
ザザッ…ザリザリ…。チューニングが合わないテレビのように、ノイズ音と青黒い横縞模様の砂嵐が視覚と聴覚を覆う。
やがて縞模様は複雑に光彩を帯びて、青単色のモノトーン映像らしきものを映し出し、ノイズ音の隙間からも人の肉声が聞こえてきた。
ザザザ「…ん宿のミ…ム、元店ち…すね。署までご同こ」ザザザザッ「…い人屋敷へか…んな化け物を連れ」ザザ…「…っている事が支離滅れ…」「…っと、幻覚を見」ザザザザッ…
「あかん。腐敗が進みすぎて殆ど見えん」譲司さんの額は既に汗ばんでいる。
それでも彼は…プロ根性で、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を握る手を更に汚泥の中へ押しこんだ!
更に、汚泥が掻き回されてあまつさえ悪臭の漂う中、「ハァー、フゥーッ…ウッ…ハァー、フゥーッ…」顔にグッショリと脂汗を湛えてえずきながら、ダウジングの深呼吸を繰り返す!
彼の涙ぐましすぎる努力と、サイコメトリー・ダウジングの相乗効果によって、残留思念は古いVHSぐらい明瞭になった。
「新宿のミラクルガンジ…」ザザッ「…元店長の水家曽良さんですね。署までご同行願えますか」ザザザッ。
未だ時折ノイズで潰れているが、話の内容から女性警察官らしき声だとわかる。でも映像に声の主は映っていない。
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の低い目線視点でわかりづらいが、映像で確認できる人物はサミュエル・ミラーらしき男性だけだ。
「あ?はは、なんだ…」ザザザッ「一体何の冗談…」ザザッ「さあ、怪人屋敷へ帰るぞ…」ザザッ。
オリベちゃんの口角が露骨に下がった。これは水家曽良、つまり殺人鬼サミュエル・ミラーの声だろう。
「言っている事が支離滅裂で…」ザザザッ「…え。彼はきっと幻…」ザザッ。
サミュエルとは違う男性と、女性の声。彼を連行しようとしている『見えない警察官』は、複数人いるようだ。
「幻覚?何を今更。…あれも、これも!ははは!ぜんぶ幻覚じゃねえか!!!」ザバババババ!!
錯乱したサミュエルが周囲の物を手当り次第投げる。
ファティマンドラの安徳森氏は哀れにも戸棚に叩きつけられ、血と脳肉が飛び散った。
その瞬間から、またノイズが酷くなっていく。
「はいはい。後でじっくり聞い…」ザザッ「暴れな…」ザザッ「…せ!どうせお前らも俺の妄そ」ザリザリ!ザバーバーバー!!
残留思念はここで途絶えた。
「アー!」色々と限界に達した譲司さんが千鳥足で、駐輪場脇の水道に走る。
譲司さんは汚い手で触れないように肘で器用に蛇口を回すと水が出た。
全員が安堵のため息を漏らす。幸い廃工場の水道は止まっていなかったみたいだ。山の湧き水を汲んでいるタイプなんだろう。
同じく安徳森氏に触ったイナちゃんも、譲司さんと紙石鹸をシェアしながら一緒に手を洗った。
◆◆◆
グロッキーの譲司さんを車に乗せるわけにもいかず、私達は扉が開けっ放しの廃工場、通称怪人屋敷のエントランスロビーで休憩する事にした。
「あんた根性あるのね。見直したわ!」リナが譲司さんの周りをくるくる飛び回る。
対して満身創痍の譲司さんはソファに横たわり、「やめてぇ…」とヒヨコのような弱々しい声で喚いた。
<無茶した割に手がかりにならなかったわね。サミュエルはまだ指名手配犯だから、あれは警察じゃない。
でも正体はわからないままよ>手厳しいオリベちゃん。
「無茶言わんでくれぇ…あんなん読めへんもんもうやあわあ…」最後の方は言葉にすらなっていない譲司さん。
結局、あの偽警察官は何者だったのか…もし残留思念の通りなら、生きた人間じゃない可能性もある。
それでも、イナちゃんにお祈りされ、譲司さんにあそこまで記憶を読み直してもらった安徳森氏は、浮かばれるだろうと願いたいものだ。
カァーン!…カァーン!…電気の通っていないはずの廃工場で、突然電子音質の鐘の音が鳴った。
リナとイナちゃんがビクッと身構える。…いや、リナ、あんた怪人側の人じゃん。
「俺や」音源は譲司さんのスマホだった。
彼は以前証券会社の社長だったから、これは株式市場の鐘の音なのかもしれない。
譲司さんがスマホを出そうとスウェットパンツのポケットをまさぐる。指が見えた。穴が開いているのを着続けているみたいだ。
「もしもし?」譲司さんはスマホを耳に当てた。着信は電話だった。
(もしもし。すまない、テレビ通話にしてくれないか?)
女性の声だ。静かな廃工場だから、スピーカー越しに相手の声が聞き取れる。
電話をかけておいて名乗りもしない相手を訝しみながら、譲司さんは通話をカメラモードに切り替えた。すると…
「あ…あなたは、まさか!」
驚嘆の声を上げた譲司さんに、私達全員が近寄る。
皆でスマホの画面を覗かせてもらうと、テレビ通話のカメラは私達の顔ではなく、誰もいないロビー奥の方向を映している。
でも画面の中では、明らかに人工霊魂とわかる、翼の生えた真っ赤なヤギが浮遊していた。
0 notes
Text
【新北市。瑞芳區】台灣必遊秘境之地!大自然下雕鑿的天然美景@深澳岬角象鼻岩

四個女人又要去旅行了!
一大早在台北集合準備,我們要繞向北海岸,前往台灣秘境之一-象鼻岩
▼ 跟著導航走在濱海公路上,目的地到達是在一個小小的空地上,車子只能停在這裡,其餘的路只能靠雙腳了!

▼ 停車後要到象鼻岩的距離其實不遠,只是沿途的路不太好走,一會兒碰到消波塊、一會兒又碰到許多石頭


▼ 不過,路上的風景不錯,偶爾可以停下腳步欣賞一下

▼ 我們走過一片蕈狀岩

▼ 北海岸因地形之故,長期受到海水侵蝕及風化的關係,造成特殊的自然奇景,雖然這裡沒有像野柳地質景觀那麼狀觀的蕈狀岩,不過小小顆的蕈狀岩,其實蠻可愛的。

▼ 很佩服大自然雕鑿技術!將巨岩雕出一道天然的拱門

▼ 但走進一看,還真的像大象的鼻子

▼ 遠方那座小島應該是基隆嶼吧!


▼ 這張很像是正在笑的大象,對吧?!

▼ 已經有人先登頂了!

▼ 對於這種有"高度"的地方,請原諒我…給我一點時間適應一下!我還是先幫各位拍些"致青春"的青春照好了!


好熱血哦!

▼ 終於,我也上來了…難得有的四人合照!

▼ 天啊~~我是花了多大的力氣和勇氣來到這裡的。想到拍到不同的照片,真的需要犧牲…

▼ 還好拍得夠遠,不然會看到我顫抖的容顏....不過,可以爬上與象鼻合照,對我來說真的很難得…


▼站在高處,可以看見懸崖上的蕈狀岩。有時,要挑戰自己,看的世界才會不一樣!

▼ 算是有登頂了啦!我們沿著來時路往回走下去

▼ 意外發現,隔著海灣,另一邊就是九份的水湳洞

自然界無形的力量創造出鬼斧神工的傑作,如此壯麗令人囋嘆不已!下次有機會帶著家人一起來欣賞這天然奇景。
深澳岬角象鼻岩怎麼去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深澳
開放時間:全天開放(建議白天)
開車:國道1號→62快速公路→濱海公路(台2線)→續行深澳路即可以抵達
台北市更多景點~~
【台北市。士林區】逛科學@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台北市。中正區】走進藝術@寶藏嚴
【松山區->新店區】天北���南慢慢遊@松山機場觀景台&碧潭
【台北市。中山區】迷宮花園的探險@花博新生公園
【台北市。信義區】要往「記住」的旅客們,請搭乘月亮公車
【台北市。中山區】陪伴台北人共同兒時回憶的遊樂園~~臺北市立兒童育樂中心
【台北市。士林區】新樂園怕人潮多嗎?看我的聰明玩法@臺北市兒童新樂園
【台北市。中正區】幾米概念店悄悄進駐華山文創園區!故事團團轉-Never Ending Story
【台北市。松山區】騎士堡-小美人魚的家(京華堡)
【台北市。中山區】暑期玩水第一彈~2015大佳童樂會@大佳河濱公園
【台北市。信義區】穿越時空,回到採礦年代,感受舊礦坑的特色風情@和興炭坑
新北市更多景點~~
【新北市。烏來區】內洞。深呼吸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綠寶石@二叭子植物園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牛伯伯蝴蝶園
【新北市。新店區】呵佬甲會答舌的陽光運動公園
【新北市。三峽鎮】皇后鎮森林
【新北市。新店區】健行淨山校外活動-再訪二叭子植物園
【新北市。新店區】充滿書香氣息,改走文青路線的一天@新店北新圖書閱覽室之兒童館
【新北市。新店區】親子共讀的好地方@安坑青少年圖書館
【新北市。新店區】隱身在都市中的小森林@安康森林公園
【新北市。新店區】一篇值得自省的遊記@角塾山居(原驛馬圓園)
【新北市。新店區】自己動手作,好吃又好玩@伊薇特冰淇淋夢工場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秘境林蔭小徑,我家的後花園~文筆山系統-將軍嶺步道
【新北市。土城區】流汗流淚的登山行,我們竟然登上小百岳!土城天上山步道
【新北市。萬里區】金山必吃中途美食知味鄉烤玉米、求財求緣就是要來金山財神廟&萬里情月老廟
【新北市。新店區】公園散策"櫻木花道"賞河津櫻@陽光運動園區
【新北市。石門區】不用等到四月,現在就綠了!絕美海濱奇景@老梅綠石槽
【新北市。三芝區】超吸睛!以貝殼及珊瑚打造的海底廟宇@富福頂山寺十八羅漢洞(貝殼廟)
【新北市。新店區】雙線步道!綠線一覽山水美景、藍線橫渡百年輕舟@和美山登山步道
還有更多…
歡迎來到我的部落格 http://blog.xuite.net/shoran63/blog
喜歡我的文章,請給我一個讚哦!愛玩。不累。PLAY
3 notes
·
View notes
Link
範主說:時勢造英雄這個問題似乎已經不是 "TVB 還能否達到過去的高度 ",而應該是 "TVB 為甚麼再也不可能達到過去的高度 " 了,因為這個問題本質上已經沒甚麼懸念。因為當下的情勢繼續下去,無線已經不可能再回到巔峰,已經是大家都能夠看到的現實,我的看法是,這個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是單一的。長久以來,很多人都把 TVB,包括臺灣和新加坡等地影視業的衰退,視作是內地影視業和影視資本崛起的必然結果;也有人提到,新生代的香港演員實力不濟,相比前輩來說水準大幅褪色,是無線電視劇一落千丈的本質原因。其實在我看來,這全都是香港影視行業大幅衰退的原因,但也並不是全部原因,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催成了這種情況的產生,這些因素甚至可以用互為因果四個字來概括。(一)首先,我想要說的是,香港影視行業的繁榮,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是吃了內地的紅利,尤其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建國初期那會,一方面是不少在內地的優秀青年中年演員紛紛來到香港,另一方面大批當時的社會中上層攜家帶口地逃到香港,這波紅利恰恰就是讓香港電影行業繁榮起來(電視劇在後來才出現,但是電視劇草創時期就是很多電影演員轉電視劇的)的根本我在這裡舉些 TVB 觀眾都非常熟悉的例子,比方說已經去世多年的兩位老演員," 蝦叔 " 關海山,以及鮑方。" 蝦叔 " 是廣州人,出身於粵劇世家,很小就開始登臺表演了,1937 年抗戰爆發之後來到香港;鮑方是南昌人,同樣也是當時民國的中上層出身,在抗戰期間就登臺演了大量的話劇,在解放戰爭期間來到香港。除此之外,包括比他們兩位略微年輕一些,出生於 1930 年左右的李香琴(順德人),胡楓(廣州人),穀峰(上海人)等等,這些都是 TVB 觀眾不會陌生的老演員,他們都是在不同時期來到香港的。再來說說其他一些人,比如著名的 " 長城三公主 " ——陳思思,夏夢,石慧,她們都是來自滬蘇杭地區的江南姑娘,其中夏夢和陳思思都是上海人,石慧是浙江吳興人,這三位也都是在解放前後跟隨家人遷居到香港的。既然說到上海人,那就順便再提幾位,比方說另一位上海人,當時著名的電影小生嚴化和他的夫人,同樣是著名影星的紅薇,也在上世紀 40 年代末那會來到了香港,而他們的兩個兒子,TVB 的觀眾也再熟悉不過了——秦沛和薑大衞,當然,他們還有一位同母異父的弟弟爾冬升 ……和秦沛,薑大衞基本同輩的香港上海人,還包括岳華,陳鴻烈等人,以及岳華的夫人恬妮(當然,還有恬妮的妹妹恬妞)等等,當然,還有 TVB 觀眾不會不認識的 " 阿姐 " 汪明荃,以及 " 肥姐 " 沈殿霞。。。當然,還有出生在蘇州的潘迎紫,等等等。嗯,畢竟答主是上海人,所以可能這方面比較熟悉 …… 胡蝶演藝生涯的最後歲月,同樣也是在香港度過的了 …… 當然,像容如意,容小意姐妹這些名字,也很值得一提。簡而言之,香港影視行業的起飛,靠的是背後整個粵語地區的大量演藝人才。在 30 年代至 50 年代紛紛來到香港;靠的是隨著解放戰爭的進行,作為當時中國電影行業中心的上海,已經成名的演員,以及大量社會中上層的人士都來到香港,形成了一個基數龐大的香港上海人社區;同樣的,還有從全國其他地區逃到香港的那批人,包括北京和東北等地的中上層人物 ……光靠香港本土的彈丸之地,沒有這種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紅利刺激,香港的影視圈哪能一飛沖天?現在香港影視業的逐漸衰敗,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這波吃了六七十年的紅利已經到頭了。我就打一個最簡單的比方,今時今日的香港,還有做出比如,讓陳凱歌,陳道明,張國立,鞏俐,章子怡,周迅等(以下省略幾十個甚至一百多個名字)一大批內地頂尖演員,把它作為演藝事業重心的能力嗎?香港在六七十年前,吃到的就是這個級別的紅利。事實上,香港影視圈吃內地的紅利,絕對不止吃這麼一波,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從內地遷移去香港的人可是很多的,而這批人很多又成為了香港演藝圈的中堅力量,比如楊恭如,比如葉璇,比如陳法拉,等等。。。在 90 年代,有不少優秀的內地演員,以交流的方式去香港接戲,而且幾乎從來沒有接過最核心的角色,比如蔣文端(94 射彫英雄傳裡演瑛姑,刑偵 1 裡演鐘可兒,就是李忠義的第一個女友,等等),張延(95 神彫俠侶裡演何沅君,刑偵 1 裡演藍恩美),以及何美鈿(96 笑傲裡演儀琳,97 天龍裡演鐘靈),等等。想必現在大家都難以理解,像何美鈿這樣一個無論顏值還是演技都完爆楊幂等人的演員,張延這樣一個極具古典端莊氣質的美人,竟然只能去香港電視劇裡演一些主要配角,或者是只出場一集的醬油角色,這就是當時香港影視圈如何吃內地紅利的真實寫照,這樣的故事現在還可能發生嗎?現在還有哪個內地的頂級演員,會願意到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演一堆亂七八糟的配角?(二)其次,演技問題。這裡我要說的是,香港電視劇行業的衰落,從演員的層面上來說,花旦始於 1980 年左右的這批人,小生則始於 1970 年左右的這批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年輕一代的演員,所擁有的閱历,所經历的身世浮沉,和老一代的人是沒法相比的。我剛才提到了關海山和鮑方這兩位,也提到了前者是粵劇出身,後者則是話劇出身,而且在解放前就已經長期登臺了,另一位資深的女演員李香琴,同樣也是粵劇出身。比他們幾位更年長的著名演員鄭君綿(在《義不容情》的開頭飾演和岳華打對臺的朱小山律師),不僅演話劇,還做電臺波音,還是名噪一時的歌手。當然,我還沒有提到一位隱藏 boss 鐘景輝老師,各位有興趣的話,不妨看看鐘老師的履历。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這些人的演藝事業從很早就起步了,而且經历過諸如話劇,粵劇(或者京劇等其他地方劇種)的燻陶,這些磨練經历是年輕一輩的演員所難以相比的——同樣值得一提的是臺灣的那些老一輩電視劇演員,同樣也是有類似經历的,尤其是不少演員都有歌仔戲的經历,甚至本身都是歌仔戲的大咖。生活的閱历更加不在一個層次上,有一句話叫做藝術來自生活,這句話對於演員來說真是再恰當不過了——周遭環境時勢的更易,自我生活的幾經沉浮,尤其是少年時代的艱難困苦,甚至顛沛流離,這些並不是所有人都有經历的。演技的退步,普遍來說,和年輕一代的生活閱历相對老一輩人的不足,以及在演藝經历裡所接受的培養培訓方式相對單一,我覺得是不無關系的(嗯,我覺得年輕一代的國內演員也普遍存在這樣一個問題,簡而言之就是從小過得太舒服了,當然,考慮到國內演員接受的高等教育方式,我覺得相比香港等地的藝人培訓班,功底還是要紮實很多的。。)(三)我想要提到一個或許沒有人提到的問題,民族意識,而這其實折射出了很多內在的東西。各位不妨想一件事,大家小時候所看的電視劇,電影,所接受的愛國主義教育,其實並非完全來自於國內的各種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電影電視劇,還有不少來自香港人的手筆。黃飛鴻,霍元甲,陳真這些代表著中華民族精神的形象,在塑造的過程中,香港影視圈做出了多大的貢獻?還有不少壯懷激烈的粵語愛國歌曲,也是香港影視黃金年代的傑作,比方說葉振棠的《萬裡長城永不倒》,汪明荃的《勇敢的中國人》等等。那個年代的香港民國劇,創造出多少鐵骨錚錚的中華男兒形象?看一部黃飛鴻,看一部精武門,甚至各種民國劇裡的情節,都足夠感受得到熱血沸騰的民族情懷,比自己在中小學裡接受到的那些枯燥的,教條式的愛國主義教育,這樣的電視劇才真是更能夠讓人對中華民族的熱愛油然而生啊!上文曾經提到,在當時的香港影視圈有很多上海人,這個人數眾多的上海人社區,也令很多以民國時代的上海為主題的電視劇,不僅在香港,也在內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嚮,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周潤發,趙雅芝,呂良偉在 1980 年主演的《上海灘》。而後來在 1996 年,TVB 又推出了一部由鄭少秋,陳錦鴻,陳松伶,林家棟主演的《新上海灘》,同樣是 1996 年,已經破產的 ATV 拍過一部《千王之王重出江湖》,也是以上海灘的龍爭虎鬥作為背景,同時期小部頭制作的民國劇還有不少——《黃浦傾情》,《刀馬旦》等。這些電視劇不僅代表了一代香港上海人對故土的眷戀,同樣也是历史大背景下充分展現民族情懷,愛國情懷的佳作。當年的香港電視劇,或許有諸多的細節問題,比如大家都說爛了的布景,但是氣魄和格局都是很大的,那些風雲際會的历史節點上,都能夠演繹出風起雲湧,蕩氣回腸的故事。老一輩電影人電視人,對國家對民族的歸屬感,恰恰是他們能夠奉獻出諸多佳作的重要原因——想想阿姐汪明荃如今在面對 ** 分子的時候,依舊高唱《勇敢的中國人》,就足以令人動容。老一輩的香港電影電視人,有些經历過抗日戰爭,那種整個民族所蒙受的屈辱在他們心頭不可能不留下印象,而所有人都經历過的,是港英當局治下,華人抬不起頭來的那種社會地位,是香港皇家警察作為港英當局的打手,行為行事與地痞無賴無異,令良民們深受其害的社會現實,所以他們能夠更加清楚民族精神意味著甚麼。這裡不得不提到,上世紀 70-90 年代,香港產生過很多具有中國古典美韻致的經典影視作品,包括歌曲,當時有很多優秀的譜曲大師,比如顧嘉輝和黎小田等人,都曾經寫出過很多用宮商角徵羽五音所作的經典音樂,配合黃霑,鄧偉雄等人同樣極具中國古典美特色的詞工,堪稱是天作之合。隨���舉幾個例子——除了我之前列舉過的之外,還有張德蘭演唱的《鮮花滿月樓》,汪明荃演唱的《京華春夢》,葉麗儀演唱的《上海灘》,羅文甄妮演唱的 83 射彫主題曲《鐵血丹心》,葉振棠葉麗儀演唱的 84 笑傲主題曲《此際情也可永》,梅豔芳演唱的《似是故人來》等等等等。當年的香港雖然是小地方,但是影視劇的格局卻非常大,立意卻非常高,但是如今的香港,影視劇的格局也隨著社會格局的越來越小,格局越來越窄,立意也越來越低——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05 年之後的那些香港時裝劇,明目張膽貶損內地人的橋段有多少,相信一直看 TVB 的觀眾不會不了解,諸位作為內地觀眾,看到那些橋段的時候會不會覺得發自內心地不舒服呢?最近十多年來,大部分的港劇都是只拘泥於香港一地的意識,說香港的是,道香港的非,這就是民族意識在年輕一代身上逐漸缺失之後,影視行業也會因此深受其害的最有力證據——千萬不要小看社會風氣的轉變對電視電影所形成的沖擊,就像宋詞再妙,往往也只是風花雪月式的精致,比起唐詩那種磅礴的氣韻相差不可以道裡計。大家有沒有發現,TVB 已經很久很久都沒有優秀的古裝劇了,尤其是古裝劇裡最獨有的金庸劇,自從 01 版倚天屠龍記之後,也再也沒有新的作品問世了?曾幾何時,很多人認識到 TVB,其實是通過金庸劇的,比如風靡全中國的古天樂,李若彤版《神彫俠侶》,黃日華,陳浩民版《天龍八部》這些。除此之外,直到本世紀初,TVB 還能夠拍出《帝女花》,《再生緣》這樣的,或者是傳統民間傳說,或者是傳統文學的經典作品,但現在呢?——個中缺失了寫甚麼,想必大家心知肚明。(四)其他的很多東西我想也不必我重複了,比方說 ATV 的倒閉導致 TVB 一家獨大,進而在缺乏競爭壓力的情況下越來越沒有進取心,比方說 TVB 對於員工那種一毛不拔的待遇讓大量優秀藝人流失,進而到內地來尋求發展機會,這些東西都說多說爛了,再展開說也沒太大意思。但是我更想說,香港影視業的繁榮,本身只是特定历史節點上所產生的機遇,這種東西如果沒有足夠的後勁支撐,是沒法長盛不衰的。然而香港社會如今愈發自我封閉,在沒有新鮮血液流入,沒有民族認同感作為支撐,說來說去只是香港一地的陰晴雨雪(哦好吧,香港應該不太會有雪),老一輩演藝人的老本終究會有吃完的一天。這些年香港老一輩的演員,包括很多內地 TVB 資深觀眾熟悉的甘草演員,去世的去世,離巢的離巢,如果無線還不痛定思痛地自我反省過去 20 年來逐漸衰落的原因,那麼有 TVB 特色的電視劇,也會像曾經陪伴過內地觀眾的臺灣劇和新加坡劇那樣,徹底成為历史 ……
1 note
·
View note
Text
超淫蕩的騷婦
美女主播高清無碼直播,註冊會員免費看~
www.twuu.cc
s383app模特主播,腿長胸大臀部翹,有私下的…
www.s383app.com
深夜睡不著,超大尺度一對一私密表演,註冊會員免費看
www.ddimm.com
騷婦:劉晴,年齡28,身高165,漂亮的臉蛋上長著一頭烏黑的長髮,身材保持的非常不錯,豐滿的乳房上有著二顆堅挺的大乳頭,平坦的小肚腩,濃密而不雜亂的陰毛下長著一付非常美的蝴蝶逼,(在這重點介紹一下騷婦的陰戶,騷婦長著二片淡咖啡色很厚的大陰唇,最特別是陰唇的長度非常長,大約有3厘米長,分開陰唇那粉色的洞穴中吐著一粒肉芽),一雙36碼的小腳經常在絲襪的呵護顯得白玉嫩滑!
敏感帶:乳頭(極其敏感),陰蒂,陰唇,腳趾!
性慾亢奮,做愛時有時會潮吹!喜歡使用跳蛋,電動棒等!不過騷婦很少會和其他人做愛,因為她非常享受著那種被人視姦而帶來的快感!
三年前剛認識晴子的時候,並沒感覺有什麼不同之處,只是發覺她的穿著有點與眾不同,後來慢慢的才發覺她原來非常喜歡被人家窺視的感覺!當時心想:「靠,這麼騷的我還是第一次碰見,看來運氣還不錯啊!」
晴子平時很喜歡穿一些透明薄紗的衣服,因為這類衣服很容易透出乳頭來讓路人窺視(騷婦平時從來不帶胸罩),而下半身基本上都是一些很短的超短裙(翹一下屁股或者走高一點的樓梯都能看到內褲的那種)搭配長筒蕾絲邊的超薄絲襪,裡面穿著非常淫蕩的內褲進行走光(有時候是故意走光)來讓人家窺視,騷婦平時都是穿開擋丁字褲或者非常透明而且小到可以把丁字褲的襠部卡在陰唇裡的那種,她說喜歡那種陰蒂被摩擦的感覺,所以此類內褲可以說是騷婦穿的最多的,除了例假可以說天天都是如此,當騷婦走光被人窺視時,乳頭會自己勃起,下面的淫水可以把丁字褲的襠部弄濕,因此騷婦出門一般在包裡還會帶上一條備用!而我也享受著暴露她而帶來的快感!
某天週末我去騷婦家,可是進門後發覺家裡沒人,打了手機才知道她今天自己一個人出去逛街買東西了,等回來後一看,哇!騷婦今天穿了一條黑色的薄紗長裙,上面一件蕾絲上衣裡面帶著一款黑色的胸托,二顆飽滿的大乳頭在蕾絲上衣中微微的翹著,外面罩著一件黑色的搭肩針織衫,仔細一看發覺下面那條薄紗長裙在燈光下非常透明,裡面配了一條紅色的細繩丁字褲,這條T褲是騷比自己在淘寶上買的,前後都是一條線,穿上後等於那條線直接就卡在二片陰唇中,所以前面的陰毛在光線比較好的時候,絕對是若隱若現的,甚至有幾根陰毛已經從裙子中戳了出來,後面的紅色丁字尤其明顯,整個屁股包括臀溝清晰無比!
「親愛的,你終於來了啊,想死你了」
「是啊,最近工作忙,你看,我今天剛剛下飛機就直接過來看你了,來,過來讓我親親」
我一把把她拉在腿上,手直接在陰戶上摸了一把
「哇,想我想的都濕成這樣拉」
「討厭,哪有啊,都是這條T褲害的」
怎麼了,我假裝糊塗的問道:
「早晨出門的時候,我隨手拿了條T褲,出門後才發現有點緊,你看勒在肉肉裡好深哦,走路的時候一直摩擦著下面,今天都走了一天了,-所以害的我下面一直濕噠噠的」
騷婦隨即把長裙撩了上來,讓我看看
真的哦,怎麼那麼緊啊,說話之際我摸著她那卡在T褲外的二片大陰唇揉搓著。。。。。。
我跟你說哦,我回家的時候在公車上還碰到了色狼,那人站在我後面一直用那玩樣頂我,嚇得我都不敢動,後來車上人越來越多了,擠得要死,沒想到那人的膽子也大了,還好我今天穿的是長裙,他竟然把手放在我裙子外面摸我下面,還時不時的拉扯我下面那二片肉肉,我下車的時候那人竟然還跟我說:小姐你能跟我回家嗎!
「哈哈,那不是正合你意嗎!你又不是沒被人摸過!誰叫你每天都穿那麼騷啊」
騷婦一聽,說了聲:你好討厭!就往我懷裡撲了過來!我知道這個騷婦今天一天下來肯定性慾高漲,老子當時就來了個欲擒故縱!因為今天來就是打算晚上帶騷婦去酒吧放鬆一下的!所以就沒給她!
吃過晚飯我坐在沙發上,當時騷婦又來摸我的雞巴!我說:我們等一會去酒吧玩玩,回來後再操你吧!騷婦興奮的說道:「好啊!我好久沒去酒吧了!那我現在就去換衣服!
親愛的,我穿哪件好啊?
隨便吧
最後我過去一看她還是選了一件她經常去酒吧穿的衣服!這是一件黑色小花的真絲裹胸式連衣裙,胸部那塊是全透明的黑紗,二個乳房及乳頭可以說是看的清清楚楚,下面的裙擺是不規則的真絲碎片,騷婦有一次自己動手把大腿上的裙叉開到了胯部的地方,這裙擺只要走路快點或者有風吹過,裙擺下的T褲及那烏黑的陰毛在那一瞬間就展現在路上了,所以蹦迪的時候她特別喜歡這條裙,因為那裙擺隨著身體的擺動就會自然的分開而時不時的露出她那淫蕩的下體!再往下看,腿上是一雙黑色的蕾絲邊的高筒網眼襪,腳上一雙跟高15厘米的露趾高跟鞋!
這時騷婦把我的手拿過去放在她的乳房上,我摸了一下說道:還沒碰呢,乳頭就已經那麼硬啦!騷婦聽了在那鬼笑!說道:什麼啊!我在二個點點上扣了根皮筋(黑色很短很細的那種)!我有點納悶,因為以前從沒看見她這樣過,也不知道扣在上面有什麼用!當時我就問道:在乳頭上扣根皮筋幹嘛啊?
「哦,因為這件衣服胸部的地方有點緊,二個點點被壓得癟塔塔的而且很難看的,我在上面扣根皮筋,點點不就翹起來了!再說我上次去酒吧有人抱著我跳著跳著,衣服往下滑,乳頭就露出來了,今天我就不怕了,就算滑下來二個點點正好能把衣服掛住!」
我心想:你絕對是個天生的蕩婦啊!
恩,這樣是蠻好看的!虧你想得出來!來,我來看看,下面穿了條什麼內褲啊?我一看,原來騷婦穿了一條明黃色玫瑰圖案型的開襠丁字褲,濃密而不雜亂的陰毛大部分露在了外面,在黃色的襯托下顯得淫蕩無比,二條連接臀部的帶子已經被她卡在陰唇裡了,二片閃著淫水的陰唇就像蝴蝶一樣在花中采著蜜!
你個騷貨,又想去被人家摸啊!騷婦口是心非的答道:哪有啊!我覺得這條T褲配這件衣服比較好看呀!
就這樣我們到了酒吧,找了個靠近舞池(在舞池的旁邊有好多這樣的位置,這個舞池也就高過地面六七十公分)的散���坐了下來,點了一瓶芝華士,玩了一會骰子,就去舞池蹦迪了!
因為是週末酒吧人特別多,我跳了一會就下去了(因為我知道我在旁邊有些人還不太敢來靠近她,這樣就沒意思了!等氣氛熱了,我再上去!)離開的時候摸了一下騷比下面,發覺已經很濕了!
我在下面邊喝酒邊看著她在那邊扭,只見騷婦的半個乳暈已經因為她的跳動而露了出來,那件衣服也真的就掛在二個乳頭上面,!下面那條卡在陰唇裡的T褲隨著騷婦臀部的擺動時而時現的!因為這條T褲是明黃色的,,從兩邊露出的陰毛在舞池燈光的閃爍下顯得分外扎眼,甚至有時候還能看到那二片又長又大的陰唇!我知道當時舞池的周圍已經有好多人在注意她了!
騷婦就像一個脫衣舞孃一樣在上面跳著,時不時的還對著我做著一些很淫蕩的動作!
這時只見有個人慢慢移動到騷婦身後,用二手放在她的胯部在後面用他的雞巴貼著她的屁股跳著,騷婦一見有人來了,屁股開始扭動的更厲害了,也許那人不是故意的,那人的手放在她的胯部正好把那條裙叉拉開了,所以那條淫蕩的T褲就這樣敞在外面(這時下面有個女的好像發現了,悄悄的在和她邊上的朋友說),就這樣過了一會又來了一個人,那人在騷逼的面前跳著,二手先是試探的在她胸部摸著,後發覺沒有反對的意思,那人的雙手就肆無忌憚的在她胸前邊跳邊摸,後來那人越來越大膽,把她的衣服往下拉了一下,騷比的一個乳頭就出來了,我看了一下騷婦好像沒有往上拉的意思,反而更靠近那個人了,那人的手直接就摸著她露出的一個乳頭,另外一個手已經往下摸去,只見騷婦非常興奮把那個人抱著,屁股在很淫蕩的抖動!而後面那個人的手也沒閒著,似乎也放在騷婦的襠部(後來據騷婦自己說,當時那二個���的手指都在她的陰道裡面插弄,但之後,後面那個人就一直在扣她的屁眼)!就這樣騷婦在上面已經輪流的和好多人都玩了三明治遊戲了!之後因為累了就下來休息了!
騷婦邊喝酒邊色迷迷的看著我,我知道她的酒已經喝的差不多了(騷婦酒喝到一定程度,就會慢慢進入忘我的狀態,之後她淫蕩的另一面就會表現的更加淋漓盡致)!
這時她起身走過來對著我又開始扭動起來了(我還是坐著),邊跳邊把我的手指塞進她下面的陰部讓我扣她,我說道:騷貨是不是再上面被人家扣的很爽啊?騷貨很迷離的答了一聲:恩!
這時我也不客氣了,用三根手指在陰道裡快速的抽動,另一隻手則不斷的拉冊著她那二片肥大的長陰唇,搞得騷婦的淫水把我的手掌都弄濕了!後來騷婦說她去上個廁所!
就在她離開去廁所的時候,突然有個男人走過來:「大哥,嫂子很漂亮啊!」
我笑笑沒有回答!
「哥,我們兄弟幾個在那邊的卡座開了好幾瓶洋酒,你和嫂子一起過來玩玩吧!人多氣氛好一點啊!」
我看了看他,隨後就答應了!其實我知道他們的意思,所以很直接的說道:「等一會怎麼玩都可以,但是有一點,不能操她!」
那人猶豫了一會說道:「放心吧,大哥!」就先回去了!
過了一會騷婦回來了,我跟她說那邊卡座裡的幾個人想叫我們一起去喝酒!她點了點頭!隨後我們就到了卡座那邊!
卡座裡一共有8個男的,一看到我們過來,很客氣的招呼我們!在沙發上就坐後大家先在一起玩骰子,邊玩邊有人不斷的在恭維騷婦,說她長的漂亮,身材好,舞也跳得好!騷婦被人說得有點輕飄飄的,又喝了不少酒!
這時我突然突發奇想,說道:「這樣吧,她的酒已經喝的差不多了,不能再讓她喝了,如果她輸了,就懲罰她自己在下面放片水果!」(桌上有好幾盤水果拼盤)
騷婦一聽用手掐了我一下,這時大家一聽都笑著說好,不過最後說好她輸給誰,就要讓那個贏的人來塞!如果騷婦贏了,就要那人在她下面拿塊水果出來吃掉!(從此之後這個騷比竟然對此上了癮,經常會在自己的陰道裡塞一些東西然後就這樣出門了!)
遊戲就這樣開始了,第一回騷比正好輸給我 ,我隨手就在水果盤裡挑了個櫻桃番茄塞了進去,第二回輸了,被人塞了一片哈密瓜,第三回是一片西瓜,,其中有一會騷比連續輸了好幾把,所以陰道裡面塞滿了各種水果(有西瓜、哈密瓜,蘋果,葡萄,火龍果,櫻桃番茄等),最後有人想放一個葡萄都已經放不進去了,這時候騷比竟然自己用手把陰道裡的水果往裡面又塞了一點進去,然後又被人塞了一個葡萄和一片西瓜!不過此後騷婦又贏了幾把,所以陰道裡的水果也少了一些,此時我藉著閃爍的燈光看了一眼騷婦的陰道(這時騷婦已經呈M字坐在沙發上了),只見騷婦的陰戶大開,卡在陰唇裡的線已經被人撥到旁邊,裡面紅色的陰肉摻雜著一些西瓜之類的水果渣,陰道口竟然還在滴水,這時我也不知道是她的淫水還是被人扣弄後擠壓出來的水果汁!
就這樣玩了一會,騷婦說她想去舞池跳舞,當時大家都說就在沙發中央的那個茶几上跳吧!
只見騷婦二個被皮筋扣著的大乳頭和整個乳房都已經完全露在外面,閉著眼睛站在桌上淫蕩的扭著屁股,此時我第一個走上去,從後面把她的裙叉拉開並塞在她腰中的吊襪帶上,這時那條淫蕩的T褲就毫無保留的展現在大家面前了,大家一看都這樣了,也都上來了,有個人站在騷比面前扯著那根卡在陰唇裡的帶子,上上下下的摩擦她的陰蒂,搞得騷比叫聲連連,而上面的乳頭又被2個人含在嘴裡,我則在後面扣弄騷比的屁眼!
過了一會,其中有個人拿了個小瓶喜力啤酒的空瓶站在她面前,把酒瓶的前端插進逼裡來弄她,插了一會只見騷比抱著那人的頭(因為她站在茶几上)瘋狂的用下體去迎合那個酒瓶!當時我一看,也隨手拿了個空酒瓶,往她的屁眼裡塞了進去(騷比的屁眼早就被我開發過了,所以酒瓶前端的尺寸對她的屁眼來說,毫不費勁)!騷比後面那個洞突然也被酒瓶塞入,當時就像瘋了一樣在那邊抽動!
大概就這樣持續了幾分鐘後,我坐在沙發上開始欣賞騷比被人玩弄的樣子!此時騷婦後面的屁眼被另外一人的手指在扣弄著,這時只見有二個人也站到了茶几上,在用力拉扯她的二個乳頭,同時茶几下面的兩側也站著二個人,他們一左一右的在用力拉開揉搓騷比的二片陰唇,而站在騷比前面的那個人則開始扣弄她的陰道,另外二個人的手則在騷婦身上空餘的位置亂摸!
此時的騷婦就這樣被8個人在同時玩弄著,而她好像也很享受這一切!當時看的我簡直是慾火焚身!
最後看看時間差不多了,就帶著迷迷糊糊的騷婦叫了一輛車回去了!回到家後騷婦就像一頭餓狼一樣,和我翻雲覆雨了一番!
第二天因一早因約了客戶,早早的就出去了,中午時分接了個電話:
「兄弟啊,好長時間沒見你了,聽說你出差回來了?」
「哈哈,楊兵啊,我昨天剛回來,怎麼,找我有事啊!」
「下午,陳勇和李建說要打麻將,三缺一,一定要叫你來!晚上兄弟們再幫你接風!」
「好啊,我正好沒事,現在就過來。」
下午就在一場麻將中度過了。。。。。。
麻將過後,楊兵他們在飯店訂了2桌酒席,叫上了一幫商界上的朋友為我接風,飯局中,大家就在吵著說飯後要去夜總會放鬆放鬆!此時坐在我身邊的楊兵側過臉在跟我說話:
「兄弟,等一會叫嫂子一起來吧,有嫂子在才玩的開心啊!另外我跟你說哦,等一會我還幫你約了2位高官,你不是一直想結交他們嗎,今天可是個好機會!不過這2個傢伙可色的很!」
「呵呵,那我打電話給晴子,讓她等一會過來」
「喂,晴子嗎,我在和楊兵他們吃飯,等一會去MJ CLUB,他們一定要叫你過來,對了,今天還有2個重要人物,你等會打扮漂亮點啊,昨天你不是吵著還沒玩夠嘛,今天楊兵他們在,我們好好玩玩!」
「你壞死了,老是叫我陪你那些重要人物,知道啦,我打扮一下等一會就出來!」
(這裡稍微簡單說一下,「楊兵」是我最鐵的一哥們,我和楊兵二人有時候一直和晴子3P,不過晴子還蠻喜歡楊兵的,這小子有點輕微的SM傾向,老是出新花樣來挑弄晴子)
掛完電話,我們一群人就先到了MJ CLUB,這地方我們經常來,所以老闆和我們也很熟,一看到我們過來了,就幫我們騰出了一個大包房!
這是個圓形的包房,頂頭有個小小的舞台,舞台上有著一根鋼管,這包房平時其實就是一個小型的演藝吧,舞台前放著一隻紅色的圓形大沙發,圓形沙發前有著一圈弧形的沙發!這房間平時能容納40個人左右,我們這20幾個人坐在裡面一點也不顯得擁擠!
這時一群人已經在舞台上面蹦開了,楊兵這時正好帶著2位高官走了過來
「兄弟啊,我來幫你介紹一下,這2位就是孫局長和馬副局長」
「啊呀,久仰二位大名,今日真榮幸啊,來,坐坐坐」
當時我們幾個坐在了一起,邊喝酒邊聊了些生意上的事,聊了一會就聽孫局長說到:「我一直聽楊兵說,兄弟有一位長的很漂亮的情人啊,今天怎麼沒看見啊?」
「咳,別聽楊兵瞎說,不過晴子應該一會就到了吧,差不多在路上了!」
半個小時過後,晴子到了,一進門所有男人都露出了本性,眼睛都直勾勾的盯著晴子的身體!
晴子今天穿了一件白色透明雪紡的上衣,胸前那二顆堅挺的大乳頭清晰的頂在衣服上,連乳暈都看的清清楚楚,下身穿了一條同色的雪紡緊身迷你超短裙,裙子的二側是鏤空綁帶式的設計,裙擺則只有剛好能遮住臀部,腿上用吊襪帶吊著一雙歐洲復古沒有彈力的肉色玻璃絲長筒襪(這雙絲襪雖然是肉色,但後跟和腳尖的襪頭都是黑色的,非常性感,看過歐洲老片子的人都應該知道),十個纖長的腳趾塗著紅色的指甲油,在黑色透明絲質的襪頭中顯得非常漂亮,腳上一雙銀色的細帶高跟涼鞋!
在仔細一看,白色的裙中朦朧中透出了一隻紫色蝴蝶的圖案,在蝴蝶圖案下面能隱約看到一團黑色。
這條紫色的蝴蝶內褲是楊兵從日本帶回來給她的,這條內褲的設計非常特別,蝴蝶形狀的布料正好在陰毛上面,而從蝴蝶二個翅膀下面伸出了2條線從陰唇旁邊繞向了臀部,這條內褲穿上後,那二片肥大的陰唇因為繩子的張力會被分的好開,所以那淫蕩的洞穴則一直是張開的!而臀部也因被繩子高高的托起撐開,因此那朵美麗的菊花也是同樣的情況!
這時,楊兵走了上去把晴子帶了過來!
「晴子啊,都等你好長時間了,咦,一段時間沒見到你,又風騷了好多啊!」
「你這個傢伙,老沒正經了,不理你,哼~~~」
「來,晴子我給你介紹一下:「這二位就是孫局長和馬副局長,今天你可要好好陪二位局長喝喝酒啊!」(晴子平時一直幫我接待一些重要的客戶,因為她生性淫蕩,不但能幫我照顧好那些客戶,而且自己在性慾上又能得到很大的滿足,所以晴子從來不推脫)
晴子就在二位局長中間做了下來,陪著他們喝著酒聊著天,而這二個人的眼睛則一直盯著晴子那透明上衣裡那對豐滿的乳房和下身窺探!其實在場每個人的眼睛都在晴子的身上!
突然我聽見陳勇、李建他們一幫人在那邊說:
「晴子的乳頭好漂亮啊,怎麼都翹起來了啊,你們快看晴子的下面,我好像都看到那粉色的洞穴呢,連毛都看的見啊!」
我隨著他們的說話,眼睛也向晴子望去,哇,真的啊!
只見晴子半個屁股坐在沙發上,雙腿故意微微的張開,那條短的不能在短的超短裙因為一坐下,裙擺更往上跑了,可以說晴子現在的陰毛幾乎一半露在外面,那二片在下身抖動的大陰唇也因為坐下的關係被分的更開了,那洞口的肉芽正向外微微的吐露著
晴子就這樣,一邊享受著被眾人的視姦,一邊陪著二位正副局長喝著酒
慢慢的晴子側坐在了孫局的一條腿上,把一隻乳房貼在了他的臉上,而孫局長則在用舌頭隔著衣服舔弄晴子那敏感而勃起的乳頭,另一邊的馬局長則在撫摸著晴子那濕漉漉張開的陰戶,用那粗糙的手指不斷的刺激著她的陰蒂,並時不時的把晴子那二片原本就很長的陰唇拉的更長更開,而晴子則閉著眼睛,嘴裡發出了淫蕩的呻吟聲!
「二位局長,我上台為大家跳個舞吧」
晴子醉熏熏的走向了我和楊兵,並從包裡摸出了2個東西放在了我們二個的手中,我們低頭一看,居然是二個無線遙控器!
「靠,原來晴子放了2個跳蛋在陰道裡啊,楊兵說到」
「晴子現在越來越騷了,我快吃不消他了!還放了二個」
就在我說話的同時,我一抬頭突然看見走向舞台的晴子的後庭中,有一粒紅色的珠子在外面閃著亮光!這時我才明白原來她在陰道裡塞了一顆跳蛋,而後庭中則插入了一串電動按摩珠,這串電動按摩珠一共有12顆如玻璃彈珠大小的珠子,平時晴子最多能塞進8顆,而今天卻塞進了11顆,還有一顆因為塞不進了而露在了外面,一看到此情景,我的雞巴也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
晴子在舞台上,跳著性感的鋼管舞(在這交代一下,晴子曾經學過幾年的舞蹈,所以舞跳的非常好)
這時楊兵打開了晴子陰道中那個跳蛋的開關,就在打開的同時突然看見晴子身體不自然的抖動了一下,然後跳的就更瘋狂了
只見晴子用臀部靠在了柱子上,雙手摸著自己的乳房,然後搖晃著那圓渾的臀部慢慢的蹲下,仔細看還能看見那被跳蛋強烈刺激著的陰道中還流下了一滴一滴的淫水,一會兒晴子又慢慢的站了起來,翹著臀部背對著大家緩慢的拉下了裙子的拉鏈,在裙子落下的一瞬間,首先步入眼簾的則是那被繩子分開的後庭中夾著一顆紅色的珠子!
晴子轉過身用腳尖把那條薄裙踢向了楊兵,然後又慢慢的退下了那件透明的上衣!這時的晴子可以說是四點全露了,現在身上除了那條紫色的蝴蝶開檔內褲,就只剩下一副吊襪帶和一雙長筒絲襪和腳上那性感的高跟鞋了!
晴子不斷前後抖動著雙乳,時不時的用拇指和食指捏著自己那對勃起的乳頭轉動拉扯著,這時我也已經打開了她後庭中的開關,被電動玩具前後刺激著的晴子應該到了最忘我的境界了!
就看見晴子用雙手各扯著一片肥大的長陰唇往二邊分開,然後居然用內褲上的那二根繩子固定住了陰唇,這樣一來被完全分開的陰唇中那粉色的陰戶就這樣展露在所有人的面前了,甚至連那勃起的陰蒂也能清楚地看到,而晴子好像還不過癮,又用二根手指插進那流著淫水的陰戶在裡面扣弄著,突然就見晴子在陰道中拿出了那顆還在抖動的跳蛋放進了口中!
這情形實在是太淫蕩了,我想在場的每個人都恨不得能馬上上去操他,但大家好像都在享受著晴子為我們帶來的這一幕!
晴子在台上又跳了一會,然後走下來,慢慢的邁向了舞台下的那個紅色的大的圓沙發!
在沙發上她脫下了高跟鞋,半躺在沙發上用那被透明黑色襪頭包裹著的腳尖挑弄著孫局長的嘴唇,而孫局似乎很享受似的在吸吮著晴子那纖長的腳趾,這時旁邊的馬副局長第一個忍不住了,上前把頭埋進了晴子的襠部,在那貪婪的用舌頭舔著那淫蕩的陰戶,而雙手則抓住了二個乳頭用力的捏著,似乎要把那二顆乳頭捏扁似的!
噢,馬局長你添得我好舒服啊,乳~~~頭~~~~也~~~~好爽啊,不要停,晴子用手抓著馬局長的頭讓他繼續舔著!
有了孫馬二個人的加入,大家似乎都受不了了,慢慢的把這個圓沙發圍了個水洩不通!陳勇和李健此時正在舔弄著晴子的絲腳,而馬副局長和孫局長正在吸吮晴子的乳頭,剩餘的人則在晴子身上胡亂的摸著!
在我的記憶中,晴子好像還是第一次被那麼多人玩弄著。。。。。。
這時,晴子正跪在沙發上,嘴裡含著孫局長的那條烏黑的大雞吧,而楊兵則在晴子的身後,玩弄著她後庭中的按摩珠,最後連原本露在外面的那顆也被塞進了晴子的後庭!過了一會,楊兵慢慢的脫下了晴子的一隻絲襪,然後只見他拿著絲襪用2只手指把襪口一點一點的往晴子的陰道中塞去,最後整只絲襪幾乎完全沒入了陰道中,只剩下半個腳部形狀的絲襪垂懸在陰道外面,而那些垂懸在外面的肉色絲襪和那只黑色的襪頭在陰道口顯得十分扎眼!見此情形,我似乎也爆發了獸慾,學者楊兵把另外一隻絲襪也慢慢的塞進了晴子的後庭,最後整只絲襪也如陰道口的那只那樣,只剩下那半個腳部形狀的絲襪懸掛在了肛門口!
此時我和楊兵二人,把跪著的晴子拉了起來,讓全身赤裸的她站在沙發上再為大家表演一段��舞!
晴子微瞇著雙眼,又慢慢的扭動起了那淫蕩的臀部,而那2只露在陰戶和後庭外的絲襪也隨著她的扭動在下身飄動!
這時楊兵和我對了一個眼,我們2人不約而同的拉住了飄動在她下身的絲襪,一點一點的拉了出來,也許因為絲襪的塞入把陰戶中的淫水有點吸乾了,所以拉出來的時候晴子皺著眉從喉嚨中發出了一些低吼聲,可我和楊兵並沒有理睬,把拉出來的那2只沾滿了淫水的長筒襪又慢慢的塞進了她有點乾澀的陰戶和後庭中!
就這樣我和楊兵二人反覆玩弄著晴子陰道和後庭中的絲襪,而晴子的陰道也許習慣了異物的塞入,慢慢又變的濕潤了,現在陰道內的那只絲襪完全被淫水濕透了,此時在我們身邊的孫局長盡學著我們把晴子脫在沙發上的那條紫色蝴蝶開檔內褲也塞進了她的陰道內!最後晴子被我們這種變態的行為激發出了最強的性慾!
此刻晴子迫不及待的想要一條雞巴的插入,只見她騎在孫局長的身上,抓住那條烏黑的大雞吧坐了下去!
「噢,孫局長你的大雞吧頂到我花心了,快用力幹我,插爛我,噢,好舒服,嗯~~~噢~~~」
晴子瘋狂的淫叫著,這時馬副局長跑到了她身後,快速的拉出了塞在肛門中的絲襪,把雞巴頂了進去,楊兵則把雞巴塞進了她的口中,而我和陳勇拉出了那充血的乳頭用力拉扯著!
晴子就這樣被我們玩弄著
突然聽到晴子大叫了一聲,斷斷續續的喊著:
「噢,逼逼~~~好~~~舒~~服啊,好~~癢~~啊,再~~用~~點~~~力~~幹我的~~騷~~~屁~~眼~~,噢~~噢~~噢~~~我~~~~要飛~~~~了」
說完這句話,只見還趴在孫局長身上的她,下身噴出了一股淫水,晴子居然潮吹了!
晴子就這樣被在場的20幾個人輪流的操著,有人射在了她的口中,有人射在臉上,頭髮上,屁眼裡,陰道裡,最後渾身都是精液的晴子因為體力不支,而昏睡在了沙發上,而此時晴子的陰道中和屁眼裡不斷的流出精液。。。。。。
寶島台灣美女主播 成人午夜聊天室
www.18chatroom.com
【Android/安卓手機】小姐姐等你來撩哦,歡迎下載𝐀𝐏𝐏體驗!
www.18chatroom.com/APK/?FID=10395
美女高清無碼直播,註冊會員免費看~
www.twuu.cc
✔還想看更多嗎?歡迎下載無碼直播神器𝐀𝐏𝐏
www.twuu.cc/APK/?FID=2187
↓註冊會員即贈送150點免費體驗激情慰慰秀↓
www.twuu.cc/index.phtml?PUT=up_tel&FID=2187
小姐姐的福利 激情裸聊
www.ddimm.com
下載𝐀𝐏𝐏看更多福利↓↓↓
iOS載點 www.ddimm.com/APK/?FID=22605&O=IOS
Android載點 www.ddimm.com/APK/?FID=22605&O=AN
大尺度直播平台app大全,在線提供全網最新大尺度直播平台app免費下載,最新、最全、最火爆,真正能看福利的直播!
嘿嘿,不多說,老司機必備開車直播!www.gxxxnight.com
0 notes
Text
她紅遍全國被葛優苦戀 出國後離婚…
大陸直連看禁聞:https://j.mp/jproxy
wordcount=6326;
近日,蟄伏許久未露面的演員張瑜又在社交網站上有了動態。我們常常感嘆80年代那個時候美女多,不像現在的明星老撞臉,其實人是越長越好看的,只不過我們現在的審美比那時候單一。他們當中有的人,從青澀可人到沉穩大氣,一步步登上女王的寶座,比如劉曉慶、陳冲、鞏俐;也有的人高開低走芳蹤難尋……比如說張瑜。
她是80年代初最紅的女演員。她貢獻了中國銀幕第一吻,引發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波時尚潮流,是第一個在電影里穿露背泳裝,小熱褲的女演員,第一個金雞百花獎雙料影后,享受國人的萬千寵愛,也是80年代出國留學女星當中的一員……
61歲的張瑜迄今也只有過一段婚姻,但因出國深造後夫妻聚少離多,最終兩人心平氣和地辦理了離婚手續,而單身至今的她至今也沒有生子,活得十分洒脫。
張瑜出演的這張《廬山戀》的劇照,在1980年的中國絕對是一個轟動的場景。據說葛優在很早以前就曾將張瑜當做心中的女神,偷偷暗戀了多年。
幹部家庭出身的上海女孩張瑜,從小就倔強大膽,做事出挑。14歲就當一個游泳小將陪毛主席橫渡過長江。16歲加入上影廠,20歲就在《青春》、《啊!搖籃》中演重要角色。
《青春》這部戲裡,集合了上海電影廠當時老中青三代實力派演員:秦怡、朱曼芳、張瑜、陳冲。張瑜當時在戲裡演主角的亞妹(陳冲)的好朋友阿燕。
張瑜是1974年被招進上影演員訓練班的年輕演員,曾經在謝晉執導的《春苗》、《青春》、《啊!搖籃》等影片中扮演過一些小角色,基本上還屬於名不見經傳的小字輩。這樣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姑娘,堂堂一廠之長為什麼對她有印象呢?
那是因為謝晉導演拍《啊!搖籃》的時候,徐桑楚曾經代表廠里到拍攝現場慰問攝製組,剛好看到了張瑜的一場戲。張瑜在影片里扮演過一位身上帶有小資氣息的八路軍文工團員。這個場景中,她有一個上馬動作,但是那匹馬不聽她使喚,把她從馬背上摔了下來。
張瑜在鏡頭前非常投入地做戲,但謝晉就是不滿意,站在一邊哇啦哇啦地大叫。張瑜給嚇的,表演上更加賣力。多年後,張瑜回憶那個場面,還不好意思的說,為了這個動作,屁股都摔青了。當時,徐桑楚就站在一邊看,覺得這個小姑娘身上有一種難得的單純和率真。雖然張瑜的動作很簡單,卻給徐桑楚留下了不錯的印象。
這樣,在確定《廬山戀》女一號的時候,徐桑楚就想到了她。但導演黃祖模心裡有些不舒服,雖然答應了讓張瑜試戲,卻顯得比較勉強。所以23歲時候,她就遇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廬山戀》的女主角“周筠”。
這部戲現在看來很簡單稚嫩,但在當時是相當前衛大膽的。在這之前,我們電影的旋律大多是歌頌革命和勞動,演員們都是工農兵形象。而《廬山戀》說的是一對青年男女的相遇和相愛,不是遊山玩水就是談情說愛,這史無先例的題材讓導演為難,選角更是難上加難。
劇中的女主“周筠”是歸國華僑。但沒人知道歸國華僑是什麼樣的……洋氣又是怎麼樣的。郭凱敏和張瑜並不是導演的第一選擇,當時有兩對備選情侶,一對是郭凱敏和張瑜,一對是楊紹林和宮雪花(對啊,就是36歲去參加亞姐的性感尤物宮雪花)。
而且宮雪花這一對明顯是導演更心水的,覺得宮雪花(下圖右)長相更洋氣,張瑜之前演的都是工農兵角色,相對土氣了點。但據說後來宮雪花為了讓自己更漂亮就去做了微調,就這樣被刷下來了。張瑜和郭凱敏才被定下來。而張瑜在拍的過程中也是忐忑著的,導演隨時會把她換下來。
《廬山戀》不僅對張瑜本人意義重大,對整個80年代,乃至整個中國影壇而言,都是極其重要的一筆。戲裡張瑜輕輕的一個蝴蝶吻,融化了國人心中某種道德禁忌,愛原來可以大大方方坦坦蕩蕩表現的。
現在看來稀鬆平常的一個吻,張瑜措不及防就吻了上去。所以我們看到郭凱敏的表情,是真實的流露,就是影片都褪了色,都還能看到他臉都紅到脖子了。這場吻戲當時把整個劇組都搞得戰戰兢兢。又是做演員思想工作,又是清場的。張瑜更加是緊張到找不到嘴在哪裡。
張瑜在戲裡色彩斑斕、款式多多的時裝,也成了80年代女孩們的穿衣聖經。披肩小捲髮、畫家帽、窄絲巾、超大眼鏡、A字裙、皮衣、風衣、開衫、白襯衫、花襯衫、熱褲、露背泳裝、百褶裙……應該說中國第一個帶貨女王是張瑜。
關於張瑜戲裡的服裝,還是有一段故事的。當時整個劇組都沒見過華僑是怎麼穿的。所有服裝都是劇組到香港去買的。
這部全民熱捧的《廬山戀》也把廬山變成了國人熱愛的旅遊聖地,愛情聖地。廬山上現在還有一個“廬山戀”電影院,每天只循環播放《廬山戀》。《廬山戀》也把張瑜送到了一個無法跨越的巔峰,給了她在當時至高無上的榮譽,讓她成為時代的寵兒。當時的好劇本,好角色都送到她面前。
《小街》是郭凱敏和張瑜合作的第二部電影。這部電影雖然沒有《廬山戀》影響深遠,但它的電影敘述方式,開放式的結局在電影史上是很重要的轉折點。張瑜和郭凱敏的表演也更加成熟,兩人的合作更有默契了。
這首主題曲也是當年街頭巷尾的街歌,或許你的爸爸媽媽還能哼上一兩句呢。張瑜在戲裡穿的高領衫,剪的短髮也風靡起來。翻翻你媽媽,姑姑,表姐的相冊,或許能找到一張“張瑜頭”。
《知音》里,她是有情有義的名妓小鳳仙。電影版的《雷雨》,她又變成了身世可憐的四鳳。張瑜和劉曉慶、潘虹、斯琴高娃、陳冲成為了80年代初,全民公認的“五朵金花”。這就相當於世改革開放後,人們心目中第一批玉女掌門人吧。
時隔三十年後,崔永元看見小時候的偶像,還是激動不已,張瑜姐姐這身材也真是沒誰了,保持得真好啊……
1985年,張瑜作為大陸演員的代表,和馬季、姜昆還有港台的明星代表一起主持春晚。但成名也給張瑜帶來了不少困擾。上街被認出來直接造成了人群圍觀,後來乾脆交通擁堵這都不算什麼,最著名的一樁公案是有粉絲借張瑜的名字去談戀愛。
那時候最能吸引全民關注的人有兩種:演員和運動員,當時演員最火的是張瑜,運動員最帥的莫過於國家排球隊的汪嘉偉,雜誌上常見的面孔就有他倆。兩個無聊的女生打賭,要讓當時最火的演員張瑜和最紅的運動員汪嘉偉談戀愛起來,於是借張瑜的名義給汪嘉偉寫表白信。
在沒有手機,沒有網路的年代,人們交流靠書信,汪嘉偉馬上就信以為真了,並迅速墮入愛河,把正牌女友張潔雲,當時女排種子選手給甩了,還把自家的祖傳家寶給女騙子寄了過去。要不是後來報紙說張瑜去了澳洲拍戲,汪嘉偉還蒙在鼓裡。
更冤枉的是張瑜,平白無故被郎平這些女排的人痛恨了很久……世事難料以及最有趣的是,三十年之後現在的她和郎平居然成了好朋友……只能說,張瑜註定和排球有緣。
張瑜不止一次在訪談里說,感覺自己就像金魚缸里的魚,完全暴露在全國人民的眼皮子底下。更重要的是,不斷重複的劇本相似的角色,讓她覺得沒勁。
作為一個讀完中學就出來演戲的演員,張瑜是有幾分內怯的。當年的演員也比較老實、好學,都想回學校再學點東西,於是郭凱敏進了北影進修班,張瑜眼界更高了些,去了美國讀電影製作。
在美國的5年,可以說是張瑜最矛盾的5年。沒有了觀眾的關注,一下子變成普通人的她時常感覺到孤單,甚至開始懷疑出國的意義。想進好萊塢,但又因為角色不好,自尊心不允許。
想回家,但顏面更受不了。抱著一種複雜的心態學習,徒添壓力。和她前後腳出國的女演員,有陳冲、鄔君梅、龔雪、白靈……龔雪到了美國後嫁人息影了,陳冲、鄔君梅和白靈在張瑜所不屑的好萊塢演著小角色艱難度日。她們的選擇不同,但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選擇咬牙堅持著。
1990年,好不容易熬到快畢業,台灣的電視台找到張瑜,邀請她到台灣發展。台灣當時的影視環境還蠻寬鬆,對大陸明星接受度也很高。這對當時的張瑜來說,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台灣方面也很重視張瑜,給到的劇本和資源都不錯,《李師師》和《黃土地外的天空》里都是女一號。收視率都不錯,走在街上大家都喊她“李師師”。張瑜也成了台灣三家電視台爭搶的香餑餑。
張瑜在《包青天》中扮演的柔弱美貌的如夢,和戲裡顏值杠把子展護衛有一段情。
當時的香港演員、大陸演員在90年代初的台灣都很吃香。和大美人趙雅芝站在一起,張瑜也沒輸。她還以頒獎嘉賓的身份出席亞太影展的頒獎晚會,這在台灣影壇上,也屬第一回。
張瑜1990年剛到台灣的時候,參加過的台灣的綜藝《連環炮》。看得出台灣人對這個大陸來的“雙料影后”的疼惜,但也隱隱地說出了張瑜日後離開台灣影壇的最重要的原因:受不了他們高強度的工作壓力,還有邊寫邊拍的節奏。
張瑜是一個特別固執的人,很難適應外界的變化,個性也極為拘謹,需要額外細心的呵護,身段絕不柔軟,這和娛樂圈的瞬息萬變極為不合,張瑜對台灣高強度快節奏的影視製作環境感到不適。1993年,在台灣拍了三年電視劇的張瑜,放棄在台灣苦心經營的名氣和影響,回到大陸。
但回來時候,她面對來更大的落寞。大陸影壇出現了巨大的變化,新人如雨後春筍,當年和自己平分秋色的劉曉慶,早已成了圈裡的一姐。和自己一起出國留學的女明星,陳冲和鄔君梅都等到了機會,在香港或者好萊塢站穩了腳。
“五朵金花”的紛紛離巢,讓一直堅持留在國內發展的劉曉慶開啟了霸屏模式,全面開掛。百花獎蟬聯三年。1995年更是憑著《武則天》從15歲演到82歲,角色入心入肺,也讓她成為最經典的武則天。據黃小姐說,前段時間香港書展上,不少七十歲的老爺爺,把劉曉慶的書一買就是四本,場面相當熱鬧啊。如果能坦然接受這份落寞,以張瑜的實力,可能是另外一番光景,不過自尊心極高,又特別有自信的張瑜,選了另一條路——製片人和導演。
從2008年起,張瑜開始轉向幕後,當導演、製作人、出品人一肩挑。導演了包括《八十一格》、《廬山戀2010》《雲之錦》在內的三部作品,但藝術成就和觀眾反饋都很一般。
《廬山戀2010》這部跟《廬山戀》基本上風馬牛不相及的電影,出動了方中信、秦嵐和冰冰家的大黑牛,但一樣挽救不了口碑。再說了,張瑜作為其中的一個配角,居然佔據了海報里最大的一塊,這存在感也是蠻強的。
她曾經找過郭凱敏來拍《廬山戀2010》,郭凱敏毫不猶豫拒絕了。對方還上節目,一針見血點出了張瑜的問題,稱張瑜去重拍經典,是吃力反而兩頭不討好,
不僅是導演,張瑜的統籌全局的能力,也不見得出彩。娃娃臉的林志穎曾經低調地拍過一部電視劇《陸小鳳》,這部戲實際上張瑜也是有份參與製片。但拍到一半,張瑜和合作的新加坡電視機構因為賬目問題,一直僵持不下。本來40集的電視劇拍了20集草草了事。從2000年一直到2015年,林志穎都生二胎了,還沒解決呢。
拍完《雲之錦》後,張瑜到現在再也沒有一部作品出現。影迷們也只能在微博上看到她四處雲遊,做瑜伽的照片,或者在貼吧時不時說一句:好久沒有張瑜的消息了。
作為中國銀幕的第一對CP,多少人熱切盼望著郭凱敏和張瑜在現實中能成為真實的一對啊,多希望他們是中國版的“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但他們就是沒能在一起。直到三十年後,歲過半百看盡千帆後,兩人才鬆口說:當年是有過想法的,但不敢往更長遠的方面去想。
郭凱敏做過的最大膽的事情也就是幫忙打個飯打個水,就是不敢開口說。但張瑜對郭凱敏的信號反應遲鈍,當時不知道這就是“喜歡你”。最重要的是,郭凱敏攻守意識都不強,把張瑜介紹給了張建亞,然後就沒他什麼事兒了。
張建亞是張瑜唯一的一段婚姻,也是張瑜唯一承認愛過的人。她和張建亞之所以能認識,還是郭凱敏介紹的。最後知道真相的郭凱敏不知道眼淚有沒有留下來。張瑜欣賞張建亞的才華,張建亞表達愛意的方式也比郭凱敏要明朗大方得多,打什麼飯呀,寒風中苦等兩個小時送張瑜回家,送玫瑰示愛,寫情信啊。
1981年,紅遍中國的張瑜和當時還在北影上學的張建亞低調地戀愛。一年後,張建亞調入張瑜所在的上影廠。1984年,他倆就結婚了。但是,婚後卻是各有各忙。1985年,張瑜就去了美國留學。兩人感情維繫只靠書信,連越洋電話都打不起。
張瑜不願意中斷學業回去,張建亞不願意到美國發展。兩人的生活環境、見識偏差越來越大。到最後張瑜連張建亞的樣子都模煳了。在去台灣發展之前,張瑜提出跟張建亞離婚。
但張建亞心裡還是對張瑜有感情,張瑜從台灣回到大陸,張建亞親自到機場拿著玫瑰等候,又請張瑜當了自己電影的女主角,給張瑜回歸後的一個漂亮的起點。張瑜卻很清楚自己不愛張建亞,把界限劃得很清楚,只能當朋友了。
張瑜還與台灣小生張佩華有過一段情。這段極其低調的感情,我們是從男主角的口中得知的。1997年,張瑜擔任製片人和主演的《煙雨紅塵》,請了台灣男演員張佩華當男主角。兩人惺惺相惜,互相欣賞。張佩華是80年代台灣當紅的瓊瑤小生,在瓊瑤的戲裡扮演了情深意切的翩翩公子。《雪珂》、《昨夜星辰》、《青青河邊草》……有印象了吧。他還跟瓊瑤女郎劉雪華有過一段感情。
張佩華為何與張瑜有緣無分,史料不詳。但後來張佩華舍張瑜後迅速奉子成婚,和一個空姐結婚又離婚,然後又迅速和另一個空姐在一起。而張瑜,對這段不了了之的感情從不談及,從台灣回來,怕也已與此情傷有關。
三十多年前,張瑜能風頭一時無兩,除了本人的天資,更重要的timing,彼時國門初開,人人都渴望自由和新鮮,《廬山戀》應運而生切中人們心中的痛點和癢點,加之當年人們對女明星對審美才從“銀盤大臉”中切換,秀美的張瑜自然成為了毋庸置疑的女神,聚焦了全國人民的目光。
二十齣頭就獲得了巨大成功,張瑜的心氣極高,不相信自己handle不了場面,不管是當年遠走美國還是後來選擇去台灣,還是自己當製片人,她都牢牢把選擇權握在自己的手上。
年輕時太過順遂的人生是能給人自信的,但這自信背後,需要更多運氣之外的支撐才能hold住場面,要再演戲需要調整心態,要做導演製片,需要才華和能量,而不管要做成什麼事,無一例外需要吃苦。
而年少成名只感受到人間善意的美女張瑜顯然對吃苦並不感興趣,做不了什麼事就不做吧,不能處理的問題就把它擱著,時間總是能解決。我自保持身材環遊世界享受生活,這樣也是一種活法(電視劇),讓那些想要嗟嘆她落魄人的都看著呵呵一笑。
算了,不紅就不紅,沒有什麼大了。之前說過,紅,是被時代選中,這是極之幸運的事,不紅,則是被時代拉下,這也是意料中事,有誰能永遠立在潮頭呢?
作為人,一個普通而正常的人,最強大的內心無非也就是接受,接受命運的起伏,接受自己可以很紅,也接受自己很不紅,誰讓你只是一個人呢?紅不是註定的,但有一天不紅了是註定了的事。
既然是註定的事,又有什麼好為它不自由?我想張瑜是自由的吧,你看她練著瑜伽,跟女性朋友去旅遊,生活絕不寂寞,時時有人陪伴,寄情山水,其樂融融,未嘗不是美人最好的選擇……
歷盡起伏的張瑜在佛學裡找到了平衡:“學會用超然和從容的心態包容自己所遇到的一切,才是最佳的人生態度。我們無法左右命運,但可以選擇怎樣面對現實。”
也因此,她成了一個遠比過去寬闊的女人,過去她只愛白雪,現在她學會愛白雪後的泥濘,“原本就沒有黑白,都是我們的界定而已,不是嗎?
只有深深領悟過生活的人才知道世界並非除黑即白,接受這個世界的黑與白,還有各種深深淺淺的灰色,穿梭自如,才能得到真正的寧靜和自由……
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美人依然是美人,只是己悄然沉潛生活的深海,頗有點“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的味道,是為《惘然記》。
如今的張瑜僅在網上分享自己周遊各國的旅行照。
來源:鳳凰網
王岐山重返政壇 美官員:王厲害 能幫中共對付美國
觸目驚心 美國「殭屍粉製造工廠」曝光
美國公布俄羅斯政界商界人士名單但不制裁
一紙定乾坤 — 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四)
在美國退休安度晚年 存夠多少錢才行
美國華裔夫婦從中國走私假鞋被判刑 出獄後遣返
陳破空:華為行竊美國,失手!川普版5G網路,防共防盜,暗助中國民主化
美國稱俄軍機從美國飛機前方1.5米處掠過
測試愛滋病毒不用抽血了!美國有新方法
原文鏈接:她紅遍全國被葛優苦戀 出國後離婚… - 娛樂新聞
本文標籤:世界, 中國, 主角, 代表, 全國, 全民, 出國, 劉曉, 劉曉慶, 製片人, 動作, 動員, 十年, 華僑, 印象, 發展, 台灣, 合作, 在台, 大陸, 女演員, 好萊塢, 導演, 年代, 廬山, 開放, 影片, 心中, 心態, 戀愛, 感情, 扮演, 找到, 時代, 時間, 明星, 曾經, 朋友, 演員, 環境, 瓊瑤, 生活, 電影, 電視, 電視劇, 留學, 離婚, 美國, 自信, 自己, 自由, 葛優, 角色, 謝晉, 運動, 運動員, 選擇, 問題, 陳冲, 雪花, 青春, 香港
from 中國禁聞網 » 娛樂新聞 http://ift.tt/2Ep33vt
via
via Blogger http://ift.tt/2FvCWlJ
0 notes
Text
各地句会報
花鳥誌 令和2年11月号

坊城俊樹選
栗林圭魚選 岡田順子選
………………………………………………………………
令和2年8月1日
零の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青山へ八月の雲のし上がる 和子
魂も今蝶と化すてふ墓所の百合 眞理子
雲の峰青山墓地に崩れけり 梓渕
薄闇にラジオときには蚊遣香 順子
蚊取線香みだらに燃えてゐたりけり 公世
からつぽの鳥籠吊つて婆の朱夏 光子
空蟬の破られし背に光満つ 小鳥
白き糸濡れてをりけり空蟬に 和子
岡田順子選 特選句
黒揚羽ぬかづく人へ入れ替はる 要
槙剪つて明るき墓所や雲の峰 梓渕
揚羽来る墓に朽ちたる名刺受 俊樹
草いきれよりマリア仏の上半身 光子
かき氷ひとつに父と娘かな 同
からつぽの鳥籠吊つて婆の朱夏 同
神愛し薔薇を愛せし寝墓とも 俊樹
蟬時雨彼を一瞬隠しをり 久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2年8月6日
うづら三日の月(八月六日)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秋の夜の澄みし青空何処までも 柏葉
土用干し守る着物に仕付け糸 さとみ
墓参り避けたつもりも鉢合せ 同
天筆に願ひを込めて星祭 都
留守居して語る人なき盆の月 同
七夕や一つを願ひ糸結ぶ 同
客帰り独り帯解く夜半の秋 同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2年8月7日
鳥取花鳥会(八月七日)
岡田順子選 特選句
友の墓訪ふも吾のみ原爆忌 益恵
蟬の穴被爆の眼窩に似て静か 都
八月や浜辺に白き船並び すみ子
抽出しにしまふ西日や能事足る 悦子
蜩の破調に夜明け整へり 宇太郎
油照お濠の亀は泥を負ひ 都
雲の峰サーファー起てば動き出す 益恵
帰り行く友や日傘をまはしつつ 幸子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2年8月7日
さゞざれ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昨夜の色閉ざしてをりし月見草 かづを
蟬しぐれ故山に溢れをりにけり 同
故山より風渡りくる施餓鬼寺 同
月見草夢に終りしことばかり 雪
炎天下大きくきしみバス停まる 和子
法堂に集ふ百僧蟬しぐれ 笑
暮六つや七堂伽藍の蟬しぐれ 希
母の背に負はれて逃げし終戦日 千代子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2年8月8日
札幌花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病院の小児病棟星祭 清
ぐづる子を放り入れたる踊の輪 晶子
銀河から金平糖のお裾分け のりこ
魔法めく夜店にかざしみる指輪 岬月
老僧の盆経朗朗たる気迫 同
とび出しもはみ出しもゐる砂日傘 同
搗ち割の角なめ���かや蕎麦焼酎 慧子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2年8月8日
枡形句会
栗林圭魚選 特選句
やはらかな色に隠元大揃へ 秋尚
ひと頻り法師蟬鳴き風起る 同
空蟬の登る姿勢を崩さずに 同
音の無き蒼茫怖し星月夜 ゆう子
新盆の信女の墓碑の径細し 三無
星月夜野辺山走る小海線 幸風
蜩や夕餉のお菜鉢ふたつ ゆう子
鬼灯の色乾きたる寺の畑 秋尚
隠元の色鮮やかにバターソティー 瑞枝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2年8月10日
武生花鳥俳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墓洗ふ母の育てし供華を持ち 信子
サングラス粋なる人と恐き人 みす枝
裸電球に照らされてゐる地蔵盆 上嶋昭子
日もすがら響動もす鐘や盂蘭盆会 時 江
丸き笊丸く並べて梅を干す 信 子
蟬時雨つり橋の子の声消され 中山昭子
神々の光さづかる大御祓 ただし
星祭壺にさしたる笹の竹 錦子
野も山も深く沈みて星月夜 みす枝
蟻の列ラベルのボレロまだつづく 上嶋昭子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2年8月11日
萩花鳥句会
秋風や万里の長城行きし旅 祐子
少し愚痴呟きながら墓洗ふ 美恵子
新盆に帰る家なき仏たち 健雄
弟と母住む故郷鰯雲 ゆかり
庭仕事合間に西瓜ご馳走に 克弘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2年8月14日
さくら花鳥句会
岡田順子選 特選句
田舎道兜虫売る小屋に遇ふ みえこ
迫真の演技の子役夏芝居 登美子
幼な子も数珠握りたり墓参 実加
イヤホンを片耳づつに星月夜 登美子
晴天にシーツ洗ふや原爆忌 実加
永遠に在り続くかに花氷 紀子
蜩を聞きつつ帰り仕度の子 裕子
野の花を供へて母の展墓かな 登美子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2年8月17日
伊藤柏翠俳句記念館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サングラスかけて犬にも恐がられ 英美子
酒呑まぬ父はお洒落でパナマ帽 千代子
終ならん声を聞き入る秋の蟬 かづを
秋の雲落暉に燃えて消えにけり 同
ギヤマンに盛られ清しき夏料理 みす枝
口紅の朱の沁み出る極暑かな 同
遺骨待つただそれだけの盂蘭盆会 同
無人駅帰省子ホームまで送る 世詩明
羅の女の視野に万華鏡 同
帰省子の戻る車窓に掌を重ね 同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2年8月19日
福井花鳥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黒髪で顔を隠され西瓜食ぶ 世詩明
口紅が熟れた西瓜を齧りつく 同
九頭竜の流れおだやか終戦日 千代子
海凪いで沖行く船に盆の月 同
流行りもの一つ身につけ生御魂 同
終戦日一男優の死すと云ふ 同
炎天や路面電車の軋み来る 美代
これ以上青くなれざる青蛙 雪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2年8月21日
鯖江花鳥俳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手枕で昼寝をしたる沈金師 世詩明
虫干や母の袂に恋の文 みす枝
小恙を顔に出さじと踊りの輪 一涓
肉魚を下げて八月大名来 同
虫の世に火取虫とし果つ定め 雪
白と云ふ哀しき色の盆灯篭 同
赤と云ふ色は淋しや盆灯篭 同
煎餅屋ののれんの奥の扇風機 上嶋昭子
捩花のねぢれる時に媚少し 同
美しきことに飽きられ水中花 同
物干の続く町並夜は秋 同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2年8月10日
なかみち句会(八月十日)
栗林圭魚選 特選句
芭蕉葉に道草を食ふ風ありて 三無
恒例の枝豆届き安堵かな エイ子
海沿ひの蕎麦屋の遠く秋暑し 貴薫
裏庭に風探しけり夕残暑 和 魚
枝豆や父の遺影と酌む忌日 三無
ゆらゆらと芭蕉広葉の青き翳 同
家事とても遣る気奪はれ残暑かな せつこ
公園の要一本大芭蕉 怜
影広げ海辺の宿の芭蕉かな せつこ
枝豆の彩りとなり皿の上 ます江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2年8月
九州花鳥会(投句のみ)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双手上げ銀漢しづく待ちにけり さえこ
天の川渡る媚薬を飲んでより 伸子
黒日傘ひらりと海へ消えにけり 朝子
ゆくりなく女と生まれ天の川 美穂
盆の月透き通るまで踊りけり 愛
その先は有耶無耶なりし道をしへ 伸子
天の川の端より天の川仰ぐ ひとみ
星よりも暗き島の灯月見草 豊子
走馬灯曼陀羅の闇廻しけり 喜和
蟬の殻蹴りし少年黙り込む かおり
天の川尾は聖堂の十字(クルス)まで 志津子
病窓よりビアガーデンの見えるらし 順子
水をくれムンクの叫び原爆忌 喜和
色鳥来ルドビコ踏みし甃 寿美香
難しく考へる鶏頭の襞 伸子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0 notes
Text
大哥 by priest (part.2)
|卷一|卷二|卷三 |
【卷二•獅子】
第三十章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郭沫若。
那兩年的生活幾乎是平靜無波的。
魏謙以全班第一的成績升入了高中的最後一年,每天看見鏡子裡穿著校服的自己,他心裡都會不由自主地浮現「人模狗樣」四個字。
繁重的學業壓縮了他的課餘時間,卻沒能壓縮他那顆恆星般熊熊燃燒的財迷之心,他的寒暑假和全部的週末,都獻給了偉大的打工事業——其中待遇最優厚的,要數在老熊的藥鋪裡打短工的經歷。
老熊的大名起得非常之厚顏無恥,叫做「熊英俊」,眾人每每呼喚其名,都忍不住想在後面加個「呸」,於是久而久之也就沒人叫了。
年輕的時候,別人叫他小熊,可惜他沒能「小熊」幾年,實際年齡才不過三十啷噹歲的大好青年,長相卻已經超前到了十年後,自然而然地成為了「老熊」。
老熊是個非常不著調的富二代,狗攬八泡屎,哪都有他,什麼事都想攙和一腳。只可惜分身乏術,於是整天神龍見首不見尾,藥店經常處於沒人經營的狀態,經常要找人幫他打理。暑假期間,老熊機緣巧合地雇到了魏謙這個短工,就甩手把藥鋪丟給了他,自己不知道死哪去了,魏謙又是店長,又是服務員,又是會計,又是保潔員,就這麼幹了倆月,老熊才回來。
見面就給魏謙結了五千塊的工資。
先前講好的一個月一千塊,被老熊這個二百五自己給忘了!
魏謙開始嚇了一跳,差點沒好意思接——這個時刻準備著要倒閉的破藥店,倆月的利潤究竟有沒有四千塊都還不好說——不過後來還是接了,魏謙想通了,冤大頭這種生物活在世界上,可不就是上趕著送給人坑的麼?
壓根不用浪費一點愧疚的感情在這種該被燒死的有錢人身上。
而魏之遠在老老實實地念了一年書以後,直接跳級進了畢業班,他似乎是為了兌現異鄉的深夜裡,強忍著眼淚對大哥說出的那些承諾,從南方回來之後,就一直處心積慮著準備這件事。
魏之遠的心和身都成長得迫不及待。
跳級的事,是小崽子自己跑到老師面前申請的,招呼都沒和家裡打,先斬後奏,不過魏謙知道了也沒說什麼,雖然口頭不提,但是魏謙心裡有數,以魏之遠的智商,和小寶念一樣的書,想起來也確實挺委屈人家孩子的。
就在小寶吭哧吭哧地上五年級的時候,魏之遠已經進了畢業班。
常理來說,女孩會比男孩先長個子,他們家徹底反過來。
在小寶還是個小丫頭模樣的時候,魏之遠只用了大半年,就從剛過魏謙胸口的高度,躥到了堪堪碰著了他大哥的鼻子。
與他非人類的生長速度相匹配的,是他那日漸瘮人的飯量,全家人都用正常的飯碗,只給魏之遠換了大碗公。
大大碗公比臉還大,三胖有一次來他家吃飯的時候,著實長了一番見識——他親眼目睹了魏之遠用那臉大的碗吃了滿滿冒尖的兩大碗飯,末了沒菜了,魏之遠就用熱水沏了一碗菜湯,兩口喝下去,算是給胃裡灌了縫。
三胖戰戰兢兢地問:「弟弟,飽了嗎?」
魏之遠喝完菜湯一抹嘴,矜持地回答:「差不多,七八成,晚上我要出去跑步,今天就先吃到這吧。」
三胖一把辛酸淚地向魏謙控訴:「為什麼這小子一頓飯頂我兩頓吃,竟然還沒我一半胖!」
魏謙頭也不抬地說:「因為你老了,代謝慢了,三大爺。」
「又老又胖」的三大爺聽了這樣赤裸裸的真相,不禁感到萬念俱灰,默默地走了。
魏謙對飯桶魏之遠早已經見怪不怪,他知道,等魏之遠跑完步回來,還能再就著白開水啃一個幹饅頭。
這小子的戰鬥力秒殺全人類,能將一切的剩飯剩菜碾成渣渣。
相比起來,小寶簡直讓人著急,她上學本來就晚,結果和同班的小女孩站在一起,反而像是比人家還小一兩歲的。
宋小寶同學的生長髮育過程極其奇葩,從青春期直到二十多歲,她都始終保持了每年兩公分的勻速生長,不慌不忙、不緊不慢。
十二三歲的宋小寶就像一棵營養不良的小白菜,魏謙曾經一度懷疑她這輩子就這樣了,成人了也是個女「根號二」,誰知等到十五六歲,大多數女孩子開始停止長高的時候,她又蝸牛一樣一點一點地追了上來,等長大了一看,竟然也不比誰矮。
魏謙即將高考的這一年,宋老太簡直把他當成了萬歲爺伺候,一天到晚只要逮著機會,必須噓寒問暖一番,以喋喋不休的獨特方式給萬歲爺請安。
可把魏皇上煩死了,恨不得一個竹板子扔她個斬立決。
可是每週末一燉雞湯端上桌,看著老太太跟伺候月子似的慇勤地敦促他多吃兩口,魏謙又對她沒了脾氣。
有一段時間,宋老太也不知道受了誰的矇蔽,跟流竄到本地的一個傳銷小團體搭上了關係,每天四處去聽人家保健品的品種和價錢。
她好像計劃著一咬牙一跺腳,把魏謙那一顆腦子補成兩顆大。
……幸好要交錢的時候,被三胖他媽看見了,三胖及時跑來通風報信,讓魏謙趕到了保健品宣講會現場,把宋老太給領回來了。
出來的時候,傳銷小團體流氓本質盡顯,見他們沒買東西,一個小眼鏡跳出來攔著不讓走,宋老太這個腦積水還屁顛屁顛地給人介紹:「這就是我大孫子,快要高考了,成績可好了,我就想買點那個什麼『腦力強』給他吃……」
魏謙:「閉嘴,吃你媽。」
推銷的小眼鏡作風流氓,可人大概有點不機靈,還沒看明白怎麼回事,就急急忙忙地拉著魏謙要給他洗腦,兩片嘴唇上下翻飛地說:「同學,我們這個產品是經過美國有關部門批准專利的,服用一療程,記憶力能提高百分之八十……」
魏謙冷冷地看著他:「我不用一療程,一板磚就能讓你永遠活在人民群眾的記憶裡。」
他一身匪氣畢露,小眼鏡一路隻顧著坑蒙拐騙,還沒有丟付過這路貨色,當下忍不住嚥了口唾沫,往後退了半步,可魏謙仍然嫌他擋道,一抬手把他推了個屁股蹲,拎著那越發神經的小老太婆打道回府。
宋老太攪合得全家雞飛狗跳、人心惶惶。魏謙覺得要不是自己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少年經歷坎坷、心志堅定,非讓她活生生地給折磨成神經病不可。
這一年四月初,魏謙正在教室裡上自習,李老師推門進來,把他叫了出去。
魏謙每天睡不滿四五個小時,來來回回吃東西也匆忙得很,有時甚至邊走邊吃,在路上解決,著實瘦了不少,人高馬大地往老師面前一站,校服看起來空蕩蕩的。
從高二下半學期開始,李老師讓他當了班長,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和他在社會上的經歷有關,他顯得穩重的同時,特別會拿捏那群調皮搗蛋的小男孩,那幫小子一個個都挺聽他的話。
李老師自己的小孩和魏謙差不多大,兩廂一對比,總是看著心疼。
李老師把他叫到樓道裡,對他說:「我們是重點班——你知道的吧,咱們學校每年重點班都有一個優秀學生幹部的保送名額,今年給的名額是A大的,A大當然是好學校,而且就是本地的大學,我想著你家裡情況特殊,留在本地上學,方便顧家,你考慮考慮,想去嗎?」
魏謙足足愣了半分鐘,才有點不確定地問:「不、不是,老師……你的意思難道是,要保送我去嗎?」
李老師被他逗樂了,好脾氣地反問:「不然我問你幹什麼呢?」
魏謙被這個消息砸傻了,他從沒想過這種事會落在他身上。
他過早接觸的三教九流的社會,培養了他陰鬱而憤世嫉俗的精神世界,雖然隨著年齡和見識的增長,那種少年時代的偏激已經變得不再那麼尖銳,但魏謙從內心深處依然認同著這樣一個道理——像他這種出身的人,想要出人頭地,必須比別人都兇狠,也必須比別人都拚命,除了自己,誰也指望不上。
而保送上大學這種充滿「貓膩」的事,難道不是當官人家、有錢人家、有關係的人家的孩子的特權嗎?
他從未想過一個保送名額會落到他身上。
「我……」魏謙難得一見地詞窮了,他腦子裡一坨漿糊,只好強作鎮定地問李老師,「那、那就給我行嗎?別人沒意見嗎?別的同學,或者別的班的……」
李老師說:「有什麼不行?保送決定也不是我說了算的,是要年級組統一討論定下來,經過教導主任審核,最後由校長簽字拍板的,校長簽字剛送到我辦公室,你想看看嗎?」
魏謙沉默良久,他胸中千言萬語,全都一窩蜂地堵在了嗓子裡,他在比他矮了整整一頭的班主任面前低下了頭,雙手捏緊了,好半晌,才咬了咬牙,壓抑地啞聲說:「謝謝老師。」
李老師看著他,嘆了口氣,她知道自己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學校,經歷過的風雨起落反而不如這個孩子,所以她拿不準自己該對他說點什麼,能對他說點什麼。
好一會,李老師才斟酌著,輕聲細語地說:「你天資不錯,更難能可貴的是比別人肯努力,我對你期望很高,所以希望你能成為一個好人,明白我的意思嗎?」
魏謙點點頭,低聲說:「明白,您是說走正路比走邪路難。」
因為走正路比走邪路難,所以走正路的人比走邪路的人強。
這是每一個在兩條路的夾縫裡求生過的人都有的切身體會。
而人不就是要一直追求一個更強大的自我嗎?
李老師推了推眼鏡:「你心裡明白,我就不多說了,回去吧,晚自習到我辦公室來,填幾張表,填完就可以回去和家裡人商量商量,看選個什麼專業。」
魏謙就這樣爛尾般地結束了他才一年半多的高中生涯,爛尾得既莫名其妙,又讓人欣喜若狂。
他很快提交了表格,徵詢了一下李老師的意見,選了當時熱門的生命科學專業——其實當時最熱門的是計算機,可惜計算機的學費比其他專業高,又需要自備電腦,魏謙多少有點捨不得成本。
他於是正式成了一個准大學生,魏謙離開學校的時候,教學樓門口的大櫻花樹花期正盛,他站了一會,真的被落下來的花瓣埋了腳。
魏謙在家無所事事地晃蕩了兩天,應付完險些激動出心梗的宋老太,終於想起來關心一下放養的兩個小崽子。
他無意中發現自己的小妹妹在寫作業的時候做的小動作變了,她以前做不出題目的時候,喜歡摳手指,現在卻變成了用筆桿子繞自己的頭髮,繞完以後還用手捏一下固定,眼前一縷頭髮就會短暫性地形成一個波浪形狀的小髮捲,她會獨自臭美一會,然後再繼續寫作業。
魏謙留了心,發現這丫頭知道臭美了。
小寶小時候愛睡懶覺不愛早起,都是他給拎起來強行按在水池裡,才貓似的拿涼水在臉上劃拉兩把,現在她洗臉完全不用大哥提醒,週末在家,她一天洗了好幾次,每次都在廁所的鏡子前照半天。
而女孩子的變化,簡直是生物學上另一種程度的「變態發育」,真的能女大十八變地長成面目全非的模樣。
小時候是黑猴子的宋小寶的開始脫胎換骨般地變白,眼睛也開始拉長,長出了長而濃密的睫毛,鼻樑雖然依然不高,卻隨著軟骨的定型,至少看起來不塌了,嘴唇下面收出一個小小的下巴,魏謙驚奇地發現,她就像只毛毛蟲一樣,轉眼就奔著蝴蝶的方向長去了,竟能看出一點小美人的雛形來。
不過,這一點雛形在她那軍閥一樣的大哥看來,根本什麼都不算。
在魏謙看來,宋小寶依然是「半個人」,這些小崽子在沒長大之前,都是一樣不男不女的樣子,根本沒有什麼性別可言。
她前沒胸脯後沒屁股,豆芽菜似的那麼一個小東西,魏謙理解不了她到底有什麼好美的。
他堅定地認為,小寶的臭美,除了耽誤時間影響學習以外,沒有任何的益處。
於是他在又一次瞥見小寶有拿筆卷頭髮的時候,走進了小寶的房間,以賈政對待賈寶玉的方式,非常嚴肅地和她談了一次……不,是單方面地訓了小姑娘一頓,還從宋小寶的書桌裡搜出了一小瓶指甲油,拿走沒收了。
最後,他專橫跋扈地規定,宋小寶每天照鏡子的時間不得超過一分鐘。
小寶委屈極了,第一次對大哥生出了逆反心理,而魏謙竟然還嫌不夠,走出去之前一隻手扶在小屋門框上,義正言辭地回頭說:「哦,對了,我看你們學校裡別的小丫頭都把頭髮剪了,乾脆你也剪了得了,早晨起來省得梳那麼長時間,再說我聽說頭髮太長吸收營養,影響腦子。」
這話遭到了宋小寶的激烈反抗,她跳了起來,膽大包天地衝著大哥大吼一聲:「我不剪頭髮!就不剪頭髮!你要是剪我頭髮,就把我的腦袋一起剪了!」
魏謙愣了一下,沒想到頭髮對她而言居然這麼重要,可他還沒來得及開口訓斥,小寶就被自己的大逆不道嚇壞了,自行「嗚嗚」地哭了起來。
魏謙嘆了口氣,拿她沒辦法,只好板起臉來:「哭什麼哭?再哭抽你。」
他想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給宋小寶判了個緩刑:「那行吧,看你成績和表現,期末要是退步,甭給我廢話,麻利的把你那破頭髮剪了,聽見沒有?」
宋小寶抽抽噎噎地問:「剪……剪什麼樣?」
魏謙想也不想地說:「前後一塊都齊耳吧,涼快。」
宋小寶想像了一番前後都齊耳的頭髮是怎麼個熊樣,當場給嚇了個魂飛魄散,從此開始了她一生中讀書最用功的一段日子,堅決要捍衛她小腦袋上的一畝三分地,絕不能落在大哥的魔爪裡。
魏謙從宋小寶屋裡退出來,正好被從廚房退出來的魏之遠撞了一下,魏之遠的腦門差點撞在他的鼻子上,忙一手撐在魏謙身側的牆上,側身避過。
魏之遠悶聲悶氣地叫了一聲「哥」——他開始變聲了,嗓子不舒服,所以說話的時候還要把聲音再往下壓八度,聽起來居然低沉得像個大男人了。
魏謙一時有些恍惚,想起剛把他撿回來的時候,他還沒有狗站起來高,現在竟然也成了半大小夥子了。
哥倆雖然還住在一起,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魏之遠已經不往他懷裡鑽了……想鑽也鑽不下了。
真是……有苗不愁長。
魏謙想起宋老太交代,讓他去郊區批發點雞蛋來,於是拖出自行車出了門,往郊區的養雞場騎去。回來的時候,他正好經過了老熊的店,只見老熊正指揮著幾個年輕人往車上裝行李,好像是要出遠門的模樣。
魏謙停下來打招呼:「老熊,你這是要把自己發配到哪扶貧去?」
熊老闆看了他一眼,慢吞吞地說:「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
魏謙跳下來,把車停在一邊:「好吧,這回發哪的財?」
老熊說:「夏至前後是收蟲草的日子,我打算進藏倒騰點藏藥——對了,正想找你呢,你週末還找短工嗎?有空來替我看店嗎?」
魏謙心裡一動,兩年前他帶回來三萬塊錢,經過宋老太的勤儉持家和倆人抓緊一切時間找活幹補貼家用,眼下竟然還剩了兩萬二……而其中大部分還是給麻子媽花的。
萬八千塊……夠不夠他搭著老熊的順風車,也跟著倒騰點小買賣呢?
第三十一章
可惜他的提議被老熊想也不想地一口拒絕了。
魏謙:「為什麼?」
老熊用他那種固有的、火上房也能陌上花開緩緩歸的腔調說:「我們倆三觀不合。」
魏謙:「……」
同時他心裡想:你媽。
魏謙問:「你雇我看店的時候怎麼不說三觀不合呢?」
老熊有理有據地回答說:「那是僱傭關係,現在你要和我一起走,你還要出資,那我們就是合作關係了,我不能要一個三觀不合的合作夥伴。」
魏謙耐心地問:「不是,你到底想要什麼樣的三觀?」
老熊:「問出這個問題,說明你根本就難以用有效的語言描述自己的三觀,你壓根就沒有那玩意兒的概念,唉,可悲的世俗之人,生命中沒有一盞指路的燈塔,活得該有多麼渾渾噩噩啊!」
魏謙想知道,到底是哪個精神病院院長玩忽職守,竟肯把這路貨色放出來禍害社會。
老熊淡定地看著他:「你肯定覺得我有病,那是因為咱倆三觀不合。」
魏謙深吸一口氣,耐下性子和他討價還價三百回合。
老熊活像王八吃秤砣,鐵了心地不肯帶他,魏謙心裡磨拳霍霍地想把他揍扁,可是又不想得罪一條人傻錢多的財路,於是掏心挖肺地說:「吃喝費用我自理,平時幹得了苦力,打得了群架,你就權當多雇個人,還不用你給工錢,你他媽就多帶我一個人怎麼了?」
老熊一開始入定一樣地充耳不聞,聽到這裡,忽然神色一動,懷疑地看著魏謙:「打群架?你還會打架?」
魏謙:「是啊,第二專業。」
老熊打量他一番,嚴肅地思考了一分鐘,出乎他意料地點了頭:「那行,只要你能吃苦,就帶你一個。」
魏謙心滿意足,踩上自行車:「得嘞,謝謝您了,熊老闆。」
老熊又叫住他:「哎,我們沒準過兩天就出發,你學校那邊行嗎?」
魏謙豪爽地說:「沒問題,不念了。」
老熊靈芝一樣多肉的臉上露出了一點讚賞的笑容:「雖然咱倆三觀不合,但我還是得說,我特別佩服你這種敢於逃學奔前程的精神,真勇士。」
魏謙騎在自行車上,遠遠地回過頭來��答:「我保送了,等秋天開學。」
老熊:「……」
片刻後,被欺騙了感情的老熊拖著老旦般的長音,開始在魏謙身後叫罵:「臭不要臉的保送黨!你還想妄圖混跡勞苦大眾隊伍,你、你……」
魏謙哼著小調騎遠了。
就這樣,魏謙開始了他生命中又一次要錢不要命的作死之旅。
這一回,臨走的時候,魏謙沒有不聲不響。
一來,跟著老熊出去做點小買賣不是不能說的事,二來,他也確實又長大了兩歲。
設身處地,魏謙想,如果自己是三胖,突然收到莫名其妙的求救短信,又聽到那麼駭人聽聞的事實真相,非得瘋了不可。
流逝的時光並非毫無痕跡,它開始讓他意識到,當年是麻子和三哥一直慣著他、遷就他,現在是宋老太容忍他、照顧他。他也開始承認,自己滿心的苦大仇深,實際卻一直在任性妄為。
麻子他這輩子是沒機會了,但是剩下兩個,他想對他們倆好一點。
魏謙臨走的時候通知了宋老太,告知了三胖,最後跑到麻子家裡,和麻子媽說了一聲,給她留下了一千塊錢,哄她說是麻子寄回來的。
沒告訴那倆孩子。
沒必要,而且經過上次的南方之行,魏謙幾乎怕了魏之遠。
那小子個頭是不小,卻老也長不大一樣地粘人。
兩年前是暑假,這回魏謙生怕他連學也不上了,直接就撂挑子跟他走人了——魏之遠絕對幹得出這種事。
然而魏之遠還是察覺出了蛛絲馬跡。
起因是魏謙臨走的前一天晚上,為了出遠門做準備,他買了一包常備藥,剛回家放下,麻子媽就推著輪椅出來,在樓底下喊他,說是電視機壞了。
魏謙匆匆忙忙地跑去幫她修,就把這事給忘了。
等他回來的時候,發現魏之遠正坐在椅子上,仔細地研究那些藥的種類。
魏之遠張嘴就問:「哥,你這是要去哪啊?」
魏謙自己也不知為什麼,聽他這麼一問,汗毛都豎起來了,幾乎升起某種被捉姦的惶恐,舌頭打了個結,磕巴了一句,才用忽悠的方式稟告他們家小祖宗:「去、去哪?去什麼哪?沒有啊!哦,那個是快夏天了,人容易中暑熱傷風,我準備提前的。」
魏之遠默默地抬頭看了他一眼,沒吭聲,把裝著藥的塑膠袋放回了原處,他分明看見裡面有一包預防暈車的藥和幾支口服葡萄糖。
宋老太被魏謙囑咐過,甭告訴那兩個小的,怕他們心浮,尤其怕魏之遠不好好上學,她從廚房端飯出來,瞥見此情此景,連忙欲蓋彌彰地說:「那是我讓你哥買的,他沒要往哪去,這孩子,真能瞎想。快拿筷子去,咱們要吃飯了。」
她這瞎話說得,口氣一唱三歎,幾乎要湊成一出沙家濱。魏之遠哪會聽不出來?
他再回頭一看,只見飯桌上是幾盤餃子——得,滾蛋的餃子接風的面,她還挺尊重傳統。
魏謙對鍥而不捨地往他的話裡插刀的老貨無話可說,他算是看透了,讓她擴散小道消息,她保證能對得起組織,讓她保守秘密,那是自作孽不可活。
宋老太保守秘密的方法,自古只有一個:生怕別人不知道。
魏之遠不是什麼溫吞的性格,但是也從來學不會勃然作色,天生性格使然,他內心不管多麼腥風血雨,也不會大吵大鬧地發洩出來,只會用無聲無息的表情和眼神表達他的極度失望和委屈。
他已經聽出來了,大哥要幹嘛去,奶奶是知道的。
而他們一致把他當成了不懂事的小孩……儘管他已經不再裝瘋賣傻地和小寶追跑打鬧、不再假裝天真無邪地撒嬌,儘管他正櫛風沐雨地向著大人的標準一路狂奔,俄頃也不敢停歇。
十三四歲的男孩子,青春期的躁動和急劇的身心變化,讓魏之遠越來越難以忍受大哥對待他的態度,他心中鬱憤無從排遣,只好如地火一樣壓抑在心裡蠢蠢欲動的火山下。
晚上臨睡前,魏之遠拿出了一份通知書遞給魏謙:「給我簽個字行嗎?」
他說這話的時候活像是遞了一份檢討書,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腳尖,眼皮也不抬,表情冷漠。
魏謙掃了一眼:「夏令營?什麼夏令營?」
魏之遠冷淡地說:「前一陣子我們學校組織了奧數的選拔賽,我被選上了,暑假被選派去參加培訓……哦,參加過培訓的小升初可以直接進本校初中部重點班。」
這換成任何一個其他孩子,都會歡欣鼓舞地跟大人顯擺一番,可是魏之遠似乎就只是要魏謙作為監護人簽個字而已,臉上繃得緊緊的,一點也不見喜色。
他喜不出來,反正再怎麼樣,他在大哥面前都是無能為力的。
可他年輕的監護人卻覺得十分驚喜——特別他看到通知單上寫著,一個學科全校只選派一個學生的時候,讓魏謙覺得異常長臉,情不自禁地笑了一下,然而隨即,他又覺得不該太過喜形於色,省得讓小孩驕傲自滿,所以他乾咳了一聲,硬是把上揚的嘴角拉平了,簽了字,一板一眼地說:「既然去就好好學,讓你去是學校老師看得起你,到時候別掉鏈子丟人現眼。」
魏之遠低眉順目地點了點頭。
魏謙摸了摸褲兜,然後想起了什麼,打開了鎖著的小抽屜,摸出了點錢,裝在一個信封裡——他做這事的時候,因為心情太愉悅,樂極生悲地把桌上小寶放的一瓶花露水瓶碰倒了,雖然眼疾手快地扶了起來,手腕上卻還是沾了一些。
魏謙隨手撕了塊紙擦乾淨手腕,把信封遞給魏之遠:「這個我給你放在外面了,要出去住的話,自己在外面吃喝都別委屈了。」
說完,他抬起手,順手揉了揉魏之遠的頭髮。
他的手腕上依然殘留著的花露水摻雜了酒精的香味,手指修長而有力,魏之遠突然覺得頭頂似乎有一股電流衝進了他的腦子裡,他竟然情不自禁地臉紅了。
臉紅過後,他心裡又開始用上莫名的羞憤交加,滋味難以言喻。
魏之遠突然開口叫了一聲:「哥……」
魏謙回頭看著他。
魏之遠想對他哥說,從今往後,他有自己的路要走,有自己長大成人的方向,不會再想莬絲子一樣死乞白賴地纏著大哥了,他再也不會像兩年前那樣不顧一切地追著大哥的腳步,千里迢迢孤注一擲地去做一個拖累。
他會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魏之遠,而不是一個無所適從的跟屁蟲。
然而迎著魏謙愉悅而克制的表情,魏之遠到了嘴邊的話在喉嚨裡滾了幾圈,又原原本本地從哪來滾回了哪去,散落成了一肚子的鴉雀無聲。
他默然搖搖頭,沒了下文,什麼也不想說了。
第二天,魏謙一路目送著魏之遠騎著自行車帶著小寶去上學了,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鬆了口氣,收拾了行李出門和老熊他們匯合。
老熊帶著大蛤蟆鏡和遮陽帽,嚼著口香糖,臨行之前還在囑咐魏謙:「帶你可以,不過咱們醜話說在前頭,那邊的鐵路至今還沒修好,咱們得開車進去,沒準去哪,平坦的地方海拔高,海拔稍低的地方路不好走,尤其山路,每年都有大批冤鬼翻車下山從此掛在牆上的,咱們最早七月底才能回來,那罪真不是人受的,你確定跟我去。」
魏謙毫不猶豫地點頭。
老熊搖頭晃腦地嘆了口氣,準備繼續用他催眠故事般地語速來頓長篇大論,被魏謙忍無可忍地打斷了。
魏謙:「熊老闆,聽你說話,總讓我想起一句詩。」
老熊看著他。
魏謙說:「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老熊帶著帶著蛤蟆鏡,在那思考良久,直到車已經開車了市區,他才如夢方醒地問:「不對啊,剛才那句是說人姥姥的吧?你個混賬東西。」
魏謙知道他不學無術,不知道他如此這般地不學無術,更令他歎為觀止的是,他這樣不學無術,竟然還敢腆著臉附庸風雅……此人真是,非同一般的一言難盡。
魏謙跟著老熊這麼一走,就悄無聲息地走了好幾個月,開始還會偶爾打電話回來報平安,後來乾脆音訊全無。
期間宋小寶還念叨了好幾次,魏之遠卻一句也沒提,宋老太懷疑這氣性賊大的孩子是給憋在心裡了。
魏之遠一個人睡空蕩蕩的大床,每天晚上必然要熬到十二點以後,用完的作業本就訂成演算紙,邊邊角角全都寸土寸金地寫滿,三四天就能用完厚厚的一整本。
宋老太看著那些她看不懂的演算過程,愣是沒捨得賣破爛,給珍藏了起來,作為每天例行公事地教育宋小寶的工具。
宋小寶就此受到了慘無人道的折磨,因為她和藹可親的奶奶對她就只剩下了這麼一句話:「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
宋小寶嘀嘀咕咕胸無大志地說:「我就是中等生嘛。」
「中等生,」奶奶用筷子打她的頭,給出了一個毫無根據的結論,「中等生就是丟人現眼!」
她連新聞聯播裡採訪外國人時候底下放的字幕都看不懂,大字不識一籮筐,居然還大言不慚地評價中等生……
中等生挺好的,又不是吊車尾!
宋小寶覺得奶奶狗屁也不懂,根本說不通。
大哥威脅要剪她的頭髮,二哥是那個該死的「人家」,奶奶變成了一個車軲轆話的碎嘴子,宋小寶覺得她在這個家裡,簡直就是個撿來的苦菜花,真是怎麼做都不對。
很快,夏天就來了,魏謙依然沒有消息。
那天魏之遠去參加學校的一個模擬考試,沒有去上課,提前回家了,奶奶讓他買二十斤大米,魏之遠就騎車去了,半路上,他經過了一個社區活動中心,魏之遠原本漫不經心地騎過,不知怎麼的,卻突然剎了車。
只見活動中心裡有一塊大平臺,大概是六一快到了,一個老師模樣的人正領著幾個八九歲的小孩在裡面排練節目,當然,小孩排練兒童節目沒什麼好看的,魏之遠的目光落在了一個男人身上。
那人也就四十來歲出頭,背卻已經佝僂了,鞋拔子臉上是沒剃乾淨的鬍子,穿著一身髒兮兮的衣服,顯得十分猥瑣。
那男人坐在一條公共長椅上,正不錯眼珠地盯著場中幾個跟著音樂蹦蹦跳跳的小孩看。
他的眼神幾乎化成實質,險惡地堪堪觸碰到那些小孩的身上。
就算這傢夥化成了灰,魏之遠也認識——這就是那個曾經被他一根鋼管打跑了的變態戀童癖。
魏謙當時一直在找這個人,可惜一直也沒找著,沒想到就這麼猝不及防地撞在了魏之遠手裡。
魏之遠推著車躲在一個牆角後面,就像一個初次狩獵卻異常耐心的小豹子,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地觀察著那個男人。
一直等了一個多小時,小孩們才結束了排練,魏之遠注意到,幾個孩子鬧哄哄地從社區活動中心的鐵柵欄門裡走出來的時候,那個變態也情不自禁地跟著站了起來。
可惜陪同的女老師一路跟著,他沒找到下手的機會。
男人就像一個被掐長了脖子的鵝,垂涎三尺地盯了好半晌,直到小孩們已經走得沒影了,他才喘著粗氣轉過身來,褲襠已經鼓了起來。
此時街上沒什麼人,男人因此毫無顧忌地把手按在自己的褲襠上,一邊走一邊揉。
他晃晃蕩蕩地往另一個方向走去,魏之遠只猶豫了一秒鐘,就把車鎖在路邊,悄悄跟了上去。
這附近的小學校是某公立小學剛剛設在這邊的分校,位置比較偏僻,魏之遠猜測可能就是這個原因,變態才會開始到這裡活動。
魏之遠綴著他足足走了將近四十分鐘,才見男人走進了一個肉食加工廠裡。
而後魏之遠不動聲色,原路返回,買米回家,到家以後隻字沒提,照例和宋小寶一個人洗碗,一個人收拾廚房,然後各自在各自的房間裡做功課。
宋老太囑咐一聲,又出門去做活。
魏之遠溫習了功課,看了一部分老師送給他的奧數書,屋裡安靜得連鐘錶「滴答」的聲音都聽得見,做完這一切,魏之遠才抬起眼睛掃了一眼小寶緊閉的房門,漆黑的眼睛如同濃墨點的。
然後他掏出了一個新的筆記本,寫下了日期、肉食加工廠的地址。
第三十二章
第二天早飯的時候,魏之遠對宋老太和小寶說:「這兩天晚上老師要留我補課,我晚點回來,不用等我吃飯。」
宋老太和小寶絲毫沒有起疑心,畢竟,比起魏謙那嚇人的違法亂紀前科,魏之遠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懂事,乾淨整潔,守規矩,自製力強,從不幹出格的事——在小寶他們學校,魏之遠的出類拔萃也是眾所周知的。
所以宋老太聽了,立刻把重點攻擊對象轉向小寶說:「聽見沒有,跟你哥他們學學,你大哥哥以後就是大學生了,你小哥哥還代表學校去參加比賽,你呢?」
小寶毫無壓力地說:「讓他們去吧,我看家。」
宋老太舉起鍋鏟要打她,宋小寶就像只小猴子,三兩步躥到了門口,狗腿地替魏之遠打開門,點頭哈腰地說:「二哥,您先請。」
魏之遠非常有大家風範地點了個頭,拿起車鑰匙,在她前面走了出去,宋小寶屁顛屁顛地跟上,就像個鞍前馬後的小太監,回頭沖宋老太吐了吐舌頭。
由於她的肉體的成長比老熊的語速還不著急,魏之遠又長得太心急火燎,兩人儘管最開始看起來差不多大,現在卻好像已經真的拉開了年齡差距。
宋老太憤憤地扔下鍋鏟,罵小寶:「爛泥糊不上牆,唉,不成器的東西!」
當天晚上,魏之遠果然是將近八點才回來,宋老太已經去給一家火鍋店幹活了,宋小寶從屋裡探出頭來:「二哥,回來啦?廚房有飯,鍋裡奶奶給你留了倆煮雞蛋!」
魏之遠「嗯」了一聲,打開鍋一看,只有一個。
宋小寶連忙補充:「我偷吃了一個!」
魏之遠:「……」
宋小寶「嘿嘿」地笑了起來:「對了,給你看這個!」
她說完,跑到客廳,從茶几的玻璃墊下面摸出一張皺巴巴的明信片,是從青海寄來的,上面是魏謙有些褪色的字跡,時間還是一個月前,大概是他正好經過的時候心情好了,聽了誰一句話,買來寄回來哄他們玩的。
可惜,他連哄都不認真哄,寫了通訊地址後,連句話也沒有,就畫了兩隻小烏龜,一隻光頭代表男烏龜,一隻頭上戴了一朵花,代表女烏龜,兩隻烏龜乖乖地待在一起玩耍,蘊含了大哥寄回來的全部訊息——魏之遠和宋小寶你們倆崽子在家好好待著,都給老子老實點。
那位「神龜真人」毀人不倦,不知不覺中對魏謙的審美觀和藝術細胞有了深遠的影響。
……他終身落下了沒事愛畫小王八的毛病。
魏之遠心裡情不自禁地一跳,魏謙已經半個多月沒有音訊了,小遠莫名地想起了那隻沾滿了花露水味的手,忍不住問:「他沒打電話嗎?」
「沒有,」宋小寶說,「二哥,青海是不是有犛牛肉乾?好吃嗎?」
魏之遠嘆了口氣,放棄了和她的正常交流:「你怎麼就知道吃。」
「哎呀,你別學大哥說話,學得又不像,應該是這樣——」宋小寶擺擺手,隨後板起臉,拗出一個橫眉立目的表情,壓低了聲音,語氣短促而凶神惡煞地說,「小兔崽子,就知道吃!」
她的模仿能力與日俱增,惟妙惟肖。魏之遠忍不住跟著小寶笑了起來,大哥板著臉訓小丫頭的模樣幾乎近在眼前了。
等小寶回屋裡了,魏之遠才坐下來,拿出了他的秘密筆記本,在「肉食加工廠」後面填上了幾個字「倉庫管理員,三班倒」,而後憑著記憶,完整地複製了一張值班時間表。
別的少年第一個寫在本上的秘密,通常是慕少艾的事,魏之遠第一個秘密筆記本卻讓人毛骨悚然地記載著一個人的全部蹤跡。
隨著時間的推移,魏之遠關於那個變態男人的姓名、家庭情況、工作排崗表、生活習慣等等內容,已經事無钜細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一開始,魏之遠只是對社區活動中心留了神,不過帶隊的女老師雖然年輕,卻看得很嚴,變態一直只能遠遠地看著,沒有走進過。而「六一」過去以後,那些排練的小朋友完成了表演,也就不再去了。
變態似乎很不甘心,但也無計可施,有大人在場,即使只是個瘦弱得像小鳥一樣的年輕姑娘,他也不敢怎麼樣。之後的幾天,此人都在附近轉悠過。
魏之遠一直在偷偷觀察他,然而跟蹤也好,記錄也好,他此時都只是順便收集了這些資訊,還並沒有想好自己應該怎麼辦,他不是魏謙那種瞪眼殺人的急脾氣,做任何事都習慣提前說服自己。
魏之遠合上筆記本,鎖好藏好,然後盯著喝水的杯子發了一會呆——杯子是大哥的,魏之遠其實有自己的杯子,可是他不愛用,總是喜歡來蹭大哥的水喝,同樣寡淡的涼白開,他卻好像能大哥的杯子裡喝出味道。
魏謙從不在意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隨便他喝……不過喝完要重新倒滿,否則會挨罵。
他難以抑制地想起很多和魏謙有關的事,同時越來越生大哥的氣。
魏之遠決定用沉默的冷暴力對那個自以為是大人的大哥反抗到底,哪怕大哥再來電話,他也絕對不接。
然而大半個月真的過去了,魏謙卻一個電話也沒打過,繼那封明信片後,再無音訊傳回。
天氣越來越炎熱。
連宋老太都按捺不住了,主動讓宋小寶給魏謙的手機打了電話——在宋老太的認知裡,電話費這種看不見摸不著就產生的費用讓她畏懼,只要家裡沒著火,她就不用電話,還不讓別人用。
可是沒接通,魏謙關機了。
宋老太心急火燎,立刻就要去樓上找三胖。在她眼裡,魏謙雖然是個說話和棒槌一樣的王八蛋,卻也是家裡的支柱,支柱不在了,她除了三胖,根本不知道該找誰商量。
魏之遠卻冷靜地攔住了她:「找他也沒用,三哥頂多會多打幾個電話,小寶打不通,難道他就能打通嗎?」
宋老太仰著頭看那已經比她高的男孩:「那你說怎麼辦?」
魏之遠想了想:「你說我哥是和誰一起去的來著?那個開藥店的人嗎?」
宋老太六神無主地點點頭。
魏之遠:「你把地址給我。」
當天正好是週末,魏之遠就帶著魏謙最後寄回來的明信片,拿著宋老太給他的地址,騎車去了老熊的藥店,他冷靜得就像在解決一道步驟繁瑣的數學題,一步推著一步走,有條不紊,鎮定得不正常了。
等宋老太也冷靜下來,她看看明顯蔫了的小寶,又想想那少年毫不慌張的臉,心裡卻開始有點不是滋味了。
至親的人失去消息,久去不歸,正常的人難道不應該六神無主嗎?
哪怕只是六神無主一會呢……魏之遠的反應遠超出了同齡人的水準,可宋老太卻不免有點心寒。
她以前覺得這孩子伶俐,仁義,現在卻不得不開始懷疑他沒有人情味。
魏之遠一路找到了老熊的藥店,按著老熊的尿性,這店員又是個臨時雇來的短工,面對著一人分飾多角的藥店正適應不良,一問三不知。
魏之遠和他要了老熊的聯繫方式,又說了幾句好話,用店裡的電話給老熊打過去,對方也是關機。
魏之遠心裡像是沉了一塊石頭,冰冷而沉甸甸的,似乎要把他的三魂七魄一起墜下去,他只好用力和那沉甸甸地石頭拉鋸,強逼著自己做正確的事。
少年和店員艱難地溝通良久,終於,店員想起來,抽屜裡有一張老闆的個人資訊,上面除了聯繫位址和通訊方式外,似乎還有一個緊急聯絡人。
就這樣,魏之遠找到了老熊的妻子。
然而電話接通的那一瞬間,裡面卻傳來一個焦急的女聲,不分青紅皂白地問:「老熊?是老熊嗎?」
她一句話,徹底磨滅了魏之遠心裡的希望。
至此,魏之遠知道,大哥是真的失去聯繫了。
從藥店出來,魏之遠徑直去了派出所報案,一個值班女警看他是個半大孩子,比較耐心地詢問了他很多具體情況。
可魏之遠偏偏什麼情況也不知道——魏謙只在剛走的幾天打過電話,可由於魏之遠賭氣不肯和他說話,魏謙頂多是逗小寶幾句,和奶奶交代個平安,三言兩語就掛了,每次留下的信息都少得可憐。
魏之遠只好拿出明信片給女警看,女警接過來,仔細觀察了一下郵戳和日期,搖搖頭:「弟弟,我們可以受理,也可以按著這上面記錄的行程和日期幫你查查他當時所在的位置,但是他很可能只是路過,不是在這裡失蹤的,你明白吧?你連人是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失蹤的都不知道,我們能找到的希望也很渺茫,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有那麼一瞬間,魏之遠看著她的表情顯得茫然而不知所措,好像被突如其來的變故打蒙了,然而只是一小會,他就克制住了,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女警透過他的反應觀察出了什麼,於是輕輕地問:「你家裡還有大人嗎?」
「只有個奶奶,年紀很大了。」魏之遠回過神來,垂下眼,而後頓了頓,「謝謝姐姐。」
說完,魏之遠站起來離開了,他已經做了他能想到的所有的事。
再無計可施了。
魏之遠以勻速騎車回家,到了半路上一個沒人的地方,他突然毫無徵兆地伸腳踩地剎住車,然後緩緩地彎下腰,趴在了車把上,把臉埋在了胳膊中間。
少年急劇生長而顯得削瘦的後背彎成了一個繃緊的弓,魏之遠終於牽不住心裡那塊石頭,任由它筆直地掉了下去,砸得他從肝膽肺腑一直痛徹了心扉。
「我該怎麼辦?」
茫茫然間,他心裡似乎從十方呼喊亂作一團,逐漸轉為渺無聲息的萬籟俱寂,而後只剩下了這麼一句沒有答案的問話。
大哥走得那麼遠。
如果他真的就這麼……就這麼……再也不會來了呢?
曠達無邊的遠方,與螢火如豆的希望。
自他出生到現在,「無能為力」似乎要貫穿他生活的每一天。
那天晚上直到新聞聯播,魏之遠才推門回家,小寶和宋老太忙一起抬起頭,眼巴巴地看著他。
宋老太問:「怎麼樣?」
魏之遠神色木然地走到客廳中間,端端正正地坐在沙發上。
他邏輯清晰地敘說了整個一下午的所做所聞,而後清了清嗓子,抬起眼,目光在奶奶和小寶的臉上掃過。
魏之遠輕而緩地說出了自己的後續決定:「現在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等消息,如果我哥……那以後就是我來退學養家。」
宋老太猛地跳起來,急赤白臉地用腳跺地:「呸呸呸!反話反話,童言無忌!小崽子胡咧咧些什麼?」
「奶奶。」魏之遠脊背挺直,靜靜地看著她,「我聽說我哥的父母沒了的時候,他就和我現在差不多大,從今往後,他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他能背動的家,我也背得動,你放心。」
宋老太愣愣地看著他。
小寶的眼圈卻忽然紅了,一眨巴眼,眼淚「啪嗒」一下掉了下來,她輕輕地拉著魏之遠說:「二哥,反正我學習也不好,讓我退學得了,我還能當自己是耗子掉進米缸裡了。」
魏之遠的目光落在她身上,然後他似乎是學著記憶裡某人的動作,有些彆扭的、不熟練地伸出手,輕輕地放在小寶的頭頂上。
他說:「你能幹什麼?你看起來那麼小一點,又沒有力氣,離開學校會被人欺負的。」
小寶不知怎麼的,聽了這句話,哭得更凶了。
「我哥是拼了命才走到今天的,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就肯定會在開學報到前回來——別哭了,沒事的。」魏之遠不慌不忙地說完這句話,而後擠出了一個不太成功的笑容,轉向奶奶,「以後要是天黑或者颳風下雨,我騎車接送你。」
魏之遠竭盡所能地調節家裡的氣氛、竭盡所能地想要成為一根新的支柱。
然而當夜深人靜到來的時候,他一個人坐在自己的小書桌後面,卻想不出大哥當年是怎麼把小寶帶大,撐起這麼一個四處漏風的家的。
他年幼的時候經常常口出狂言,動輒放出「養家餬口」的厥詞來,而今他終於遠近無依,一股來自內心深處的惶恐卻幾乎要把他壓垮。
比幼年時期懵懵懂懂、僅憑著天生一點機靈和運氣四處流浪的時候惶恐,比拿著鋼管面對變態的時候惶恐,甚至比跟著大哥謹小慎微地逃命時還要惶恐。
因為他不能懵懂,不能攥著心口一點熱血衝動做事,也沒有了那麼一個讓他翹首企盼的人。
上有奶奶,下有小寶,他得照顧他們,還有對面矮平房裡蝸居的麻子哥他媽,大哥不會允許自己扔下她不管的。
他感受到了一種幾乎暗無天日的壓力。
魏之遠深吸一口氣,在心裡默默地問自己:「我哥會怎麼做呢?」
他靠在椅子上,努力平復著起伏不休的心緒,開始了對魏謙一切的漫長的回憶。
魏之遠就像在認真仔細地審一道數學題一樣,一絲不苟地推敲著生活中所有的點滴需要,一件一件地思考該怎麼解決。
而儘管他做著最壞的準備,魏之遠心裡卻依然不肯承認魏謙是無故失蹤了,他始終堅定地認為,即使這個夏天他不會來,下一個秋天到來之前,大哥也一定會回來。
這彷彿成了他心裡最後一根浮在水面的稻草。
轉眼臨近了期末考試,魏之遠依然每天會往派出所跑,可他偶爾會得到一飯盒餃子或者餡餅,卻沒有得到一點關於大哥的消息。
每一次失望而歸的時候,魏之遠就會覺得自己被逼到了臨近崩潰的邊緣。
回程正好要經��一段靠近小學校的偏僻路段,這一天天色已經很晚了,魏之遠猝不及防地又看見那個變態——由於家裡的事,他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精力再去跟蹤了。
只見那變態手裡拿著幾根路邊買的棒棒糖,正彎著腰對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說話。
那小男孩看起來呆呆的,��能智力上有點慢,男人���語速對他而言太快了,他有些半懂不懂,卻本能地感覺到對方有點不懷好意,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了一步。
變態伸出鹹豬手去抓小孩的肩膀,就在這時,他突然從身後被人重重地撞了。
魏之遠裝作剎不住車的樣子把他撞到一邊,冷冷地說:「好狗不擋路。」
他已經長大太多,加上黑燈瞎火,對方根本沒有認出他,只是突然被撞破,有些慌亂地往旁邊縮了一下,魏之遠彎下腰拎起小男孩,扔在車的橫樑上,不耐煩地說:「坐好了別亂動。」
然後徑直把他載了出去。
小男孩果然是反應遲鈍,騎出了老遠,他才呆呆地看著魏之遠說:「大哥哥,我不認識你。」
魏之遠:「我也不認識你。」
這種對話超出了小傢夥的智力範圍,他睜大了眼睛,不知道說什麼好了,魏之遠一直騎出了窄小的胡同,才把他放在了鬧市區的路口:「走吧。」
找不到大哥的焦躁而絕望的心,與即將面對的家裡人帶給他的壓力兩相作用,終於點燃了魏之遠心裡壓抑已久的負面情緒。
而這天晚上的事,讓魏之遠認為自己找到了一個理由——他決定要弄死那個男人。
好像非要這樣,他才能找回一點他無能為力的手對生活的控制力。
第三十三章
轉眼,一個學期就到了頭,期末考試了。
考完試那天,學校裡的學生們一窩蜂地湧而出,宋小寶的裙子不小心被一個撒歡叫喊著跑過去的小男孩掛住了,書包拉鏈正好卡在了鏤空的花邊上,一下就撕了一條長長的大口子。
小寶狠狠地皺了皺眉,可是毫不知情的小肇事者早跑沒影了,她也沒辦法。
魏之遠到家的時候,宋老太還沒回來,他看見宋小寶坐在沙發上,腿邊放著宋老太平時用的針線盒,把裙子底下爛了一部分的花邊全部撕了下來,低垂著頭,仔仔細細地把裙邊往上摺起,笨拙地拿著針線鎖一條針腳彎彎扭扭的邊。
魏之遠問:「你幹什麼呢?」
他突然出聲,宋小寶猝不及防地被紮了一下手,她甩了甩手,呲牙咧嘴地抱怨說:「哎喲哥,你嚇我一跳,我這個裙邊扯了,縫不上,只能全撕下來重新縫一個邊。」
她話音頓了頓,歪頭看了一眼:「完了,好像有點歪了。」
小寶同志的手工能力難以企及勞苦大眾的基本水準,從來是手比腳還笨的,也從來沒有自己縫過衣服,以他們家眼下的經濟條件,名牌是不用想,但給小姑娘買一件新衣服還是不算什麼的。
可宋小寶這個「有條件要撒嬌,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撒嬌」的大嬌氣包卻連提都沒提。
魏之遠才知道,大哥不見了,不止給他一個人造成了壓力。
小寶縫歪了,只好用小剪子把線剪斷,拆下來重新弄,可惜沒過多久又歪了。
她難以忍受地嘆了口氣,把針線摔回了針線盒裡,大概心裡也很委屈,抽了抽鼻子,可是她抬眼看了看,發現只有自己和魏之遠在家,於是又把眼淚忍回去了——她只是看起來小,其實並不小了,在她心裡,魏之遠和大哥奶奶他們不一樣,大哥更像一個強大但是代溝深邃的父親,魏之遠是平輩的小哥哥,她不好意思在他面前也表現得那麼不懂事。
過了一會,小寶走過來,拿走了魏之遠尺子:「二哥你這把長尺子借我使使。」
說完,她彎著腰,趴在桌子上,用尺子壓著邊,艱難地走針,避免再次縫歪。
魏之遠低著頭,好像在看書,可面前的書卻一頁沒翻,有好幾次,他都想抬頭對小寶說,別縫了,明天再給你買一條新的。
但他不敢。
家裡縱然眼下寬裕,可是失去大哥就等於幾乎失去經濟來源,沒有來源的錢,總有一天要花完的。
他們倆心裡都懷揣著同一種恐懼,互相似乎都心照不宣地不捅破。
就在這時,三胖來了。
三胖總是顯得喜氣洋洋的,這傢夥能日復一日的窮開心,好像有高興不完的事,用魏謙的話說,就是他「臉上時刻泛著剛喝完喜酒的紅光」。
三胖探頭往屋裡看一圈,疑惑地問:「哎,你哥那倒楣孩子還沒回來?他是在哪被人搶去做上門姑爺,打算樂不思蜀了嗎?」
魏謙他們一行人失去聯繫的事,在魏之遠的要求下,誰也沒有告訴三胖,三胖至今還被樂觀地蒙在鼓裡。
魏之遠說:「差不多就是這一兩個禮拜了吧,昨天聽說往回走了。」
「哦,」三胖見他臉色坦然,也沒往心裡去,低頭看了看小寶手裡的活計,「寶兒,你這是要當裁縫啊?」
小寶抬起頭,視線撞上魏之遠,她打小不會看人臉色,此時卻不知為什麼,突然之間進化到了一個新的平臺——能看懂別人的眼神了,小寶配合著扯了個不甚高明的謊:「我不喜歡這個花邊了,想弄掉。」
三胖理所當然地說:「不喜歡讓你哥給你買條新的去,費這勁幹什麼?」
宋小寶是個實誠孩子,從來不怎麼編瞎話,她一時不知道該怎樣說,連忙低下頭,懷疑自己很快就要露餡。
好一會,她才抿了抿嘴,憋出了一句:「我……我想省著點。」
三胖吃了一驚,沒心沒肺地說:「瞧咱這妹妹,忒懂事,你哥那孫子要是聽見,可真能瞑目啦。」
他是開玩笑,三胖本來就是個沒煙兒的大嘴炮,跟魏謙也是生冷不忌,什麼「鹹話淡話」都滿嘴跑,百無禁忌,可是就在他這句話的話音落下時,小遠和小寶突然一起抬起頭來看向他,倆孩子的臉色都極其難看,只是難看,卻誰都不吱聲。
三胖反應非常快,一愣之後,立刻在自己嘴邊上輕輕拍了一巴掌:「呸,看三哥這張臭嘴,這胡說八道勁兒的,沒事啊,都別往心裡去。」
好一會,魏之遠才衝他擠出一個笑容,小寶卻沒那個城府,完全笑不出,她抓起衣服和針線盒,低聲撂下一句:「這看不見,我回屋做去了。」
而後轉身就走了。
至此,三胖再瞎也明白了有什麼不對勁。
可他衝著魏之遠張張嘴,正打算詢問時,一看那小孩隱隱含著某種倔強的眼神,就知道什麼也問不出來了。
三胖算是看明白了,這倆孩子心裡都不好受,只是礙於自己在場,都使勁忍著不露出來。
「得,」三胖心說,「我還是走吧,再在這待著,非把倆小崽憋壞了不可。」
他和魏之遠告別離開,決定晚上去堵宋老太,問個清楚。
而魏之遠始終記得自己還有一件事沒做完。
第二天,他選了一個靜悄悄的午後出了門,臨走的時候,魏之遠拿出了魏謙給他夏令營用的錢,看了看,連信封一起塞進了自己的書包裡。
這是哥哥留給自己的東西,魏之遠想隨身帶著,這樣他心裡踏實。
等做完那件事,魏之遠決定用這個錢去給小寶買一件新的衣服,反正要是他哥真的不回來,他也就不去夏令營了,沒意義。
此時,上班的都已經上班了,沒上班的也都在炎炎夏日中午休。
魏之遠已經弄清楚了,那個變態曾經結過一次婚,後來又離了,現在是獨居,他手裡有對方整個值班安排表,知道這一天變態正好值從午後到半夜十二點的班,不在家。
魏之遠連跟蹤再踩點,已經在那人家附近轉過了四五回。
他靈活地爬上了筒子樓附近的圍牆,雙腳一蹬一攀,一躍到了二樓的陽台。
魏之遠用隨身帶著的小刀把那男人家的紗窗劃了條堪堪夠他一隻手塞進去的口子,而後把手縮進了特意穿出來的長袖外套裡,隔著外套伸進了紗窗,撥開了裡面的插銷,從窗戶裡翻了進去。
他在做這件事之前,就已經認真地思考過了每一個細節,包括哪個環節會遇到什麼意外,幾乎是胸有成竹的。
魏之遠做賊仿似天賦異稟,第一次就行雲流水如慣犯,悄無聲息,一氣呵成。
但是直到此時,他依然本著嚴謹的態度,抱著大膽假設、謹慎求證的想法,先是參觀了此人的家。
很快,魏之遠就知道自己的謹慎求證完全多餘。
他在髒亂差的臥室裡找到了大量的色情海報和圖片,大部分都是以兒童為主角的,從圖片來看,這個人似乎對六到八九歲之間,還沒有發育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格外情有獨鍾。由於是獨居,這傢夥連藏都懶得藏,貼得滿牆都是。
魏之遠不想留下自己的痕跡,隔著衣袖,他翻了翻那些東西,心裡盤算著舉報的可行性。
隨即,他就否決了這個想法。
魏之遠只在他哥和三哥的隻言片語裡,聽說過這個變態似乎害死過一個小女孩,可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小女孩早就死無對證,連家人都不肯報警,他完全沒有憑據說就是這個人幹的。
至於自己遇見的那一次,只能說是未遂,對方如果一口咬定說他只是想搶小孩的零花錢,那似乎也是說得通的。
至於在家裡私藏兒童色情物品,縱然會給這個人帶來些麻煩,可那又能怎麼樣呢?人家家裡藏什麼,關別人什麼事?
他不會因為這個被判刑,而魏之遠本人從跟蹤到私闖民宅,這一系列的事卻都是上不得檯面的。
他已經夠麻煩的了,不能再因為這件事沾上更多的麻煩。
最後,魏之遠又翻開了一個抽屜,在裡面找到了一些明顯屬於孩子的東西——小姑娘的卡通發卡,他熟悉的、他們學校的校服鈕子,甚至還有幾件兒童內衣。
旁邊是一打錄像帶。
魏之遠抽出了最上面的一張,放在旁邊的舊式錄像機裡,噪音和白點過後,螢幕上出現了一段以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女孩為主角的色情視頻。
魏之遠對這個沒什麼興趣,他皺著眉把帶子往後快進,見識了世界上還有這麼荒誕不經的東西——整個一盒錄像帶,來回來去都是那一個小女孩,還、來回來去都是那點內容,竟然還頗有表演性質地切換了好幾個拙劣的主題。
魏之遠不覺得自己在為民除害,只是覺得有這麼個人活在世界上,讓他覺得有點噁心。
他領教夠了,準備退出錄像帶,悄悄離開,去實行他的下一步計劃。
就在他將要按下暫停鍵的前一秒,快進的錄像跳入了下一個片段。
這些帶子都數是粗製濫造的盜版帶,刻錄的人大概也是不小心,把一段其他的視頻也給混了進來,開頭幾個畫面在快進的作用下飛快掠過,魏之遠看了一眼,覺得背景風格好像變了,將要按下去的手情不自禁地頓了頓。
隨後,他突然瞠目結舌地瞪大了眼睛。
他看到了兩個人高馬大的歐美男人都穿得十分清涼,點到為止地說了兩句前言不搭後語的台詞,隨後竟然態度曖昧地抱成一團,親著親著就滾到了一塊。
魏之遠不知什麼時候停止了快進,不錯眼珠地盯著螢幕上的兩個人,兩位男主角都是身體修長有力,肌肉有棱有角,該有的地方絕對不缺……也絕不是假的。
而那兩個讓人難以理解的男主角似乎還幹得十分津津有味!
魏之遠呆立在原地,伸出去的手僵在了半空,完全忘了縮回來,就在那片裡的兩個男人哼哼唧唧罵罵咧咧地直奔主題的時候,外面突然傳來敲門聲。
魏之遠如遭雷劈一般地飛快地關了錄像機,屏息凝神一動不動地站在陌生的、亂糟糟的客廳裡。
外面有人大喊了一聲:「收電費?人在不在?」
魏之遠閉上眼睛,握緊拳頭放在身側,靜靜地數著自己如雷的心跳。
他深吸一口氣,整個房間的構造在腦子裡閃了一圈,瞬間選出了好幾條撤離路線——如果外面的人突然開門或者……
好在,外面那人等了一會,就低罵了一句:「一收錢就沒人,什麼人呢,呸!」
而後似乎是走了。
魏之遠這才鬆了口氣。
他後背已經被汗濕透了,行動卻有條不紊,先是退出錄像帶,而後小心謹慎地把動過的東西恢復原狀,最後,他在一個小櫃櫥下面找到了一個放現金的地方,從裡面抽出了三百塊現金。
他心跳已經稍稍平復,卻依然面紅耳赤,回頭把被他割開的紗窗壓平整,然後在門上的「貓眼」裡觀察了一陣,確定樓道裡空蕩蕩的一個人也沒有,又確定變態離開的時候沒有反鎖門,這才小心地推開門,回身帶上,悄無聲息地從樓道裡走了出去。
魏之遠覺得自己心裡有一把火,燒得他口乾舌燥,似乎有種黏膩不去��東西糾纏在他身上,他懷疑是自己是出於義憤和噁心,於是在路邊買了一瓶泛著冰碴的北冰洋,三口灌進了肚子裡,才算把那把火給澆滅。
魏之遠冷靜地回到家,給小寶寫了張字條,說是去市圖書館借閱資料了,晚上不用等他吃飯,然後他徑直去了那變態工作的廠子。
他的秘密筆記本上最後一頁寫了「邱建國」三個字,然後用紅色水筆畫了個大叉。
哦,邱建國就是那個戀童癖的名字。
邱建國當晚和平時一樣,在食堂吃了飯。
他最近盯上了一個長得像小丫頭一樣的小男孩,這個年紀的男孩子貪玩,放暑假在家四處亂跑,父母也更粗心一些,非常容易找到機會,反而比女孩更容易得手。
就在他吃完飯的時候,門衛拎著幾瓶酒過來了:「你買的,剛人家給送來了。」
邱建國一愣:「我?我沒買呀。」
門衛隱約知道這人有些不正常,雖然不知道他具體是哪種不正常,卻本能地不願意多和他接觸,因此只是愛答不理地看了他一眼,就把酒和簽字單子都放在了他面前:「就是你的,你的名——不是你買的是誰買的?錢都給過了,三百多,挺貴的呢。」
門衛說完,不想理會他,只吩咐了讓他臨下班把簽字單送到傳達室,就走、離開了。
邱建國核對了一下單子,發現是附近一家他經常光顧的小酒館的送貨單,也確實是他的名字,沒問題。
他尋思著,說不定是送貨的時候記錯人名了,平時去酒館的都是熟客,這事很可能發生,反正錢都給過了,有便宜不佔是王八蛋,要是有人來找,他就一推二五六,反正是酒館弄錯了才出的問題。
於是他心安理得地收下了酒,留下喝了,就著一小碟花生豆,他三瓶酒下去,整個人已經醉成了一灘爛泥,落成一坨地在躺椅上躺屍,一點都沒有自己在工作的意識,玩忽職守得簡直理所當然。
就在他半睡半醒間,男人聽見了「哢噠」一聲,他沒理會,只是翻了個身。
又過了一會,他聽見了小女孩脆生生的說話的聲音。
是那種沒發育過的,嫩得能掐出水來的聲音。
他正似醉非醉地陶醉著,一下子起了反應,兩眼通紅,猛地坐了起來。
他聽見聲音是從門外來的,小女孩好像在自言自語,時而自己一個人哼兩句歌,伴隨著細碎的、似乎蹦蹦跳跳的腳步聲。
他知道前面的車間員工宿舍裡,有一個女工帶著她的八歲的女兒住在這,他每次看見那小女孩都心裡癢癢,可他十分小心謹慎,不怎麼對身邊的人下手,只好一直憋著。
但眼下……正好夜深人靜。
被酒精加熱的腦子「轟」一下炸了。
男人的汗毛都激動地立了起來,乾渴地舔了一下嘴唇,難耐地伸手揉了揉自己的褲襠,然後站了起來,他酒醉沒醒,眼前一片白茫茫的,循著那忽遠忽近的聲音,頭重腳輕地往前走。
走著走著,他感覺周身一陣涼意,男人一哆嗦,多少清醒了些,他皺皺眉,意識到這裡是保存肉製品的低溫冷庫,裡面正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
男人恢復了點神智,衝著裡面說:「哎,冷庫裡不能隨便進!」
小女孩似乎嘰嘰咕咕地說了什麼,聲音太低了,他沒聽清。男人的喉頭猥瑣地上下滾動了一番,理智在慾望中艱難地掙紮了片刻,慾望贏了。
他看了一眼倉庫門口的大鐘,此時距離午夜十二點換班還有一個多小時,他知道冷庫白天隨時入新庫存,門是不上「大鎖」,只上「小鎖」的,內部人員都有鑰匙,只有後半夜換班,才會由換班人員加大鎖鎖死,第二天淩晨六點才準時打開。
一個多小時,夠做很多事了。
他放柔了聲音:「小妹妹,這裡面不能亂闖,快跟叔叔出來,叔叔領你去吃好東西……」
他徑直走了進去,絲毫沒有看到,冷庫門口的鐘早已經停了。
他循著女孩的聲音,越走越深、越走越往裡,最後捕捉到了聲音——就在一堵牆後面!男人舔了舔嘴唇,猛地跨前一步:「抓到……」
那裡並沒有什麼小女孩,只有一個他自己兩三年前淘汰下來的舊手機,正反覆播放著一段鈴聲,曖昧的童音不停地響著。
突然,似乎是沒電了,鈴聲停了。
整個冷庫寂靜無聲。
男人悚然一驚,就在這時,身後「咣當」一聲巨響——那聲音他無比熟悉,是他的同事將外層門關上,大鎖落下的聲音!
等等!還沒到換班時間,怎麼會有人這時就上鎖!
男人連忙跑到門口,聲嘶力竭地喊:「裡面還有人呢!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魏之遠等過了十二點,就把他的秘密筆記本燒了,徑直回到了家,把以前寫的厚厚一打演算紙攤在床上,做出十分用功的模樣——奶奶和小寶都沒去過圖書館,誰也不知道圖書館幾點關門。
他身上沾著外面帶來的露水,本以為自己成了這樣一個壞胚,會睡不著覺,誰知頭一挨到枕頭,立刻就感到了四肢百骸一般的舒暢,他把魏謙的枕頭擺在旁邊,好像這樣大哥就在旁邊陪著他一樣……
魏之遠是在這樣摻雜著罪惡感和隱憂的舒暢中睡著的,他迷迷糊糊地做了一個夢,夢見他的哥哥全身上下只穿著一件沒有系鈕子的襯衫,躺在床上看著自己,他身上那麼多的傷疤,卻一點也沒有破壞那漂亮的身體的線條。
魏謙的眼睛肖似其母,眼神中卻含著清澈的淩厲,鼻樑高挺,嘴唇上卻帶著某種……來自魏之遠臆想的、說不出的笑容。
魏之遠看到他袒露的身體,心裡那股粘膩的感覺似乎又來糾纏,少年著了魔一樣地走過去,忽然鬼迷了心竅地想要大逆不道地摸一摸。
夢裡的大哥只是懶洋洋地看了他一眼,竟然隨便他摸,魏之遠難以自抑地激動起來,忍不住生出了某種更陌生、也更深的渴望。
魏之遠被一串電話鈴聲驚醒,他猛地坐了起來,表情空白了一秒,心裡海嘯一樣地驚濤駭浪。
他下身冰涼一片,遲疑片刻,姿勢彆扭地從床上下來,拿起了電話。
「喂……」
「我。」熟悉的聲音有些沙啞地從聽筒裡傳過來,「沒睡醒呢吧?之前哥這邊出了點事,手機暫時不能用了,告訴奶奶別著急,我過兩天就回去。」
魏之遠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應答完這通電話的,他覺得自己渾身上下簡直是麻的。
第三十四章
魏謙一個電話打回來,說到做到地在一個禮拜之後回來了。
只不過不是自己走回來的,老熊不知從哪叫了輛車,一直開到了他家樓下。
正是炎炎夏日的一個下午,三胖正獨自一人在家裡吃著遲來的午飯:一碗方便麵。
本地電視台正播放著幾個無關痛癢的新聞,比如——倉庫保管員違規酒醉,誤入冷庫,換班同事照常落鎖,誤將此保管員鎖入冷庫中致其死亡。
被魏之遠強逼著自己寫暑假作業的小寶,抓耳撓腮表情痛苦,時而溜號走神,抬起頭聽了這一耳朵的新聞,她忍不住問:「冷庫是什麼?」
魏之遠頭也不抬地說:「是一個大冰箱。」
宋小寶又問:「那是誰的責任?」
魏之遠露出了一個冷酷的笑容:「人家按點落鎖,他自己超時進入冷庫,當然是他本人違規操作的責任。」
宋小寶不能理解地說:「那他幹嘛超時進入那個……呃……大冰箱?」
魏之遠一語雙關地說:「誰知道呢?大概是有病吧。」
宋小寶想了想,評論說:「唉,我第一次聽說人還能凍死,他跳跳不就不冷了嗎?」
魏之遠終於抬頭看了她一眼,用遙控器關上了電視。
小寶吐了吐舌頭,苦大仇深地低頭繼續寫作業。
魏之遠打量了她片刻,匪夷所思地想:「她竟然和大哥是一個媽生的?」
也就是在這時,曬成了一顆烏黑油亮的羊屎蛋的熊英俊先生走下車來,在魏謙家樓下站定,先是彎下腰對著車窗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領和髮型,而後站直了沖樓上喊:「談先生在嗎?談魚談先生在嗎?」
旁邊的車窗拉下來,魏謙的聲音從裡面傳出來,對未來「財路」的尊敬已經在數個月的不靠譜行程中被磨滅得一乾二淨,魏謙毫不客氣地說:「喊他幹什麼?扶我一把能把你累死嗎,傻逼?」
老熊同志緩聲細語地回答:「我接受你以後多鍛鍊身體的建議,但就我目前的體力,恐怕連個煤氣罐都扛不上去,別說是您老人家了。」
魏謙氣結,過了好一會,他才虛弱地說:「別叫他大名,小心他跟你急。」
老熊得體有禮地問:「哦,那請問我該怎麼稱呼?」
魏謙:「……三胖。」
老熊點點頭,直起身子,彬彬有禮地衝樓上喊:「請問三先生在嗎?」
車裡的魏謙默默地扭過了頭。
好在三胖天賦異稟,正在家吃午飯的時候,聽見了這麼幾聲飄渺的「三先生」,竟然還頗能領會精神地扔下筷子,從視窗探出頭去:「叫我啊?」
魏謙有氣無力地推開車門,在樓下衝他揮揮手:「三哥,下來扶我一把。」
三胖眯細了原本就不大的小眼睛,凝神靜氣地看了好一會,大驚失色地說:「媽耶!兄弟!謙兒!你不是說跟著個『人傻錢多的胖頭魚』倒騰藥去了嗎?我怎麼看著你像跟買買提烤羊肉串去了!怎麼變成這個色的啦?」
「人傻錢多的胖頭魚」就那麼不聲不響地站在一邊聽著。
聽見了聲音的三樓窗戶猛地被人推到了一邊,開窗戶的人手勁太大,窗戶「咣當」一下撞在牆上,又彈了回來。
魏之遠:「哥!」
少年變聲期的嗓子幾乎破了音,魏謙抬起眼皮掃了他一眼:「叫魂啊?」
他也沒比老熊強到哪去,整張臉只有倆地方是白的——牙和眼白,可在魏之遠眼裡,這個黑炭頭的出現簡直像是一盞阿拉丁神燈,頃刻間就點亮了他的整個生活……當然,由於那個光怪陸離的噩夢,這盞神燈下面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陰影。
宋老太白天不在家,魏之遠、小寶和三胖連忙下了樓,這才知道魏謙為什麼一直坐著沒動地方,他一條腿上打著石膏。
三胖一看,眼睛都瞪圓了:「這……這個不會影響你開學吧?重不重啊?」
魏謙還沒來得及說話,胖頭魚老熊就唸經一樣幽幽地開了口:「不會的,傷筋動骨一百天,他大概就剩下五十天左右了,考慮到他皮糙肉厚,應該下個月就能拆下來了。」
魏謙就著三胖的手單腿站起來,沖老熊揮揮手:「行了,你可以滾了,倒計時牌。」
老熊羞澀扭捏地說:「看在咱們一同出生入死的份上,收留我幾天,讓我緩緩。」
魏謙:「你家發生局部地震了?」
老熊更加羞澀扭捏地說:「見笑,家有河東獅,這麼長時間一直沒給內人打電話,愚兄實在有點畏懼她咬我。」
三胖一聽樂了:「大哥,你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真的猛士敢於面對慘淡的人生,還是回去給領導跪搓板吧!」
老熊微笑著對他說:「我不是真的猛士,我只是個『人傻錢多的胖頭魚』。」
三胖:「……」
魏謙:「……」
三胖反應過來,臉都青了,乾咳了一聲,狠狠地瞪了魏謙一眼——這小子居然也不提個醒。
他氣沉丹田彎下腿,紮了個馬步,拍拍自己的肩膀對魏謙說:「你……唉,上來吧。」
三胖背起魏謙,依然心有不平罵罵咧咧地說:「我這寬廣的肩膀還是塊處女地呢,是留給我未來媳婦的,就便宜你個孫子了……唉。」
他說著,低頭看了一眼魏謙的胳膊,試圖從他刷了漆的膚色上找點優越感,於是嘲笑說:「三哥問你,你一會洗洗,還能掉色不?」
「怎麼不能呢?」魏謙涼涼地說,「還會縮水呢。」
他竟然還有心情開玩笑,三胖的心徹底放進了肚子裡——可見是傷得不重,有驚無險。
老熊這個慫玩意,最終還是沒敢回去。
但是魏謙家裡實在沒地方,而且魏謙認為魏之遠可能是小時候心理陰影太重,一直有些「認生」,比如他看老熊的眼神就恍如帶著某種敵意。
於是最後老熊去了三胖家住——三胖的父母出門進貨了,晚上不回。
兩個大忽悠一拍即合般地忽悠到了一起,如同兩隻對比明顯的黑白豬,友好地並肩上樓,進行思想會晤去了。
魏謙連口飯都沒吃,把行李一扔,倒頭就睡了個昏天黑地,真是一動不動,身都不翻。
晚上吃飯,宋老太思考了良久,才決定把他叫起來讓他吃兩口東西再睡,魏謙是累到一定程度了,知道有人叫他,卻怎麼都醒不過來,最後憑藉著他活生生地忍受了老熊這麼多天的堅強意志,魏謙行屍走肉一樣地爬了起來,嚼都不嚼吃草草吃了兩口東西,又爬回去躺屍了。
當天夜裡,魏之遠寫作業寫到了淩晨一點。
他原本打算用夏令營的錢給小寶買件衣服,自己就不去了,現在顯然要修改計劃,夏令營是一定要去的,否則大哥也不會答應,他只好把前幾天已經丟下的額外奧數作業一氣補全——去那邊老師要檢查。
至於宋小寶那熊丫頭,看來他是暫時不用顧忌了。大哥剛回來,她就從短暫的苦情懂事小白菜狀態裡解脫了出來,又歡實了,下午就跑出去找同學玩,手裡的零用錢也不攢著了,光速給自己買了條新裙子。
他合上書本,靜靜地坐在椅子上端詳了魏謙片刻,大哥眼下這個熊樣和他夢裡那個叫他悸動不已的模樣當然是搭不上邊的,魏之遠定了定神,四隻手指蜷縮在手掌中間,輪番用修得很短的指甲掐著自己的掌心。
「一個夢而已,什麼也不代表,」新長成的少年冷靜地想著,「夢見裸奔的人難道真的會去裸奔嗎?夢見掀翻小汽車的難道真的有力氣掀翻小汽車嗎?不可能的,夢如果不荒謬,就沒人用『做夢』倆字來代替『滾』的意思……大哥這個姿勢躺了一下午加一晚上了,胳膊不麻嗎?」
魏之遠這樣想著,就慢慢地走過去,輕輕地板過魏謙的肩膀,仔細地避過魏謙的傷腿,給他翻了個身,又把他的頭搬到枕頭中間。
魏謙平穩的呼吸一點也沒有被驚擾,掠過了魏之遠的手腕,帶起一陣溫熱的小風。
他黑暗中的輪廓讓魏之遠心裡一跳,慌忙縮回手,中規中矩地在旁貼著床邊躺成了一具殭屍。
魏之遠陷入了一種奇異的狀態——魏謙回來讓他緊如琴絃的精神一鬆,本能地湧上一股愉悅的疲憊感,本應該沾枕頭就睡著,可偏偏他又被某種說不出的亢奮左右著,每一根血脈裡都是加速著奔騰流過的血流,靜靜地透過血管將那股動態的溫熱傳達到了他的皮膚上。
他怎麼也合不上眼。
當他以年幼的視角仰望身邊的少年的時候,曾經覺得他高大而無所不能,而今那種仰望已經隨著他視角的改變而蕩然無存。
他發現,他哥也不過是肉體凡胎的一個人。
而這芸芸眾生中渺小如蟻的一具肉體凡胎、曬成了一具非洲裔木乃伊的肉體凡胎,卻好像一束龍捲風,頃刻將他精神世界裡的黑雲和苦雨席捲一空,轉眼就曠野茫茫天高雲淡了。
魏之遠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扒著自己條分縷析的心弦,帶著放大鏡,要找出自己每一個骨頭縫裡隱藏的細枝末節的心情,如同漂浮在夜空中的第三人,居高臨下地審視著自己——依然充滿畏懼和惶恐的……懦弱無能的自己。
魏之遠得出了一個結論,他認為自己依然是太弱小了,才會需要大哥這樣一個精神世界裡的支柱。
他決定要把這條支柱徹底清理出去。
然而即使這樣,他的心情依然沒有豁然開朗,他的靈魂裡依然有什麼地方始終還是黏連的。
魏之遠對自己靈魂的解剖卻在此處止步了,他似乎是本能地畏懼那一小塊陰影地帶,裡面似乎藏著那股在他身上縈繞不去的粘膩感的真相,而出於自我保護,他將那塊小小的真相封存了起來。
那是與死亡摻雜在一起的,扭曲變態背德而又荒誕可怖的愛慾,已經超出了一個少年能夠承擔的底線。
「春風不解風情,吹動少年的心」,唱詞美好,可動了心的少年,卻不一定每個都是光風霽月的。
魏之遠清晰地知道自己正在滑向一個深淵,然而他不知該怎麼阻止。
魏謙這一覺,卻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傍晚。
他在家人各種擔心的目光中搖搖晃晃地爬了起來,整個人瘦成了一個移動的衣服架子,鑽進了衛生間裡,隨手打開水想洗個淋浴。
他家的淋浴構造非常原始,就兩根簡陋的管子,一邊連著熱水箱一邊連著自來水龍頭,自來水來得更快些,所以每次打開淋浴之後,十秒鐘之內,水都是涼的。
涼水把魏謙沖得一激靈,本能地往後退了一步,這才想起自己已經回到充斥著氧氣泡泡的平原了。
他睡得渾身骨頭都發酸發疼,吊著一條腿,高難度地草草沖了個澡,然後一口氣吃了三碗飯,這才感覺自己又活過來了。
他手上佈滿了各種刮蹭出來的傷疤,在飯桌上居然依然是下箸如飛,一點也不影響發揮。
宋老太看了直嘆氣,絮絮叨叨地說:「你這沒良心的白眼狼啊,究竟到底是上哪瘋去了啊?你打算坑死我們是不是啊?」
上哪去了?
還真一言難盡。
魏謙其實真的不是故意讓家人著急的,他這一路,可是把能吃的苦都吃了,把能倒的黴也都倒了。
除了魏謙,老熊還帶了三個人,都是年輕力壯的小夥子,誰知這幾個小夥子中除了一個叫小六的之外,其他幾個一個塞著一個的反應強烈。
他們的第一站,就到了青海雜多縣,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魏謙是一路吐過去的。
那真是把苦膽都吐出來了,最嚴重的時候整宿睡不著覺,覺得胸口好像被重物壓著,太陽穴被夾得生疼。當時他所有人都對小六羨慕嫉妒恨,可沒兩天,小六竟然死了。
小六在一片愁雲慘淡中身體倍棒吃嘛嘛香,產生了自己是銅皮鐵骨的錯覺,晚上在小旅館稀裡嘩啦地好好地洗了一通澡。他們住的旅館條件有限,熱水也是有一會沒一會的,小六前半截洗了熱水澡,後半截變成了沖涼。
晚上太陽下山,氣溫驟降了將近二十度,小六半夜就發起燒來,他一開始沒留神,以為是正常的高原反應,扛不住了才摸到電話和老熊說,老熊連滾帶爬的起來,淩晨把他送到了醫院,到了一看,腦水腫,嚴重了,轉移來不及,只好就地搶救。
到底是沒搶救回來,小六沒了,剛二十七。
從那以後,魏謙他們不用任何人囑咐,每天都把自己包裹得像個鵪鶉。
而這只是開始,天災後面還連著人禍——老熊本人就是個行走的人禍。
他先是帶著魏謙他們在當地轉了轉,試水似的收購了點蟲草,大致瞭解了個行情,存在了當地,而後老熊大筆一揮做了決定——南下進藏!
那時魏謙還天真地沒有質疑這貨的決定,以為他是另有深意,直到在拉薩往南的一個小鎮上,老熊看上了一口鍋,並決定為了這口鍋跋山涉水走徒步的時候,魏謙才真真正正地意識到熊英俊這個男人腦子裡有坑的事實。
隨著他們越來越往沒人的地方走,最先沒了的是手機信號,而後沒了的是手機。
那天半路中途停下休息,有人在車裡吃東西,有人下車喊山歌——哦,就是野地裡撒尿的意思。
魏謙沒什麼胃口,剛想下車透透氣,突然,方便完回來的老熊指著他們一臉驚恐地大喊:「下車!下車!快下來!」
老熊表情很少那麼猙獰,聲音更是淒厲得如同爛鏟子刮過的破鐵鍋,鑽進人的耳朵裡,幾乎能激起一股尿意來,眾人訓練有素地抓起隨身的貴重物品包,紛紛打開車門往下跳。
說時遲那時快,魏謙最後一個被老熊伸手拽了下來,連同著他生死相依的財產一起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而後所有人都喘著粗氣,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車從懸崖上翻了下去,一聲巨響,沒了。
後來老熊說,他往這邊走的時候,發現原本停在路邊的車的後半部分的地面泥土開始鬆動,他當時就預感不好,連忙叫喚了一嗓子,眾人一跳車,車子的重心變了,鬆動的泥土直接塌了,一路陪他們走過來的越野車就這樣永垂不朽了。
前不著村,後不著店,腳下兩條十一路。
魏謙誠懇地問:「熊老闆,你能重申一次,我們這麼悽慘地走在這條鳥不拉屎的路上,是幹什麼去嗎?」
熊老闆這個王八蛋同樣誠懇地說:「買鍋。」
魏謙說出了真心話:「你丫就是一個大傻逼!」
大傻逼帶著一群小傻逼,跟外界失去了聯繫,好在,川藏線上偶爾有從四川藏區徒步到拉薩朝聖的佛教信徒,這些人中有獨自上路的,也有瞪著三輪車馱著物資、幾個人一起上路的,魏謙他們飢寒交迫地走了好幾天天,終於佛祖保佑地遇到了這麼一波藏民。
雖然對方的財產稀少,固定資產更是只有一輛需要腳蹬的小三輪,但是見到人就是好的,起碼能蹭幾口吃的,老藏民經驗豐富,還知道怎麼去弄補給,好歹是沒餓死他們。
一路上,他們幾個人見車搭車、風餐露宿,真是什麼洋罪都遭了,老熊開玩笑,說他們這夥人,別看現在東跑西顛地混飯吃,將來必成大器,過去走西口的晉商和從徽杭古道南下的徽商,就是這麼討生活的。
沒有人理他,他們都想弄死這個胖頭魚。
後來老熊如願以償地買到了他的鍋——那是一種產自無人能征服的處女峰南迦巴瓦懸崖上的皂石打的石鍋,石頭非常軟,手指甲能劃出痕跡來,所以無論做什麼都只能人工手制,即使魏謙被老熊稱為「沒見過世面的鄉巴佬」,他也能看出東西是好東西來。
可惜,當地不通公路,當他們每個人身上掛著一堆和當地村民收購的蟲草紅花與幾大口鍋、面朝黃土背朝天地負重徒步時,所有人都對鍋這種物品產生了某種說不出的階級仇恨。
途中簡直是一言難盡,過雪山爬草地一樣,魏謙還從山坡上滾下去,把腿摔傷了。
幸虧魏謙心裡雖然沒有信仰,但是有要錢不要命的境界,用夾板固定了一下,活生生地拖著一條傷腿又跟著他們走了一天,才到了有人的地方。
牧民那裡和外界依然沒什麼現代通訊聯繫,但好在民風淳樸,收留了他們,有一家跑拉薩做生意的人家有一輛小型皮卡,但是主人都不在家,老熊只好在當地逗留了小一個月,才租到了那輛車,倒騰到了成都。
直到到了成都,魏謙才得到了和家裡聯繫的機會。
在成都逗留了三四天,老熊以近乎翻雲覆雨的三寸不爛之舌,用翻了將近十倍的價格把石鍋轉手賣了,就把這一趟的成本全部收回了,甚至還餘出一點。
還有想收藥材的,被老熊拒絕了,藥材一根都沒賣——因為那些東西輕,容易攜帶,帶回內地,他有更好的效率。
鍋一出手,他們一天都不逗留,當天晚上就啟程回了青海,拿走了寄存在那的行李,就這樣又連滾再爬地回來了。
個中千言萬語,堪比九九八十一難。
然而魏謙面對著這一家老小,最後,心裡的責任感戰勝了他大難不死後想要顯擺一番的少年人天性,他只是老成持重地說:「沒什麼,那邊信號不好,一直打不通電話,我們倒騰了點東西,能賣點錢,你年紀大了,以後不要出去幹那麼重的活。」
第三十五章
第三天,魏謙家就已經完全恢復了正常。
雖然魏謙就只是回來養傷,什麼都沒幹,但他的作用宛如一個定海神針和吉祥物的混搭,只要往那一戳,大家就都能自如的該幹嘛幹嘛了。
清晨,魏之遠打了招呼,收拾好包準備去夏令營報導,剛一開門,樓上一個搪瓷杯子就「咣當」一聲摔了下來,魏之遠縮了縮腳,抬頭一看。
只見樓上三胖家門口站著一個頗為漂亮的女人,正用嗓門衝著三胖家發動百萬分貝衝擊波:「熊英俊,你給我滾出來!」
老熊鎖著防盜門,把裡面的大門拉開一條縫,躲在裡面弱弱地喵了一聲:「夫、夫人息怒。」
夫人息不了,眼睛都氣紅了,整一隻大眼睛雙眼皮的兔子:「好,你長本事了,一走好幾個月,一聲都不言語,老娘還以為你死了呢!你怎麼不就乾脆死在外面呢?一回來就往小狐狸精家裡一縮,我說熊英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要點臉能死嗎?!」
魏謙險些把豆漿噴出來,忙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出來,把魏之遠打發走:「趕緊上學吧,別拾樂了。」
然後他自己回手帶上自己家門,靠在樓道裡,雙手抱在胸前,用一種聽演唱會般享受的表情聽著樓上的「天籟之音」。
眼看屋外要上演一場正房抓小三的奇景,三胖連忙愁眉苦臉地把老熊擠到一邊,拉開了自家的防盜門,低聲下氣地說:「鐵扇嫂子,算我求求您了,您仔細看清楚了,有長成俺老豬這樣的『小狐狸精』嗎?」
熊夫人當場就被三胖那張佔據了她整個視網膜的大臉給震懾住了,足足有半分鐘沒吱聲。
老熊這個慫人趁機踮著腳尖往屋裡縮,不料很快被熊夫人發現意圖。
熊夫人大喝一聲,伸出尖利的指甲,四兩撥千斤地一把扒拉開三胖,兩步闖進人家家裡,把老熊捉了出來,擼起袖子對他進行了一番單方面的家庭暴力,給抓回去了。
三胖肅然起敬,空手光膀子地模擬出一個脫帽的動作,彎腰伸手地目送著他們下樓,魏謙忍不住做了一個和三胖一樣脫帽致敬的動作。
倆人喜聞樂見地看著老熊活生生地被拖��,用一種別人難以理解的默契,異口同聲地說:「人賤自有天收!」
……老熊的表情悲憤莫名。
不過過了兩天,老熊就又回來了。
他敲開魏謙家的門,魏謙見了他,第一句話就是:「你竟然還沒有被打死?」
「……」老熊沉默了片刻,「依然健在,讓你失望了。」
老熊給魏謙提供了兩個方案供他選擇,一種是魏謙在公平價格的基礎上,稍微打個折,把他收的那部分價格賣給老熊,他拿錢走人,一種是他的錢當入股,老熊統一賣出去,和他分利潤。
但凡魏謙不缺心眼,他就會選第二種,於是老熊雙掌一合,說出了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太好了,反正你還沒開學,暑假跟我賣藥去吧。」
魏謙把自己的傷腿伸到了老熊面前,問他:「熊老闆,摸摸你的良心,告訴我它還在,沒被狗叼走。」
老熊面無表情地問:「你就不想親眼看著自己的長途跋涉是怎麼變成人民幣,搖搖晃晃排著隊地走進你的賬戶的嗎?」
魏謙:「……」
老熊轉轉眼珠,隨即又提出新的建議說:「我覺得三先生這個人和我很投緣,以後可以把他一起拉上賊船。」
魏謙發自肺腑地問:「你是怎麼看出這一點的?」
老熊說:「我認為三先生這個人非常有禪意,你看他的名字——據說他小時候有一個和尚經過他家的時候,非得說他和佛有緣,要帶他剃度,只是凡俗的父母不捨得,所以才折中了一下,取了『木魚』的『魚』字,取了談魚這個名字。」
魏謙眯著眼聽了一會,發現三胖的臉皮厚度更上一層樓,竟能把「痰盂」這種終身恥辱的大名掰扯到這這樣的地步,於是問:「他沒告訴你他本姓『林』,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當年雷峰塔就是他落地的時候砸倒的?」
老熊長籲短嘆地說:「三觀不合啊,凡俗之人啊……」
魏謙:「找你『臨行密密縫』的姥姥說去。」
說話間,小寶正好從外面跑回來,老熊細細打量她一番:「這是你妹妹啊,小姑娘有多大年紀了?」
魏謙順手在小寶的腦袋上按了一下:「馬上就十四了,小土行孫,還不如人家十歲的高呢。」
「沒事,長得晚,」老熊慈祥地看著小寶,透過現象看本質地說,「你看她的大腳丫子,以後矮不了。」
小寶好生嘔了一下,愣是沒聽出來這是句好話還是壞話。
臨走,魏謙把老熊送了出去,老熊狀似隨意的問:「你弟弟呢?」
魏謙說:「參加夏令營去了。」
老熊沉默了片刻:「夏令營?學習不錯吧?」
魏謙虛偽地一笑:「哪裡,他不行,也就一般般吧,不過比我稍微強點。」
「聰明,唸書唸得好,」老熊彷彿喟嘆著什麼似的搖搖頭,對魏謙說,「可得好好教育啊。」
魏謙一愣:「啊?」
老熊慢吞吞地伸出手比劃了一下:「這個刀劍,薄到一定程度,渾身上下就會好像只剩下那一層刃,古時候的邪器妖兵大多走這個路數。這種東西劍走偏鋒,一出鞘就要帶下一層血肉。可人不是鋼鐵,要是把自己活得太『薄』了,就太危險,容易福薄命也薄……」
「那什麼,您等會,我這人有點沒文化,」魏謙掏了掏耳朵,「能麻煩您老人家能用人類一點的語言表達嗎?」
「……」老熊看了看他,大仙一樣的臉上緩緩露出了委屈的表情,「我他媽哪得罪你們家那小兔崽子了,居然給我老婆通風報信,再這樣、再這樣我饒不了他!」
說完,老熊邁著殺氣騰騰的小碎步走了。
魏謙認為魏之遠打小報告這件事,怎麼說呢?辦得有點缺德,但是缺德缺得大快人心。
不過話說回來,既然人家告狀告到了自己這,魏謙決定還是表示一下,於是週末魏之遠放假回家的時候,他大哥就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地對他一招手:「你給我滾過來!」
魏之遠心裡一跳,溜溜地滾過去了。
魏謙把傷腿搭在一邊的矮幾上,「啪嗒」一下點著了一根煙,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語氣問魏之遠:「自己說,你都幹了什麼?」
魏之遠當時腦子裡就一片空白,本能地以為是肉食加工廠的那件事被發現了。
然而他第一反應不是自己會落個什麼下場,不是會不會有員警來抓他,也不是他會不會沾上什麼罪名——而是大哥知道了,他該怎麼辦。
大哥會不會覺得他處心積慮?會不會覺得他很可怕?會不會覺得自己在身邊養的是個面目可憎的小鬼?
魏之遠頓時慌了,臉色「刷」一下就白了。
魏謙沒料到他那麼大反應,愣了愣,反省了一下,發現自己也確實沒說什麼重話。
他乾咳一聲,翻了翻眼皮,讓自己聽起來沒那麼的凶神惡煞:「你說說你,多大了,啊?還幹這種事,幹也就幹了,還讓人知道了告到我這來……咳,當然,並不是說不讓人發現就是對的!」
魏之遠飄遠的理智終於一點一點回籠——對了,大哥方才那個口氣叫他過去,怎麼會有什麼大事?
再說,倉庫裡那個人雖然是死了,可門是換班的人鎖的,人是自己走進去的,他所作所為也不過就是用那傢夥的錢買了點酒而已,別說他已經處理乾淨不會有人去查,就算有人前因後果全都查清楚了,誰能僅憑著這一點就定他的罪?
魏之遠被震了震鬆動的心回籠,重新回到鐵石心腸的狀態。
看了魏謙一眼,魏之遠心裡狠狠地唾棄自己方才的方寸大亂。
這小少年的心就像一片海,表面上平靜無波,似乎總是理性而寧靜的,內裡卻蘊含了巨大的叛逆和此起彼伏的躁動,長期平衡在一個危險的、一觸即發的臨界點上。
在這樣的心海中,魏之遠想著:哥知道了又能怎麼樣呢?反正自己發過誓,以後要好好照顧大哥一輩子,自己有什麼,就給大哥什麼,哪怕大哥要他的命,他也權當是還了當年撿他回來的養育之恩,兩清。
那麼大哥對他有什麼看法,又有什麼關係呢?
魏之遠自欺欺人地想:「我反正就這樣了,別人怎麼看我,都無關緊要。」
但是表面上對魏謙,魏之遠還是保持住了他一貫的乖巧,從善如流地承認了錯誤:「我錯了,下次一定打匿名電話。」
「呸!」魏謙站定了家長的立場,保證了表面上的不認同,同時,也暗地裡表達了自己內心的喜好,決定給魏之遠一個獎勵。
他單腿蹦起來,搭住魏之遠的肩膀,放緩了語氣說:「一會叫奶奶別做飯了,咱們出去吃。」
魏之遠神色自然,似乎沒有一點異常,扶著魏謙腰部的掌心卻浸出了汗。
暑假的最後一個月,魏謙和三胖跟著老熊東奔西跑地談了好多次生意。
魏謙這才發現,老熊絕對不像他表現出來的那麼熊,他人路非常廣,手裡什麼生意都沾——聯想起他們西北一行就明白了,儘管大家的目的是倒騰藥,路上卻絲毫不受最終目標的影響,只要能賺錢,看得見商機,什麼賺錢就倒騰什麼。
老熊的東一鎯頭西一槓子,似乎也不是在沒頭蒼蠅一樣的亂撞,而是在積累、摸索著什麼。
沒事的時候,魏謙依然喜歡泡在老熊的藥店裡,偶爾應付幾個客人,大多數時候閒聊,偶爾和三胖一起擠兌老熊。
老熊宰相肚裡能撐船,不和他們小青年一般見識。
聊起老熊死活要買鍋那事,三胖忍不住問:「熊老闆,你說我們謙兒這種見錢眼開的窮鬼也就算了,您老人家家大業大,怎麼也這麼玩命地幹呢?」
老熊悠悠地說:「當然是為了利潤。所謂商人,就是靠承擔某種風險以賺取利潤的人,你們承認吧?承擔風險和謹慎抉擇是商人的基本功。」
魏謙當場拆臺:「恕我眼拙,就看出您承擔風險、以及拉人上賊船一起承擔風險的功力了,其他太隱晦,沒看出來。」
老熊短促地點評了一下他的意見:「頭髮長見識短。」
三胖忽搖著蒲扇,笑得牙床都露出來了。
魏謙決定趕在開學前,把自己奔著野獸型藝術家方向去的半長頭髮剪一剪。
「當初可是你死皮賴臉要搭上我這賊船的,小魏子先生你別顛倒黑白啊。再說了,你應該感謝我,我把你們拉上的這條賊船是真正的諾亞方舟,」老熊大言不慚地一敲桌子,開始發表個人演講,「我跟你們說,未來的十年是個什麼樣的十年吧。首先,勞動密集型的行業沒有任何未來,像那些個什麼……開飯館的、做製造的、做代工的,那都不行,他們只能在日復一日的同行競爭和勞動力價格上漲中被擠壓得沒有生存空間。」
「比如你,」老熊指著三胖,「三同學,你那個什麼開火鍋店賣五花肉的想法,就最好丟開,你那玩意勉強餬口尚可,想做好,太艱難了,以你的智商,甭想多有出息。」
三胖遭到了人生理想層面上的打擊,呆若木雞地看著熊老闆。
「技術密集型的企業……哦,什麼文藝的、高精尖的,全都算上,它們比前者有生命力得多,所以上大學是有好處的,知識和技術的確能改變命運,」老熊掃了魏謙一眼,加重了語氣說,「但是,技術密集型企業的春天至今還走在半路上,咱們整個社會沒來得及到那個層面上,說���定十年後,我們會培植出技術產業的溫床,但是現在不行,現在還在萌芽,未來十年間,這種產業會在一種被壟斷的陰影下,跌跌撞撞地成長,你在裡面很容易混成中產,也可能會有出息,但是後者就需要時間了。」
魏謙閉了嘴,仔細地聽著老熊的話。
老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用力吧嗒了一下嘴:「只有資本密集型的行業,那才是未來十年間不會衰落的真高端,一兩個人,幾個億,幾十個億的項目,你都可以撬動,那是什麼境界?你手上源源不斷的現金流流過,你腦子裡將根本就沒有『掙錢』倆字這種小氣吧啦的概念。但是一條,這種行業有天然的高門檻,就是你首先得先有資本,資本的原始積累是一個篳路藍縷的過程,比你後來所做的一切都要艱難,你搭上我的方舟,就等於走了原始積累的捷徑,懂嗎?嘖,不識好歹的小崽子。」
三胖用胳膊肘撞了魏謙一下:「謙兒,他的意思是,你跟著他出生入死一回,是中彩票一樣的運氣。」
魏謙說:「是呢,你說我怎麼就沒把這點稀有的運氣用在買彩票上呢?」
老熊睨了魏謙一眼,表情略微沉了些:「不過我承認錯誤,我這次是有點錯估形式,對風險判斷有誤,特別是對不住小六,可惜,他們家沒什麼人了,不然我還能彌補彌補。」
提到小六,三個人都沉默了一會,唯一沒有參與的三胖嘆了口氣:「兄弟沒這個命。」
老熊點了根煙,倒插在煙灰缸裡,讓縷縷的香煙自己上升,就像插了根香。
三胖和魏謙對視一眼,突然覺得有點親切——他們倆在大槐樹下紀念麻子的時候,也是這麼著倒插了根煙。
老熊對魏謙說:「其實我一開始不想帶你,你這個人……」
魏謙:「跟你三觀不合。」
老熊翻了個白眼,魏謙跟他出生入死一番,說過命的交情也不為過,很多話他就不再有顧忌,於是直白地說:「你第一次上我這看店,有條不紊沒麻爪,我本來覺得你是個人才,事實證明你確實是,膽大機靈會抓機會——可那回我給你五千塊錢,你就真接著啊?」
魏謙:「哦,合著你沒真心想給啊?」
「不是……」老熊噎了一下,「我倒不是那個意思,超出你應得,你起碼要推拒一下吧?」
魏謙:「我推了你就不給了?」
老熊:「還會給。」
魏謙翻了個白眼:「你有病吧熊英俊同志?」
老熊嘆了口氣:「你要知道,你這個年紀,機會、眼光和見識經驗才是最重要的,總盯著那麼兩塊錢幹什麼?錢是一時的,長遠得了嗎?我跟你說錢就是水,越攥越少,你信不信?」
貧窮,原本是魏謙的逆鱗,然而此時他的賬戶裡已經有了六七萬塊的資產,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財產了,奇蹟般的……他對這片逆鱗的態度也不知不覺地放鬆了些,甚至能自嘲似的拿到桌面上和人討論起來。
魏謙一笑:「您也別站著說話不腰疼,大道理誰不會講?我不知道錢就是王八蛋嗎?你一個穿金戴銀的富二代,別跟我們小老百姓來這套。你要是也上有老下有小,過過那種吃了上頓沒下頓、隨時隨地捉襟見肘的日子,你也得和我一樣,一分錢一分錢的卡。」
老熊雙手捏住魏謙的臉,硬生生地把他的眼皮往下一拉:「你把白眼給我翻回來——咱倆到底誰站著說話不腰疼?你哥我是正經八百改革開放前的一代,你回家問問你們家老太太,我們小時候有什麼?我們家窮得揭不開鍋,我十來歲跟著我爸冒著殺頭的風險下海那會兒,你們這幫小王八蛋的還不知道在哪個猴山上扯旗呢���」
他說得是事實,魏謙和三胖不吱聲了。
「頭髮長見識短,你就是頭髮長見識短。」老熊恨鐵不成鋼地說,「傷害人的不是貧窮和物質上的匱乏,是對比,對比懂嗎?你是總看著別人,心裡焦慮,沒底氣。」
三胖想起魏謙做過的那些混賬事,立刻拍手稱讚:「謙兒,熊哥說得對啊!」
魏謙一擺手:「你說的這都是廢話,深山老林裡那些七老八十的大和尚,他們一個個比你還想得開呢,有本事你跟人家比坐禪去。我沒見識怎麼了?我焦慮怎麼了?我一個泥裡滾出來的小青年,我拿什麼當底氣?賣身嗎?真是最煩你們這種嚴於待人寬於待己的老男人。」
三胖想了想,似乎覺得也有道理,於是立刻倒戈:「熊哥,謙兒說得對啊!」
魏謙和老熊同時看了他一眼,無視了這棵牆頭草。
九月份,魏謙終於短暫地離開了老熊的鋪子,去學校報導了,經過了一場軍訓,一個多月好不容易白回來點的皮又光速黑了回去,拎行李回家的時候撞上了三胖,三胖指著他笑得見牙不見眼:「來,兄弟,快給哥唱一齣鍘美案,你這造型,不用上妝,貼個月牙就能『夜審陰、日審陽』!」
而魏之遠上了初中,開始展露他更加非人類的一面,第一年上初一,第二年他就跳進了初三重點班。
彷彿是為了驗證老熊的話,他真的越長越「薄」,後知後覺的魏謙終於對他留了心,魏謙發現這小孩不說話也不笑的時候,平靜的眼神裡像是藏了兩把鋒利的小刀子,唯有在家裡,還依然像以前一樣懂事貼心。
可是魏之遠小時候就知道裝傻賣可愛,只是那時候尚且能看出形跡來,眼下,魏謙卻有些摸不準了。
只是偶爾飯桌上,全家人就著電視裡的大小新聞順口閒聊的時候,魏謙才能從魏之遠的隻言片語間,聽出一點不經意流露的、偏激的蛛絲馬跡來。
還有就是魏之遠不愛粘著他了——當然,男孩長到一定年紀,這本來就是一個必經之路,魏謙以前覺得小崽子粘人很煩,現在卻突然覺得失落起來。
而魏之遠對他其實還不止是「不黏」。
有一天,小寶瞥見魏之遠用的演算紙是學校關於冬季長跑大賽的通知,就隨口問了一句。
魏之遠搖搖頭:「我不想參加,不報名。」
他嘴上說得客氣,其實心裡想,一圈一圈繞著一個東西跑,那是驢才幹的事,蠢死了,他才不去。
幸虧他嘴上的話聽起來很客氣,宋小寶才接了他的話茬繼續說:「我記得哥上初中的時候好像參加過,好像還拿了個二等獎……哎,是二等還是三等來著?記不清了。」
魏之遠筆尖一頓。
半個月以後,小寶就在他桌上看到了「冬季長跑大賽一等獎」的獎狀和獎品本。
宋小寶長到了這個年齡,晚熟的心智總算跟上了平均水準,她沒有蠢到開口問魏之遠不是之前說不想參加,只在心裡暗暗地尋思:二哥這是在和大哥比嗎?
魏謙平靜地度過了他半工半讀的大學生活,他選擇性地無視了老熊告誡他「別鑽錢眼裡」的話,接受了「萬物皆可倒騰」的那部分——小到學校裡的電話卡,大到跟著老熊倒賣醫療器械,一天到晚不閒著。
別人的業餘時間是「踢球玩耍談戀愛」,魏謙的業餘時間就是「賣東西賣東西賣好多東西」。
魏之遠也彷彿成了一座休眠的火山,一直牽著魏謙一根心神,卻也一直老老實實地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沒人刺激他,他也沒幹任何出格的事。
當然,出不出格只是魏謙不知道而已。
魏謙十天有八天跟著老熊在外面或者是住學校,忙起來恨不得一個禮拜回家看一眼。
而每當他回家的時候,睡眠就會變成對魏之遠的折磨。
隨著魏之遠一點一點長大,身高趕上甚至隱隱超過大哥,某種說不出的躁動越加難以忽視。
那一小片少年時候被他鎖在心裡最深處的陰影愈加濃重、愈加瀰漫。
魏之遠本能地抗拒,卻日漸抵擋不住那種說不出的乾渴和焦躁。
好在,這時候,也就是魏謙大四這一年,一切彷彿否極泰來一樣,他們這城市裡毒瘤一般的棚戶區終於被整改了,他們要從這裡搬出去了。
第三十六章
老城區,多好的地方,雖然一堆七扭八歪的小胡同,可是走出去就是市中心,去哪都方便。
因此刁民眾多,釘子戶們一會排成「人」字一會排成「一」字,讓拆遷辦好生滾了一番釘子床,險些剝掉了一層皮,才總算把這些人都擺平了。
老街坊們都能得到一比不小的補償款。
三胖一家人和魏謙都商量好了,在老熊的攛掇下,他們在一個不錯的地段看中了三套房,正好是一梯三戶——剩下那個他們倆打算留給麻子媽,她是個殘疾人,幹什麼都不方便,得有人就近照顧才好。
新房子那邊,被老熊的夫人大包大攬地全權接過去了,三胖的父母還會經常過去,三胖和魏謙壓根就當了甩手掌櫃,看都不看。
老熊的夫人是個挺讓人費解的人,她的性格就像個隨時準備奔月升天的二踢腳,火爆極了,尤其對待老熊,動輒抓耳朵擰肉地家庭暴力一番……當然,老熊這個趴耳朵也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她就好像《紅樓夢》裡那個王熙鳳,但凡碰見一點能顯示她能力的事,都忙不迭地往前湊,重在攙和地往自己身上攬責任。
她辦事也如同她的人一樣乾淨利索,面面俱到。
魏謙有一天順路,過去看了一眼,被半成品給嚇了一跳,像他這種五星酒店和豬窩一樣住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熊嫂子的品味是達標的。
種種跡象,說明熊嫂子這個人很可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而這樣一個性格和能力都不安於家室的女人,竟不知道怎麼的,離奇地做了老熊的全職主婦——說真的,老熊家實在沒什麼好全職的,雙方老人都不用他們費心,家務請人做,而這兩口子結婚十年也沒孩子,熊夫人一天到晚在家也不知道能幹點什麼,非得閒得蛋疼不可。
三胖曾經好奇過她為什麼不工作也不要孩子,被魏謙沒好氣地喝止了,魏謙從小就不耐煩打聽人家家裡的雞毛蒜皮。
熊嫂子那邊進展一切順利,魏謙他們卻不怎麼順利。
這天三胖跑到了魏謙家裡,魏謙也少見地早早回家哪都沒去,倆人主要是為了合計麻子媽怎麼辦的事。
他們倆這幾年,經過了苦日子,後來跟著老熊,也確實是東奔西跑、小有積蓄,然而從始至終,都兌現了說給死人聽的諾言。
麻子媽沒短過一口吃穿,時刻有人照應,逢年過節,一定是三胖和魏謙輪流把她接到自己家裡。
可幹兒子再親,也不是親兒子。
六七年了,她那醜兒子麻子一眼也沒回家看過,除了匯款回家,就只有偶爾寄來幾封信。字跡稚拙可笑,歪歪扭扭,話也是隻言片語,每次魏謙唸給她聽,她都覺得沒來得及聽出滋味來,就沒了。
然而偽造書信的辦法已經越來越不好用了,這幾年隨著手機的普及和通訊的便捷,麻子媽有時候總是疑惑,她的兒子出去跑生意,每次給她那麼多錢,為什麼自己就不裝個電話呢?
每次她跟魏謙他們絮叨這件事的時候,都能讓那倆小子出一後背冷汗。
好在,最近她已經不提了。
眼下老房子就快要拆了,麻子媽不出意外地不樂意走,縱然倆人已經輪番把新家吹得天花亂墜,她依然捨不得——麻子媽說,她怕搬走以後兒子回來找不著家。
魏之遠推門進來的時候,就發現三胖和魏謙站在窗邊上,一人手裡夾根煙,一人靠著一邊的窗戶,一同望著大槐樹的方向,比著賽的沉默。
魏之遠猝然見到魏謙,在門口遲疑了一下:「三哥……哥,你怎麼回來了?」
他一嗓子打破沉默,三胖這才動了動,回頭仰望了這個大小夥子一眼,痛苦地說:「謙兒,咱弟弟讓你餵了什麼東西,怎麼長成了一個大房梁呢?」
魏謙心裡很煩,隨手把煙掐在窗檯上:「房梁也比你長成個大門板強——你……唉,算了,我再去和她說說。」
說完,他快步地走下了樓,麻子媽正坐在大槐樹下納涼,她的臉依然是凹凸不平的,才不過中年,眼珠已經渾濁了,泛起老年人那種沉沉的暮氣來。
看見他來,麻子媽抬頭對他笑了笑:「謙兒。」
「姨。」魏謙走過去,拎起褲腳蹲在她身邊,同時心裡琢磨著措辭,他實在是已經沒詞了,但凡能想到的他都說到了,再說就成車軲轆話了。
魏謙真有點崩潰,他每天忙得腳不沾地,自己新家只匆匆看了一眼就再也抽不出工夫了,還要一天到晚地打擊精神,來跟麻子媽來回扯皮。
要是別人他早跳腳急了,可麻子媽……魏謙委委屈屈地蹲在地上,苦笑了一下,只好捏著鼻子忍了。
他有點鬱悶地對麻子媽說:「我就不明白了,咱們這鬼地方有什麼好住的,新房子哪不比這好啊?」
麻子媽緩緩地垂下眼睛,溫柔地看著他。
魏謙繼續說:「我覺得您想得也太多了,麻子都那麼大人了,又不是三五歲的小崽子,回來就算真找不著家,他就不能跟誰打聽打聽嗎?我……」
麻子媽突然問:「姨是不是給你跟三兒找麻煩了?」
何止是麻煩,簡直麻煩得要命啊!魏謙心裡抱怨,他是為了這事專程匆匆趕回來的,晚飯之前還要把自己收拾出個人模狗樣來,跟著老熊充當跟班,連夜趕火車去看一個外地的項目。
魏謙一口氣堵在嗓子裡,苦膽汁都快從胃裡翻上來了,到底還是生硬地擠出一個笑容來:「不會……那怎麼會呢?」
麻子媽看了他一會,忽然出乎他意料地鬆了口,她說:「那……那要不就算了吧,姨真不是故意給你們添麻煩,我年紀大了,在這住了大半輩子,突然讓我搬家,我反應有點軸,一時掰不過齒來。」
魏謙聽出了她口氣鬆動的弦外之意,簡直欣喜若狂,沒想到自己幾次三番地居然真能感天動地,讓麻子媽這老頑固鬆口,忙趁熱打鐵地問:「姨,那您是願意搬嗎?」
麻子媽避開他的目光,垂下腦袋,好一會,才小幅度地點了點頭:「那就搬吧。」
魏謙一時間如釋重負,忙從地上站了起來:「行!那沒問題,明兒叫我三哥帶您去簽合同領補償款好吧?哎喲我的親姨,您可算是點頭了,要不然我可真要給您跪下了。」
麻子媽說:「以後就走了,我想再看看老街坊,你推我一圈行嗎?」
她只有一條胳膊使得上力氣,坐輪椅把自己推出院子還勉強可以,路長了就不行了。
魏謙二話不說地單膝跪下來:「推什麼,我背著您!」
他背著麻子媽緩緩地走過每一條髒亂差的小胡同,依舊是熙熙攘攘,依舊是滿地跑的小崽子,只是上一代的小崽已經長大了,在樓下跑著玩的已經換了一批;依舊是亂停的自行車,隨處可見的非法涼棚,用自己陽台改的居民小賣部;依舊是那棵一到夏天就沒完沒了地掉綠油油的「吊死鬼」的老槐樹。
魏謙一邊走一邊說話逗麻子媽高興,比如當年他和麻子是在哪個路口聯手收拾過三胖,三個人後來又是怎麼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比如他們家舊油條攤原來是在什麼地方……突然,一滴冰涼的液體落在了魏謙的脖子上,讓他陡然住了嘴。
隨後,接二連三的眼淚紛紛地落在魏謙的脖子上、臉上,他背後傳來壓抑嘶啞的嗚咽聲。
魏謙腳步一頓,那一刻,他只想給自己一個大嘴巴。
他們倆花了六七年的時間編的漏洞百出的謊言,終於在無數次的岌岌可危後,還是被戳破了。
他第一次聽見麻子媽那樣說的時候,就應該能意識到的。
活人怎麼會找不著家呢?
魏之遠一直在窗邊看著。
他看見麻子媽那張佈滿傷痕的臉,一哭起來,傷疤紅得厲害,越發嚇人了。大哥不在家的時候,魏之遠給她送過飯,每次過去,她都很慇勤地抓一把糖或者小零食放在他兜裡——即使他已經不小了。
魏之遠從她身上每每感受到的是一種認命的木然,和近乎是低三下四地討好,好像哪怕留他五分鐘,多說幾句話也好。
她那樣的寂寞隱忍,魏之遠從沒有見過麻子媽這麼痛哭過。
而她的眼淚落在魏謙的臉上,就好像他也哭了一樣。
可魏之遠知道,大哥是不會哭的。他從大哥咬緊的牙關和深深的眼神中,看見了某種心如刀絞的克制。
魏之遠不知道為什麼,看到那張側臉,心口的熱血好像突然逆流了,溫溫熱熱地流轉過他的整個胸口,把他的心泡得幾乎是酥軟的。
三年了,每每靠近大哥,魏之遠都會覺得周身那種讓他噁心又焦躁的黏膩感揮之不去,在這片刻的光景裡,那股粘膩感竟然奇蹟般的消散了。他一直盯著魏謙把泣不成��的麻子媽重新放回輪椅上,推進麻子家的小院,直到看不見為止。
魏之遠一瞬間悵然若失——他一直在試圖模仿、超越大哥,以此降低他對靠近大哥的緊張感,他也一直不怎麼盼著大哥回家,因為那人總在眼前晃,會攪亂他難得的平靜——而此時,魏之遠心裡忽然產生了某種近乎「思念」的情緒,即使魏謙剛剛還在他眼皮底下,他迫切地想和大哥心平氣和地說幾句話,想放任自己貼近大哥一點,聽聽他都是怎麼想的。
他胸中一直熊熊燃燒的獵獵業火似乎突然剝落了專橫跋扈,漸弱漸緩,成了一把暖烘烘的火苗,蔓延出某種幽暗婉轉、一波三折的情愫。
魏謙很快就回來了,仰面把自己往床上一摔,先重重地嘆了口氣。
過了片刻,旁邊一動,魏之遠在他身邊坐了下來。
魏之遠隨手取過桌上的小刀和蘋果,仔細地削好蘋果皮遞給魏謙:「哥,你為什麼對油條姨那麼好,她也不是你親媽。」
魏謙接過來,嘴角牽動了一下:「哪那麼多為什麼,不為什麼。」
魏之遠:「怎麼會不為什麼?」
魏謙頓了頓:「你麻子哥……你還記得你麻子哥嗎?」
魏之遠點點頭。
蘋果不大,魏謙一口啃掉了小半個,腮幫子鼓起好大一塊,只是裡面正在長智齒,嚼東西很彆扭,好一會才嚥下去,而後他對魏之遠說:「當初如果死的是我,你麻子哥就算砸鍋賣鐵,也會把你和小寶帶大的。」
魏之遠一條長腿曲起來搭在床邊上,安安靜靜地低頭仔細打量著魏謙的眉眼,從中感受到了一絲不同尋常的意味來,他幾乎想要伸手摸一摸。
少年心裡想,為什麼也對我這麼好呢?我也不是你親弟弟。
可這句他沒有問,在心裡轉了一圈,最後消散在了四肢百骸裡。
魏謙卻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一翻身從床上坐了起來,叼住蘋果騰出手,拎過一個包,對魏之遠招招手:「來。」
說完,他又往小屋張望了一眼:「小寶不在家吧?」
魏之遠:「她們校舞蹈隊訓練去了。」
「舞蹈隊是什麼玩意兒……她那點心思就不能用在正地方。」魏謙皺了皺眉,顯然是聽到這個組織,挺不滿意,但是很快拋到了一邊,把包遞給魏之遠,「打開看看。」
那是個電腦包,魏之遠早就看出來了,他遲疑地看了魏謙一眼,小心地打開,只見裡面是一台嶄新的筆記本電腦。
魏謙翹著二郎腿坐在椅子上,數落說:「你不是要參加那個計算機競賽嗎?你們老師昨天都給我打電話了,說你老往學校機房跑特別不方便——你怎麼也不跟我說一聲?以後缺什麼就跟我直說,我賺錢是為了什麼的?」
魏之遠笑了笑,他像個真正的孩子一樣有點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指尖珍而重之地擦過電腦光亮的蓋子。
魏謙低頭一看表:「哎喲不行,我得走了,別給小寶玩,最好也別讓她看見,她夠玩物喪志的了,聽到沒有?」
魏之遠:「謝謝哥。」
那天魏之遠一直目送著魏謙拿好隨身的行李,還不忘隨手拎了一本書,大步走到路口,叫了輛出租車走了。
少年站在那裡,回味著自己方才的心情,似乎想弄出個所以然來,好好明白明白,然而很快就放棄了。
如果不是來得莫名其妙,怎麼能算是怦然心動?
到了陽曆年底,魏謙正被開題報告和老熊那頭一個懸而未決的項目一起折磨的時候,他們一起搬進了新家,魏之遠也終於有了自己的房間。
宋老太第一次推門進去的時候,簡直就像是進了大觀園的劉姥姥,她一輩子沒住過這樣漂亮的家,拘謹得手腳都不知道往哪放了。
宋老太整個人像分裂了一般,一會夢遊一樣地問:「這是咱們家嗎?咱們以後就住這嗎?」
一會又橫眉立目地罵魏謙:「我看那兔崽子純粹是有點錢燒的!才吃飽飯幾天,尾巴都翹到天上去了!這得花多少錢啊這敗家折壽的混賬東西,他怎麼不乾脆買個王府住啊?剛賺來仨瓜倆棗錢,嘖嘖,陽世三間要容不下他了!」
���回哥仨一起默契地無視了她喜氣洋洋的罵街聲。
一方面慶祝喬遷之喜,一方面也是感謝熊嫂子出的力,三胖和魏謙兩家人合起來請了老熊兩口子一頓,吃到一半才知道,那天正好是熊嫂子的生日。
於是晚上三胖和魏謙又陪著熊嫂子一起過生日去了,熊嫂子一個電話叫來了一大幫年輕人,一群人到附近一家會所裡包了個包廂。
熊嫂子叫來的人裡大部分是年輕姑娘,不但普通的年輕姑娘,這些姑娘的精氣神都和別人不一樣,甭管是五官驚豔的還是長得比較一般人的,身上都帶著某種說不出的藝術氣質,特別賞心悅目,三胖這丟人現眼的肥肥看得眼都直了。
老熊妻管嚴,一群美人在眼前,他連頭都不敢抬起來,眼觀鼻鼻觀口地坐在一邊參禪。
三胖:「乖乖,嫂子哪認識這麼多大美女啊?」
老熊小聲對告訴他們:「你嫂子以前是文工團的,這些都是她帶過的小姑娘。」
「以前」?老熊沒說現在為什麼不是了,魏謙也沒打聽,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落在其中一個女孩身上。
她……那個女孩漂亮得光芒四射,而那種美不是女孩子式的可愛,也不是女學生式的知性和清純,而是一種純粹的、毫無雜質的女性美。
有的女孩讓人聯想起鄰家妹妹,有的女孩讓人聯想起某種小動物,有的女孩則讓人聯想起某種風格的畫,可這個姑娘不會讓人聯想起任何東西,她站在那的時候,就只會讓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這是個女人。
熊嫂子慧眼如炬,眼光一瞥就發現了,偷偷用胳膊肘頂了老熊一下:「哎,你看。」
老熊以為組織的考驗來了,連忙誠惶誠恐地表明立場:「我不看。」
熊嫂子掐了他一把:「我讓你看小魏,你發現沒有,自從婷婷進來,小魏那眼神就連掃都沒掃別人一眼——哎哎,我問你,他沒對象呢吧?」
把老熊愁得,長籲短嘆地對他老婆說:「你怎麼又迷上說媒拉縴了呢我的姑奶奶?」
「積德,積德你懂不懂?」熊嫂子說完,揚聲沖那個女孩子打招呼,「婷婷,過來,姐給你介紹個人!」
婷婷應了一聲,從女孩堆裡站起來走過來。
三胖這才從眼花繚亂的美女裡回過神來,乍一看見婷婷,他先是愣了一下,隨後睜大了眼睛,立刻出聲阻止:「嫂子,別……」
可是熊嫂子已經快人快語地拉過了魏謙:「這是嫂子以前一起工作的,叫婷婷,這是小魏,魏謙,你姐夫帶來的,婷婷姐告訴你,這小夥子可厲害,青年才俊,還是名牌大學的,長得也帥吧?你們年輕人多認識認識……」
魏謙猛地一縮手,熊嫂子不明所以地抬起頭,卻發現他的臉都白了。
婷婷友好地和他打招呼:「你好。」
魏謙的表情卻像見了鬼一樣,他定了定神,勉強維持住了自己的風度,對婷婷擠出了一個微笑,然後飛快地道歉說:「嫂子我今天有點喝多了,胃不大舒服,得出去醒醒酒。」
說完,他就逃也似的跑了。
三胖「哎喲」一聲,立刻也追了出去。
魏謙一路衝到廁所,反手鎖上隔間的門,扒著馬桶吐了個翻江倒海。
三胖忙在外面敲門:「謙兒?謙兒沒事吧?」
魏謙沒有答話,他把能吐的都吐了,最後幾乎是精疲力竭,這才緩緩地順著牆根坐在了地上。
三胖聽見他的聲音低而微弱的傳出來:「沒事三哥,你讓我自己歇會。」
三胖縮回了手,不敢吱聲了,靜靜地等在隔間外面。
魏謙手肘撐在膝蓋上,抬起頭,眼皮眨也不眨地看著房頂刺眼的白色燈光,覺得空虛而難過。
他不認識婷婷,也從沒有在任何地方見過這個姑娘,而當她走進來的一瞬間,魏謙就有種被擊中的感覺。
他沒來得及反應過來她身上的似曾相識是哪來的,只是本能地被她吸引——魏謙有生以來,從生理到心理,還從未對一個異性起過這麼大的興趣。
那一刻魏謙忽然發現,原來自己只會被一種類型的姑娘吸引,還沒等他想明白這個姑娘屬於哪種類型,熊嫂子就自作主張地把她叫到了面前。
而當她走進,身上隱約的花香暗流湧動地衝他襲來,又抿唇一笑的時候,魏謙簡直難以形容自己的感覺。
他面對面地明白了她身上的似曾相識從何而來。
她那種純粹的、不受任何行為舉止乃至容貌美醜影響的女性氣質,竟然神似他十年前去世的媽。
年輕的身體裡澎湃的荷爾蒙還沒來得及冷卻,魏謙的心已經被拖入了一個冰冷的深淵,他一點也不想回憶自己是怎麼不完美地應對完,是怎麼一路忍到了廁所才吐出來。
他觸碰到了自己揮之不去的浮生夢魘,無論如何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
那天魏謙不記得自己是怎麼回的家,他並不是醉,只是累,累得他開門到家,沒來得及回屋,就癱在了沙發上,什麼也不想思量,倒頭就想睡。
片刻後,身後的臥室門「吱呀」一聲打開,魏之遠走了出來。
「哥?」他跪在沙發邊上,輕輕地推了魏謙一把。
第三十七章
魏謙沒有睜眼,只是極輕地應了他一聲。
熊嫂子在沙發上安了一個別緻的閱讀燈,魏之遠伸手擰開,溫暖的燈光一下就灑了下來,鋪滿了整條沙發。
它不刺眼,也不昏黃,像是某個冬日午後的陽光,營造出「添一分做作,短一分不足」的恰到好處的舒適來。
魏之遠還是第一次開這個燈,摸索了兩下才找到開關,而後他愣了一下——燈光妙筆生花般的在魏謙身上鑲了個淺淡的金邊,連他沒來得及摘下的圍巾都好像軟成了一團雪,藏住了一半的下巴。
魏謙側過臉,伸手擋住眼睛避開燈光,那手臂的陰影與修長的眼眉連在一起,好像一直要沒入鴉羽般的鬢角中。
華韻內斂,流光暗藏。
魏之遠的心劇烈地跳了起來,一直以來,渴望和理智都成為盤踞在他心裡兩股揮之不去的力量,後者有千萬種道理,而前者唯其一條——想,喜歡,割捨如斷腸。
而此時,魏之遠覺得自己胸中那千萬種道理都在崩塌,堪堪只剩下一根支柱一樣孤零零的燈塔,凝滯不動的光落在一個人身上。
少年的喉嚨不由自主地動了動,好一會,才按捺住自己起伏的心緒,推了魏謙一下,低聲說:「去屋裡睡吧,這冷。」
魏謙按住他的手,有氣無力地搖搖頭。
魏之遠打量著他的臉色:「哥你是喝多了嗎?我給你倒杯水好不好?」
魏謙又搖了搖頭,眉頭漸漸地皺了起來,好一會,他才深吸了口氣,半睜開眼,看了魏之遠一眼,揮揮手說:「別管我了,你睡覺去吧。」
魏之遠定定地看著他:「你怎麼了?」
魏謙沉默了好一會,他覺得自己累極了,一句話都不想說,尤其不想應付小孩子。
可也許是心裡太難受了,也許是酒意上了頭,魏謙突然移開目光,魏之遠竟驚異地在他的臉上發現了一閃而過的脆弱。
魏謙啞聲說:「我有點難受。」
這話說完,他就後悔了,魏謙感覺到自己心裡的閘門被他一時失手,居然開了一條小縫,他連忙費力地堵了回去,唯恐再露出一絲一縷來。
他閉了嘴,也閉了眼,不再言語,裝作只是頭暈酒醉,想睡一覺的樣子。
魏之遠等了一會,遺憾地沒有等到任何的後續表達,於是默不作聲地走進魏謙的臥室,從裡面抱出了一條毯子,搭在魏謙身上,回身倒了杯溫開水,又走到廚房,把晚上剩下的一碗米飯拿了出來,用熱水沖泡開,然後切了些菜葉火腿,打了一碗蛋花,一起在火上煮了一會,煮到米粒軟糯得徹底爆開,和乳白色的米湯難捨難分時,魏之遠才用勺子一攪,細細地灑了一把鹽,關了火。
魏之遠會做很多簡單的夜宵,他長個子的時候半夜經常會被餓醒,已經習慣自己爬起來找東西吃了。
「難受就趁熱喝兩口,喝完就好了。」魏之遠把勺子塞進他手裡,自己坐在燈下,拿起一本書,安安靜靜地陪著他。
粥的熱氣撲臉,帶著一股特殊的香味。
魏謙呆了片刻,窸窸窣窣地坐起來,端起來喝了。他冰冷的指尖被有些燙手的瓷碗燙出了淺淡的血色,胃裡壓的石頭奇蹟般地被化開了。
「家」一個字,似乎都融化在了那小鍋慢火煮出的一碗稀飯米湯裡。
好像能包治百病,喝完真就好了。
魏之遠一直陪著他,直到魏謙自己站起來回屋睡了,才收拾好碗筷關上燈,回到自己的臥室。
他床下有一個紙箱,雖然才搬到新家沒多久,但他的紙箱裡已經積攢了不少東西了。
最上面是魏謙一張泛黃的舊照,下面壓著一打大部分都沒有拆封的色情雜誌。
……非常規的,裡面沒有一個女的。
魏之遠一開始出於好奇翻看過兩本,很快就對條件反射一樣千篇一律的生理反應失去了興趣。然而,之前魏之遠被兩種矛盾的心情拉鋸時,他始終非理性地把這些炸彈一樣的東西保存在了自己的床下,儘管一直是藏,他心裡卻一直隱約地有種瘋狂的、希望被大哥發現的願望。
可惜,魏謙對他太放心,從來沒有翻過他的東西,一直也沒發現。
現在,魏之遠心裡的矛盾解決了,他下定了決心,所以決定要把這些都處理掉,開始他所擅長的步步為營。
魏之遠把大哥的照片抽出來,塞進隨身的包裡,第二天又把床下的雜誌混在其他的書裡,帶出去處理掉了。
可惜這一次,運氣似乎拋棄了他。
魏之遠的床有點矮,紙箱要倒過來才能往外拖,清早出門的時候小寶一直在外面催,魏之遠開口應了她一聲,一本翻開的雜誌就趁機滾到了床底下的最深處,魏之遠沒能聽見。
魏之遠為防有遺漏,還特意用長衣架在床下掃了一圈,以確保萬無一失,然而掃到最裡面的時候,衣架又勾住了床腿,好不容易才拿下來。
床腿下靜靜躺著的、翻開的雜誌就成了個「美好的燈下黑」,他到底沒掃出來。
大雪一落下,寒假很快就來了。
魏之遠又一次開始集訓——宋小寶覺得他怪作孽的,打從魏之遠第一次跳級不跟她一班之後,小寶就覺得他其實是跳到了異次元,從此過上了水深火熱的日子,沒看過一晚上的電視,沒有一個囫圇個的寒暑假,數年如一日的早出晚歸。
回家以後除了幫奶奶和大哥做些事,大部分時間也是躲在自己屋裡做題。
宋老太已經不再出去撿破爛了,不過她每個月依然是把魏之遠用過的演算紙和練習本紮成一捆拿出去賣,能買一大碗炒田螺。
在這種情況下,宋小寶一個正常少女,幾乎讓魏之遠給對比成了個不學無術的後進生。
不過即使這樣,小寶對她的小哥哥也沒什麼意見,主要原因是魏謙老卡她的零用錢,但是不卡魏之遠的,所以魏之遠成了她主要的蹭吃蹭喝對象,成了她半個衣食父母。
臘月二十四,已經是年關當頭,魏謙卻在辦公室裡和老熊吵架。
還是關於那個外地的項目,當時是老熊的一個朋友介紹的,當地政府圈了個商業圈,現在已經漸成氣候,周圍幾塊住宅用地水漲船高,成了肥肉,一時間吸引了一些虎視眈眈地盯著的目光。
老熊很有自知之明,沒打算攙一腳,只是帶魏謙過去長長見識。
結果這見識就長出問題來了。
魏謙幾乎對那塊地害了相思病,有一段時間三句話不離那個項目,險些到了走火入魔、茶飯不思的地步,而眼下已經到了隆冬,北方的冬天是沒法開土動工的,因此這時候是最好的拿地和跑各種前期手續的時間,如果效率高,來年開春解凍,就能第一時間做起來了。
為這事,魏謙在老熊辦公室和他拉鋸了大半個月了。
三胖在老熊屋裡打俄羅斯方塊,老熊正在附庸風雅地扒拉香爐裡的香灰,魏謙坐在他對面,看著他這悠悠閒閒的熊樣,恨不得大蒲扇把香灰都吹進他的鼻孔裡。
「你給我三千萬,三千萬我保證給你做下來。」
老熊忙伸手攏住風,小心翼翼地護著他的香,哭喪著臉對魏謙說:「且不說你做不做得下來,哎,兄弟,你看你哥我長得像三千萬嗎?」
魏謙:「那不是問題,你不是說……」
老熊擺手示意他住嘴,小心翼翼地劃了一根火柴,點找了香,蓋上香爐蓋子,吸了一大口,抽吧抽吧鼻子,搖頭晃腦地眨巴了幾下眼,似乎下一刻就要打噴嚏——這貨完全是把篆香當鼻煙壺用了。
然後他牛嚼牡丹地對風雅的篆香發出了高屋建瓴的評價:「香!」
魏謙翻了個白眼。
老熊這才吧唧著嘴對他說:「年輕人啊,讓功名利祿一沖,真是北都找不著啊。」
魏謙翹起二郎腿,重重地往椅子背上一靠,雙臂抱在胸前,跳著青筋忍耐著老熊。
「我早說了,你小子急功近利,出門跑過幾次就自以為有點見識了?」老熊詩朗誦似的抑揚頓挫地說,「你寫的那些可行性分析什麼的我看了,唉,都是扯淡。一塊大肥肉擱在那擺著,還分析個屁,但凡不傻的都想咬一口。但是你也不想想,那肥肉憑什麼就讓你咬了呢?您那牙口是金鑲玉的?」
三胖打了個寒戰。
老熊撇他一眼:「你幹嘛?」
三胖說:「您能換個腔調麼熊老闆?你這麼說話我感覺有好幾百隻蝸牛在我身上爬,怪麻心的。」
老熊:「……」
三胖又小聲對魏謙說:「我的乖乖,三千萬,不是三千塊,你別獅子大開口地就張嘴就要行不行,嚇死我了。」
老熊哼哼唧唧地接話:「謙兒,以你的聰明,要是有三兒一半的穩當圓滑,將來必成大器。」
三胖一拍大腿:「可不是嘛!」
片刻後,三胖又琢磨過來這話不對味:「等等,剛才那句好像不是誇我吧?是擠兌我比較不聰明嗎?」
「你那叫大智若愚。」老熊安撫了他一句,繼續對魏謙說,「多少人都盯著那塊地呢——行,就算你熊哥狗仗人勢一回,仗著我們家老爺子,給你弄來這三千萬,可三千萬你就想撬動這個項目?別做夢了小子,你連地都拿不下來,信不信?」
魏謙沉默了片刻,沉聲說:「你的意思是,我們還沒準備好,沒有一戰之力,對吧?」
老熊覺得吸了一鼻子香灰,有點癢,於是歪頭擤了一把鼻涕,甕聲甕氣地說:「你才看出來?那你該配副眼鏡了。」
魏謙沒理會他擠兌自己,目光尖銳地直視著老熊:「熊老闆,照你的意思,我們永遠都準備不好。路上沒人摘的李子都苦,每個好項目下面都有嘴接著——這只是個三線城市的小項目,大財團和大國企連看都懶得看的玩意,已經是我們現在能找到的最低、最理想的門檻,這一步你都邁不上去,遲早被遊戲規則甩下,連門都別想進。你沒發現嗎?地價在漲,你能確定自己準備得比它漲得快?如果來不及了呢?」
老熊悠悠地說:「那就是命。」
魏謙狠狠地一拍椅子把手:「我這輩子要是認命,早活不到今天坐在這跟你叫板了!」
熊老闆不跟他針鋒相對,依然是放鬆地靠在自己的椅子上,輕輕鬆鬆地問:「我們現在就是進不去門,怎麼樣?你有資質嗎?拿的下立項嗎?你在地方政府有人脈嗎?擺得平那一摞許可證嗎?你錢夠嗎?東拼西湊借來千八百萬塊錢,萬一那塊地公開競拍,你拍得過人家嗎?一看你就沒玩過牌,拿著塊八毛的籌碼也敢上桌,莊家一把大注下來就能把你擠出去。」
魏謙:「你說的都是問題,但不是沒辦法。」
老熊立刻輕輕地一按桌面:「辦法在哪呢?你說啊!」
魏謙頓了頓。
老熊放緩了口氣:「我很欣賞你這種只要見到機會,不顧一切也要抓住的精神,但是啊……小夥子,踏實本分一點吧!」
二十來歲的青年男人和三十來歲的成熟男人分坐在一個商務桌的兩邊,最後,年紀大的勝利了。
老熊邁著四方步走到一邊打電話,請示自家領導晚上買什麼菜了。
三胖走過來,拍著魏謙的肩膀:「小夥子,走吧。」
魏謙甩開他的熊掌:「滾,少說風涼話。」
凜冽的大雪淹沒了整個城市,樂呵呵的三胖和心事重重的魏謙就像一對沒頭腦和不高興,一人拎了兩大包火鍋用的各種料和菜往家走。
路上,三胖問魏謙:「你以前不是夢想當個實驗室裡的科學家白大褂嗎?為什麼今年沒考研?」
魏謙似乎正在思考別的事,聞言愣了愣:「我說過嗎?」
三胖:「你屬耗子的,撂爪就忘是不是?」
魏謙仔仔細細地回憶了一番,和天一樣陰沉沉的臉上露出一點自嘲:「小時候二逼,還以為上了大學就能當科學家,現在意識到錯誤,正在努力改正。」
三胖說不出為什麼,有點期冀地問:「努力改正技���問題,向著目標前進?」
魏謙輕描淡寫地笑了笑,呵出一口白氣:「努力改正航線,遠離烏托邦這種不可能之鄉——我還不信了,這項目我還非做下來不可了。」
是消遣,要是宋小寶能像魏之遠那麼省心,別說她沒事想跳個舞當消遣,她就是整天玩蹦極,魏謙也不管。
可是現在就不行,宋小寶這是玩物喪志,絕對的玩物喪志!
魏謙挑剔地打量了面前頭也不敢抬的小寶一番,真是橫看豎看看不順眼——大冬天的,小寶穿了一件在魏謙看來不倫不類的紅毛衣和小格子短裙,一張小臉越發的白淨,緞子似的長頭髮披在肩膀上,為了臭美不肯梳起來,一笑起來細眉細眼初具風情,標準的鵝蛋臉上唇紅齒白。
二八年華的少女,身上有種行將怒放的、灼眼的美麗。
魏謙卻完全不去欣賞,他覺得好女孩子就是應該留短髮,就應該穿著不合身的校服,拖著明顯長出一截的褲腿,穿著下襬耷拉到膝蓋的外套。
好像只有男女莫辨、腰長腿短的樸素和醜,才是正經人該有的樣子。
他不自覺地又想起那天在熊嫂子那碰到的女孩,純女性的美麗讓他覺得噁心,他把那種美麗與不好的、不潔的、風塵的東西聯繫在一起,當它們出現在小寶身上的時候,魏謙開始感覺到了某種危機。
他覺得小寶已經長得超出了他的心理安全範疇,出了圈離了譜。
火紅的衣擺,刻意凸顯出的小小的胸脯,都讓魏謙覺得自己心裡的淨土受到了污染,羞恥而隱秘的記憶連帶著惱怒,他心裡五分的火頓時暴漲到了十分。
魏謙越是憤怒,他的表情就越是平靜,黑沉沉的眼睛掃了小寶一眼,輕描淡寫地說:「放假了吧?」
小寶不明所以地點了個頭。
誰知下一句就是她的晴天霹靂。
魏謙說:「明天正好有空,我帶你去把頭髮剪了。」
「我是不是對你太放縱了?」魏謙打量著她的裝束,還嫌不夠地補了一刀,「你看看你穿得是什麼?像什麼樣子?像個學生嗎?」
宋小寶腦子裡一片空白,說不出話來。
宋老太終於徹底給夾在了中間,一方面她作為長輩,也希望小寶能有出息,能理解魏謙的專制和不講理,另一方面,作為女人,她也能理解小孫女愛漂亮的心情。
「那……她哥,」宋老太忍不住替小寶說了句話,「頭髮就先留著吧?她們過年的時候好像還要去演出,據說還有電視台的……」
「跳舞?」魏謙冷冷的一句話,終於打破了宋小寶的全部希望,「書讀成這樣,還有臉去跳舞?寒假我給你請個家教,哪也別去了,家裡待著吧。」
他在家裡積威甚重,宋小寶其實也只敢逮著他心情好的時候撒嬌,基本不大會頂撞他,可對於一個這個年紀的女孩來說,剪掉頭髮已經是一種生不如死的酷刑,不讓她去跳舞,更是和毀了她的全部「事業」、把她徹底囚禁起來一樣嚴重。
於是宋小寶就像反抗封建大家長的梁山伯和祝英台一樣爆發了:「你根本不講理!什麼事都得你說怎樣就怎樣,你就是大獨裁者,你就是拿破崙,就是希特勒!」
難為她能說出幾個歷史人物來,一聽就知道在學校裡是個不學無術的,希特勒就算了,拿破崙又是怎麼回事?魏謙都沒弄清她到底是罵自己還是誇自己。於是他更加鐵了心地說:「對啊,我就是說了算。」
宋小寶一看事情毫無轉機,頓時撒潑起來:「我就不剪!我就不剪!剪我頭髮,我……我死給你看!」
魏謙靠在沙發上,涼涼地看著她:「死給我看?好,我看了,你倒是死啊。」
宋小寶同志要是真有那說死就死的尿性,初中這點破功課她早就唸成學霸了,還用得著在這跟他跳腳?
小寶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本事還是和奶奶學的,想當初奶奶作為一個資深潑婦,如果不是魏謙礙著妹妹投鼠忌器,她都是鬥不過的少年版本的大哥的——何況小寶只學了個半吊子,眼下的大哥卻已經今非昔比,修煉成精了。
宋老太愛莫能助,不忍心看,不是不看了,默默地轉身去廚房收拾了。
魏之遠在一邊裝死,從始至終不存在一樣不吭聲。
宋小寶眼見沒了希望,終於嚎啕大哭起來。
她的頭髮那麼漂亮,每個人見到多會稱讚,她費盡心機從一眾灰頭土臉的小中學生裡奪目而出,還沒來得及自我感覺良好,就被大哥毫不留情地踐踏了。
無論怎樣,這一刻,宋小寶是恨著這個冷面冷心的大哥的。
因此她毫無顧忌地口不擇言起來:「我知道,你就是不喜歡我!你什麼都偏向二哥,從小到大,他零花錢一直比我多!你還偷偷給他買電腦!你給過我什麼?你連一個好臉色都不給我看!」
魏謙險些讓她給氣樂了。
且不說哪個才是親生的,就算都是親生的,做哥哥的也會多疼妹妹些。
魏謙終於緩和了些口氣,耐著性子跟她講道理:「我偏心?小遠跳過兩次級,免試上重點,考試年級第一,人家還從來不亂花錢,放假從來不出去亂跑,你就算跟他比,也比點有志氣的行不行?你……」
他難得這麼講道理,可是宋小寶根本聽不進去。
「你就是偏心!」她尖叫,「我才是你親妹妹!我知道你為什麼不喜歡我!你不就是因為媽的緣故才討厭我的嗎?」
魏謙的太陽穴開始突突地跳。
而宋小寶猶自不知好歹,跳著腳地跟嚷嚷:「你恨媽,媽死了你就繼續討厭我!你覺得她丟人我就會一定丟人!我怎麼樣都是不學好,因為你壓根就認為我根本學不好!我媽是隻雞,雞的女兒就是……」
魏謙狠狠的一巴掌已經招呼上去了。
他的巴掌帶著淩厲的風呼嘯而來,宋小寶腦子裡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躲,而這一巴掌卻沒打到她臉上,因為裝死的魏之遠終於出來制止了。
他一把從側面抱住了魏謙的腰,把他往後拖去,四腳並用地按在了沙發上,轉頭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地瞪了宋小寶一眼:「還不閉嘴!」
第三十八章
魏謙被宋小寶氣得一陣陣耳鳴,渾身發軟,魏之遠人高馬大地壓在他身上,他掙紮了兩下,竟然沒有掙脫開。
廚房的宋老太忙扔下掃帚,快步走進來,見了此情此景,真怕魏謙沒輕沒重地跟小寶動手,忙以一種狡猾而微妙的方式護了犢子——她自己先照著小寶的後背輕輕地摑了一巴掌,責怪說:「怎麼跟你哥說話呢?瘋啦?」
宋小寶梗著脖子,依然想要表現自己態度強硬和決不妥協,可眼淚卻先大雨瓢潑了。
宋老太嘆了口氣,站在這場家庭矛盾的漩渦裡——魏謙和小寶之間,以一種主持大局的態度和稀泥說:「要我說,小寶,都是你不對,你哥說你說錯了嗎?你現在小小的年紀,不好好上學,將來幹什麼去?跟我上菜市場買個菜都算不過零錢來,還中學生呢,唉!」
小寶狠狠地抹了一把眼淚:「中學生學的才不是算零錢那點事!」
宋老太以其獨特的純文盲視角,理直氣壯地反駁說:「放屁!我們那村支書就是中學生,當年算盤打得可好了。」
經過老太太不可理喻地一攪合,魏謙青筋亂跳的腦袋終於冷靜了些,他往後一仰頭,盯著天花板看了一陣,而後深吸了一口氣,緩和下語氣,對魏之遠說:「放開我。」
魏之遠一直壓制著他,感覺到他劇烈的心跳終於一點一點平復下來,才緩緩鬆開了按著他手腕的手,結果低頭一看,發現大哥的手腕已經被自己掐紅了一大片。
魏之遠連忙輕輕地攥在手心裡,用指腹揉了揉:「哥,你不在的時候小寶可懂事了,她就是跟你撒嬌呢,你看那丫頭都快哭成孟薑女了,別生氣了。」
一邊的宋老太聽得連連點頭,同時扼腕地想,這就是有文化和沒文化的區別,她怎麼就說不出這麼順耳的話來呢?
宋老太連忙幫腔說:「就是,她哥,有話好好說。」
魏謙打出娘胎就沒學過什麼叫「有話好好說」,此時,他已經不想再說了,他心裡湧起一種近乎飢寒交迫的疲憊,儘管他什麼也不想吃,暖氣也足夠暖和。
魏謙緩緩地站起來,胸口有些發疼,他似乎懶得再看宋小寶一眼,徑直越過了她,轉身回到自己的房間,回手甩上了門。
一場危機度過,宋老太這才轉過頭瞪了小寶一眼,低聲呵斥:「還哭!你有什麼好委屈的?存心找挨打是不是?」
宋小寶「嗷」一嗓子衝她叫喚:「我不剪頭髮!我就不剪!」
魏之遠匪夷所思地看了她一眼,別說頭上那兩根毛,只要大哥一句話,把他的腦袋剃光了掛在客廳裡當燈泡都沒二話。
宋小寶敏銳地從他們倆的眼神裡就讀出了自己沒有盟友的這個事實,一時間,她覺得自己像是茫茫宇宙、如海星辰裡的一葉小舟,獨行無岸的孤獨令她傷心欲絕起來。小寶一屁股坐在沙發上,自顧自地哭了個肝腸寸斷——她就快要和她心愛的長發生離死別了。
可惜,沒有人能領悟她少女的悲傷。
宋老太不想看著她耍小孩子脾氣,繼續去廚房打掃衛生了,魏之遠則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間裡,忙著回味方才情急之下抱的那個滿懷……魏之遠明白了自己想要什麼之後,就不再克制,開始放任自己的想入非非,幻想似乎給他搭建起了一個世界,時常在裡面坐一會,魏之遠總是能得到足夠的撫慰和平靜。
那一點少年人特有的、如陽春三月般的青澀情懷神通廣大,連他本性中固有的偏執和冰冷都給沖淡了不少。
宋小寶繼直面了大哥恐怖的暴力之後,又遭到了全家人不當回事的忽略,她心裡賭氣地想著:「敢情他對你們都好,就討厭我一個人。」
就在那麼彈指間,宋小寶腦子裡兩根異常的線路前言不搭後語地勾連到了一起,短路的火花「劈啪」一閃,她決定了,要離家出走。
走了,就從此海闊天空,再也沒人逼著她上學寫作業,再也沒人逼她穿難看的校服,也再也沒有人逼著她剪前後齊耳的獵奇髮型了。
宋小寶就像千百年來一代一代與父輩鬥爭的自由鬥士一樣,拿出了她百年不遇般稀有的行動力,把這個帶著火花的想法實踐了。
一般早晨起得最早的是宋老太,儘管魏謙叫她不要去幹重活了,但她當了一輩子的勞動婦女,享清福是她學不會的技能,所以每天早晨依然堅持去賣茶葉蛋和煮玉米。
第二個起來的是魏謙,魏謙上了大學以後沒見得輕鬆,理工科的課時安排本身已經不輕鬆,他還要擠出時間四處去撈錢,每天能睡五個小時就算不錯,眼下放假,雖然學校是不用去了,但又趕上他為了項目的事跟老熊嗆聲,所以需要早早起來準備,上午開會還有一場硬仗要打。
至於魏之遠,他們老師已經瘋得超凡脫俗了,一個寒假,魏之遠他們就年三十、初一初二休息三天,其他時間全在上課訓練,沒有雙休日沒有節假日。魏之遠基本上起來就走,早飯拿到路上吃。
三個人出於以上種種原因,沒有一個是在清晨七點半之後出門的,太早了,因此也就沒人去叫宋小寶起床。
不過這一天,最後一個走的魏謙反鎖了門,他生氣歸生氣,確實不打算放任小寶跟個大野馬一樣整天往外跑了。
可他不知道自己這個行為是多餘的,他也不知道,此時宋小寶已經不在家裡了。
頭天半夜裡,宋小寶越想越想不開,於是等到夜深人靜,她就倒騰出了自己積攢的全部零用錢,總共是兩百零八塊五毛——由於隨時可能因為一兩個小錯誤被扣零花錢,宋小寶已經習慣了像個小倉鼠一樣給自己留儲備糧了。
至於平時的開銷,她花的大多是從魏之遠那蹭來的。
小寶把最禦寒的衣服穿在了外面,又在包裡塞了幾件換洗衣服,帶上了她最喜歡的頭花和發卡,裝好了水壺和一袋小麵包,就這麼自以為準備充分地走了。
整整上午半天,忙碌的一家愣是沒人發現。
魏謙依然在心無旁騖地折磨著老熊,一大早,他就把整個項目的操盤模式事無钜細地擺在老熊面前,列印出來足足有半釐米厚,也不知道他在那麼短的時間究竟是怎麼弄出來的。
這是要鬼迷心竅的前奏啊……老熊無可奈何地說:「你小子還真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了啊?」
「你那天問我的幾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我都寫在裡面了。」魏謙不跟他逗,簡單交待了一句,拿起杯子一口喝下了半杯的水——也不知是著涼,還是被小寶活活氣得上火,他清早一起來就覺得嗓子難受得很,咽口唾沫都疼,像是發炎的前兆。
老熊唉聲嘆氣地把他的方案接過來,感覺自己對面坐了個要賬的活債主。
他簡要地翻了翻,頗為歎為觀止,老熊雇過一些和魏謙年紀差不多的小青年,當中不乏有異想天開的,可他們真是加在一起都沒有這傢夥膽大包天。
老熊挪了挪屁股坐正,乾咳一聲,擺出一張公事公辦的面孔:「不考慮實際可操作性的情況下,有些地方確實有點見地,也挺有創意。但是滿大街跑的小青年哪個都不缺創意,我不需要一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方案。糖精餡餃子前無古人吧?你試試煮一鍋站在大街上賣不賣得出去?你拿這東西,說服不了我。」
魏謙看著他,不鹹不淡地說:「我從來不異想天開,寫得出我就做得出。」
老熊盯住魏謙的眼睛,男人的目光一如既往的溫厚,卻始終是綿裡藏針的。魏謙寸步不讓,一字一頓地說:「只要我想要的,哪怕是天上的月亮,我也要把它當成月餅啃下來,你信不信?」
老熊表面上不動聲色,心裡卻覺得,這真像是魏謙這小子能說出來的話,而以老熊這幾年對他的瞭解,他說不定也真能辦得出來。
有那麼一小會,老熊幾乎被魏謙身上那種孤注一擲感染,大概一往無前的、堅定的人是能連著別人的血也一起點燃的。
然而,畢竟只是「幾乎」。
老熊心裡喟嘆:到底是年輕啊。
三四十歲的男人,在事業上依然是朝氣蓬勃的,他們精力充沛、年富力強,野心也會隨著條件的成熟,而到達人一生的頂點,可二十出頭時,那種屬於小夥子的橫衝直撞卻不可能再找回來了。
老熊幾乎記不起他再年輕個十來歲時是個什麼樣的光景,當他看著魏謙的時候,他開始懷疑自己是老了。
這小子,怎麼到了現在這個地步,還能像一無所有一樣地奮鬥呢?
可能魏謙要麼是精神上依然認為自己「一無所有」,要麼他天生就是個賭徒一樣的瘋子。
別管老熊心裡閃過幾多崢嶸歲月,他胖頭魚一樣顯得呆而忠厚的臉上卻始終不露出一點端倪,老熊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一字一頓地問魏謙:「那好吧,我再和你討論最後一個問題,三千萬,現在這個資金風險,我承受不了。如果我把錢給你拿來了,項目你拿不下來怎麼辦?你拿不下立項,拿不出任何保障,『過橋』【注】都沒人敢給你辦,到時候光是佔用這筆錢的利息,每天少說就得有一萬,我有什麼理由替你承擔這個資金成本?」
魏謙眼睛也不眨地說:「我有一家老小,房子我不能動,其他的,這幾年積蓄,我能給你湊出小二十萬來,你要是答應,我今天晚上連夜就過去,二十天之後成與不成,給你個大概齊的結果,真要是一點戲也沒有,我砸鍋賣鐵,也把錢還給你。」
老熊搖頭一笑:「砸鍋賣鐵,但還沒要賣房子,你倒還不算個亡命徒。」
魏謙:「你答應嗎?」
老熊思量了片刻,也許是年輕人喚醒了他年輕的血,也許是被魏謙給他的保證打動,老熊最終讓了步:「這樣吧,這兩天我想轍給你弄錢去,不過就算找我們家老爺子做擔保,怎麼也得二十來天小一個月,加起來我給你一個半月的時間,不說規劃許可,你至少要拿給我一份和政府的用地協議,那我這次豁出去了,跟你二百五一回,怎麼樣?」
魏謙的眼睛一瞬間亮了。
老熊怕他得意忘形,敲了敲桌子:「不過醜話說在前頭,親兄弟明算賬,你真要拿不下來,趁早回來給我賠錢,聽見沒有?」
魏謙臉上露出了一整天來的第一個笑容,他這才感覺嗓子幹疼得難受,笑容還沒來得及展開,就被咳嗽堵了回去。
就在這時,魏謙兜裡的電話突兀地響了起來,他低頭一看來電顯示,居然是從家打來的。
魏謙有些疲憊地嘆了口氣,不知道宋小寶又鬧了什麼么蛾子,���時間連著太陽穴都發緊了,趕緊喝了幾口溫開水把咳嗽壓了下去,這才接起來:「喂……」
電話那頭卻並不是特地來找事的宋小寶,魏謙聽見了宋老太有些哆嗦的聲音:「她哥,是你最後出門把門反鎖了嗎?」
魏謙:「嗯,怎麼了?」
宋老太:「小寶不見了!」
魏謙:「什麼?」
他再也顧不得再爭辯什麼項目是肥肉還是瘦肉,再也顧不得這是一場豪賭還是精心設計的角逐,窗外沒完沒了的鵝毛大雪轟然落下,魏謙亂鬨哄的腦子裡只剩下一個問題——
這大冷的天,小寶能跑哪裡去?她有錢嗎?衣服穿夠了嗎?她吃什麼?喝什麼?
魏謙沒了魂一樣從老熊辦公室衝出來的時候,正好迎面撞上了來給老熊送飯的熊嫂子,熊嫂子莫名其妙地看著他趕投胎般的步伐,不明所以地問:「他家裡著火啦?」
老熊伸手從飯盒裡捏出一個餃子,將什��叫做「慢性子」演繹得淋漓盡致,不慌不忙地嚼完了嚥下去才回答:「沒有,小女孩離家出走了。」
熊嫂子聽了,睜大了杏核眼,抬起巴掌給老熊來了個烏雲罩頂:「那你還吃什麼吃?作死啊?趕緊找人幫著找啊!」
老熊險些被這天打雷劈一樣火爆的攻擊噎死,萎頓在桌子上,死命地捶了半天胸口。
他覷著夫人的臉色,只好謹遵聖旨,委委屈屈地空著肚子,跟在自己風風火火的熊嫂子鞍前馬後,幫著一起尋找離家出走的青少年去了——他和小寶有幾面之緣,知道那小姑娘是個怎麼樣缺心少肺的人物,壓根不認為她能走遠。
誰年少輕狂的時候還沒離家出走過?錢花完了自然就回來了,著什麼急嘛。
魏之遠得到消息,臨時請了半天假回來,回家掰開了小寶的存錢罐,往裡看了一眼就斷言說:「她帶走了二百多塊錢。」
宋老太:「她哪來那麼多錢?」
魏之遠看了她一眼:「……跟我要的。」
宋老太病急亂投醫,本能地逮著誰埋怨誰,一拍大腿,幾乎帶出了哭腔:「她跟你要你就給啊?你慣著她這毛病幹什麼?這不是疼她,這是害她呀!」
「行了!你別跟著添亂了。」魏謙從小寶屋裡走出來,喝住了宋老太,摸出電話對那一頭的三胖說,「她應該是穿著一件白色的羽絨服,背著個包……啊?包是什麼樣的?包……」
他說到這皺皺眉,太陽穴越夾越緊,頭越來越疼,魏謙用力地掐了掐自己的眉心。
魏之遠在旁邊輕輕地提了他一句:「橙色雙肩包,拉鎖上掛了一隻米老鼠頭。」
魏謙迅速重複了一遍他的話,然後掛上電話:「我再出去找一圈。」
宋老太立刻跳起來:「我也去!」
魏謙沒理她,已經甩上了大門走了。
魏之遠連忙披上外衣,對宋老太說:「你別跟著去了,外面那麼大雪,滑一跤摔一下,到時候更亂,我去看看。」
宋老太果然就聽了他的話。
這是第二次,她已經習慣了——所有人都蔫了急了的時候,魏之遠異乎尋常地保持著他慣常的冷靜,宋老太始終不知道他這是有點慢性子,還是只是天生冷血,朝夕相處也處不出多深的感情來。
她不知道什麼才能觸動魏之遠,這麼看來,好像什麼也不會,他就是隨時知道該做什麼。
雪碰到人臉就化,大雪中穿梭的人們很快被淋得頭面盡濕,魏之遠追上魏謙的時候,感覺他的兩腮似乎有些不正常地泛紅。
魏之遠匆匆趕上去,對他說:「她被子整齊,我估計不大可能是走之前特意疊好的,應該是昨天晚上就沒睡,半夜直接走的。昨天晚上零下十來度,出來滴水成冰,她不可能在外面閒逛,最可能是叫了輛車,找地方住下了……哥,你是不是病了?」
魏謙搖搖頭:「她能住哪?」
魏之遠眉頭一皺,思考了幾秒,條理清晰地說:「小寶膽子不大,深更半夜到陌生的地方去的可能性很小,昨天已經那麼晚了,她也不可能往同學家裡跑。學校附近……學校附近應該也不可能,她剛因為成績的事跟你吵過架,應該不想去學校,要不我們去她排練的地方附近找找看?」
魏謙站住了,頭疼欲裂。
他張了張嘴,想問小寶排練的地方在哪,卻死活說不出口。
魏謙有些茫然地想,他把他的小姑娘忽視的多麼厲害啊,連她喜歡玩什麼,喜歡和誰在一起,喜歡在什麼地方做什麼都一無所知。
他一天到晚究竟都在幹什麼呢?
「我知道地方,」魏之遠察言觀色,立刻明白了他在想什麼,趕緊補充說,「在市中心的少兒活動中心的舞蹈教室裡,我帶你過去。」
大雪天連車都不好打,好不容易等到了一輛,兩個人趕緊給攔了下來。
誰知半路又不知怎麼回事,前面堵成了露天停車場,怎麼也開不過去。
魏謙回頭問:「還有多遠?」
魏之遠說:「一站地左右。」
魏謙直接付了車前,在冰天雪地裡一路狂奔。
魏之遠連忙跟上,他還是覺得魏謙的臉色不大正常,追上去解下圍巾,掛在魏謙的脖子上。
兩人在大雪中不知走了多久,暴露的皮膚凍得近乎麻木。
而後他們看到了堵車的源頭,路口似乎出了車禍,周圍好幾輛警車,已經圍了一大幫人。
魏謙正想撥開人群走過去,突然,路人的隻言片語鑽進了他的耳朵。
「小姑娘還不大呢。」有人說,「作孽,這麼大雪,怎麼不慢點開車?」
魏謙當即頭皮一炸,一股惡毒的涼意爬上了他的脊樑骨。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開口問的,反應過來時,已經聽見了自己那如同從別人嘴裡發出來的聲音。
「……什麼小姑娘?」
「剛剛路口撞了一個小女孩,也就十六七歲吧,那血流得……哎喲,我估計人是夠嗆了。」
又有一個人回過頭來,比比劃劃地對他描述著:「可不麼,這邊紅綠燈壞了好幾天了,也沒個人修,又下這麼大雪,剛才我就眼睜睜地看著一個穿白衣服的小女孩……」
後面的話,魏謙已經聽不清了,他覺得有人在他的胸口上打了一錘,撐著他的胸骨碎了,五臟六腑幾乎給絞成了渣。
一陣天旋地轉。
作者有話要說:
註:過橋,長短期貸款互換
第三十九章
然而縱然五內俱焚,魏謙也就只是不易察覺地晃了一下,幅度之小,甚至除了魏之遠沒有人注意到。
魏之遠一把攥住他的手,感覺到他的手滾燙,他心裡一驚:「哥,你……」
魏謙充耳不聞,甩開了他的手,大步往人群裡走去。
就算地上等著他的真是一具撞得亂七八糟的屍體,他也得親眼看清楚了。
魏之遠剛要抬腳追上去,突然聽見遠處有人叫了他一聲:「謙兒!小遠!」
魏之遠回頭一看,只見老熊的車就停在不遠處,人太多,他們過不來,車門開著,熊嫂子正打著傘站在那又蹦又跳地喊人,而她旁邊的,是頭也不敢抬的宋小寶。
對啊——魏之遠舒了口氣,他發現自己其實也把這茬忘了——哪個民間高手乍一見宋小寶,能火眼金睛地看出她的真實年齡其實都已經十六了呢?
魏之遠緊走兩步扯住魏謙的胳膊,硬把他從人群裡拽了出來,扳過他的肩膀轉了個身:「哥,別急了,小寶找著了,在那呢。」
魏謙順著他的手指看了一眼,片刻後,他繃緊如弓的身體驟然鬆懈了下來,魏謙情不自禁地往旁邊踉蹌了半步。
而後他自己站穩了,面無表情,既看不出喜色,也看不出怒色,只是後知後覺地發現自己渾身上下,連冷汗再雪水,都已經濕透了。
他結結實實地打了個寒戰。
熊嫂子是個咋咋呼呼的熱心腸,一聽說就發動了很多朋友幫忙留意,也巧了,她一個閨蜜正好業餘時間在少年活動中心當合唱團輔導老師,小寶那一身衣服穿得鮮亮非常,那位老師剛好看見了有印象,老熊兩口子這才開車過來碰碰運氣。
其實宋小寶這個同學從小就慫,骨子裡就是個漢奸叛徒的好苗子,難得熱血上了頭,能幹出一檔子這樣的壯舉。
然而威武雄壯在她的生命裡始終如曇花一現的,被冷風一吹,她熱血涼了,立刻就後悔了,小寶當時第一反應,就是趁夜偷偷跑回家,假裝這件事沒有發生過,結果一摸兜,發現出來得太急,又忘帶鑰匙了。
鑰匙這個俏皮的小玩意,簡直生來就是專門來克她的。
可以想像,這時候回家一敲門,把大家都敲醒,她意圖離家出走的行為肯定也就暴露了,到時候大哥一定會活剝了她的皮,恐怕連奶奶也救不了她的小命了。
一想到那樣血腥暴力的場景,宋小寶連肝都顫悠了起來,末了,她只好把心一橫,像被逼上梁山一樣,硬著頭皮繼續她的離家出走大業。
她跑到少年活動中心附近的一個小旅館,想湊合住一宿,誰知隔壁是一對意志堅定、冒著嚴寒來開房的野鴛鴦,嚴酷的自然環境絲毫沒有影響人家為人類千秋萬代繁衍而戰的決心,床板嘎吱了一宿。小旅館隔音不好,小寶足足一宿沒睡著。
在這樣一種惡劣的環境裡,宋小寶記吃不記打的天性冒了出來,她那滿腔六月飛雪般堪比竇娥的委屈在隔壁的叫床聲裡蕩然無存,開始擔驚受怕起來。
老熊他們找到她的時候,小寶正繞著少兒活動中心後面的體育場一籌莫展地來回走圈。
老熊得意洋洋地指著她對老婆說:「你看,我說丟不了吧?」
魏謙過去的時候,已經問明白原委的熊嫂子正在訓小寶:「你這小丫頭,膽子怎麼這麼大呀?因為這麼一點小事就往外跑,萬一遇到壞人怎麼辦?錢不夠花怎麼辦?出點意外怎麼辦?坑死你哥啊?」
小寶摳著自己的手指,見到魏謙走過來,緊張地抬頭看了他一眼,又迅速地低下頭做懺悔狀,十指橡皮泥似的稀裡嘩啦地攪在了一起。
老熊不知從哪抽出了一條毛巾給這狼狽的兄弟倆:「嘿,這倆落湯雞,快擦擦。」
熊嫂子見到魏謙,本著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則,也沒繞過他:「你,有你這麼當哥哥的嗎?剪小妹妹的頭髮,你怎麼不拿把刀往她臉上劃一下?我們跳舞的怎麼了?跳舞的低人一等啊?世界的美好都是靠我們這些不、務、正、業的人呈現的,你就狹隘吧你,年輕輕的就這樣,等你老了,不定變成個多討人嫌的老頑固呢。」
老熊忍無可忍地拉了她一把:「你快行了吧,哪都有你,怎麼那麼有演講欲呢?你那話省著點說,等我哪天出息了,讓你上聯合國大會上講去,行了吧?」
魏謙卻不知是無話可說還是說不出來,沒有應聲,只是有點僵硬地挑起嘴角,沖熊嫂子笑了一下,輕聲說:「謝謝嫂子。」
原本還想針對發言權問題鎮壓老熊三百回合的熊嫂子,莫名地被他這麼一笑弄得說不出話來了,只好訕訕地閉了嘴。
一路上,魏謙一聲沒吭,小寶覷著他難看的臉色,心裡越發忐忑。
老熊通知了三胖和其他人,一直開車把他們送回家後才告辭了。
結果小寶一推門進去,就遭到了宋老太的爆發。
頭天晚上宋老太怕魏謙打她,還在使用各種小手段維護她,今天,她卻擼胳膊挽袖子地自己上了。
老太太接到「人找到了」的通知,懸著的心咣當一下落了地,連忙念了幾句菩薩保佑。
謝完了菩薩,她就拿著掃帚站在了門口,做好了女子單打的準備,在小寶第一聲「奶奶」出口之後,宋老太就掄圓了掃帚桿,劈頭蓋臉、打蒼蠅一樣地揍了她一頓。
宋老太但凡想幹點什麼,必須得雞飛狗跳,得有足夠的場地任其發揮才行。
魏之遠和魏謙自覺遠離戰圈,貼著牆站住了。
魏之遠還正奇怪大哥為什麼不攔著,突然,他肩上一重,魏謙一隻手壓在了上面。
「扶我一把。」魏謙的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他眼皮好像要被黏在一起,費力地睜開一條縫隙,卻基本看不見東西。額角的冷汗順著鼻樑不停地往下流,連口氣都喘不上來。
魏之遠還沒來得及伸出手,魏謙的膝蓋就軟了,他整個人晃了晃,一頭栽了下去。
魏之遠一抄手把他撈了起來,透過厚厚的冬裝都能感覺到他身上好像燒了火炭一樣的熱度。
宋老太一愣,連忙扔下掃帚,大呼小叫地跑過來:「這是怎麼了?這是怎麼了?」
魏之遠伸手在魏謙額頭上試了一下,好,都能煮雞蛋了,立刻彎下腰背起已經毫無知覺的魏謙:「發燒了,奶奶,你把溫度計和常備藥找來。」
宋老太應了一聲,回頭看見小寶還手足無措地站在那裡,頓時又氣不打一處來:「看什麼看?還不都怪你!都是你氣的。」
魏之遠噓了她一聲:「別吵。」
宋老太莫名地順從了他的指示,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她就已經開始像當年信服魏謙一樣信服這個半大小子了。
魏之遠把魏謙背到了他的臥室裡,把小寶和奶奶支使得團團轉,又剝下魏謙身上帶著潮氣的外衣,倒好熱水餵他吃藥。
這時,魏謙就已經從短暫的昏迷中醒了過來。
他先推了魏之遠一把:「可能是感冒,你離我遠點,傳染給你。」
魏之遠被推開了,然後又原封不動地湊了過來。
這少年也不和他爭辯,只是盯著他吃完藥,然後在他身上又加了一層被子,仔細地壓住了被子角。
這時,有人小心翼翼地在外面敲了敲門,一聽就知道是小寶——宋老太學不會敲門,她通常都是用砸的。
魏之遠用眼神請示了魏謙一下,魏謙則一聲不吭地把臉轉到一邊,同時閉上眼睛,似乎光速睡著了,魏之遠笑了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小寶站在門口看著來應門的魏之遠,此時兩個人的身高差距已經到了讓人髮指的地步,如果站得很近,小寶就必須要仰脖子才能看到魏之遠的臉,她就像一朵被陽光曬蔫了的向日葵,仰著頭看著魏之遠,一抽一抽地仍在嗚咽。
魏之遠伸出一根食指豎在自己嘴邊:「吃了藥睡了,明天再說吧。」
小寶透過朦朧的淚眼,覺得他眼睛裡有某種很莫測的東西,以她的智商和閱歷分辨不出那是什麼,也無計可施,只好順從地點點頭,一步三回頭地走了。
魏之遠打發了她,又關上門,搬了把椅子,拿了本書,坐在床邊守著魏謙。
過了一會,藥裡的安眠成分發揮了作用,魏謙真的睡著了。
魏之遠手上翻開的書沒有往下走一頁,他乾脆把書丟在一邊,十指撐在一起,肆無忌憚地盯著魏謙看。
在這樣異常的靜謐和寧靜裡,他突然發現自己理解了大哥在家裡的沉默。
本性上,魏謙絕不是那種特別安靜內向的性格,否則早就讓三胖那個碎嘴子給煩死了,不可能會跟他混到一起,魏謙的話其實不少,脾氣上來了嘴還挺毒,只是他對家人在言辭上有些格外吝嗇。
他在家從不傾訴,甚至不怎麼交流,似乎有人在他耳邊說話都能讓他覺得聒噪。
為什麼呢?
魏之遠看著魏謙逐漸被厚重的被子捂出了一點細汗的臉,忍不住伸手把他額前汗濕的一縷頭髮撥開——少年就想通了,因為那是大哥獨特的逃避和軟弱的方式。
魏之遠用眼神描摹著魏謙的輪廓,心裡想著,這個人再年幼一點、再弱一點、再沒有辦法一點的時候,背著一個家,雖然嘴上一聲不吭,但他心裡真的會毫無怨憤嗎?
他真的能始終一片坦然,始終無怨無悔嗎?
怎麼可能?他又不是石頭。
這個男人,他一生所渴求的,全都傷他至深。
而他一生所憎惡的,全都令他魂牽夢縈。
他簡直就像石縫裡億萬年間擠壓而生的一小撮樹芽,搖搖欲墜,形容扭曲,但鬱鬱蔥蔥。
魏之遠知道自己在人格上是不大健全的,他缺乏同情的能力,這種缺失並不是成人式的、被磨礪出的冷酷,而是他大多數時候不知道該怎麼同情。
每當小寶和宋老太對著苦情劇哭得死去活來的時候,他都覺得無法理解。
這與年齡無關,與智力也無關——很小的孩子都會被週遭成人的情緒影響,而即使是小狗也會用動物的方式對哭泣的陌生人表達安慰。
魏之遠發現自己很難同感到別人的情緒,更加難以和人建立感情聯繫,大多數時候,他都是為了融入環境而採用某種程度上合群的偽裝。
唯有大哥不一樣。
魏之遠揣摩著魏謙心裡的感受,就像是個撬開神殿頂部偷窺的孩子,感受到了那種珍貴的感情聯繫。
關於一個……他年幼時奉如神明的人的,所有真實的喜怒哀樂,強悍和懦弱。
像一片透明的靈魂橫陳在他面前,魏之遠甚至覺得自己的心都要化了。
第二天魏謙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竟然是躺在魏之遠懷裡的。
大概是他昏睡中無意識的企圖踢被子,魏之遠乾脆把他連被子一起抱住了。
這本來沒什麼,他們從小就一起住,可是睜眼的一瞬間,魏謙還是莫名地覺得有點彆扭。
魏之遠存在感太強了。
他佔了一半的床,頃刻就把寬敞的空間給弄得逼仄了,手腳都纏在自己身上,魏謙覺得自己是太多心了,可他就是有種動物那樣……自己的地盤被入侵的危機感。
清早再一量體溫,魏謙就已經從高燒轉成低燒了。
宋老太壓著小寶進來道歉,小寶大概又是一宿沒睡好,兩隻眼睛紅得小兔子一樣,眼巴巴地看著魏謙,詞不達意地表述了自己的罪孽深重。
魏謙也不再提剪頭髮和退舞蹈隊的事,這件事就這麼稀裡糊塗地被揭過了。
在至親面前,原則、底線的條條框框都是紙糊的,風一吹就爛成了渣,末了算來,好像也只剩下稀裡糊塗與得過且過。
中午的時候,熊嫂子無事不登三寶殿地來了,她看中了小寶的資質,想自己帶回去教。
魏謙也沒有阻止,打起精神應付了熊嫂子兩句,道了謝,對宋小寶徹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魏之遠冷眼旁觀,心裡忍不住想:有那麼一天,你對我也會這樣毫無底線地一再容忍嗎?
下午,魏謙讓魏之遠該上課上課去,結果這小子給他低眉順目,一句一稱「是」,就是有本事同時陽奉陰違,無視他的意見。
魏謙咳嗽兩聲:「你聽見沒有!」
「嗯,知道了——哎,哥,給你看這個。」魏之遠就像個聽不懂人話的弱智兒童一樣,聽見了,忽略了,而後他獻寶似的拿出自己專用的筆記本電腦,打開裡面一個小遊戲,「這是我最近交的一份作業,不完全是原創,借鑑了一點『推箱子』那個遊戲改良的,給你解悶玩。」
魏謙沒好氣地說:「推你個頭。」
半個小時以後,他就趴在床上玩起了這個「推個頭」的弱智小遊戲。
魏之遠在他的臥室裡踏踏實實地寫作業,偶爾會過來煩他一下,比如逼著他把水喝了,逼著他把掀下來的第二層被子重新蓋上去。
魏謙前所未有地感覺到了「這小子竟然不知不覺間已經這麼大了的」事實,有點不適應,但這點不適應很快被魏之遠的小遊戲吸引走了。
遊戲設計得很好,開頭很循序漸進,一點一點地讓人積累成就感,先開始每個關卡只有一個扣,解開就能過,中後期每一關開始有七八個扣,挑戰感和成就感的積累一步一步地引著人上癮。
到了後期,魏謙發現自己的小人基本已經被困在一個蜘蛛網一樣眼花繚亂的大陣中間了。
魏謙卡在最後一關上,死也打不過去,他失敗了無數次後,開始懷疑是程式有問題,根本就走不出來。
兄弟倆就像兩個小孩一樣,爭論了一陣究竟是某玩家太笨還是遊戲本身設計有問題。
最後,魏之遠擠在他旁邊,一步一步地為他展示了這喪心病狂的一關是怎麼做到十八連環扣的,然後他有點得意地看著魏謙,小孔雀似的顯擺說:「我聰明吧?」
「切,逗小孩玩的玩意。」魏謙說著把電腦推遠,以示撇清關係……好像剛才抱著不撒手的那個人不是他一樣。
魏謙在床上點了根煙,他的燒退了,身上有些乏力,但人已經舒服多了,那顆暫且偃旗息鼓的工作狂之心開始忍不住地蠢蠢欲動。
他雖然嘴硬,卻真的從魏之遠的小遊戲裡受到了某種啟發,隱約抓到了一點怎麼拿下那個項目立項的思路。
魏謙思考得太入神,幾乎燒著了自己的床單,幸好被魏之遠眼疾手快地奪了下來。
魏之遠像個醫學權威一樣站在旁邊,頗有威嚴地說:「哥,你該休息了。」
魏謙瞠目結舌地想:「我被這小子管制了嗎?反了他了!」
魏之遠果然是要揭竿起義,強行關了他的床頭燈,然後利用體重和蠻力把病病歪歪的大哥按回被子裡,像個監工一樣坐好,等著監督他休息。
魏謙由於太過震驚,竟然沒想起來反抗。
不知多久,魏之遠才聽見魏謙忽然問:「頭天晚上,你怎麼知道小寶要去哪?」
魏之遠正調試著程式,頭也不抬地抬頭說:「猜的——真心誠意地想離家出走的人哪會跟她一樣什麼鮮亮穿什麼?肯定生怕被人中途抓回去,恨不得往臉上抹二斤泥。」
直到這時,魏謙才恍然想起來,這看似和普通青少年一樣上課寫作業的大男孩年幼時,有過那樣如同苦兒流浪記般的經歷,他突然覺得有點心疼。
然而魏謙不知該如何表達,他踟躕了半晌,才用一種「要麼哥給你買根冰棍吃」這樣的語氣問魏之遠:「哎,小子,學習這麼好,將來想出國嗎?我可以先給你攢……」
他一句話沒說完,魏之遠突然抬起頭來,被顯示屏映得發青的臉色難看極了,好像聽見了什麼可怕的話。
過了好一會,魏之遠自己也意識到自己反應過度了,這才匆匆垂下眼,掩飾著什麼一樣地低聲說:「不想,你早點休息吧,別說話了。」
魏謙只休息了這一天,第二天,他就照常爬了起來,訂好了去項目所在地的火車票,玩命似的去工作了。
老熊點了三胖跟著他,老熊認為,三胖這人,內心和外表一樣圓潤,比魏謙穩當。
魏謙跟個肺癆病人一樣帶著口罩,在車上咳得死去活來,三胖只好任勞任怨地照顧他,順便嘴貧口賤地嘮叨幾句:「你三哥我這個監軍當的啊,真是窩囊,就是個小太監,伺候大爺來的。」
魏謙:「嗯,挺合適的,監軍多太監。」
「你媽!」三胖惆悵地捶了魏謙一下,想起身後背負的三千萬,真是跳松花江的心都有,一籌莫展地哼哼起來,「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
魏謙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三胖愁苦地問:「爹爹,真不行,你是打算賣了喜兒我還債嗎?」
「不會。」魏謙說。
三胖老懷甚慰。
魏謙補充:「閨女你太醜了,我怕黃世仁看見你嚇尿了褲子。」
三胖長嘆了口氣:「你說你是有病嗎小同志,你現在有房有事業,大學畢業證也快到手,他媽的春風得意啊!你作什麼死啊你?說真的,咱倆下站下車,賣回程票,現在打道回府還來得及。」
魏謙翻著項目材料,像是要把每個標點符號都印在腦子裡:「我能拿下來。」
三胖搖頭嘆息:「你就是一塊茅房裡的石頭啊,又臭又硬!」
他一雙蒲扇一樣的胖手不安地搓著膝蓋,好一會,才破釜沉舟一般地一拍大腿:「行吧,你三哥上輩子欠了你的,你說吧,怎麼辦。」
第四十章
魏謙和三胖到了目的地,老熊已經提前打好了招呼,上回給他們介紹項目的朋友舉著個鞋盒子上裁下來的硬紙板牌子,在車站迎著他們。
老熊這個朋友原名李狗蛋,長大後自己改成了李風雅,是個農民出身的企業家,早年當包工頭帶建築隊發家,是老熊倒騰茶葉的過程中認識的。
李風雅的副業是全國各地四處倒騰土特產,主營業務則有倆,一方面搞建築,一方面搞拆遷,連拆再蓋,一條龍服務,包了。
然而他賺的依然大抵是辛苦錢,早就瞅著投資開發的那些人眼紅了,只可惜手頭弄不來那麼多錢,才想著拉人入夥。
可惜上回老熊來看了一眼,似乎並沒有表現出很大的興趣,李風雅本來以為這事黃了,沒想到還有轉機,因此接人接得歡欣鼓舞。
李風雅有四十來歲,其貌不揚,長得又黑又瘦,雙眼內凹,身高不足一米七,腰圍不足二尺一,乍一看,像一塊黑乎乎的牛肉乾。
寒冬臘月裡,他也不嫌冷,外套拎在手上,身上穿著件名牌襯衫,袖子捲著,也不知道多長時間沒洗了,揉搓得像一塊鹹菜幹,前擺塞在了褲腰裡面,後擺露在了褲腰以外,走路時隨著他歡快的步伐活蹦亂跳的起伏,活像穿了個屁簾子。
雖說是人靠衣裝馬靠鞍,可世上就是有那麼一種人,即使身披金縷玉衣,別人也只會以為他把家裡竹片子涼蓆抱出來捆身上了。
魏謙已經見過一面,因此見怪不怪,三胖卻沒見過這麼富貴的窮酸,大吃一驚,偷偷跟魏謙咬耳朵:「喲,這位大兄弟是從哪個煤窯裡爬出來的?」
魏謙說:「黃世仁一號坑。」
三胖恨不得縫上自己的嘴。
有客遠來,按規矩,李風雅自然是要招待一番,到了飯桌上酒過三巡,互相「青年才俊」「老謀深算」之類臭不要臉地吹捧一番,李風雅才開始說正題:「上回是我想得太簡單了,眼下除了咱們,還有好幾家都盯著這塊地,聽說有一家還請了個外國設計師來規劃,狗長犄角裝洋啊,弄得挺是那麼回事的。」
三胖忙問:「我們都是外地人,不懂裡面水有多深,那您覺著這事靠譜嗎?」
李風雅砸吧了一口小酒,搖晃著腦袋嘆了口氣:「難說。」
「怎麼?」
李風雅壓低了聲音,用筷子沾著酒在桌子上劃了一道,伸長了脖子,壓低了聲音說:「因為我一直惦記這事,所以也活動了不少關係,不瞞你們倆小兄弟,國土局和市政府那邊,我都說得上話——當然,也別以為老哥我有多了不起哈,我說得上話別人當然也說得上話,沒點人路,誰也不敢打這事的主意對吧——國土局那周主任,以前是我們老鄉,前兩天剛跟他一塊喝完酒,也聊了聊,哎呀,這個事,現在真不好說啊……你們知道那幾塊地中���的商業街是吧?」
見兩個人點頭,李風雅繼續說:「那是咱們當地一個公司投資搞的,他們老闆姓張,這個張總是咱們書記的表弟,現在是這樣的,一條商業街建得紅紅火火,但是我們張總不知道哪根筋搭不對了,只租不賣,說是要保證檔次,不能讓這條商業街變成小商品批發市場,現在檔次有了,資金鏈『啪嘰』斷了,上億的項目砸進去,貸款都到期了,要不然周圍那幾塊住宅地能便宜咱們?不可能的,就是現在,各家都流著哈喇子等著,前提也是盼著姓張的弄不來錢,大家才能吃吃人家牙縫裡漏出來的,萬一張總想開了,『咣』把商業街一賣,或者弄到了新的資金,咱們都白扯。」
三胖:「他幹嘛不賣?」
李風雅一拍大腿:「想不開嘛!」
三胖:「沒錢了他可以找人合作啊,背景這麼硬,難道沒人借錢給他?多少借來點,再找個人合夥出資,不是齊活了嗎?」
李風雅比比劃劃地說:「不,胖兄弟,你沒明白,說好聽點,是他一時回不來款,難聽點就是他的現金鏈已經崩斷了,『嘎嘣』一下,斷啦,死翹翹啦!你明白了吧?」
李風雅極愛用擬聲詞,好像這樣能增加他的詞彙量似的,「嘎嘣」倆字,噴了三胖一臉唾沫星子。
三胖抹了一把臉,從他沉重的唾沫星子裡感受到,拿下這件事的艱難困苦。
「再有背景他也是個民營,民營最怕什麼?沒錢啊我的胖兄弟!」
李風雅說完,伸手抓起桌上的一個大肘子,三口啃了,吃完一抹嘴:「跟你們直說了,咱們張總那人吧,有點酸,我見過一面,哎喲我的老娘,那眉頭一皺高高在上的模樣,我看他像是剛從南天門出差回來——人家看不上我們這些土財主,不然我用得著千里迢迢地找上你們嗎?」
直到這時,魏謙才開口問:「李哥,照你的意思,他除了賣了手裡這條商業街,沒別的辦法了?」
李風雅琢磨了片刻:「也不一定,真開土動工,他沒準吃力,但要是肯借個殼子,找人替他出面包裝出個新項目公司,以項目公司的名義再立項融資拿下這塊地,然後直接溢價脫手也不是不可能,還能回流一大筆現金,就是時間長點,而且吧……這事要是放我頭上,我幹也就幹了,張總那人我不是跟你們說了嗎?這種桌子底下的事,他老人家不一定樂意做。」
魏謙垂下眼想了想,最後跟李風雅商量了片刻,一行人決定第二天去走訪一遍商業街,到附近踩個點。
晚上回到旅館,魏謙就著半涼不熱的水,洗了個澡把酒醒了,頭髮都沒擦乾淨,他就把自己之前的策劃書找出來,撕了。
三胖冷眼旁觀,直說風涼話:「跟你預期有出入吧?傻眼了吧?沒轍了吧?要我說,咱還是收拾收拾東西,明兒買車票回去吧……你聽聽你那咳嗽的,喘氣都有雜音,兩片肺氣門芯都掉了,直漏氣。」
魏謙瞥了他一眼,懷疑老熊讓三胖跟著來根本就是不懷好意。
三胖完美地扮演者豬八戒的角色,逮著機會就提議分行李回高老莊,實在是動搖軍心的不二利器。
老熊那個外表憨厚內心猴精的貨,說不定上次來就知道了,就是想讓他知難而退。
三胖接著說:「謙兒,我看這事壓根沒戲,人家老李一個地頭蛇都淌出水深了,你還想怎麼樣?難不成要派你三哥我去色誘政府官員?我可告訴你啊,士可殺,不可辱。」
魏謙好容易止住了咳嗽,痛苦地看了三胖一眼:「三哥……咳咳,算我求你了,要點臉吧!」
「別誣陷我,我的節操和肥膘一樣永垂不朽,」三胖站起來扭了扭腰,「得,您老人家慢慢琢磨,我覺得晚上吃那烤雞不錯,在咱們班師回朝之前,我決定多批發幾隻,回去給孩兒們嘗嘗鮮。」
魏謙打開李風雅走後門給他弄來的一張規劃圖,鋪在床上,低啞地說:「要回你自己回,我反正不走。」
三胖一屁股坐在床沿上:「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啊!」
魏謙氣定神閒地說:「見了棺材我也不落淚,落淚有什麼用?沒事,我有第二計劃。」
三胖眼睛一亮:「你還挺神,早料到……」
魏謙:「現想的。」
三胖沉默地打量了他一會:「謙兒,我怎麼就弄不明白了——上火車前你是這樣,火車上你是這樣,到了地方瞭解了情況你還是這樣——你那底氣都是從哪來的?你憑什麼就認為你肯定能拿下來呢?」
魏謙抬起頭,因為病和休息不好,他的眼睛裡略有血絲,而眼神是沉的,儘管經年日久地沾著一點含而不露的陰鬱,核心卻又是堅定而心無旁騖的。
「攘外必先安內。」魏謙說,「我精力有限,決定了做的事,如果再反覆懷疑反覆猶疑,那我一天到晚真是什麼都不用幹了。我也不知道我憑什麼,但我已經決定做了,在這個前提下,我就不想別的。」
三胖隨之嚴肅下來,問他:「那如果你失敗呢?」
魏謙平靜地搖搖頭:「我不考慮這個。」
三胖急了:「你怎麼能不考慮這個呢?你這不是瞎搞嗎?來之前你考慮過這個張總嗎?總有你想不到的事,你什麼都不想,不覺得自己太輕率了嗎?」
魏謙衝他笑了一下:「暫時的失敗不是失敗,只是意外,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就算有意外,我需要考慮的也是怎麼彌補損失和利用意外帶來的機會,沒別的。」
三胖算是服了他這詭異的、近乎邪教信仰般的精神境界,認命地暫時揮別了他親愛的小烤雞,去了另一張床上躺屍。
魏謙他們已經走了好幾天,魏之遠終於放假了——那意味著春節到了。
這個春節大哥不在,全家人都過得沒滋沒味。
只有新年鐘聲響起來的時候,魏謙的一個電話才打回了家,可是四下都是炸碉堡一樣的炮竹聲,魏之遠連他說的什麼時候回家的消息都沒能聽清楚。
少年掛了電話,開始正式思考起他註定坎坷的情路。
魏之遠知道,他的感情太驚世駭俗,沒有人能乍一聽說就坦然接受的……何況還是大哥那樣的人。
魏之遠其實考慮過,如果他透出一點傾向來,大哥會不會礙著他的感受,多少捏著鼻子瞭解一些,容忍一些呢,繼而慢慢習慣呢?
那將是一個漫長的拉鋸過程,而且魏之遠沒有自己會成功的信心。
少年心事面前,人總會不由自主地多愁善感、踟躕不前,何況這場註定了暗無天日的暗戀。
魏之遠在這方面難得不自信,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大哥會不會像對待小寶一樣對待他,肯為他一再退讓,乃至於底線全無。
如果他乾脆認為自己瘋了呢?
如果他覺得這噁心得超出了他可接受、可退讓的範圍呢?
一聲巨響,巨大的煙火在空中爆開,樓下的私家車給嚇的嘰喳亂叫,魏之遠的耳朵被震得有些耳鳴,他情不自禁地偏了偏頭,否決了這個想法。
他無法接受魏謙對他形同陌路,一想起這個,他那種源自幼年的、時刻擔心被��棄的恐懼感就會再一次把他淹沒在裡面。
他必須要穩妥、平和、有效。
魏之遠不知道自己還有多長時間,他認為自己首先需要營造一個潛移默化的環境,就像蜘蛛織網一樣,得先有個大框架,而後循序漸進。
除此之外,他認為自己還需要一個隊友。
魏之遠把目光移到已經靠在沙發上睡了不知多少覺的宋老太身上,片刻後跳過了她——她比大哥更難說服,說不定跟她解釋明白整件事就很痛苦。
最後,魏之遠的目光落在了小寶身上。
怎麼……不動聲色地,想辦法讓她想辦法站在自己這邊?
魏謙這一走,連最後一個學期的開學報到都沒趕上,是魏之遠拿著他的學生卡到學校,替他註冊完的。
這期間,魏之遠活像罹患了神經病一樣,在家裡羅滿了各種艱深難懂的書、資料和文藝作品。內容設計哲學心理學社會學乃至於一些獵奇的藝術等等。
宋老太不識字,看見大部頭的書就心懷敬畏,每次發現魏之遠帶著淺度的近視眼鏡翻書的時候,她連經過都會躡手躡腳。
小寶卻覺得她小哥哥有點不正常,在青少年堆裡,不做功課的業餘時間裡不踢球打鬧的青少年顯得都不怎麼正常,哪怕是傳閱閒書,傳得也都是武俠玄幻漫畫言情一類,沒有人會看這東西。
小寶覺得他太陰鬱了,正好新學期的語文課上選讀了臥軌詩人的作品,小寶看了以後心驚膽顫,越發覺得魏之遠有隨時想不開的先兆。
她先是跟奶奶說了,可奶奶不信她那套,認為她自己不學無術不讀書,所以也看不慣別人讀書。
宋小寶第一次期盼起大哥快點回來。
一直到了陽春三月,魏謙才回來。
正月底,當魏謙把幾分協議一字排開地擺在老熊面前的時候,老熊用表情充分說明瞭什麼叫做「驚呆了」。
當時魏謙從那商業街裡走過一圈,心裡立刻就有數了。
他開始緊鑼密鼓地考察,市場定位,同時也給李風雅出了個難題——讓他一定要去接觸一下張總。
這把李風雅愁的,他是真不願意和張總這樣高端洋氣的人打交道。
大過年的,頭髮都掉了一把,誰知此時,「老天爺」卻給了他一個機會。
張總的兒子正在念初中,當地民風比較彪悍,初中小男孩經常是一語不合就能在路邊抓撓著打起來,李風雅見到那小子時,他正被七八個小混混圍著。
李風雅發財不忘本,逢年過節願意和他的民工兄弟們混在一起喝酒吃肉,當時身邊有好幾條喝得微醺的漢子。但小混混打架,李風雅他們早看慣了,老李這把年紀,不再會路見不平一聲吼了,他原本視而不見地要徑直經過。
誰知就在這時,腦殘的受害人大聲自報身份:「我爸是大老闆,我表叔是當官的!弄死你們,信不信?」
魏謙整天給李風雅施壓,讓他去接洽張總,巨大的壓力幾乎把李風雅弄出神經衰弱來了,他原本就對張總唸唸不忘,一聽這話,本能地停下了腳步。
民工兄弟們跟著停了下來,伸長脖子看著。
老李思量了片刻,伸手一指:「大過年的,這都幹嘛?讓他們別打了!」
他一聲令下,儘管沒人動,幾個小混混見此陣容也先害怕了,互相看了一眼,打了個呼哨,跑了。
老李裝作和顏悅色地把「受害人」拉起來一問,真他媽是閉眼就有人給遞枕頭,這二頭巴腦的小子就是張總那寶貝兒子!
那龜兒子蹦起來拍拍屁股上的土,直眉楞眼地伸手一搭老李的肩膀,沒大沒小地說:「哥們兒,謝謝啊!以後你就是我大哥,有什麼事我罩著你!」
李風雅心說:「這小兔崽子肯定缺心眼。」
臉上哈哈一笑,豪情萬丈地說:「不算事,都是緣分!」
三胖得知後,對魏謙感慨說:「老李那孫子挺有兩下子啊!能來事還有運氣,福將。」
魏謙的聲音被他自己咳嗽得嘶啞極了,然而一點也沒有妨礙他高深莫測地對三胖冷笑,他說:「那幫打人的小崽子是我雇的。」
三胖:「……」
為防止他們出現顯得刻意,張總那頭,一直是老李在接觸。
而邪魔歪道的小手段只是輔料,真正打動了張總的是以老李的名義遞上去的一紙框架協議。
表面上這個協議是老李和張總雙方的,老李出資佔股25%,同時約定壟斷了上下游的工程,張總作為明面上的大股東,佔了剩下的股份,負責整個的項目操盤。
但張總沒錢啊,於是這裡引入了協力廠商的隱形股東,李風雅直到這時,才把魏謙他們介紹給張總,魏謙和張總之間簽訂了第二份協議,在整個項目的框架協議上和張總一方綁定,老熊作為不記名的實際股東,負責出錢,張總作為登記在冊的名義股東,全權負責整個項目包括拿地、走手續和銷售全部的操盤工作,末了享受15%的分紅權。
張總他們空手套白狼,玩了一回在當時極其前沿的「輕資產」概念,減輕了風險的同時,最吸引張總的,是他可以把周邊住宅和商業街弄成一個整體。
他之所以怎麼也不肯賣商業街,就是希望能弄出這麼一個地標性的、品牌的東西,張總是個個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者,他做夢都想在市中心挖出一塊地,弄出一片他自己的王國一樣的極具個人風格的建築,可惜過於精雕細琢,才導致之前的項目週期拉得太長,乃至於資金鏈崩斷。
交給他來操盤,在張總看來,比仗著關係擺弄個土地收點溢價,讓他熱血沸騰得多。
他和魏謙一拍即合,月底就拿下了用地協議,期間魏謙和三胖也沒閒著,借助著張總這根橋,把所有的關係門路用酒瓶子鋪了過去,平均一天兩到三頓的酒,每天晚上回賓館第一件事必然是吐個死去活來。
同時,跟著張總跑前期,盯規劃,半夜爬起來研究一摞一摞的法律條款,草擬各種協議,送交專業人士審閱,各種測算和現金計劃修改了一版又一版,列印出廢稿摞起來足有兩尺來厚。
跟著魏謙這個工作狂,三胖那聲稱和節操一樣永垂不朽的肥膘竟然一個月去了十斤,腰帶鬆了個扣眼。
老熊也沒想到,三千萬,竟然讓這倆孩子活生生地給啃下來了。
而魏謙原本是想一直跟到項目開始預售、資金大筆回流的時候,反正大四下半學期也沒課了,他交論文答辯的時候露個臉就夠了,不過沒想到最後還是出師未捷身先死了——死胖子一語成讖,他的肺真的漏氣了,咳嗽了一冬天,不負眾望地轉成了肺炎。
最後被老熊親自趕來給拎了回去,扔在家裡休養。
魏謙非洲難民一樣地回了家,被宋老太逮著了大呼小叫的機會,連著給吃了三天燉雞,弄得他看見砂鍋直噁心。
他這次回家,直覺魏之遠不對勁,然而乍一看又和以往一樣懂事用功,魏謙說不出是哪裡不對勁。
到了週末,魏之遠估摸著他的隱形同夥宋小寶要和大哥反應情況了,所以早早地如往常一樣出門去上額外的課,把發揮的機會留給小寶。
宋小寶果然不負所望,心裡憋不住話很久了,魏之遠一出門,她就偷偷跑過去跟魏謙說:「二哥可能是要得自閉症。」
「……」魏謙,「你還是看動畫片去吧。」
「真的!」宋小寶指天發誓,「不騙你!不信你去他屋裡看看!」
魏謙:「多大人了他還自閉症,不願意搭理你就是自閉啦?我也懶得搭理你。」
宋小寶和熊嫂子說好了,週末去她那學舞蹈,耽擱不了多長時間,眼見大哥一點也不把她的話當回事,她跳起來拖起魏謙,死乞白賴地推著他一路到了魏之遠屋門口,擰開門:「你自己看啊!不跟你說了,討厭!我走了。」
第四十一章
魏謙對魏之遠屋裡有什麼,真是一點興趣也沒有。
魏之遠那種越來越單薄的性格一度曾經讓他掛心,但他仍然認為,那小子已經這麼大了,一切都應該知道分寸。
在魏謙眼裡,小寶和小遠總是不一樣的。
宋小寶畢竟是女孩子,讓魏謙去理解她,實在是有些困難。她長得太顯小,性格也不見得有多大人,魏謙有時候其實也知道,她也勉強能算是大姑娘了,好歹是知道要臉要面了,就不能像小時候那樣沒遮沒攔地隨便說隨便罵,可卻總忍不住把她當成小孩看。
對魏之遠卻不存在這個問題。
魏謙看見他,偶爾會想起自己像他那麼大時的光景,很奇怪的,他只會覺得魏之遠「年輕」,卻越來越不會覺得他是個孩子了。
既然不是孩子,他也不想顯得很多嘴。
所以魏謙打發走了宋小寶,就從外面帶上了魏之遠的屋門,逕自走了。
晚上魏之遠回來驗收二貨少女宋小寶的豐功偉績,結果推門一看,就知道屋裡沒人來過。
他在屋裡留了幾個扣,用來判斷他不在的時候都發生了什麼事。再裡頭的就不說了,比較清晰明瞭的屋裡有倆——早晨他走的時候,書桌前的椅子是故意歪著放的,方椅子腿正好卡著一條地板縫,地板縫是他的參考刻度,如果有人要翻他的的書櫃,必須會把那把怎麼都礙事的椅子擺正或者挪開。
還有就是屋裡面那一側的門把手上被他貼了一層非常薄的塑膠膜,塑膠膜就像手機螢幕,平時會沾上人眼看不見的細小灰塵,所以手抓上去就會留下肉眼可見的清晰的指紋,有人進了他的屋再出來,當然要拉門把手,就會留下痕跡。
而椅子沒有移動過,內把手和他臨走時一樣乾淨。
只有門縫裡拴著的一根頭髮被拉扯斷了,如果門是被輕輕推開的,頭髮會掉下來,直接崩斷,代表有人蠻力推開過他的門,不大可能是大哥,多半是宋小寶那個冒失鬼幹的。
而大哥……他大概是掃了一眼,趕走了小寶,又把門給他帶上了。
至此,早晨發生了什麼事,居然愣是讓魏之遠猜了個八九不離十。
魏之遠的心情瞬間就變得很複雜——他不是什麼掏心挖肺的人,從某種層面上來說,甚至是有點獨的,與人交往大多是面子活,真心實意的時候少。
儘管他有刻意引導的成分在,可畢竟是感情上白紙一張的少年人,當他把自己的一部分展示給大哥看的時候,始終是不可避免的心懷惴惴,羞赧乃至於有些憂慮的。
可魏謙竟然不看!
大哥的好奇心是都被狗叼走了嗎?
魏之遠有種深深的感情被浪費的感覺,無處著力同時,他也不免有些心情微妙。
如果是小寶變得很不對勁,大哥也會在打開的門口止步嗎?當然,小寶是女孩,肯定不大方便,可如果……她是個男的呢?
魏之遠緩緩地擺正了自己的椅子,在書桌前坐下。
魏之遠和小寶兩個人,一個省心一個不省心,大哥於情於理肯定是要多看著那個不省心的一點,而這會讓兩個人都不舒服,小寶認為哥什麼事都針對她,整天找她麻煩,一點也不自由,而魏之遠……
他覺得自己非常矛盾,當他為了那個人而儘可能地讓自己盡善盡美的時候,那個人卻反而不關注他了。
魏之遠知道自己這種想法是無理取鬧,他也知道自己的心是亂的,可他無法平靜下來。
如果他能平靜下來,如果他能不再讓這件事那麼如鯁在喉地折磨他,恐怕那也不是什麼割捨不了的感情了。
但凡他還有一絲理智,他也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地去撲這把火。
然而魏之遠畢竟是個行動主義者,這條路走不通,他很快找到了第二個機會。
魏謙正翻一份報紙的時候,魏之遠從旁邊經過,狀似無意中指著某文藝版面上推薦的書目說:「這個挺好看的,我有,哥你看嗎?」
魏謙正在家裡待得無聊,欣然接受了這份推薦。
魏之遠把書拿給了他,耐心地等了一陣子。
魏謙對書籍沒有任何尊重的概念,從來是看完隨手一丟,要看時到處亂找,看到哪裡就在哪折一個大角……和他對待襪子的態度差不多。
對魏之遠而言,他的進度非常容易觀測。
等魏謙看完一本以後,魏之遠又適時地如法炮製,拿了第二本給他。
魏謙鮮少有閒暇能坐在家裡安安靜靜地看書,這讓他回想起高中那兩年坐在教室裡的日子……那差不多是他一輩子最輕鬆的日子了。
而魏之遠知道,再一再二不再三,再有一次,魏謙看完就會不問自取地到他屋裡拿了。
……過了兩天,魏謙果然如他所願地自助了。
開始他是把書塞回去再隨便抽一本,這麼過了一個禮拜,魏謙逐漸把魏之遠的房間當成了閱覽室——魏之遠那比他自己那屋乾淨整潔。
魏謙發現他的弟弟收藏的書非常玄,有一些是艱澀難懂的外文譯本,雲裡霧裡的敘事風格和狗屁不通的翻譯,都會對閱讀造成障礙,顯得非常枯燥。然而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卻絕不是因為晦澀難懂,一定有它的道理。
當一個人經歷到了,當他對某些東西能心領神會的時候,那麼不在乎對方在用哪種方式表達,他都能從中獲得某種程度的共鳴或者異議,這兩者是閱讀能夠繼續下去的根本。
但魏謙整整病了一冬天,又沒有得到正常的休息,即使仗著年輕恢復得快,此時也多少有些虛,先前心裡一直繃著根弦的時候還能忍耐,眼下一鬆懈下來,他整個人的精神都好像跟著衰弱了下來。
坐得時間長了他會覺得有點累,所以有時候就會乾脆躺在魏之遠的床上找一個舒服的姿勢,舒服一會,說不定就睡著了。
魏之遠這個人聰明過頭,當然,聰明本身是好事,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會像自己身無長物、僅此可依仗一樣,過分地迷戀和依賴他的聰明。他以為所有的事都可以通過合理的解釋,得到一個必然的結局,好像他一手操控的遊戲一樣。
但是難道只要他足夠聰明和謹慎,就能讓地球在公轉軌道上逆行嗎?
他還不明白,什麼叫做「盡人事、聽天命」。
他也不知道,就在他自以為已經節奏精準地把大哥帶進了他的精神世界,並準備在裡面織網捕蟲的時候,命運……不,或者說是神奇而無處不在的小概率事件就跳出來,嘲笑了他的自不量力。
有一天,魏謙在魏之遠的單人床上補了個短暫的午覺,忽然腿抽筋,把他活活疼醒了。
魏謙為了把抽搐的腿筋抻開,就用已經抽變形了的腳頂住了床一側的牆,用力把腿拉直,頂在牆上的腳,就把原本緊貼在一起的床和牆之間踹開了一條一掌寬的縫。
魏謙原本打算翻身起來,把床給推回去,誰知無意中低頭一看,卻在那條巴掌寬的縫隙裡看見了一本蒙塵的、做工精良的雜誌。
魏謙想不出什麼東西會掉到這裡來,就手伸進床縫裡,撲棱了一下土,撿起了那本雜誌。
封皮上是一個只穿了條內褲的男人,那貨一隻手插進自己的巴掌長的短褲裡,表情是擠眉弄眼的,姿勢是搔首弄姿的,儘管因為是個男的,魏謙一開始愣了一下,但那露骨的封面很快讓他就明白了,這是一本限制級的色情雜誌。
都是男人,都經歷過一樣的年紀,魏謙那時雖然累得像死狗一樣無暇他顧,但也知道生理上急劇變化帶來的躁動是什麼滋味。
以魏之遠這個年紀,收藏幾本這樣的東西,雖說魏謙作為家長,多少覺得有點彆扭,但作為哥哥,他基本也能理解,只是有些尷尬。
懷著這樣的尷尬心情,魏謙隨手翻了兩頁,當那高清銅版紙圖片,以連個馬賽克都懶得打的坦誠,極具衝擊力地撞到魏謙眼睛裡的時候,他臉上的尷尬凍結了。
魏謙先是震驚,很快震驚轉為了迷茫和難以置信,到最後,他的表情簡直是空白的。
一分鐘之後,魏謙猛地從床上彈了起來,不只是氣的還是怎麼的,原本有點缺少血色的臉一直漲紅到了耳根。
他「刷啦」一下把雜誌丟在旁邊,怒不可遏地說:「混賬東西!」
此時正是下午,小寶和小遠自然都去上學了,宋老太在隔壁睡午覺,她年紀大了,這兩年耳朵越發的不靈敏了,睡死了過去,魏謙鬧出這麼大動靜,也沒能驚動她。
魏謙沒收了這本雜誌,困獸一樣地在屋裡轉了好幾圈,心裡真是起火落火的,折磨得他嗓子眼都冒了煙,有心想咳嗽兩聲,又想起大夫說咳嗽傷肺,讓他能忍就儘可能忍著,於是他生生地把咳嗽憋回去了,抬手摔了桌上的一個瓷杯子。
總之,魏謙從頭髮絲到腳趾甲,渾身上下每一個細胞都跳起來鬧革命了,心火燒得最旺的時候,魏謙衝到自己屋裡,挑了一條最硬最沉的皮帶,準備一會魏之遠放學回家,必須要先給他來個三堂會審,只要這小子有膽子認,他就把這王八蛋抽成陀螺。
真是從小到大沒打過,這是積攢到一起給他上房揭瓦了!
魏謙原本以為宋小寶已經是熊孩子的極致,沒想到魏之遠這個「從不出格」的好孩子在這等著他呢,魏謙又低頭看了一眼攤開在桌子上的雜誌,上面一群沒穿衣服的男人正沒羞沒臊地滾在一起,還正衝著他拋媚眼,再次氣得他心肝一陣亂顫。
魏之遠讓他哥活生生地體驗了一把心臟病人的滋味,魏謙的血管裡像安裝了十架機關槍,同時突突起來,他深吸幾口氣,感到胸口一陣一陣地發疼。
簡直是……傷風敗俗!
魏謙一屁股走在旁邊,恨不得掰開魏之遠的腦子,看看那小子到底是怎麼想的,或者什麼玩意佔領了他弟弟的身體,來地球的目的是要幹什麼?
這些因為出離憤怒而亂七八糟匯聚到一起的情緒,最後終於通過毫無邏輯的整合,江流入海般地合成了一個念頭——他決定要打死魏之遠那個小兔崽子。
這件事東窗事發是在午後,魏之遠一般晚自習會上到九點多,他從十二三歲開始就有晚上跑步的習慣,通常上完晚自習會自己順便跑幾圈,活動活動筋骨,等回來就差不多將近十點了。
當中七八個小時,足夠魏謙冷靜下來了。
宋老太晚飯依然做得賣力,可魏謙沒心情也沒胃口,草草吃了兩口就走了。
他回到自己的書桌前,對著那本下午讓他怒不可遏的色情雜誌,終於開始用人類的腦子——而不是機關槍一樣的心血管來思考這個問題了。
魏謙不知道這到底是魏之遠的一時好奇,還是那孩子本人真的有這個傾向。
他想不出任何原因,也想不出任何理由。
先哲中,同性間也有超出友誼的感情,但魏謙一般認為,那都是他們研究學問研究癡呆了,神經病的另一種表達方式。
他並沒有接觸過現實的同性戀,也不瞭解。對那些人應該是什麼樣的毫無概念,只好依照主流的想像來妄加揣度,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喜歡男人的男人,大多是讓人��了就彆扭的娘娘腔。
魏謙往後一仰,靠在椅子上,脖子軟噠噠地往後垂著。
「我們家小遠,」他茫然地想,「打架穩准狠,從不捏蘭花指,從不扭著屁股走路,也從沒有見過他對女孩子的玩的東西起過任何不正常的興趣……他怎麼會是那種人呢?不可能的。」
真的只是好奇,不可能的……吧?
魏謙雙手蓋住臉,狠狠地上下揉搓幾次,心說:「愁死我了。」
直到這時,他對宋小寶嘴裡那句「二哥要得自閉症」才有了一點認識,小寶雖然毫無常識表述不準確,但肯定是魏之遠不正常的沉默和情緒不良才讓她有此聯想的,要麼她好端端地幹嘛造謠呢?
還有那一櫃子的書……整潔到近乎嚴苛的室內環境,門後貼著的光怪陸離的梵古畫海報,無不凸顯出某些不屬於少年人的壓抑和掙紮。
魏謙恍然發現他的後知後覺,這個年紀的男孩子難道不應該喜歡某些運動明星嗎?有個性一點的也不過是崇拜一些科學家或者著名大富豪,哪個會把自己屋裡活活弄成社會學圖書館?
他竟然還沒當回事。
魏謙簡直懷疑自己身上有與宋小寶同志如出一轍的沒心少肺。
晚上魏之遠一手拎著書包一手拎著外套進屋時,就發現大哥在客廳的沙發上,似乎是等著他。
魏謙:「小遠,你過來。」
魏之遠應了一聲,覺得他的態度有點不對勁,他心裡飛快地過了一遍自己最近的所作所為,一時沒想通到底是怎麼回事。
魏謙也不知道自己把他叫過來到底是要幹什麼,他想開口問雜誌的事,問不出口,少年的目光澄澈而專注,居高臨下看著自己的時候,顯出一點可愛的溫柔來。
準備好的皮帶靜靜地掛在屋裡,被魏謙盛怒之下失手打碎的杯子碎片還包裹好了躺在垃圾桶裡,而他竟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魏謙忽然站起來,抬手攬住魏之遠的肩膀。
魏之遠好像受到了某種驚嚇,激靈了一下之後猛地一僵,隨後又小幅度地掙紮了一下,好像既有些不安,又不捨得這樣掙開,有些不好意思地小聲解釋:「哥我一身汗,我……」
魏謙用力拍拍他的後背,心裡很酸,勉強擠出一個笑臉來,放開了魏之遠:「別太累了,有什麼不順心的事告訴哥,嗯?」
魏之遠內心十分疑惑,不明白他唱得哪一出,可是本能地知道自己最好別問,於是乖巧地點了點頭,應了一聲。
魏謙看著他回屋,重重地嘆了口氣,內心無比滄桑地跑到陽臺上抽煙去了。
他有種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的感覺,明明就是個小青年,操心的全是中年人的事,想起前兩天老熊和他開玩笑說要給他介紹對象的話,魏謙憤憤不平地想:「我自己還沒對象呢,都已經開始操心起這幫小崽子搞對象的事了,怎麼活得這麼扭曲呢?」
魏謙忍不住找仍然外地留守戰場的三胖傾訴。
三胖好容易清靜一天晚上,早已經睡得人事不知,被他一個電話野蠻地拖出了夢境,當場恨不得和小子割袍斷義。
魏謙沉重地嘆了口氣,他這麼唉聲嘆氣弄得三胖十分不習慣,三胖撲棱撲棱腦袋,醒醒盹問:「怎麼了謙兒?你那肺炎擴散啦?」
魏謙無比糾結地說:「三哥我跟你說,小遠這小子……這小子……唉,他可能要出格。」
三胖以為什麼大事,一聽這話,頓時鬆了口氣,「哈哈」大笑起來:「出格?哈哈哈哈,大半夜���別跟三哥逗悶子,天底下有幾個出格能出過你的?你逗死哥哥了,謙兒,哎喲喂我都不困了——你知道我聽這話什麼感受嗎?就跟那梁山好漢李逵邁著小碎步跑到他宋江哥哥面前,嚶嚶嗡嗡地說『山下有土匪劫道人家怕怕不敢走』一樣啊!」
魏謙:「……」
他停頓了片刻,對著話筒喊了一句:「操你大爺的死痰盂兒。」
然後他不由分說地掛了電話,獨自一邊惆悵去了。
第二天魏之遠下了晚自習,如往常一樣來到了學校體育場,把書包一扔,熱身片刻打算跑兩圈,正在扭腳腕,無意中一抬頭,險些把腳扭了——魏謙正幽靈一樣悄無聲息地在看臺上看著他。
魏之遠:「……哥?」
魏謙清了清嗓子:「嗯,我……咳,我過來鍛鍊身體。」
魏之遠匪夷所思地打量了他片刻,遲疑不定地說:「那……那行吧,你慢點別嗆風,醫生不是不讓你劇烈運動嗎?」
結果果然就沒有劇烈活動,魏之遠足足比平時慢出了一倍多,倆人一路溜躂一樣地繞著操場跑,不時被放學回家穿越操場步行的同學超過,最後魏謙終於忍受不了了,退下來站在一邊:「你去吧,我在這等會你。」
魏之遠跑完步,推著自行車,和魏謙一起緩緩地走了回去,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過了不知多久,魏之遠突然聽見魏謙說:「小遠,你在哥這,跟小寶都是一樣的。」
魏之遠抬起頭看著他,魏謙把目光移到一邊,似乎不習慣這種語重心長的角色,他努力回憶著學校裡的老師是怎麼做的,放緩了聲音,儘管已經盡力了,語氣卻依然顯得有些生硬:「小寶……她老出么蛾子,我不得已多管她一點,你比較懂事……唔,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反正我心裡沒有偏著她,你就跟我親弟弟一樣……唉,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吧?」
魏之遠其實不知道,可這不妨礙他享受大哥難得一見的溫情。
他突然停下來:「哥,我能抱抱你嗎?」
魏謙:「……」
他覺得有點肉麻,可生怕傷到他腦補中的少年人那顆「纖細敏感」的心,於是壓下自己的彆扭答應了。
魏之遠一把把他抱了個滿懷,摟得緊緊的,把臉埋進了魏謙的頸窩裡,閉上眼睛,嘴唇似有意似無意地掃過了魏謙的脖子,落下了一個似是而非的親吻。
魏謙本能地一激靈,然而他認為這只是意外,不想顯得反應太大,只好默默地忍了。
兩人一路回了家,剛開門,迎面卻飄來宋老太怒不可遏地吼小寶的聲音:「你每天都在幹什麼?都在幹什麼?這上面寫的都是什麼?別扯淡!我不相信!」
小寶的書包掉在地上,有幾張紙飄得到處都是,她抬頭瞥見魏謙回來,先哆嗦了一下。
魏謙無力地往門邊一靠:「祖宗們,這又是哪來一出嘣噔嗆啊?」
第四十二章
宋小寶看見魏謙,就像老鼠見了貓,臉上呈現出某種「大限將至」的絕望來。
宋老太撿起地上的一頁紙,一蹦三尺高地把自己發射到魏謙面前,扯著嗓子衝他嚷嚷:「你看看!太不像話了!這都什麼人?哦,你們學校教育出來的都是這路臭不要臉的貨色?你告訴我這誰,我找他去我!」
魏謙接過來大概齊地拜讀了一下,頓時啼笑皆非。
宋老太遞過來的,毫無疑問,是一張情書。
至於不認字的宋老太是怎麼看出來的,那要歸咎於情書製作人,他創意十足地把一張三十二開紙畫得滿滿噹噹,簡直就是小學老師經常讓小孩們辦的那種「小報」範本。
最上面是一個巨碩的大標題「給宋小寶」,外面奇葩地用某種類似樹藤的拙劣手繪給圈起來了,還用水彩筆挑染了不同的顏色……魏謙不知道此人是不是想表現出一圈霓虹綵燈的效果。
左下角畫著一個被箭穿起來的大桃心,右邊是一男一女兩個小人……
宋老太就指著那兩個小人,炸毛的老母雞一樣跳腳:「還親嘴呢!」
情書的內容與其繁瑣的形式相比,倒是非常簡潔易懂,正文就一行字:宋離離,你是個大美女,我非常喜歡你。
前因後果說得一清二楚,毫不扭捏。
末了,彷彿為了表現一下自己的文藝素養,此少俠在讓人眼花繚亂的花邊外面,用歪歪扭扭的「藝術字」畫了兩行也不知從哪抄來的古詩詞,抄得不求甚解,讓人看了十分摸不著頭腦。
左邊是「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右邊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得嘞……這是要生離死別的節奏。
魏謙知道自己應該保持嚴肅,但又實在忍俊不禁,嘴角在壓抑和笑噴之間哆嗦半晌找不著頻率,他覺得自己的表情從視覺效果上來看,很可能更接近獰笑。
然而隨即,他不可避免地又想起自己在小遠房間裡發現的那本雜誌,終於沒心情嘲笑這一封「少年情懷儘是詩」的情書了。
他終於轉為苦笑,糟心地看了魏之遠一眼,對他說:「別在這看熱鬧了,你該幹嘛幹嘛去。至於你……」
他轉向宋老太。
宋老太咆哮:「天天上學就幹這個!我看這個學趁早別上了!」
魏謙往後退了一步,嘆了口氣:「你能不能消停會,別嚷嚷了?噴我一臉。」
宋老太也意識到自己的砲彈軌跡偏離了目標航線,立刻轉向縮脖端肩的宋小寶,繼續咆哮:「不行,今天你必須給我一個解釋,你是要唸書還是要搞對象!」
其實小寶這一次正經是很無辜的,她也不知道這個腦殘兮兮的小報狂人到底是哪位民間高手,她的雙肩包背在身後,放學的時候在學校裡被人擠來擠去,有人趁她不注意往她包裡塞東西,她怎麼會察覺到呢?
雖然虛榮心和好奇心讓她看到的時候不免蕩漾了一下,但她認為自己這只是正常範疇內的驚詫,絕對沒有奶奶說得那麼上綱上線。
然而即使奶奶拿掃帚疙瘩揍過她,小寶卻依然不怕這老太太,反而比較怕大哥,她覷著魏謙的神色,低聲下氣地解釋說:「我沒有,我真不知道這是誰塞我包裡的。」
宋老太一口咬定:「這肯定不是第一次了!不行,我要去你們學校找你們老師。」
宋小寶:「哎喲奶奶,你這樣我以後在學校裡都沒臉做人了!」
宋老太那張開開合合的嘴,和亞馬遜食人魚的鐵齒銅牙有異曲同工之妙,語速快得讓人捕捉不到她的嘴唇動作:「你不好好上學沒事談戀愛就有臉做人啦?我跟你說宋離離,這擱在過去就是作風問題,作風問題是大事你懂嗎?沒事耍流氓,法院能判了你!」
宋小寶有點急了:「我都說了我沒有!」
宋老太:「那怎麼不給別人寫專給你寫呢?你自己肯定也有問題!」
面對不講理的奶奶,宋小寶也只好嚷嚷著口不擇言起來:「他王八看綠豆,我哪知道!」
宋老太敏銳地抓到她的語病:「哦,你總算說實話了是吧?王八看綠豆?看對眼了是吧?」
宋小寶;「……」
說話或者寫作文,但凡她要引用典故、成語或者歇後語,十次有九次都是驢唇不對馬嘴的,她一直沒覺得有什麼大不了,還老自我解嘲說這是創意運用,這回終於把自己用創意活埋了。
見她沒有絲毫懺悔的意思,宋老太擼起袖子打算君子動手不動口了,魏謙這才不慌不忙地出面攔下,對奶奶說:「你明天不是還要早起?早點睡吧,我跟她說……行啦,沒那麼嚴重,你再給氣出高血壓來——你,跟我過來。」
托魏之遠的福,現在魏謙眼裡什麼事都顯得不那麼嚴重了。
宋小寶仇恨地看了一眼大哥手裡的那張找麻煩的小報,決定了,讓她查出這個傻逼作者是誰,一定要和他絕交。
小寶走進大哥教導主任辦公室一樣的臥室,把門一關就開始痛陳冤情,劈裡啪啦地交代了自己一整天的行程,並對這封莫名丟臉的情書是怎麼被塞進她書包的做了合理推測,最後指天發誓表明立場:「我真沒有早戀!我真不知道這個是怎麼回事,奶奶淨冤枉我!」
說完,她惴惴不安地觀察大哥的反應:「……哥?」
魏謙一直低著頭,好像在聽她說話,但是小寶以自己對他的瞭解,知道他不可能這麼有耐心,半晌不說話,多半是在走神。
魏謙被她一聲叫回了魂,猛地一抬頭,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地蹦出一句:「給你寫這個的,是個男的?」
小寶以為自己耳朵出了問題,忍不住伸了伸脖子,茫然地問:「啊?」
魏謙:「是男同學給你寫的嗎?」
小寶感覺自己進錯了頻道,莫名地說:「那、那應、應該是吧?不然呢?」
魏謙悲哀地發現,自己心裡真是一點火氣都沒有,甚至還隱約有種「謝天謝地,是男的就好」的詭異安慰感。
他撚了撚手指,又想煙了,有氣無力地衝宋小寶揮揮手:「行了,我知道了,你去吧,沒有就沒有,我相信你這次,下不為例。」
宋小寶就這麼被大赦天下地放出來了,臨走,她發現魏謙又摸出煙盒來,頓了頓,忍不住多了句嘴:「哥,大夫說讓你少抽點,他還說你那肺都熏成夫妻肺片了。」
魏謙沒好氣地說:「快滾吧,你們少惹點事,讓我多活兩年比什麼都強。」
等等……「你們」是怎麼個意��?
宋小寶的耳朵都豎了起來,感覺自己好像聽到了什麼不得了的內幕消息——難道她那一年四季溫良恭儉讓、如同勵志課文標竿的二哥也攤上事了?
一想到這,她就難以名狀地心情飛揚起來,心裡升起某種幸災樂禍的快感。
宋小寶同學自從離家出走一次以後,越發的心有天地寬……簡稱沒皮沒臉起來。見大哥沒追究,很快給點陽光就又燦爛了。
這一燦爛,她心裡的話就好像鳥類的腸子,都是憋不了太長時間的。
第二天正星期六,小寶在熊嫂子的推薦下找到了個比較專業的舞蹈老師,挺像那麼回事地學了起來,所以一早要趕公交車去老師那,她搭一程魏之遠的自行車去公交汽車站。
路上,小寶就嘻嘻哈哈地把她親愛的大哥打包賣了。
宋小寶:「二哥,你最近惹什麼事了?說出來大家一起長長見識好不好?」
魏之遠意識到自己的王派間諜來匯報情況了,不動聲色地搪塞了一下後轉移了話題:「我能幹什麼?昨晚上哥沒罵你?」
「啊哈哈,完全沒有。」宋小寶坐在後座上一晃一晃的,「昨兒晚上嚇得我腿都抽筋了,結果哥那叫一個好說話。」
接著,她沒等魏之遠問,就自覺地把事件前因後果學了一遍。
最後宋小寶總結陳詞:「其實我覺得哥他昨天有點不對勁,神兒不在家,後來還問了我一句特別搞笑的話。」
魏之遠:「他問你什麼了?」
宋小寶:「他問我給我寫情書的是不是男的,不是男的是什麼?你說這可有多新鮮哪……哎喲!」
魏之遠車把一哆嗦,自行車直接拐進了路邊的一個坑裡了,好在他車技高超,伸腳撐了一下,又騎了出來,好歹是沒把宋小寶掉進去。
宋小寶拍拍胸口,心有餘悸地說:「嚇死我了嚇死我了,二哥你幹什麼呢?」
魏之遠伸腳支起單車,簡單地說:「到了,來車了,快去吧。」
宋小寶一看,果然是她要坐的那輛公交車正好到站,立刻來不及追究,拎起書包跳下車,像條脫韁的野狗一樣撒丫子奔將過去了。
魏之遠驚險地維持住了沒失態,手心卻已經被冷汗浸滿了。
他驟然明白了前一天大哥的反常是從何而來了,而自己竟然一時得意忘形,還冒險偷親了他一口!
那……那大哥當時到底是感覺到了還是沒有呢?
一想到自己留下的漏洞,魏之遠簡直頭皮發麻。
問題是大哥究竟是怎麼發現的?
這不對啊。
接下來的日子,魏之遠再不敢輕舉妄動了,直到一個禮拜以後,張總那邊來了通知,說預售證能在一個月以內拿下來。
三方股東很快要做一次階段性的工作彙總,魏謙認為自己已經好得差不多了,趕去了外地,魏之遠才找到機會。
夜深人靜的時候,魏之遠一個人偷偷溜進了魏謙的房間,上上下下地翻了個遍,最後,終於在一個最下面的抽屜裡找到了那本要命的雜誌。
作為為數不多的幾本曾經被他打開翻開過的書,魏之遠一眼就認了出來。
魏之遠想破了頭也沒明白,這東西當初是怎麼逃過了自己亡族滅種一樣的地毯式搜索的,更匪夷所思的是,怎麼那麼巧,他本人搜了好幾遍自己的地盤都沒找著的東西,就那麼寸,一頭撞到了他哥手裡。
魏之遠把所有的東西復位,腦子裡終於閃過一句話,足以形容他現在的心情——
咿呀,此乃天亡我楚,非戰之罪!
魏謙這一走,就直到要交論文的時候才回來了一趟,他匆匆落了個腳,交論文答辯一系列的事做完,就又跑了。
而那一次,儘管就回來了這麼兩天,他竟然還給每個人帶了禮物。
要知道魏謙的字典裡本來壓根就沒有「禮物」倆字,所以魏之遠雙手接過那個上面有某個他沒興趣知道是誰的球星簽名的籃球時,內心根本就是錯愕的。
可魏之遠一偏頭,發現大哥正用某種試探的眼神觀察自己的反應,少年連忙反射性地露出一個略顯天真的笑容安撫他,假裝自己很驚喜很喜歡。
與此同時,魏之遠心裡算是明白了——大哥不知道怎麼得出的這個結論,認為自己是缺愛才走上「邪路」。
而接連不斷的家庭明暗矛盾,似乎給魏謙造成了不小的打擊,他企圖改善自己在家裡大獨裁者的形象。
當小寶穿著魏謙帶回來的新衣服在屋裡亂蹦亂跳的時候,魏之遠眼睜睜地看著魏謙把皺在一起的雙眉硬生生地棒打鴛鴦了,努力擺出一副慈祥態度。
……儘管他可能對「慈祥」的理解有誤,那神態怎麼看怎麼像「皮笑肉不笑」,好像隨時準備站起來,依照慣常冷嘲熱諷一番。
宋小寶已經習慣了她哥的沒好臉和冷嘲熱諷,一直在等,結果一直沒等到,她終於不習慣了。
在魏謙再一次拎起行囊走之前,小寶湊上前去,好生討罵地問:「哥,你這次回來,怎麼沒說我?」
魏謙:「我說你什麼?你又幹什麼了?」
宋小寶順口就說禿嚕嘴了:「哦,我期中考試語文差一分不及格,家長簽字讓二哥代簽了。」
魏謙糟心地抬頭看了她一眼,宋小寶這才意識到了什麼,驚慌失措地摀住了自己的嘴。
可想而知,由於宋小寶不遺餘力的破壞,魏謙的「慈祥」假面最終的下場,就是屍骨無存了。
等魏謙再次閒下來回來的時候,時間已經又從盛夏劃到了年底,他們這個短平快的住宅項目的預售被張總包裝得非常上檔次,整個秋天過去,所剩的工作就只差一些掃尾工作了——等來年開春,立刻可以驗收工程,而銷售也幾乎到了尾盤。
他們出了三千萬,後期老熊又陸陸續續地弄來一千多萬,總共投了四千多萬,照目前的形式看,基本是翻了一倍多不止。
老熊樂得跟個瓢似的,帶著魏謙和三胖志得意滿地回來了。
他們勉力跳著夠了一下,最終還是邁進了這個門檻。
回來那天,老熊就跟衣錦還鄉一樣挺胸抬頭,感慨萬千地對三胖和魏謙說:「你們倆小子這回真給我長臉啊,我以後在你們嫂子面前就能抬起頭來了!以後……唉,我就不要求她跟日本女人似的給我準備拖鞋,天天歡迎老爺回家了,好歹給我幾個笑臉,這不過分吧?這才是爺們兒該過的日子啊!」
三胖和魏謙同時把臉扭到一邊——這是多大出息!
老熊:「行了,咱哥幾個這一輩子戎馬倥傯算是開了個頭,這陣子大家都辛苦了,回家休整幾天,週末說好了,出來慶功!哦,對了謙兒,穿漂亮點來,你嫂子還一直惦記著給你介紹對象呢。」
三胖眼睛一亮:「熊哥,我呢?」
老熊拍拍他的肚子:「給你介紹一個廣告商,請你去拍特效減肥藥廣告——四千萬!只要四千萬!減掉十斤不是夢!減不掉也不退錢……」
魏謙到家的時候正是下午,宋老太迎了出來:「你回來啦!吃點什麼?奶奶給你做去。」
魏謙剛把東西放下,還沒來得及說話,就看到魏之遠屋裡的門開了,他那越發讓人操心也越發出挑的弟弟衝他露出一個溫暖的笑容:「哥。」
魏謙愣了一下,隨即反應過來:「哎,你怎麼在家?沒上學去?」
宋老太咋咋呼呼地說:「競賽得了好幾個獎呢!哎呀什麼獎我也不懂,反正是肯定是第一,對吧小遠?他跟你一樣,不用參加高考,唉,這墳頭上的青煙得冒出三十裡地去啊!」
「那就成森林大火了。」魏謙轉向魏之遠,「什麼時候的事,怎麼沒告訴我一聲?」
宋老太又開始咋呼:「這小子說你忙,不讓我們拿這點小事打擾你……哎你說這孩子,這是小事嗎?這在老家是要���宴席的!」
魏之遠彎下腰幫魏謙把行李箱扛進屋,輕描淡寫地說:「本來就沒什麼。」
這還寵辱不驚上了,魏謙心裡一陣孩大不由爹的心酸,更讓他心酸的是,小遠這孩子簡直了,什麼都好,偏偏……
話說,他那毛病到底好了沒有?
魏之遠幫他收拾東西的時候,魏謙就若無其事地試探了他一句:「你這也高中畢業了,以後就算大人了,想做什麼,我就不再過嘴管你了……嗯,交個女朋友也行。」
魏之遠正把手伸向一打散開的紙質文件,一聽這話,手在半空中落了下來,正好蓋在魏謙的手背上:「哥,我不打算找女朋友。」
魏謙心裡一緊。
魏之遠抬頭看了他一眼,眼神幽深,似乎裡面藏了一個深深淺淺的世界,然而沉默了一會,他還是縮回了自己的手,同時給出了一個非常健康向上的理由:「學習和多做一點專業實踐才比較重要吧,時間那麼珍貴,不想這麼早談戀愛。」
魏謙情緒不高地點點頭,有點胃疼地想:還沒好,愁人啊。
同時,魏之遠垂下眼,有些惆悵地想:這麼摸他手都連一點反應也沒有,是一點也沒往那方面想嗎?愁人啊。
晚上,小寶一回來就咋咋呼呼地問她哥要禮物。
魏謙自嘲地一笑:「得,給了一回,第二回就自己會要了——扔你床上了,自己看去。」
宋小寶歡欣鼓舞。
宋老太忍不住問:「今天怎麼這麼晚?吃飯了嗎?」
「吃了,跟露露姐吃的,哦我還看見熊哥了,他也不知道是有什麼毛病,今天回家的時候撅著肚子,嘴撇著,跟個地主老財似的,結果露露姐把手一甩,跟他說『做飯去』,熊哥就一秒鐘變長工,灰溜溜地洗菜做飯去了。」
「露露姐」就是熊嫂子,熊嫂子芳名陳露,清新得聽在耳朵裡就讓人想起迎著第一縷晨光含苞待放的小花。
可惜……名字騙人的。
「露露姐可好了,不過她今天跟我說:『小寶你十七,我三十四,有你倆那麼大,你別跟他們油嘴滑舌地叫我姐了,叫我乾媽得了』……哎呀!這個真好看,謝謝哥——然後我跟她說:『哈哈哈哈,姐你別逗了,那不差輩了嗎,你等於間接佔了我哥便宜啊!』」
這丫頭說話的工夫,脫外衣換鞋,又跑到自己屋看禮物,大驚小怪一番後自己接上自己的話茬,一系列動作和背景音一氣呵成,她繼宋老太之後,成了家裡又一大話嘮,基本沒有別人插話的餘地,她一個人能演一齣愛恨情仇的獨角話劇。
一開始聽著還挺親切,到後來,魏謙恨不得縫上她的喋喋不休的嘴。
轉眼到了週末,魏謙先陪著鸚鵡一樣聒噪的妹妹出門跳了一雙新舞鞋,又帶著缺愛的弟弟跑到社區活動中心打了場一對一的籃球——不過後期明顯變成魏之遠陪著他玩,魏謙技術實在不行,他能和同齡人玩的時間近乎於零,學生時代一切接觸籃球的機會僅限於不多體育課。
所有的運動,他只有野路子格鬥還比較精通,然而整天西裝革履地坐辦公室,他懷疑過幾年唯一精通的也要荒廢了。
當然,這不重要,重要的是魏謙希望能多和魏之遠相處一些時間,能多瞭解瞭解他究竟是怎麼想的。
過完這充實的一天,魏謙晚上去赴老熊的宴。
熊嫂子沒來,說是臨時有事,介紹對象的事當然也就不了了之……魏謙不明原因地鬆了口氣。
他懷疑老熊是回家太得瑟,被夫人好好收拾了一通,整個人看起來特別憔悴,眼泡都腫了。
從頭到尾只有三胖在插科打諢,老熊的興致一直不高,最後還喝多了。
老熊喝多了也不鬧,一聲不吭地悶頭坐在一邊,好像耳朵失靈了一樣,誰說話也不搭理。
最後散場,三胖才推了推他:「熊哥,我打輛車送你回去行嗎?喝成這樣,嫂子能讓你進門嗎?不如找個旅館湊合一宿吧?」
老熊被他一推,就往另一邊倒去,撞到了魏謙身上。
魏謙一愣,下一刻,老熊卻一把拽起他的衣擺蒙在了自己的臉上,毫無徵兆地嚎啕大哭了起來。
他哭得肝腸寸斷,到最後連聲音都已經瘖啞不堪,幾乎是靈魂深處發洩出的難以形容、難以忍受的嘶吼與痛呼,簡直不成人聲。
把魏謙和三胖都嚇住了。
倆人等他哭得疲憊不堪地昏睡過去,才一起抬著老熊找了個酒店臨時住下,中間考慮了無數種悲劇的可能性——諸如破產啦、絕症啦、父母雙亡啦、被戴綠帽子啦等等。
惴惴不安了一整宿,結果等這胖頭魚第二天起來,倆人一問,發現他竟然毫無印象了。
敢情喝醉了就哭是這貨的個人特色,被浪費了敢情的三胖和魏謙憤而聯手揍了他一頓,然後各回各家。
魏謙要去頭疼地解決魏之遠,他決定,哪怕經過漫長的拉鋸,也要把這小子從邪路上掰回來。
這是一場戰鬥。
第四十三章
魏謙原��為拿到大學畢業證的時候,他會激動的徹夜難眠,為得到自己的夢寐以求。但實際情況是,他那段日子過得實在是太兵荒馬亂了,乃至於足足一年後,他才想起來,自己竟然連畢業典禮都沒能出席。
他以為自己在爬,然而不知不覺中,竟已經站起來跑了。
老熊他們以前一直也有公司,只不過看起來都很兒戲,雇了一大堆臨時工,大多數時候都是他們幾個人在親力親為,賣茶葉就註冊個某某茶葉公司,賣醫療器械就起個名叫某某外貿公司。
他們打遊擊一樣地積攢了一批亂七八糟的產業和一批更加亂七八糟的人脈。
而就在魏謙他們把第一個涉及大規模資本的項目做下來之後,老熊他們仨終於坐了下來,租下了市中心寫字樓的一層,細緻地寫明瞭章程,修改了好幾稿之後定下,組建起了正規的公司,並把那些山寨皮包公司一樣的某茶葉公司和某外貿公司都改了名,統一品牌,形成了一個集團。
最早的成員實際只有老熊、三胖和魏謙,後來隨著他們的擴張,陸陸續續招進了不少人,整個公司就像一個充了氣的氣球,開始有了複雜的五臟六腑。
魏謙他們哥仨的狀態,也逐漸從「像死狗」,變成了「表面上光鮮,實際累得像死狗。」
這艘船開始試探著在近海航行起來。
第二年,老熊他們又先後做了兩三個短平快的小項目,不在是隱形股東了,他們光明正大地從幕後走到了台前。
老熊的野心也在與日俱增地膨脹,他似乎已經隱隱看到了即將到來的黃金時代。
這是於公,於私,魏謙決定把魏之遠掰回來的話不是說著玩的,他從來是說到做到,只要下定了決心,立刻就會行動。
魏謙就經過多方打聽後,私下聯繫了一個看起來很正規的心理機構,不久,他就在預約後,戴著個能把臉都遮住的大墨鏡跑過去了,形容舉止比未成年少女打胎還偷偷摸摸。
結果笑面虎一樣的白大褂收了諮詢費,就溫聲和氣地告訴他:「同性戀雖然還沒有被法律承認,但是我國前兩年就已經把它從性變態裡刪去了,您所說的這種情況,有可能只是青少年在生長髮育過程中產生的某種傾向,可能會隨著他身心日趨成熟以後而逐漸消失。當然,也有可能他本人是一個真正的同性戀者,成因可能是很複雜的,我們稍後討論,但是它給青少年帶來的心理壓力是很大的,家裡人更需要科學對待,不要反應過激,要慢慢疏導才行。」
魏謙聽了這麼專業的話,立刻抱著一線希望問:「疏導完以後呢?能掰回來嗎?」
白大褂笑容可掬,以一種普度眾生的語氣說:「通過耐心的疏導,讓孩子能豎立起足夠的自信,坦然面對自己和別人的不一樣,最後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幸福之路。」
魏謙看了看這位心理諮詢師,又看了看桌角的煙灰缸,慎重地思考著,如果一煙灰缸給這小子開個會怎樣。
經過這次經歷,魏謙認為這些心理諮詢師純粹是半吊子,一點也不靠譜,他得到了這個所謂「科學」的答覆,依然不肯死心,過了沒幾天就找了一張大美女的掛曆搞到了客廳牆上。
魏謙這個人品味著實堪憂,傳統意義上的東方美人他自己看不慣,於是委託三胖搜尋。
三胖要是靠得住,母豬都能上樹了。
他不知從哪弄來了一套掛曆,裡面一水的金發碧眼大胸妹,個個袒胸露背,長得全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大眼睛雙眼皮,用燦爛的笑容對中國人民恭喜發財,活能閃瞎人狗眼。
魏謙把這幅圖掛在了客廳裡,完美地破壞了熊嫂子營造出的文藝型家居氛圍,頓時把品味拉到了城鄉結合部水準,整個家裡都開始瀰漫著一股「驢肉火燒店開業大吉」的「喜慶」氣味。
魏謙企圖以基礎的肉慾來喚醒魏之遠對女性的興趣,結果魏之遠還沒來得及發表意見,宋老太先不幹了,她氣沉丹田的一嗓子:「哎喲我的媽,這些女的怎麼都穿著個褲頭就跑出來了?誰掛的?什麼?你哥?我看你哥是吃飽了撐的,越活越回去了!太不像話了,快給我摘下來!」
他們就趁魏謙不在家的時候,把掛曆給摘下來了,宋小寶連忙趁機夾帶私貨,掛上了剛流行起來的日韓男明星。
晚上魏謙回家一推門,正看見魏之遠站在牆根,打量著牆上那一群油光水滑的小白臉,大哥當時就出離憤懣了。
他大步走過去,面沉似水地問:「好看麼?」
魏之遠帶著點意味不明的笑意轉過頭來,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一般吧,我見過更好看的。」
魏謙被他這話裡的信息量震得苦膽都哆嗦了起來,立刻把小寶掛的小白臉們卷吧卷吧收起來扔了,同時決定去調查一下魏之遠平時都和誰來往,什麼叫做「見過更好看的」?
哪來的狐狸精勾搭著青少年學壞?
還是個男狐狸精。
這是多麼蛋疼的名詞。
最後,新年掛曆掛上了符合宋老太審美的「春華秋實」。
……依舊充滿了接地氣的田園風情。
兩次的嘗試都被宣告無疾而終,魏謙消停了一陣子,後來他又不知從哪個不負責任的研究報告上獲悉,說一些男同性戀者是從小缺失父愛和與父親的互動造成的。
魏謙不可能憑空給魏之遠變出個爹來,只好硬著頭皮自己上。
等到春暖花開後,趁週末,魏謙硬是擠出了一天的時間,決定帶魏之遠去做一些屬於男人的休閒運動——釣魚。
魏謙擠出一整天的時間並不容易,他那一段時間的日子過得相當兵荒馬亂,每天都是過勞死的節奏,沒有什麼加班不加班的概念,從早晨睜眼到晚上閉眼,連軸轉。
他依稀回到了那種每天早晨一張眼就要開始盤算一整天的日子該如何過的時間。
臨走前一天,魏之遠最後檢查了一遍自己要帶的東西,這才上床睡覺。
他屬於那種永遠也用不著鬧鐘的人,平時有生物鐘準點起床,而如果第二天有需要特別早起做的事,他也會自發地醒的特別早,他的身體裡好像裝了根發條。
當然,這個特長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惦記著第二天要早起有事,他會容易睡不好覺。
魏之遠三點的時候醒來了一次,之後再躺,就開始做夢。
他的夢境支離破碎的,幾乎沒有一塊完整的情節,他夢見自己從很多地方經過,有時候是疾馳的火車,有時候是骯髒的牆角,有時候是逼仄狹窄的房間,所有的地方都有個蓋子,都顯得暗無天日,顏色單調而暗沉。
魏之遠難受地在床上動了動,但是沒有醒,他的夢裡沒有突然出來嚇他一跳的怪物,也沒有突然落下去的懸崖,而他似乎就是被困在那樣漫長而真實的夢魘裡,心情不激動也不恐懼,只是覺得極端的壓抑,與麻木了一樣的習以為常。
夢裡,他四周始終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眼睛,從他身邊經過的形形色色的人,全都是面孔模糊的,而那些人平面般的臉上如出一轍地只有一雙眼睛,每一雙眼睛的目光都險惡地投注在他身上。
那些視線就像芝麻大的小蟲子,並不致命,卻一刻不停地在他身上緩緩爬過,帶來一股說不出的顫慄感。
所有的聲音都消失無蹤,所有的觸感都虛假不真,而他目光所及處,只有那些不懷好意的目光,魏之遠終於開始跑了起來。
他把自己「跑」醒了。
魏之遠大汗淋漓地從床上坐起來,按下床頭燈——淩晨四點四十五分。
他頓了頓,雙肘撐在自己的大腿上,擼了一把臉上的汗,坐在那平復著呼吸。
胸口好像被堵了一團棉花,呼吸不暢。魏之遠再也躺不下去,起床洗漱。
他從鏡子裡看到自己現在的模樣,高大而英俊,提前長成的雙肩像拉開的翅膀,行動的時候充滿了生動的力量感。
大概是沒從夢魘裡清醒過來,魏之遠突然想起一件年代久遠的事。
那時候他有……六歲?七歲吧,反正還在漫無目的地流浪,文明的社會與他之間像是隔了一道牆,透明的、觸碰不到的,卻清晰無比地拒絕著他進入。
有一天,他在街角休息,看見一個人拿著兩盒食物從一個小飯館裡走出來,一次性的飯盒大概有些不結實,那人走了幾步,底下的飯盒就漏了,他被燙得鬆了手,整個一盒的飯菜打翻了滿地。
這個人罵罵咧咧地轉身去找飯店的人理論,食物的香味瀰漫得到處都是,誘人的菜香對於飢餓的孩子而言,就像是有致命吸引力的罌粟。
魏之遠實在忍不住,終於鼓足了勇氣,悄無聲息地走過去。
他蹲在地上,偷偷用手抓著撿來吃,正在吵架的那個人發現了他,當即大吃一驚,他的表情歷歷在目——怒目圓睜,汗毛倒豎,好像看到了一隻陰溝裡的老鼠,又嫌棄又憎惡。
隨即,那人大聲喝罵起來,好像魏之遠不是撿他掉下的飯吃,而是玷污了他的食慾一樣。
「噁心死人了!」魏之遠記得那個人這樣說,而後他被毫不客氣地狠狠踢了一腳,飛濺起來的熱菜湯落到了孩子嬌嫩的皮膚上,把他的手腕內側燙壞了,至今,那裡依然有一個小得幾乎看不出來的傷疤。
這就是那堵看不見的牆——他在人們眼裡根本不算人。
可憐他的,像可憐小貓小狗一樣可憐他,嫌他髒的,像看見野貓野狗一樣心懷憎惡,對他不懷好意的,像惦記著要吃貓肉狗肉的那些人一樣,居心叵測地估量著他有幾斤幾兩。
他們可能認為他是個小傻子,或者精神不大正常,沒有人會覺得他智力正常甚至超常,甚至沒有人知道他竟然也有人類的喜怒哀樂。
所有的惡意,都坦然地刻在地球表面上,逐字逐句地橫亙在魏之遠面前,長成他自己由內而發的惡毒。
難以泯滅、難以戰勝。
魏之遠以為自己已經忘了,然而這些壓箱底的記憶卻總在不合時宜的時機出現,腦子裡像有一個小小的放映室,時而就會放些老片子,歷歷在目,恍如昨日。
可這畢竟不是真的昨天了。
魏之遠漠然地盯著自己手腕上的傷疤看了幾秒鐘。
直到現在,他依然討厭別人毫無來由的注視,卻並不再恐懼那些目光,他依然知道自己病態地追求強大,然而那又怎麼樣呢?
少年想,他總有一天會有踏平這個世界的力量,那時候將沒有人能阻止他,他甚至狂妄地夢想,要強大到影響這個世界的規則。
這時,另一個人突然在魏之遠眼前一閃,他一個恍惚,好像又看見當年被他一步一步引到冷庫活活凍死的不知名的變態的臉。傳說人腦對於不愉快的回憶會自動遮罩,可魏之遠的腦子卻像一塊冷漠的硬盤,從不讓他忘記任何事。
突然想他做什麼?死都死了。
魏之遠自嘲地笑了一下,轉身走出衛生間,一出來他就險些撞上魏謙。
魏謙的腳步幾乎是踉踉蹌蹌的,他們倆約好早晨五點鐘起床出發,結果魏謙頭天晚上回家的時候就已經半夜兩點半了,草草洗漱再加上走了困勁睡不著,估計等好不容易閉眼,至少得三點多以後了。
魏謙覺得自己剛進入深度睡眠,鬧鐘的聲音就粗暴地鑽進他的腦子,把他嬌弱的睡眠一舉殲滅了。
他用了幾乎是戒毒的毅力才從床上爬起來。
魏之遠眼看著他哥就像個不倒翁一樣,左搖右晃了好一會,一不小心撞到牆上,魏謙幾乎要順著牆壁滑下去,就睡在牆根了。
魏之遠捉住他的肩膀扶了他一把,輕聲問:「要不你再睡會?今天就別去了吧?」
魏謙一聲不吭地擺擺手,掙紮著起來走進了衛生間。
直到被冷水一激,魏謙才有一點回過神來,他身上沒一個細胞都在叫囂著不想出門想睡覺,卻仍然被集體鎮壓了。
魏謙心說,小子,哥為你可是豁老命了。
釣魚的地方一般在郊外,開車過去要將近兩個小時,魏謙剛拿的駕照,買了個中低檔的家用轎車平時開。他手頭這些年略有些錢,卻依然不怎麼往自己身上花,倒並不是他年紀輕輕就本性沉穩、不虛榮、聖人似的不想顯擺。
而是他實在還沒有富到讓自己有安全感的地步。
有多少錢才能有安全感呢?
魏謙說不好,不過他尋思著,以自己不高的修養和淺薄的思想境界,真有那麼一天,他說不定真能幹出「喝一碗倒一碗」之類揮霍無度的事來。
貧窮已經刻在了他的基因上,直接影響著他身體裡每一個蛋白質分子的合成。
而一邊的魏之遠也不知是沒睡醒還是怎麼的,一直撐著下巴,望著窗外不出聲。
魏之遠從來沒有釣過魚,魏謙也還是小時候——他繼父和親媽都還活著的時候,三胖的爸帶著他們仨玩過一次。
那時三胖他爸還年輕,就跟現在的三胖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也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好脾氣和油嘴滑舌,帶著三個高矮胖瘦不同的小男孩,男孩們一邊走一邊打鬧,三胖爸也不管,只是偶爾鬧得過了,才回頭維持一下秩序,以防他們掉進河裡。
坐下等著魚上鉤的時候,三胖爸就和三胖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地一起在背後惡損三胖媽,活像兩個翻身農奴把歌唱的窮苦人民共同痛斥壓迫階級的官老爺。
釣魚,有時候更像一種「先生們的茶話會」,他們可以湊在一起肆無忌憚地在一起討論女人,抱怨生活以及家裡永遠麻煩精一樣的小崽子們。
兩個人到得不算很早,已經有人支好魚竿了,他們倆找了一個水邊歇腳遮陽的小亭子,坐在台階上,擺開傢夥式。
魏謙以其稀薄的經驗,生疏地教魏之遠怎麼往魚鉤上掛餌,怎麼看魚漂,怎麼甩魚鉤。
魏之遠有心耍賴,故意顯得笨手笨腳,他哥只好捏起一條蚯蚓,把著他的手幫他裝在魚鉤上。
死不瞑目的蚯蚓上寄託著指縫間落下來的甜蜜,一絲一毫,魏之遠都抓緊時間地享受著。
魚漂靜靜地浮在水面上,太陽還沒有完全升起,魏謙想起三胖他爸蹲在水邊對他們說過的話,於是順口學給了魏之遠:「釣魚的樂趣在於期待的過程。」
魏之遠偏過頭看著他:「期待了半天,一條也釣不上來呢?白期待了,不是很失望?」
魏謙哽了一下,當年他們仨傻小子可沒有人問過這麼尖銳的問題。
他活動著因為睡眠不足而鏽住的腦子,最終沒能想出一句比較有教育意義的話,只好坦誠地據實相告:「那估計也挺鬱悶的,不過可能性不大,現在魚塘都是收費的,老闆做生意要是那麼不厚道,讓人一條也釣不上來,以後大家沒人來了。」
說完,魏謙伸了個懶腰,靠在一根石柱上:「不過真的一無所獲,你就當欣賞湖光山色了吧。」
天色漸陰,過了一會,竟然下起雨來,他們坐在涼亭裡,倒不怕被雨淋,帶著水汽的小風從湖面上捲來,魏之遠在旁邊看著魏謙睜著的眼一點一點地合上,最後一隻手扶在架在支架上的魚竿上,就這麼睡著了。
沙沙的雨聲漸漸連成一線,魚塘水面紛擾,更遠處是一片農田,連著天色一般的曠野茫茫。
雨幕逐漸遮眼,湖光山色都一起模糊了起來。
魏之遠早就收回目光,側頭專注地看著魏謙安靜的睡臉。
片刻後,他小心地伸出手,試探著碰了一下魏謙的頭髮,魏謙沒反應,真的睡著了。
魏之遠低下頭,並起兩根手指,輕輕地放在嘴邊,虔誠地親吻了一下,然後伸長了胳膊,把那兩根手指在魏謙的嘴唇上似有若無地劃過。
他的臉上終於蕩盡陰霾,露出一個有點孩子氣的笑容。
魏之遠伸直了腿,從早晨開始就一直困在心裡的、鬱結的黑暗,就像得到了短暫的安撫,乖乖地伏下了。
這一瞬間,他感受到了「期待的快樂」,也見到了真正的「湖光山色」。
魏謙是被手裡的魚竿突然一沉,尾部翹起來打到他的胳膊給驚醒的,他連忙抓住魚竿尾部,手腕用力一抖,站了起來,一圈一圈地收回魚線,一條足有兩斤左右的大魚時沉時浮的被拖上了岸。
魏謙回頭對魏之遠說:「給我魚簍,魚簍在哪呢?」
魏之遠彎下腰把插在岸邊泥裡的魚簍揪出來,接住了,魚就隨著吊鉤拆下掉進了魚簍裡,不安的活動了幾下,魏之遠把魚簍重新泡回水裡的時候,它的尾巴甩起了一連串的水珠。
魏謙清醒了過來,心情非常好,他做夢也夢見了魚,進而又被魚驚醒,可見是個好兆頭。
然而就在他重新坐回去,還沒來得及對自己的階段性勝利作出總結的時候,魏之遠開口了。
他在淅淅瀝瀝的雨聲中聲音平淡地開口說:「哥,我喜歡男的,你其實是知道了吧?」
第四十四章
魏謙八風不動地……把魚竿掉到水裡了。
他盯著淺淺的一截露在水面上飄著的魚竿看了一陣子,耳畔儘是細密如私語的雨聲。
好一會,魏謙才面無表情地蹲下來,挽起褲腿,一腳踩進水裡,把魚竿重新撈了起來。
魏之遠一直在旁邊以一種奇異的眼神看著他,魏謙餘光掃見,覺得他的眼神有種心如死灰的坦然和平靜。
兩人像演出啞劇一樣,誰也沒有出聲。
魏謙收回魚線和魚鉤,攥著尖銳的魚漂,好像無意識地在���邊鬆軟的泥土上亂畫,每畫一筆,他心裡就默數一下,似乎想要強制地把他亂跳亂蹦的血管都捋順、平和下來。
最後,泥土地上留下了一隻烏龜,背著一個格外大的殼,顯得沒精打采又忍辱負重。
魏謙感覺他胸口裡有一柄能呼嘯千古的利刃長刀,鋒利到能洞穿一切擋在他面前的東西,而此刻,前突後進的利刃無處安放,他聽見「噗嗤」一聲,感覺自己的肺被戳了個窟窿。
魏謙終於慢吞吞地坐了下來,抽出幾塊紙,緩緩地擦著魚竿尾部沾滿的水珠,過了好一會,他才刻意地把聲音放柔和了一些,以便讓自己聽起來很講理地開口說:「你是存心想氣死我,是吧?」
魏之遠沉默不語。
魏謙:「我想聽聽你是怎麼想的。」
魏之遠以那種奇異的目光盯著他看了好一會,才輕聲說:「有一個人,我喜歡他好幾年了,沒敢讓他知道,也沒敢讓任何人知道,每天……每天刻骨銘心一次——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哥,你的論調跟我高中教導主任一模一樣,你就是想說,再刻骨銘心的感情,也會時過境遷的對吧?」
魏謙到了嘴邊的話被他搶了,只好鬱鬱閉嘴。
魏之遠深吸了一口氣,露出了一個古怪的笑容:「可一個人始終是由過去堆積起來的,你讓誰獨一無二地住進你心裡過嗎?你試試就知道,心裡裝著他一個月,那一個月就是他的,裝他一年,那一整年就是他的,後來就算真的時過境遷了,又怎麼樣呢?他都已經成為我的一部分了。」
魏謙仔細體會了一下,感覺自己心裡裝滿了雞毛蒜皮的生計,亂七八糟得就是個活禽市場,哪還放得下人那麼大的事物呢?
他只好煞風景地強調:「你的一部分是由細胞和組織構成的,跟另一個碳基生物沒半毛錢關係,別拿這種狗屁不通的比喻搪塞我——現在你說完了?」
魏之遠無可奈何地看了他一眼,點了點頭。
魏謙忍不住偏頭避過魏之遠的目光,他不知道魏之遠是不是和別人說話也這樣,反正魏之遠跟他說話的時候,總是喜歡直視他的眼睛,而這種長時間的、無遮無攔的對視,會使再柔和的目光也變得咄咄逼人,讓人有種好像無路可逃的錯覺。
魏謙從兜裡摸出一根煙,點著了,嘆氣一樣地呼出一口白煙來,他的脾氣似乎已經被時光與漫長的拉鋸磨平了,只有字裡行間能聽出些許鬱結的憤怒:「那我說說我是怎麼想的吧,我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你就算是說出花來,我也是這個態度。魏之遠同學我建議你出門打聽打聽,十個家長九個不會接受,剩下一個多半不是親生的……」
他說到這裡,完全是順口,話音落下才反應過來自己方才禿嚕出了什麼,魏謙當即愣了一下,有些尷尬地蹭了蹭鼻子……這個好像也不是親生的。
過了一會,兩人突然一起笑出了聲,方才顯得有些緊繃的氣氛倏地就消散了。
魏之遠:「哥,你是氣糊塗了嗎?」
魏謙:「可不是麼,我跟你說,這要是宋小寶,我早大耳刮子糊上去了,什麼時間不時間的,一鎯頭打你個失憶青年,一年一個月?一秒你都甭用記住。」
說到這,魏謙緩緩地收斂了笑容:「你從小心裡比她有數,現在也這麼大了,我不會用對付她那一套對付你。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其實我小時候也走過一段歪路,現在想起來,有一部分原因是沒辦法,還有些……大概是不服氣吧。當時是你三哥和……和麻子哥把我拉回來的,現在我能把你拉回來嗎?」
片刻後沒能等到魏之遠的回答,魏謙:「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小遠,一輩子眨眼就過去了,好好活著尚且困難那麼多,你幹嘛要特立獨行地給自己找不自在?」
魏之遠沉默不語,他突然沒了先前那些試探的心情,心口湧上了說不出的難過。
他寧可不明真相的大哥跳起來給他一巴掌,或者乾脆像兩年前命令小寶剪頭髮那樣,說一不二地命令他明天就去找個女朋友回來。
……也不願意看見他像個真正的成年男人那樣,帶著無法形容的無奈,掏心挖肺地說這種話。
魏謙伸手撚了一下指尖沾上的雨水:「小遠,你這樣是不是因為我沒開個好頭?是不是因為我一直……」
魏之遠截口打斷他:「哥,你別說了。」
魏謙目光茫然悠遠地望著水汽迷離的水塘表面:「我對不起你們。」
他忽略家人良多,以至於竟然不知道魏之遠經歷了一場怎麼樣光怪陸離的青春……
然而他實在是已經盡力了。
那一刻,魏之遠幾乎想要不顧一切地撲上去抱住他,想把心裡積壓的渴望一股腦地都倒出來。
然而話到了嘴邊,他又堪堪地忍住了,那千鈞重負的心意被發絲一般細碎的理智險而又險地拉了回去,最終,分毫未露。
還不是時候,他同手背上的青筋一同繃緊的心弦這樣告訴他。
後來,雨停了,魏謙他們拎著魚簍和幾斤小鯽魚往停車的地方走去。
方才晴好的天上傾瀉出大把的餘暉,把魏謙的影子長長地拖在了地上,魏之遠一直低著頭,亦步亦趨地跟著那條被拉得細長扭曲的影子。
每走一步,他就發洩一樣地在心裡說一次:「我喜歡你,我喜歡的就是你。」
他一直就這樣默默地念叨了一路。
魏謙把漁具丟進後備箱裡,突然想起了什麼,轉過身來,猝不及防地問魏之遠:「你喜歡的那個是個什麼人?幹什麼的?」
魏之遠沒預料到他突然這樣問,一時間險些把心裡念叨的話脫口而出,他狠狠地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臉色蒼白,近乎瞠目結舌,一時沒了詞。
看起來就像驚恐地維護著什麼人。
魏謙見了他這幅樣子,心一下就沉下去了,他還真沒看出他這弟弟竟然還是個癡情種子。
一股沒來源的怨氣突然撞了他一下,魏謙想,那個人呢有那麼好嗎?值當你在我面前也這樣百般推脫維護?
他忽然難以抑制地懷念起當年窮困潦倒的舊時光起來,起碼他們在一起相依為命的時候,中間沒有夾雜著這個語焉不詳的、幽靈一樣無處不在的「外人」,他們都乖乖的,傻乎乎的,無時無刻不需要著他這個哥哥。
直到這時,魏謙才意識到,總有一天,這些小崽子終於會長大成人,等他們翅膀硬了,就各自遠走高飛了。
他緩緩地把車開出郊區的曠野,青色的麥苗隨風如浪,他感受到了一股濃重而綿延不絕的孤獨。
從那以後,魏謙和魏之遠就不由自主地共同迴避了這個話題,他們保持了表面上的平和,內裡卻彷彿僵持住了,誰也說服不了誰。
就這樣又別彆扭扭地過了小半年。
那天魏謙正在他自己的辦公室裡就著半杯茶水,急急忙忙地吞了一個麵包當早飯,準備開始一整天的工作,三胖卻突然進來了:「謙兒,張總來了。」
魏謙一時沒反應過來:「哪個張總?」
「就那個,」三胖比比劃劃地說,「就咱倆做第一個項目的時候那個名義股東,時刻端著他要上天造宇宙飛船範兒,實際比我還能嘴炮的那貨——熊哥讓咱倆過去一趟,你快點。」
張總這個人,是個高貴冷豔的人來瘋,一開始極端不好接觸,無時無刻不把裝逼奉為人生第一要務,然而有些瞭解之後,又能讓人發現他來自外星一般不食人間煙火的本質。
他是構想的腦殘粉,每次一談「構想」倆字,他就激動得屁股上長釘子。
此刻,張總正熱情洋溢地在老熊辦公室發表他的個人演講,其高談闊論沒人插得進嘴,頗有些熊夫人的風格——多虧老熊早被他的敗家老婆調教出來了,竟然一點不耐煩的意思都沒有。
張總一看見魏謙和三胖,連忙站起來,無視魏謙伸出來的手,假洋鬼子似的給了他一個擁抱,衣領上的古龍水毫無徵兆地鑽進魏謙的鼻子,簡直和芥末油異曲同工,躥鼻子醒腦,魏謙急忙後退半步,扭臉打了個噴嚏:「張哥不好意思,我這兩天有點感冒。」
張總包容地笑了笑,繼而無視了三胖打算入鄉隨俗地給他個擁抱的動作,雙手抓住了三胖的豬蹄,上下搖動了一下:「談總!」
三胖的面部表情有點癱,感覺自己受到了某種微妙的歧視。
張總特地遠道而來,是想找人合作一個新的項目,據說是個C市的海景度假別墅項目,老熊可行報告還沒翻出目錄,張總已經吹得天花亂墜了。
魏謙忍不住打斷了他一下,提出質疑:「對不起張哥,我得打斷一下,我聽說那地方前些年整個地區崩盤過一次,你覺得那邊真的還有投資的價值嗎?」
「好問題。」張總一拍椅子扶手,「魏總這種一針見血我最欣賞了。但你知道,現在對於有錢人而言,什麼才是不可複製的嗎?是健康和環境啊!稀缺的海景和負氧離子就是我們的噱頭,我還打算利用附近的經濟林開發一些度假娛樂項目,用類似療養旅遊的模式來做成這個項目,年資金回報率我算過了,能高達200%以上,你們信不信?」
老熊低頭沉默不語,魏謙和三胖彼此對視一眼,都從對方的表情裡看到了同一個資訊:傻逼早晨起來又忘了吃藥了。
上次他們看中了張總的人脈,和他合作過一次,嚴格來說那次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張總的注意力依然主要集中在商業街上,對於周邊住宅的樣式沒有搞太多的么蛾子。
但即使是這樣,「這個人不靠譜」的概念卻已經深入了魏謙他們心裡。
這個人出身好,資本雄厚,隨意他糟蹋,導致他一身理想主義者的臭毛病。
他的情商極端的低,也是極端地不會看人臉色,這當然都不要緊——最致命的,是他在用寫小說的想像力和畫漫畫的浪漫做實實在在的生意。
過去的合作夥伴既然已經找上門來了,老熊就算純為了給面子,也是要帶人跟著張總走一趟。
第二天,正趕上國慶假期,他們毫無休假概念地登上了飛往C市的飛機。
就在飛機起飛前那一瞬間,魏謙心裡忽然「咯噔」一下,他當時沒往心裡去,因為起起落落失重超重的時候人總不會太舒服的。
再一次地,他忽略了自己神奇的預感。
當時魏之遠正在學校,小寶正呲牙咧嘴地做著怎麼也做不明白的作業。
麻子媽來他家串門,正在宋老太的幫助下纏一捲毛線——她希望能在冬天到來之前,給每個人織一副毛手套。
麻子媽被燙傷的手不很利索,掰不開齒,行動也遲緩,別人織毛衣是幾根簽子捉在手裡上下翻飛,她卻只能一針一針努力地織,時而會靠上的線會掉下來,時而會因為漏一針而破一個小洞。
小寶有一搭沒一搭地對她們說話:「我高考想走藝術特長生,露露姐說應該可以,這樣文化課要求能低一點。」
宋老太毫不客氣地說:「低一點你就考得上啊?起碼得低好多。」
「你們別老潑我涼水!」小寶不幹了,過了一會,她又弱弱地補充說,「確實是低好多……哎,姨,您嘴唇都幹爆皮了,我給您倒杯水吧?」
宋老太連忙制止她:「你別起來了,我去就行了,你啊,只要學習好就行了,家裡的事不用你管。」
她說著,把撐著的毛線掛在椅子背上,行動顯得有些遲緩地站了起來,還對麻子媽笑了一下。
突然,宋老太揉了揉太陽穴,低聲抱怨了一句:「一起來起猛了,還有點頭暈。」
小寶頭也沒抬地說:「你可能有點低血壓,多吃點就好了。」
宋老太:「我怎麼也比你那點貓食吃得多。」
小寶嘴角耷拉下來:「我舞蹈老師不讓我吃,她老嫌我胖,我哪裡……」
她的話音隨著一聲巨響戛然而止,宋老太不知怎麼的被椅子腿絆住,這個腿腳向來利索的老太太竟然一個大馬趴就結結實實地摔在了地上。
她就再也沒能爬起來。
魏之遠當時正獨自在一間教室裡,他最近自己向學校申請組建了一個「網絡安全與程式研究」的小社團,剛剛招進幾個人,還沒成規模,他想把自己以前的東西拿出來當範例,正在調試中,就接到了小寶的電話。
他一個「喂」字還沒落下,小寶的哭腔已經突兀地從電話裡傳了出來,魏之遠仔細分辨了兩遍,才弄明白她哭聲裡夾雜的那句話是「大哥的電話為什麼關機了」。
魏之遠皺皺眉:「他現在應該還沒落地,你怎麼了?別哭。」
宋小寶難以自抑地抽噎了好幾下,斷斷續續,艱難地把事說明白了。
魏之遠聽她說了一半已經收拾東西站了起來:「別動她,你叫救護車了嗎?還沒有?快叫,冷靜點,哭什麼哭?客廳下面的櫃子裡有幾千塊錢現金,一會救護車來了你別忘了把錢帶在身上,聽見沒有?等我這就過去……」
宋老太很快被送到了醫院,魏之遠趕到的時候,她已經被推進手術室了。
小寶抬起兔子一樣的眼睛,茫然地抬頭看著魏之遠。
魏之遠試著撥了一遍魏謙的電話,開機了,但是沒人接。
魏之遠輕輕地吐出口氣來:「跟我說說,當時到底是怎麼回事?」
宋小寶找到了主心骨似的,交代了前因後果。
魏之遠沉默地聽完,預感宋老太不是小毛病,這次恐怕不能有驚無險了。
他站起來拍了拍小寶的頭:「行,我知道了,沒事,別害怕,你在這守著,我出去再取點錢。」
小寶含著眼淚目送著他的背影,感覺他越來越像大哥了。
魏謙已經到了C市,找旅館落了個腳,就直奔項目地了,手機落在酒店了,錯過了魏之遠好幾個電話。
張總和老熊在前面走,張總在那吹牛,什麼這要建一個高爾夫球場,那裡要建一個溫泉療養院,哪還要引進也不是日本還是韓國的抗癌理療,整一個天花亂墜。
他們走到高處往下眺望,發現半山腰上大片的經濟林中,人煙稀少,幾乎看不到幾座房子,只有再往下一點,還有農民在種地。
三胖和魏謙落後兩步,魏謙低聲說:「我看都多餘來。」
三胖嘆了口氣:「別介,好歹就當療養了,還能買點新鮮水果回去。這個張哥的異想天開症怎麼比上次見他還嚴重了?」
魏謙笑了一下,剛要回答,前面的老熊忽然一偏頭,魏謙就看見了他側臉的表情。
魏謙的表情突然僵住了,好幾年風裡來雨裡去的合作,他已經能通過老熊的神態判斷他在想什麼了——怎麼,這是幾個意思?老熊難道聽不出這個項目不靠譜?
他的意思難道是,這一回要帶領大家往火坑裡跳?
然而老熊畢竟沉得住氣,即使神態和表情已經在熟人那裡出賣了他,但當天仍然端著,沒有給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答覆,只跟張總推脫說要再研究一下。
魏謙正心急如焚地想看看老熊腦子裡哪根筋搭錯的時候,他看到了自己攤在酒店床上的手機那十來個未接。
宋老太是突發腦梗,漫長的手術時間過去以後,她被推了出來,直接轉到了重症監護室,生死不明。
魏之遠方才取來的錢正好派上了用場。
魏謙當晚就訂了夜航的機票折了回去,直奔醫院,只來得及匆忙囑咐三胖一句話:「千萬拉住了老熊,別讓他鬼迷心竅。」
第四十五章
魏謙淩晨三點半到家。
他站在門口捏了捏鼻樑,先對著家門深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吐出來。漫長的歸途中,他一路的焦灼漸漸平息,取而代之的,是發自肺腑地不想推門進家。
當然,不進去是不行的。
輕輕地打開門,客廳裡柔和的閱讀燈卻亮著,魏謙一愣,往裡一探頭,看見魏之遠正坐在沙發上翻看一本現代漢語字典一樣肥碩的書,臉上掛著一對明晃晃的黑眼圈,抬起頭對他笑了一下。
魏謙壓低了聲音問:「怎麼還不睡?」
「等你呢,」魏之遠說著站起來,「吃飯了嗎?沒別的了,家裡沒別的了,我給你煮一碗速凍餃子吧?」
魏謙:「等我幹嘛,我自己想吃不會煮?」
魏之遠頭也不回地燒上水:「我怕你著急。」
魏謙坐了四個多小時的紅眼航班,而後從機場趕回家,又是將近一個小時的車程,渾身每一塊肌肉都是痠痛的,按理說應該是疲憊至極的,但他對這種情況已經習慣了,幾乎不會往「累不累」那方面想。
可夜深人靜時,有個人在家裡等著他的這個事實,卻好像一下抽掉了他的脊樑。
魏謙一屁股在飯廳的小凳子上坐下了,弓起的後背貼著冰冷的牆面,襯衫皺成了一團,敞開的領口露出他顯得越發突兀的鎖骨和明顯的脖筋。
魏之遠把速凍餃子下到了沸水裡,轉身到了一杯水,捏了一小把蓮子心放在裡面泡開,遞給魏謙:「敗火的。」
魏謙沒骨頭似的靠在儲物櫃和牆的夾角中間,表情有點木然地問:「怎麼樣了?」
「進ICU了,今天剛做完手術,暫時不能探視,」魏之遠拉了一把椅子在他旁邊坐下,「今天我跟醫生聊了聊,他說過幾天情況稍微能穩定一點之後,每天可以安排半個小時的家屬探視時間,你別著急,著急也沒用。」
魏謙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啊,急也沒用,這是生死有命了。
他不出聲了,喝著蓮子心泡水,苦得他舌頭都麻了。
他老覺得宋老太是一個隨時準備炸碉堡的炸藥包,卻忘了這包炸已經七十多歲了。
前些年她不小心滑過一跤,可是除了把路人嚇一跳之外,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她自己又爬起來了。那件事之後,她還得意洋洋地自誇摔一跤不算事,年輕的時候她一個人能把兩百多斤的麻袋甩上車,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吹牛的。
為了省那幾塊錢,她每禮拜走出十裡地,到早市上背他們一週要吃的菜回家,十來斤乃至於二十來斤是常事,年輕小夥子拎起來都覺得壓手,她背著一路走回來,絕不坐公交車。
她的名言是:他們一毛錢也別想從我兜裡賺走。
……即使他們已經不缺錢了。
她的行為舉止幾十年如一日的粗魯,搬到相對高檔一點的小區,也沒有絲毫改變,這裡沒有一個惡老太整天跟她對罵了,她很快又找到了新的令他們兄弟三個丟臉的方法——闖紅燈,隨地吐痰,站在路邊擤鼻涕,擤完就把手往旁邊的路燈或者電線杆子上一抹擦。
有一陣子居委會倡導文明社區,打擊隨地吐痰的行為,抓到一次罰五塊錢,宋老太就跟人倚老賣老,撒潑耍賴無所不為,弄得人家文明紅袖箍後來見了她都躲著走。
魏謙雖然自己不捨得買什麼好東西,但並沒有不捨得給她花錢過,蜂王漿、西洋參、冬蟲夏草這些都給她買過,可惜老東西不領情,不光當面要罵他吃飽了撐的,背地裡轉手還會給賣出去——是從一而終、由內而外的不領情。
她認為那些都是給官太太和地主婆吃的,不該她用的東西,用了會折壽。
魏謙手頭逐漸寬裕,每個月給她五千塊錢的零用現金,她樂得見牙不見眼,拿著錢卻只會在手裡捂著,數上十幾個來回後鎖起來。
她每天挺胸抬頭,認為自己現在是有錢人家的老太婆了,然而這「有錢人家的老太婆」依然每天早早起床,在路邊擺攤賣煮玉米和茶葉蛋。
多麼沒出息、沒文化又沒素質的混蛋老「沒婆」啊。
她三天兩頭要給他找點不痛快,好像不拌幾句嘴就不是日子。可是他們一起湊合了這麼多年,魏謙幾乎想像不出,以後沒有她的日子可怎麼過。
「哥,趁熱吃吧。」魏之遠的一句話叫回了魏謙的魂。
魏謙看著那碗熱氣騰騰的速凍餃子,有點沒食慾,蓮子心苦得他倒了胃口,然而他還是勉強接過來,機械地逼著自己吃了進去。
「小寶呢?」魏謙問。
魏之遠輕聲說:「哭累了,睡了。」
魏謙不由自主地放慢了吃東西的速度,越發難以下嚥了。
魏之遠在旁邊繼續說:「最壞的可能當然就是……我還是跟你說說最好的情況吧。如果奶奶能搶救回來,最理想的,就是她能自己走路,生活勉強能自理——恢復到以前那樣是不可能的了,即使這樣,她的腦細胞也會加速衰老和萎縮,可以用藥拖延,但也只能維持現狀或者越來越壞,不可能修復了。」
魏謙不是科班醫學生,但是他生科出身,專業多少有一些重疊的地方,一聽這話,立刻就明白了。
那樣下去,最終的結果不外乎就是癡呆。
他徹底不想吃了,把碗筷放在一邊。
魏之遠條分縷析:「要是那樣,她可能會需要一個人貼身照顧,其他的事我能做,但是有些太貼身的,我怎麼也不太方便,不能指望小寶,到時候可能需要雇一個保姆。哥,你看這麼辦行嗎?」
魏謙沉默良久,點了點頭:「這些話別跟小寶說。」
魏之遠:「我知道,她都嚇壞了。」
魏之遠就這樣,一點一點地告訴他現在的情況,分析討論應對不同的情況,以後應該怎麼辦,他平穩的語氣和態度讓魏謙滿心的迷惘也跟著一點一點地沉澱了下來。
魏謙終於從「難以想像」,過度到接受了這個現實,並且有了一條明確的思路——她死不了,不管以後變成什麼樣,他給她養老;要是她幸運地沒受罪就死了,那他就給她風風光光地送終。
魏謙突然抬起頭看著魏之遠,問他:「你說小寶嚇壞了,奶奶要是有個三長兩短,你不害怕嗎?」
魏之遠捧起他一隻手,輕輕地攥了一下,在魏謙沒有感覺到異樣之前,又飛快地鬆開,站了起來:「我要是也嚇壞了,你怎麼辦?」
魏謙愣了一下,魏之遠的站起來時的陰影被燈打得越發高大,好像把他整個人都攏在裡面。他想,這小子說話怎麼越來越戳人心了呢?
先開始的那段時間,魏謙整天往醫院跑去看宋老太的情況,老熊他們這次考察的時間格外長,這使得魏謙還要兼顧公司的工作。
幸好魏之遠徹底從學校搬回來住了,魏謙才感覺事情並不像自己想像得那麼捉襟見肘。
魏之遠就像是他多長出來的一顆腦子,每天替他想一多半的事,做一多半的事。
他就像一根逐漸長高長大的樹苗,替他撐住了一半搖搖欲墜的屋頂。
而幸運的是,宋老太到底還是沒有死成。她被搶救回來了,並且在十來天之後,離開了重症監護室。
她的話說不清楚了,但是還沒傻。
住進了普通病房,家屬就要開始繁忙了,小寶還在上高中,每天能擠時間到醫院來給送個飯已經需要她一路狂奔了……而這樣大的活動量好像刺激了她的生長,兩個月過去,她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褲子居然短了一大截,青春期之長挑戰了一回人類極限。
魏之遠課業重——不光是學校裡的,他可能還在學別的東西,魏謙每次看見他,他身邊都至少有一到兩本板磚一樣的書。
魏之遠兩頭跑,時間被縮水了一大塊,魏謙好幾次看見他半夜兩三點,打著哈欠坐在電腦面前補作業,有時候乾脆做著做著就睡著了。
魏謙就再也不讓他過來值夜班了,他在宋老太的病房裡支了一張行軍床,公司那邊只好請了長假,整整兩個月,宋老太出院。
沒辦法,自從宋老太恢復了神智,她就堅決地拒絕了護工。
而當魏謙試圖和她溝通「找個保姆照顧她」的問題時,更是遭到了宋老太的嚴重抗議,她用含著一塊豆腐的模糊的聲音連比劃再嚷嚷地讓魏謙明白了她的想法,她是在說:「我是個老農民,不是那種會使喚人的人。」
魏謙說:「哎喲我的老祖宗,您老人家還活在封建舊社會呢怎麼的?」
宋老太眼睛一瞪,嘰裡呱啦又嗷嗷一通。
她不會去想耽誤家裡人的時間,耽誤他們工作學習,損失的金錢可能更多,她雖然沒傻,可腦子也轉不過那麼多彎來了,比沒病之前還要固執。
魏謙苦笑一聲:「你真是欺負我不好意思跟你對罵,開始對我也倚老賣老了是吧?」
宋老太難得佔他一次上風,得意得要命。
魏之遠細心地剪她變形嚴重的指甲,輕聲細語地問宋老太:「不請保姆,以後你讓小寶伺候你擦身洗澡上廁所嗎?」
這一句話正中紅心,宋老太不出聲了。
小寶正好從外面進來,她氣喘吁吁地拎著兩個送飯的保溫桶,只隱約聽了個音,也沒弄清楚前後語境,就莽莽撞撞開口說:「我可以啊,我會!奶奶,沒事,我伺候你。」
宋老太沒搭腔,但也沒對「請保姆」的事鬆口。
隨著身體的垮塌,她有些無所適從,只好更加地因循守舊,這在她看來,這是個原則性的問題。
但她又怎麼捨得讓小寶照顧她呢?
小寶是被寵著長大的,對小姑娘來說,最繁重的勞動也不過就是洗個碗、拖個地而已。
照顧病人是世界上最艱難的事之一,宋老太給公婆老伴一干人等養老送終,她比誰都清楚。
最後,她硬是憑藉著自己「把兩百多斤的麻袋甩上車」的毅力,每天只要抓到空隙就鍛鍊,奇蹟一樣地能拄著枴杖扶著牆緩緩挪動了。
要說內心強大,還真是誰也沒有這個活過了四分之三個世紀的老東西厲害。
宋老太出院那天,魏謙原本要去接她的,結果當天晚上就臨時接到了他們公司行政辦公室的電話,說有個重要項目推進,現在要過「三會一層」【注】,請他務必出席。
這個重大決策要通過「三會一層」的規矩,是最近才修改的公司章程內容,施行時間不到半年,還是當時老熊從他爹那挖來的一個職業經理人提的,隨著他們的公司有了點起色和規模,終於到了規範化和高速發展的階段。
魏謙走出了病房,站在樓道裡,皺眉問:「推哪個重要項目?」
那頭告訴他:「就是上次C市的那個健康療養海景度假村項目啊。」
魏謙毫不客氣地問:「誰推的,腦子有坑是不是?」
對方聽出了他的語氣不好,遲疑了一下,戰戰兢兢地說:「是熊董。」
魏謙:「那你現在給我轉接他。」
行政:「他已經回家了……」
魏謙:「那談魚呢?」
行政:「可能還在飛機上,他說趕在明天開會前趕回來。」
魏謙低聲罵了一句,平時分管行政的是三胖,魏謙和他們接觸不多,他每天來去匆匆,話也不多,後來新招來的員工基本都有點怵他。
行政的小姑娘心裡更沒底了,小心翼翼地問:「那……我能不能請問一下,您明天確定能來嗎?」
魏謙嘆了口氣:「我家裡有點事,這個……」
「哥,你有事走你的吧。」魏之遠不知什麼時候出現在他身後,伸手撐著病房門,看起來就像是半抱著他一樣,「有我呢,你放心。」
魏謙看了他一眼,繼而沉默了兩秒鐘,最後,對電話那頭的人說:「行吧,我明天過去。」
他不是裝的,是真的挺放心魏之遠。
第二天早晨魏之遠正好沒課,他當天晚上留在醫院守夜,魏謙打了老熊兩次電話,對方都不應答,他只好跟魏之遠交代一聲,自己出門找老熊興師問罪。
老熊其實在家,裝孫子不接電話。
門也沒鎖,虛虛地合著,一推就開,魏謙一腳踩進去,險些給嗆個跟頭——老熊家裡燒著好幾柱高香,弄得四處雲山霧繞仙氣飄渺,都快趕上瑤池了。
那胖頭魚不知犯了什麼病,把沙發墊放在地上當蒲團,盤腿坐在上面,手裡捏著一串木頭念珠,正面對著牆坐著。牆上掛著的一副大楷抄的《般若波羅蜜心經》全文,經書抄得字大行稀,還挺佔地方。
魏謙沒弄清這是什麼節奏,打眼一掃就知道,熊嫂子不在家。
客廳地上不是香灰就是破破爛爛的沙發墊,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魏謙淌雷似的走進來,頭皮發麻地問:「怎麼個意思?你要皈依我佛嗎?我姐呢?」
老熊好像料到他要來,聽見動靜連頭也沒回:「外地旅遊去了——她要是在家我也不敢這樣,你坐吧。」
魏謙看著他指著的地上的另一個沙發墊,果斷無視了他,坐在了沙發上——他本以為老熊瘋了,聽出了他對熊嫂子十年如一日的畏懼,才勉強承認,他大概還沒瘋徹底。
「你到底是想……」
老熊抬手打住他的話音:「等會,九九歸一,我還有最後一遍經沒唸完,你等我兩分鐘。」
接著,他真的開始低頭念起梵語寫就的經文,乍聽起來就像某種奇怪的鳥叫。
魏謙等他唸完,才本著尊重別人宗教信仰的原則,耐著性子問:「你開始信佛啦?」
老熊:「不信。」
魏謙抽出一張餐巾紙堵住鼻子:「不信?不信你還把你家弄得跟個大煙館似的?你有病啊?熏死我了。」
老熊用跳大神一樣的口氣悠悠地說:「我在尋找一個寄託。」
魏謙擺擺手:「你愛怎麼寄託怎麼寄託,我不跟你扯這個淡,剛才有人打電話跟我說C市那項目,到底怎麼回事?」
老熊有些笨拙地從地上爬起來:「哦,那個,你等著,我給你拿項目建議書去——中國第一生態療養別墅群,非常有吸引力。」
「你別拿姓張的那套忽悠我,又不是要賣給我,」魏謙重重地往沙發上一靠,「你是吃錯了藥嗎熊英俊同志?你告訴我,這個什麼療養別墅、什麼癌症發現抑制中心的核心價值在哪?」
「我跟你說過了,隨著有錢人開始追求生活品質,健康是……」
「去你的健康,你知道什麼叫健康嗎?」魏謙截口打斷他,「他們追求的健康是有面子的運動,心理安慰劑一樣的有機食品,還有能喚起小時候記憶、讓他們有自己還年輕錯覺的鄉間農家樂——迷信保健的人有幾個不諱疾忌醫的?他們寧可練氣功,也不想聽醫生說你得了什麼癌需要怎麼化療!你是打算把這個項目做成臨終關懷俱樂部嗎?」
老熊啞口無言了片刻,然而他很快就鎮定下來:「山清水秀沒有污染,這樣的地方,題材只是個噱頭,山間溫泉和隱居的感覺,才是人們真正需要的,別墅不愁賣。」
魏謙說:「你純屬放屁,別墅項目本來就比別的風險大得多,就算真心想做,你不能在城郊蓋一排嗎?非跑到那窮鄉僻壤,連當地農民都少見,你打算賣給誰?」
老熊說:「賣給那些希望逃離城市,逃離所有壓力和思慮,想在山清水秀的地方過一段與世隔絕的日子的人。」
魏謙冷嘲熱諷地說:「希望與世隔絕地等死的絕症患者?」
老熊沒有笑,也沒有反駁,他只是靜靜地看著魏謙,回答說:「絕症患者家屬。」
魏謙先是覺得今天和老熊簡直沒法溝通,他剛想由著性子,對著這個常年包容、和緩的老大哥發一次火,而隨即,他察覺到一絲不對勁。
「等等,熊哥,你什麼意思?」
「她跟著你,吃了無數的苦,等你終於想對她好一點了,她卻沒時間了,」老熊的眼圈毫無預兆地紅了,他眼珠轉了轉,轉到那一面佈滿了佛經的牆上,表情逐漸平靜下來,恢復到某種麻木一般的漠然,他盯著那些經文與佛龕,彷彿輕描淡寫地對魏謙說,「你說家屬會想怎麼彌補呢?怎麼也彌補不來的。你說這個時候,要讓這個人窮盡財力,為他的家人打造一個人為的世外桃源,同時又能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各種商業服務,既能脫離現實,又能舒適地享受生活,他幹不幹?」
魏謙幾乎是震驚地看著他。
老熊說:「要是我,我就幹。」
作者有話要說:
【注】三會一層:指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
第四十六章
「不是,」魏謙有些不確定地說,「熊哥,你……你慢點,你什麼意思?沒事別拿這個嚇唬人好嗎?」
老熊不接茬,只是站起來拿過項目建議書,四平八穩地擺在魏謙面前:「這個你拿回去看看吧,這是明天要上會的材料。」
魏謙從來沒有成功地讀懂過老熊的眼神——當然,除了是老熊比較有城府之外,還因為他眼睛太小了,不貼面都看不清他的眼珠在哪。
可老熊一直是開朗好接觸的,想來生意人大多走南闖北,除了張總那種含勺子出身好的,少有性格特別古怪的。
然而此時,魏謙第一次從他身上感覺到了那股快要瀰漫到空氣中的拒絕。老熊坐回地上的沙發墊,有點艱難地盤起腿,對著滿牆的佛經畫了個十字。
他似乎企圖讓自己看起來不可理喻,企圖讓自己看起來有點瘋。
有的時候,大概瘋了就好了。
魏謙猶豫了一下,沒再說什麼,拿起了那份建議書,起身走了。
商務建議書噱頭十足,大概很能打動人,可是打動不了魏謙。
因為他們早期的幾個項目沒那麼多人手,三胖學歷不行,文字不通順,老熊又要負責弄錢又要負責談判,所以像這種做建議書和可研報告的工作,十有八九是出自魏謙的手的。
這些沒煙的東西一個個是怎麼吹出來的,他心裡全都有數。
不過刨去噱頭,這也就是個普普通通的別墅項目,魏謙也實在說不出它哪裡不好來。
回去的路上,他捏著那份項目計劃書,想了一路——魏謙腦子裡依然總會出現那天他們仨跟著張總登上小山坡時,居高臨下地望著下面經濟林的情景。
那情景到底有什麼問題?魏謙仔細推敲了好幾遍,都想不出來。
他畢竟還是年輕,經驗太有限了。
到最後,魏謙心裡也只有一層淺淺的陰影,他說不出那層陰影蒙在哪裡,只是內心有種抗拒,覺得這個項目,能不做,就最好不做。
但老熊那邊……
第二天早晨出門前,魏謙終於成功地堵到了三胖,三胖坐他的車一起去公司。
「咳,這事啊,你別提了。」三胖糟心地擺擺手,每條肥肉的縫隙裡都寫滿了糟心。
「當時你不是著急走嗎,就留下一句說讓我攔著他,也沒說明白了讓我怎麼攔——我平時接觸業務不太多,您老人家好,『咣當』一撂挑子,給我留下這麼大個任務,好懸沒給我砸傻了——是啊,我攔了,可熊哥問,我也說不出個子丑寅卯來,壓根攔不住。當時我想著不行啊,於是就出了個邪著。我就給嫂子打了個電話。我本來想著,這不就跟上西天請如來佛祖一個效果麼,結果電話一通,我剛把這事前因後果交代明白,那頭就哭上了。」
魏謙:「誰?嫂子哭了?」
三胖呲牙咧嘴地點點頭:「可不是麼,咱陳露姐姐那可是如來神掌的一代宗師啊,好麼,她哭?我一聽,這不得是天塌下來的事啊,可把我嚇壞了,就問是怎麼回事,結果……唉,還真是……」
魏謙把車停下等紅燈,緩緩地問:「她什麼病?」
「合著你知道了啊?」
魏謙:「聽了個音,老熊沒跟我說清楚。」
三胖嘆了口氣:「他們倆結婚這麼好些年了,一直也沒孩子,也不是不想生,嫂子一直懷不上。她可能是天生的,打挺年輕的時候開始,肚子裡就長瘤子——就是生孩子的地方,你知道的吧?前後做了兩三次手術,但是擋不住復發。最保險的辦法當然是切了,但是她本人不同意,還是想要個孩子。」
怪不得……
「嫂子以前不是跳舞的嗎,她們幹那個看著輕鬆,實際是挺耗費體力的,她又是那種抓尖好勝的性格,身體實在撐不下去了才只好辭職。熊哥那時候說,斷後就斷後了,沒什麼了不起的,讓她切了,她不肯,最後倆人說好了養兩年,要是能有孩子那就最好不過,沒有也是他們兩口子的命,就不打算要了,讓她去做手術。結果年前去醫院一查,大夫說完蛋,可能癌變了。」
紅燈過去,後面的車不耐煩地按了個喇叭,魏謙才回過神來,把車開出去:「確診了嗎?」
「確診了,要不老熊那天怎麼哭得跟個真狗熊似的了呢?」三胖的聲音低了下去,他停頓良久,才接著說,「這個病,有人得了以後二三十年都不死,和沒得一樣,有人可能一兩個月就擴散了,陳露是屬於那種……運氣比較不好的——謙兒,反正就這麼個事,你怎麼說?這項目一會過會,你是簽字還是不簽吧?」
魏謙知道,自己沒有任何理由不簽這個字了。
少年喪父,中年喪妻,老年喪子——三大悲,魏謙自己趕上一個,麻子媽趕上一個,眼看著老熊可能很快要趕上另一個。
這到底是活著不容易,還是他們命比較苦呢?魏謙實在不想知道這個答案。
小時候,他想,不能沒有父母,如果連這一點感情寄託都沒有了,那還不如死了。
過了幾年,他想,不能沒有錢,如果連起碼的生活保障都沒了,那還不如死了。
後來,他想,不能沒有尊嚴,如果人人都看不起他,那還不如死了。
然而他一件一件地失去過它們,有些後來又得到了,有些再也找不回來了,他卻依然活著。
大概是車裡的氣氛太壓抑了,三胖看了他一眼,試圖活躍氣氛,就說:「前兩天,我聽張總那個大忽悠跟我侃偽科學,他說有那麼一條江湖謠言,體溫低的人就容易得癌症,體溫高的人就容易得心血管疾病,人類兩大殺手,咱們遲早都得投入其中一個的懷抱。我一聽,這江湖謠言原理上是哪也不挨,可道理上還真就那麼回事,沒災沒病活著,咱們都趁早想開點吧——你們家老太太沒事了吧?」
魏謙沒有回答,好一會,他答非所問地說:「我要是也有那麼一天,就去一個誰也找不著的地方自己等著死,不治。」
三胖沒當回事,哈哈一笑:「你現在當然這麼說。」
「以後也一樣。」魏謙平穩地把他的車滑進公司車庫,「那倆孩子將來也大了,到時候他們該結婚結婚,該工作工作,我給人家討什麼厭呢?為難的事,到我這一輩就讓它們都到頭得了。」
三胖側過頭看著他,黯淡無光的車庫中,他覺得魏謙的臉上帶著某種深沉的自嘲。
魏謙停穩車,熄火,嘆了口氣:「不過那是以後的事了,現在我還得給他們掙錢去。」
三胖忽然覺得他這話說得不對勁,他考慮到了弟弟妹妹將來組建自己的家庭,卻獨獨把自己抽了出來,放在了一個冷眼旁觀、形單影隻的位置上,似乎他從潛意識裡就沒想到自己會娶個老婆,自己也會有個孩子。
「謙兒,」三胖忍不住開口提了一句,「你是不是也該考慮成家,或者起碼找個女朋友了?」
魏謙一愣。
「你總不能老單著啊,小寶小遠眼看就都大了,你現在也沒什麼負擔,不正該找一個嗎?再說,你們家老太太那樣,以後她也需要多個人幫你一起照看著。」
魏謙飛快地皺了皺眉,心理上依然有些抗拒,然而隨即,他又想,這也是啊。
人總得有個家吧?
家裡總不能只有自己一個人吧?
這天的會議很順利,魏謙沉默的縱容給老熊掃清了最後一處障礙,老熊的提案很快就被通過了。
老熊推進的力度極大,半個月之內,就先後和張總簽了框架協議與合作協議,一個月後,項目公司和操盤管理團隊正式成立,勘探、規劃、拿地等等的前期工作全都有條不紊地展開了。
C市那頭忙起來了,項目前期需要人坐鎮的地方太多,一般操作層面上的事,三胖不怎麼插手,都是老熊和魏謙在跑,眼下倆人誰也不比誰強,各自家裡一人一個病人,只好輪流兩地亂竄。
老熊那裡好在熊嫂子肯用保姆,而魏謙這邊,好在還有魏之遠。
宋老太出院那天,魏謙開完會趕回來,正好看見出租車停在樓下,小遠背起宋老太,小寶在後面拎著東西,替他們叫電梯開門。
從遠處看,一個個都像大人了。
連小寶也說到做到,真的嘗試著照顧起宋老太來,儘管她一開始笨手笨腳,但時間長了經驗也慢慢成熟了起來。
小遠呢?
小遠似乎總是有用不完的精力,魏謙不知道他覺夠不夠睡,正常上學受不受影響,可是旁觀看來,家裡的事,外面的事,魏之遠的學業和全家人的生活,好像都被他兩隻手兼顧過來,至少在魏謙眼裡,魏之遠是遊刃有餘的。
又經過了一次和當地政府漫長的談判和拉鋸,魏謙出差兩個多月回家。
倆孩子好像都去學校了,宋老太在屋裡打盹。
眼看著快要中午,魏謙把行李箱往門口一扔,就開始洗菜做飯,菜還沒切完,魏之遠回來了。
他走進來說:「哥,我來。」
魏謙:「沒事,我來吧,今天正好我回來了,你也歇一天。」
魏之遠不和他爭辯,在他身後站了一會,而後找了個機會,猝不及防地從他背後伸出手,夾住他的胳膊肘,捏住菜刀刀背,搶過來了。
魏謙:「……」
魏之遠貼著他耳邊,低聲抱怨了一句:「都說了我來。」
大概是離得太近的緣故,那聲音一直鑽進了魏謙的耳朵裡,他情不自禁地激靈了一下,連忙有些不大自在的側頭躲開。
魏謙在旁邊轉悠了幾圈,妥協說:「你來就你來吧,還有雞蛋嗎?我弄點蛋湯當喝的……哎我操,魏之遠你要造反嗎?」
魏之遠一把從後面抱住他,搖搖晃晃地讓他雙腳離地,用搬大件傢俱的姿勢,不由分說地把他從廚房裡請了出去。
「我還正打算逼宮篡位呢。」魏之遠放下他,有點得意地說,「就先從禦膳房下手。」
這並不像是魏之遠慣常說話的口氣,魏謙一愣,靠在門邊上打量著他。
他出差這一趟回來,魏之遠身上好像產生了某種說不出的變化,魏謙發現,自己不在家的這段日子,這本該累得像狗的小子就好像煥發了某種生命力。
他不像以前那樣,總好像有些心事似的,雖然臉色上能看出魏之遠的睡眠不足,但他的精神卻是很好的,甚至變得有點開朗了起來。
「我看不行還是請個鐘點工吧,不讓奶奶看見,每天就替你們做個飯打掃一下就好了。」魏謙頓了頓,又問,「學校呢,忙不忙?」
「還行。」魏之遠心情不錯地說,「我們的社團最近在做一些常用的小工具,上禮拜拉到贊助了。」
「贊助?」魏謙一愣,「你怎麼沒跟我說?」
魏之遠回頭看了他一眼:「然後伸手跟你要錢?」
魏謙覺得他說得太赤裸裸,於是乾咳一聲,故作矜持地說:「那倒不是,還得看你們做的東西有沒有投資價值。」
魏之遠把切好的菜倒進鍋裡,在一片油花「呲啦」聲音中,他說:「你再有本事,我也不可能總靠你,男人總得自己走出去轉轉。」
不然以後我拿什麼照顧你?
當然,後半句魏之遠嚥回去了。
「得了吧,小崽子,說你胖你還喘上了。」魏謙笑起來,「跟哥說說,你怎麼找的贊助?」
魏之遠愉快地告訴他:「我們一開始嘗試登廣告,不過後來發現廣告開銷太大,效果也不怎麼樣,就停下了,然後又在網上追蹤目標投資者的聯繫方式,直接把廣告發到他們的郵箱裡,還打過一陣子非預約電話,可惜郵件經常被遮罩,非預約電話大多數時間也會直接被人家的前臺截下來。這樣也不行,最後我們就一家一家地上門。」
魏謙笑不出了——幾個大學生,貿然上門推銷自己的團隊請求贊助,得挨人家多少白眼啊?
別說是那些大老闆,就是他本人,碰見這種,估計也是頭都懶得抬,就直接讓人給擋出去的。
「求人是挺難的。」魏之遠報喜不報憂地說,「不過好歹結果是好的,總算求到了。」
中間種種經歷,魏之遠舉重若輕,並沒有描述自己的感受。他一直是那種非常出類拔萃的優等生,也許智商很高,但是他的逆商一直不怎麼樣,他比同齡人聰明沉穩得多,然而承受挫折的能力卻與這一切並不匹配——在這方面,他甚至比不上從小被大哥罵到大的小寶。
魏之遠極度痛恨那種無能為力的感覺,那漫長的、挨家挨戶帶著同一套東西,磨破嘴皮一樣上門推銷尋求投資的日子,幾乎讓他回憶起自己塵封在記憶深處中那流浪的童年時代。
他孤立無援,卻沒有告訴任何人,就這麼沒頭蒼蠅一樣地沉潛了將近一年,當中,他們的社團活動由於種種困難不得不停滯,很多人相繼離開了,魏之遠獨自承擔著壓力,與此同時,他家裡還有個病人宋老太需要照顧。
他還要小心翼翼地不在大哥面前露出端倪——只要他開口,這個贊助,魏謙一定會給,魏之遠心知肚明。
但那有什麼意義呢?
當全部的負面感情全都被激發起來,一起沉甸甸地積壓在他心裡時,魏之遠曾經幾次想要放棄,他第一次發現,承受這種看似懦弱的姿態,不比任何事簡單。
可是大哥那些年不是一直在承受嗎?
那些日子,魏之遠幾乎是靠著錢包裡那張,魏謙少年時代的泛黃的舊照片才熬過來的。
魏謙無法言喻地心疼起來,就像他第一次看見小寶給宋老太洗尿盆一樣心疼。
可他表達不出來,沉默了好一會,才只能像毫無創意地像誇獎小寶那樣,格外晦澀難解地誇了魏之遠一句:「你啊……你要是願意找個女朋友回來,哥現在就都能瞑目了。」
魏之遠平靜地說:「那不可能的。」
「一點戲也沒有麼?」魏謙幾乎是帶著期冀地看著他。
魏之遠避開了他的目光,放鹽放調料,語氣卻是堅定的:「嗯,一點也不可能。」
「為了你那個男狐……」魏謙頓了頓,臨時別彆扭扭地改口說,「男……心上人?你別看現在拉個贊助千難萬難,如果你真要走這條路,比你拉贊助可困難多了。」
魏之遠似乎覺得這個「男心上人」的說法很有趣,他不知想到了什麼,嘴角難以抑制地微微提了起來:「知道,這就是個開始。」
魏謙頓了頓,換了個角度:「那人家願意接受你嗎?」
魏之遠看了他一眼,有些遲疑地說:「還不知道,可能……可能有些不能接受吧?」
魏謙好像立刻找到了突破口,放緩了語氣,擺出耐心勸解的架勢來:「男的到了一定的年紀,都會想娶個女的做老婆,就算你不想,別人也會想,你現在還小,不考慮那麼遠,如果將來你喜歡的人結婚了,你要怎麼辦?」
魏之遠停下了一切的動作,僵持了一會,他落寞地低聲說:「哥,你別挖我的心行嗎?」
魏謙無可奈何地看著油鹽不進的魏之遠,心裡想起老熊說自己的一句話——這是王八吃秤砣,鐵了心了。
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熊嫂子,兩個月前,魏謙找了個機會,帶著小寶去探望過她一次。
熊嫂子不肯做化療,她不知怎麼說服了老熊,而老熊竟然就默然放任了。
熊嫂子終於心滿意足地聽小寶叫了她一聲「乾媽」,她看著小寶的時候,總是忍不住暢想,如果自己能有一個孩子,如果自己能再多活幾年,是不是也能看見自己的孩子長到小寶這麼大了呢?
她看著這缺心少肺的小丫頭,就忍不住暢想起自己那虛無縹緲的未來。
臨走的時候,熊嫂子對魏謙說:「有的孩子天生就愛美,有的孩子天生就不在乎,這都是天性,像貓吃魚狗吃肉,你僅憑著自己的喜好,強按著愛美的孩子讓她去剪頭髮,跟逼著不愛美的每天早起一個小時化妝都是一個道理——扼殺別人的天性,你覺得你對,可你知道自己有多殘忍嗎?」
魏謙知道,這是她的肺腑之言。
陳露女士,她也天性熱愛美,天性熱愛藝術,熱愛她的工作,熱愛家庭和孩子,也熱愛生命,然而才走到半途,一切就都被強行打斷,畫上了休止符。
她跟魏謙說這話的時候,眼圈分明是紅的。
那小遠這樣,這麼頭撞南牆不回頭地喜歡一個男人,也算是天性嗎?
魏謙不知道,然而他心緒幾次起伏,終於在自己的底線之上,又喪權辱國地給魏之遠退了一格。
他悲哀地發現,自己的底線就像是褲子,總有一天會給這些小崽子扒得褲頭都不剩。
魏謙說:「愛怎麼樣怎麼樣吧,我不管你了,該說的話我都說了,你以後別後悔。你那個……那個誰——嗯,就那個誰吧,你明白我的意思,是香的是臭的也不知道,有機會你讓我見一見。」
魏之遠立刻就領會了他讓步的意思,然而聽見後半句,又一時間不知道自己是該高興還是怎樣,心裡糾結良久,終於應了一聲:「哎。」
魏謙還要再說,不過就在這時,他的話題被打斷了,外面有敲門的聲音。
魏謙應了一聲,打開門,卻看見外面站著一個陌生的中年女人,她燙著一頭焦黃的小捲髮,就像頂著一個行動的雞窩,眼珠渾濁,眼角細紋叢生,可見是有些年紀了,身上穿著一件不大符合她年齡、顯得有些豔俗的碎花杉,拎著一個隨處可見的假名牌包。
魏謙問:「你找誰?」
對方見了他,也是愣了一下,隨即立刻說:「哦……我可能是敲錯門了,那什麼,王秀紅是住這樓嗎?」
「王秀紅」是麻子媽的名字,魏謙皺了皺眉:「你找她有什麼事?」
第四十七章
從外表上看,魏謙當然屬於「人模狗樣」的那種人。
他個高腿長,從小練就的端架子功夫,如今已經到了收放自如的地步。
平時在公司裡,他顯得太年輕,又不像三胖,到哪都會跟人家打成一片。他常年四處出差,來去匆匆是他的常態,鈕子每每系到最上面一顆,越發顯得不苟言笑。即便偶爾沒事在辦公室待著,他也關著門自己待著,寧可像個自閉症兒童一樣在屋裡畫烏龜玩,也不出來和公司裡年輕的姑娘們說笑。
這樣變態的時間長了,身上自然而然地就提煉出某種生人勿進般嚴肅的氣場來。
門口的陌生女人還以為他是什麼大人物,頓覺侷促,不自覺地捏著自己的包,擠出一個有些討好的笑容說:「哦……我是她老家親戚,他們家大小子的大姑。」
魏謙的眉頭皺得更緊了:「大姑?我怎麼沒聽說過她老家還有個大姑姐?」
陌生女人臉色變得有些難看起來,但她又摸不清魏謙是什麼人,不敢隨便發作,只好一個勁地賠笑,像是習慣了低三下四,自帶一副唯唯諾諾的面孔。
魏謙掃了她一眼,走到隔壁敲敲麻子媽的門:「姨,是我,有個自稱你們家親戚的人來了,您出來看看,認識不認識。」
說完,魏謙回頭瞟了一眼乾巴巴地戳在樓道裡的女人,眼神像是刀子一樣,刻薄地在她身上刮了一圈。
就算她不是冒充的,麻子爸去世那麼多年,麻子媽每天擺攤賣油條,孤兒寡母的時候,她這個「大姑」死到哪去了?
當年麻子媽出事,麻子那麼小的一個孩子被壞人引誘去販毒的時候,她又在哪裡?
魏謙打有記憶以來,就和麻子他們住鄰居,從來沒見過他們家任何一個活的親戚。
女人驚懼地迎著他冰冷的審視目光,不自覺地貼著牆邊站直了。
麻子媽行動不便,好一會,才把門打開,微弱的女聲從裡面傳出來:「謙兒,什麼時候回來的?吃了嗎?」
魏謙的表情這才柔和下來,彎下腰跟她說了幾句話,又回身把她從屋裡推了出來:「這就是找您那人。」
陌生的中年女人先是震驚地看著麻子媽,眼珠快要從眼眶裡掉出去了,好一會,她猛地摀住嘴,大驚失色地說:「媽呀!你……你是秀紅嗎?你真是秀紅?你……你怎麼成這樣了?我的媽呀!」
麻子媽呆愣了良久,聲音微弱得如同從喉嚨縫裡擠出來的:「你……你是大姐姐?」
女人看了麻子媽幾眼,忍不住了,眼淚不要錢一樣劈裡啪啦地掉了下來。
魏謙把麻子媽重新推進屋裡,把這個不知從哪裡來的「大姑」給放了進去,兩人就在屋裡抱頭痛哭了起來。
魏謙悄悄地退了出去,不過他出來的時候留了個心眼,沒有把麻子媽的門帶上,虛虛地露出一條縫,以防發生什麼事,他在隔壁能聽得見。
連三胖也聽見了動靜,出來看了看情況,一見了魏謙,立刻恬不知恥地跑到他家來蹭飯。
「親戚?別說你了,我都不記得他們家還有親戚。什麼親戚啊,三十年沒來往?」三胖捏了一塊油炸蝦球塞進嘴裡,吧嗒著嘴品了品滋味,「哎喲,這個可好吃!你們家小遠這手藝,簡直絕代了,比別人家小媳婦還要知冷知熱啊,也不知道將來便宜誰。」
三胖的嘴就是個火車站,什麼玩意都跑,本來沒人會跟他認真。
可魏之遠的性向問題一直是魏謙一塊心病,他妥協是真妥協,糟心也是真糟心,後者是控制不了的。
「小媳婦」仨字毫無預兆地踩了魏謙的雷,他頓時火了:「滾,你才小媳婦!」
剛罵完,話音都沒來得及砸腳面上,魏之遠就端著菜、穿著圍裙走出來了,模樣格外賢惠,用實際行動扇了他哥一個耳刮子。
魏謙和三胖的目光同時落在他身上,魏謙無可奈何地翻了個白眼,對無辜中槍的魏之遠說:「明天我就請個鐘點工去,我看咱們樓下那俱樂部裡不是有個業餘散打隊嗎?你有空多鍛鍊鍛鍊身體,或者出去多打幾場球也行,別老圍著鍋台轉。」
魏之遠把他的話當聖旨,二話不說點頭答應,而後抬起頭來,笑眯眯地問他:「哥,原來你喜歡練散打、身體好的男人啊?」
三胖不知想起了什麼猥瑣的事,捂著臉開始笑。
也不知道這小子是不是故意的,反正魏謙怎麼聽這句話怎麼覺得不對勁,感覺就跟被調戲了似的:「我喜歡……喜歡你大爺!小兔崽子怎麼說話呢?」
三胖只顧著找樂子,絲毫沒看出這其中的暗潮湧動,還沒心沒肺地在一邊開玩笑添亂:「別鬧了弟弟,就你哥這臭脾氣,必須得找個三哥這樣軟綿綿的,才能以柔克剛,禁得住他一天三回的么蛾子,我們這體型啊……」
他拍了拍自己熟透西瓜一樣的肚子:「頂多是個相撲出身。」
魏謙一腳踩了下去,三胖立刻訓練有素地躲開了,嘴裡還捏著嗓子賤兮兮地噁心他:「哎喲,這是要幹什麼呀相公,一言不合就要家庭暴力啊?打死了娘子,誰給你生孩子?」
魏謙想打死他的心是發自肺腑的。
魏之遠還唯恐天下不亂,藉著三胖的玩笑,他抓緊時間佔了點便宜,半真半假地拉起魏謙的手,含情脈脈地在他哥手背上啄了一下:「那就打死他吧,不怕,我給你生。」
三胖樂得肥肉亂顫。
魏謙一把抽回手,只覺得好生胃疼。
魏之遠給屋裡的宋老太盛好飯菜,送過去以後,就自己回來硬生生地擠開了三胖,隔開了他們倆。
魏謙:「你又幹嘛?」
魏之遠:「爭寵。」
「嘿,這熊孩子,欺負你哥還上癮了,」三胖讓出了點地方,在魏之遠的後腦勺上拍了一下,而後伸長了脖子對魏謙說,「對了,謙兒……哦不,魏總,這段時間您老人家出差不在家,有個情況我得跟您匯報一下。」
魏謙眼皮不抬地拖長了聲音說:「有話說有屁放。」
三胖的表情異常猥瑣,「渣——咱們人事部,不是有個管薪酬績效的漂亮姑娘嗎,就那個小林清,嘿嘿……人很不錯,也比較跟我合得來……」
魏謙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你個禽獸,拱人家好白菜能別挑眼皮底下的嗎?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呢。」
「我就喜歡她,而且人家那姑娘不是光看外表的膚淺女人。我那天問她了,說妹妹你看我跟你們魏總誰比較帥,你猜人家說什麼?」
魏謙:「我不猜,你以後別老來我們家蹭飯啊,看著你就倒胃口」
三胖拍著肚子,得意洋洋,轉頭對魏之遠說:「嫉妒啊,弟弟,你看見沒有,這就是一個可恥的單身漢對身處甜蜜與幸福中的男人的羨慕嫉妒恨啊。」
魏之遠頗感興趣地問:「她怎麼說?」
「我們家林清說了,」三胖捏細了聲音學,「『就魏總那張棺材板臉,每天早晨打招呼我都不敢跟他對視,帥管什麼用啊,還不夠每天伴君如伴虎地提心吊膽呢,不像談哥,讓人覺得特別溫暖,還特別有安全感。』你聽聽,說得多透過現象看本質,這就是智慧啊!」
魏之遠含笑看了魏謙一眼,眼疾手快地把最後一顆炸蝦球搶來了,放進了魏謙碗裡:「哥,你是該多笑笑。」
魏謙回了他一個皮笑肉不笑,但神色卻是柔和的,眼角眉梢充斥著某種無可奈何的縱容。
三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點神經過敏,反正他驟然心裡一跳,有那麼一瞬間,他覺得這兄弟倆眉來眼去彷彿不大對勁,特別是魏之遠。
三胖忍不住叫了一聲:「小遠?」
魏之遠:「嗯?」
魏之遠那個眼神,真的特別古怪,面對家人時神色比對著外人的時候放鬆,那是正常的,可他並不是放鬆,三胖看得真真的,他覺得魏之遠的眼神就像是藝術家看著一副絕世名畫,收藏家看著一塊極品和田,像……像一個男人看著他的情人,滿含著某種潤物無聲的、熾熱的溫柔。
剛才鬧得過分了吧?
三胖遲疑了片刻,搖了搖頭:「哦,沒事了。」
而後他隨便找了個藉口搪塞說:「你給姨留飯了嗎?今天她那屋有客人。」
魏之遠面色如常地說:「我打電話叫了外賣,既然是來客人了,請人家吃家常便飯不合適。」
正說著,他們聽見了門鈴聲和送外賣的人問:「這有人點了餐嗎?」
「我去吧。」魏謙站起來,從零錢包裡拿了點零錢,出去接了外賣。他正要直接推門進去給麻子媽,卻在門口聽見了裡面談話的聲音。
麻子的大姑一直在鄰省的某縣城裡,距離本市不到五個小時車程,這點距離說不上很近,可也絕不是千山萬水。
麻子的爸和他大姑並不是親生姐弟,他們是麻子的爺爺奶奶各自鰥居守寡之後再婚,才被硬湊在一起的異姓姐弟,血緣沒有,情份也有限。
大姑得知自己有個便宜弟弟的時候,已經成年嫁人了,兩姐弟之間本來就是面子上的事,後來老家兒們都沒了,麻子他爸娶妻生子,背井離鄉地討生活,兩家人就更加沒有來往了。
大姑的男人去世得早,她獨自帶著倆兒子,大兒子在縣城,已經工作了,小兒子才十六,唸書不行,早早輟學了,可心又野,總想著往遠處跑,說是去打工。
小嬌兒從小嬌生慣養,大姑當然不捨得,只好陪讀一樣地千里迢迢跟過來「陪工」,到了這,她才想起小兒子在本地還有個不親不疏的舅舅。
於是起了投奔的心思。
她拿著早好多年的通訊地址,輾轉打聽了好久,才得知自己便宜弟弟早就死了,麻子媽也搬到了市中心。
先開始見了麻子媽這幅模樣,大姑險些沒認出來,而後抱頭痛哭,也是真心實意的,然而等她們一起坐下來,敘完舊,麻子媽開始訴說這些年的經過的時候,大姑心裡那股屬於女性的同情心,終於逐漸的被屬於中年人的冷漠的精明給壓了過去,特別是她確認麻子已經死了的時候。
魏謙把手放在門把手上,正聽見屋裡的大姑壓低了聲音,對麻子媽說:「大妹妹,你傻啊?他們都是跟你非親非故的外人,這麼多年這麼盡心盡力地伺候你,你也不想想,人家圖什麼呀?」
麻子媽久不見外人,反應多少有些遲鈍:「圖、圖什麼?我能有什麼好圖的?」
大姑形似愛憐地抓著她枯槁而佈滿燒傷的手,嘖嘖有聲地說:「還能圖什麼?圖你這套房子唄,大妹妹,你整天在家裡,外面的事都不知道了,你知道你這套房子值多少錢嗎?」
麻子媽回答不出,震驚地看著她的大姑姐。
大姑把聲音壓得更低:「這位置、這面積——你也不琢磨琢磨��你一個人,就算能活到一百歲,才能吃多少用多少?跟這房子的價值有法比嗎?你可真是不長心啊……唉,也難怪,你身邊沒人了,我看著你心裡難受。你看這樣好不好,大姐姐明天把你小外甥帶來給你看看,那小子,虎頭虎腦的,好著呢。他正好過來找工作,你要是願意,姐姐讓他來陪著你,都是一家人……」
「算盤打得好響的一家人。」她的話音突然被打斷,門開了,拎著幾袋外賣的魏謙站在門口。
說人被人聽見,大姑的臉當時就掛不住了,她本能地強詞奪理說:「你這個人,你這個人怎麼亂闖別人家?」
魏謙走進來,冷笑一聲,把吃的放在桌上,不留情面地說:「吃吧,吃完滾。」
麻子媽小心翼翼地拽了他一把:「謙兒……」
魏謙雙手撐在桌上,居高臨下地看著臉紅脖子粗的大姑。
他的鼻樑很高,薄嘴唇,垂下的眼皮更加凸顯了微微上挑的眼角,組合在一起,就是滿滿的傲慢逼人:「我那兄弟埋在哪,你知道嗎?叔叔埋在哪,你知道嗎?麻子——孫樹志他是怎麼沒的,你知道嗎?『孫樹志』仨字怎麼寫你知道嗎?」
他一拍桌子,大姑狠狠地哆嗦了一下。
魏謙:「你算哪門子親戚?」
大姑段位不夠,還要臉,實在扛不住這樣的路數,趕緊匆匆忙忙地逃走了,宋老太聞訊,還掙紮著扶著牆走了出來,她一嗓子驚動十裡八村的罵戰功力不再,但她依然有能力字正腔圓地啐上一口,聊表心意。
三胖趕緊說:「奶奶,我知道您厲害,不過敵方火力不行,這不用您老人家親自出面戰鬥了,您快點回去休息吧——警衛員,還不把首長攙走?」
魏之遠扶起宋老太,把她送回屋裡。
魏謙細心地給麻子媽拿出餐具,把魏之遠點的菜盛出來給她吃。
麻子媽卻沒有動筷子,她拉住魏謙,第一次把心裡的問題問出了口。
「謙兒,樹志是怎麼沒的?」
魏謙輕聲說:「被壞人害的。」
麻子媽雙眼含淚:「那壞人呢?」
魏謙的手掌輕輕地撫過她花白的頭頂:「下去給我麻子哥當牛做馬去了,我們給他報仇了,您放心。」
麻子媽抹了一把眼淚,艱難地衝他露出一個醜陋可怖的笑容。
這個莫名其妙的大姑當時看來,也許只是個很小的插曲,卻像是冥冥之中啟動了某一段殘酷的樂章。
麻子媽並不覺得傷心難過,心裡反而湧出某種說不出的快樂——她找到了自己一直苟且偷生的理由,自己值一套房錢哪。
處理完麻子媽那邊的糟心事,三胖跟到了魏謙屋裡,說起公事。
三胖問:「預售許可怎麼樣,近期能拿下來嗎?」
魏謙點了根煙,坐在床沿上:「那個不是問題,當地相關規定特別不正規,先斬後奏——先開始賣後辦證的有的是……」
三胖:「等等,什麼叫『有的是』?」
魏謙吐出一大口煙,煩躁地說:「我看當地政府是窮瘋了,屁大的一個山頭,連著劃了好幾片別墅用地,賣給了好幾家。我說滿山的經濟林,怎麼附近沒幾戶農民呢,敢情都給清走了。」
三胖:「那怎麼著?咱們現在撤退來得及嗎?」
「別說屁話。」魏謙擺擺手,「前期大頭的錢都砸進去了,好幾個億吊在那,怎麼撤?咱們操之過急了,當初用地協議裡就應該有約定……唉,現在說這個都晚了,我預感這事要麻煩。」
三胖:「那熊哥怎麼說?張總呢?」
魏謙搖搖頭,苦笑:「那兩位……唉,姓張的依然認為他的健康療養題材天下無雙,其他競爭對手都不是對手。這次我先撤回來,就是想緊急把大家召集起來開個會,看看有沒有什麼能補救的。」
兩人相對沉默了好半晌,三胖突然重重地往魏謙的書桌上一靠:「唉,這樁樁件件的,我有個建議,你看好不好……」
魏謙做出洗耳恭聽的姿勢,等他的真知灼見。
三胖:「週日咱倆去廟裡拜拜得了,去去晦氣。」
魏謙:「……」
半分鐘以後,三胖被從魏謙房間裡趕了出來,魏之遠端著一盤水果,才剛要敲門,見了這架勢,忙往旁邊退了一步,以防被殃及池魚。
三胖:「怎麼這麼不友好呢?我說得也是實話,這個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是吧,你要像三哥一樣想得開……了不起申請破產,破完產咱還回去跟我老爸賣豬肉。」
魏謙說:「趕緊滾。」
「唉,小夥子火力壯啊,這脾氣急的……」三胖說著,從自己屁股兜裡摸了摸,摸出一個女孩的照片來,他抬頭沖魏謙一笑,「對,我剛才就想跟你說來著,被隔壁那地縫裡鑽出來的大姑打斷了,這是我們家林清的同學,姑娘本地人,長得漂亮,性格也好,就是口味有點異於常人,聽說就喜歡那種愛答不理的男的,我一聽,這不就是我兄弟你嗎?趕緊把照片和聯繫方式要來了,你看看,三哥想著你吧?」
他說著,就把那張照片往魏謙手裡遞,中途,卻被一隻冰冷的手擋住了。
魏之遠手背蒼白,手指尖好像泛著冰碴一樣,他背對著魏謙,從三胖手裡把照片拿了過去,聲音裡好像帶著玩笑的意思,彷彿是輕鬆活波的:「三哥,我哥這座火山都快爆發了,你還不跑,是打算拿岩漿泡個澡嗎?」
三胖的目光正好和魏之遠撞了一下,他心裡不由一驚。
只見魏之遠嘴角在不自然的、機械地往兩邊提起,眼神裡卻是一點笑意也沒有,黑沉沉的瞳孔好像某種沒有生命的石頭,表面一層冷冷的流光,露出滿溢的陰森來。
照片的一角被他捏變了形。
三胖先開始覺得自己神經過敏,了眼下卻不由自主地開始往歪處想——魏之遠這態度……這表情,是做兄弟的嗎?
三胖腦筋一繃,忍不住繼續試探了一句:「背面寫著那妹子的聯繫方式,謙兒,你看你要是有空,這週末乾脆大家一起出來吃個飯得了。」
魏謙倒是毫無知覺,挑挑眉問:「林清不是見了我就食不下嚥嗎?」
三胖挺胸抬頭地說:「有我這寶塔鎮著你這河妖,她儘管安心吃喝。」
魏謙噓了他一聲,從魏之遠手裡拿走相片,不怎麼放在心上地擺擺手:「再說吧。」
他說完就轉身進屋去了,魏之遠側對著三胖,任由那張相片被大哥抽走,看著魏謙的背影,魏之遠的眼神一瞬間晦澀難解。
三胖近距離觀測到了這一幕,覺得「咣當」一下,他整個人的「三觀」都掉地上找不著了。
打發走了三胖,魏謙才仔細看了看手裡這張年輕姑娘的照片,女孩看起來很乾淨,文靜不張揚,不太扎眼,也說不上多漂亮。
卻十分恰到好處——剛好讓魏謙看著順眼。
魏謙看著照片,當時心裡正在猶豫不定地想,三胖說的也有道理,最近煩心事太多,週末是應該出去緩緩心情,約出來一起吃個飯也不是不行……魏之遠進來了。
魏之遠手裡拿著一個精緻的小盒子:「哥。」
魏謙回過頭。
魏謙坐在椅子上,魏之遠就蹲下來,落到比他還低的位置上,打開包裝盒給他看:「第一次自己賺錢,給你的禮物。」
那是一條一看就知道很貴的領帶,魏謙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收到禮物,愣了片刻才反應過來:「啊?給我的?」
魏之遠抬起手,繫上了魏謙領口的鈕子,然後親自動手給他戴上。
他的手指有意無意地擦過魏謙頸間裸露的皮膚,那股觸感總是很不對勁,魏謙有種錯覺,好像魏之遠的觸碰不是偶然的,而是……那小子一直在刻意地摩挲他的脖子。
魏謙忍不住皺著眉躲了一下。
魏之遠無辜地抬起臉:「怎麼了?」
魏謙打量了他片刻,隨即打消了方才心裡瘋狂的念頭,他覺得自己是整天發愁魏之遠的事,發愁得太多,導致快產生幻覺了,儘是胡思亂想。
魏之遠退開些,細細地欣賞他哥這充滿禁慾氣息的衣冠禽獸裝束,感覺自己渾身的血都沸騰起來了。
他心裡湧起無法忽視地、想要撕開這個人衣服的衝動和慾望,看著魏謙的眼神近乎飢餓。
「哥,」魏之遠說,「你今天不是問我,如果那個人不接受我,自己去結婚,我怎麼辦嗎?」
魏謙被他的目光看得有些心悸,年輕人的目光讓他有股汗毛倒豎的顫慄感。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魏之遠笑了笑,接著說,「不過我大概會瘋了吧?」
他說完,把才纔放在一邊的水果端來擺在魏謙面前,重新換上那貼心小棉襖一樣的溫和表情,對他說:「哥你吃這個呀,補充維生素。」
第四十八章
魏之遠小的時候,注意力非常的集中,一切他不感興趣的東西,即使看見了也會自行忽略。
帶他進一家商場,出來以後問他裡面是賣什麼的,通常魏之遠都會表情茫然,忍不住回頭看一眼櫥窗才回答,如果他回答得非常順暢,就說明裡面多半有他想要的東西。
那時魏謙只能通過這種方法判斷他喜歡什麼。
小遠不像小寶。
小寶很小的時候,家裡特別困難,魏謙也小,不知道怎麼克制自己脾氣,小寶本人可能不大記得了,但確實有那麼一段時間,她是不大敢明目張膽地和大哥要東西提要求的,可是每次碰到她喜歡的東西,小寶都會保持著脖子要伸斷、眼睛要脫窗的姿勢,三步一回頭地戀戀不捨一番。
可見「不敢要」,和「不要」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魏之遠天生比別的小孩會克制自己的慾望,所以相應的,脾氣也顯得比其他的小孩和緩一些。
但魏謙知道,「克制」出來的性情畢竟不是真性情,就好比「不在意,不生氣」和「微笑著憋著不發火,等時機條件成熟了再狠狠報復」這兩種人,雖然在遇到事的第一反應上非常相像,但他們的差異就像隔著一條銀河。
魏之遠這個孩子,偏激、狹隘、受挫感強、安全感差,這些都不算什麼,要命的是,他太聰明。有一段時間,魏謙總覺得他就像一個危險的、時刻準備爆炸的炸彈,後來爆出了性向問題,不知道是不是魏謙的心理作用,他幾乎覺得魏之遠的陰鬱和不好溝通又上了一個全新的層次。
最近兩年,隨著魏之遠日漸成熟,他身上那種讓魏謙不安的尖銳逐漸平緩了,魏謙甚至有種他長大後性格就變了的錯覺。而他這時才發現,魏之遠並沒有變,只是隨著他思慮增多,感覺到了別人對他某些言論和態度的不讚同,而刻意隱藏起來了而已。
魏之遠說完那句話以後,魏謙足有好一會沒反應過來,脖子上的觸感揮之不去,好像魏之遠在他的脖子上按了幾個灼熱的手印,越來越燙。
魏謙從來是缺錢缺揍不缺心眼,他當然感覺出了不正常,但究竟是哪裡不正常,他卻本能地不願意去往深處想,他順從了這股本能,並且跟著惱羞成怒起來,嚴厲地看向魏之遠:「你這是什麼意思?」
魏之遠默不作聲地站直,他已經覺得自己方才失言了。
一直以來,大哥沒有找伴的意思,可他年輕英俊,甚至是成功而且前途無量的,哪怕乍看不大好接觸,也依然會有前僕後繼的女人甚至男人喜歡他,魏之遠心裡一直有這樣的隱憂,他的大哥就像一塊被歲月和生活打磨得光芒璀璨的寶石,不單他一個人長了眼睛。
然而隱憂畢竟只是隱憂,誰知這天就被三胖這麼毫無預兆地當面點了出來。
魏之遠還沒做好準備。
當他捏著那個陌生女孩的照片時,心裡清清楚楚地有一股近乎仇恨的熱流,它幾乎是無差異攻擊地橫掃了出去,對三胖、對那他見也沒見過的陌生姑娘、甚至對他哥。
他心甘情願地吃那麼多的苦,受那麼多的累,每每承受不了的時候,大哥都是他心裡的支柱,他緊緊地握著這如同信仰一樣的東西,咬著牙逼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人、更配得上對方的人。
「可你為什麼不肯等一等我呢?」他垂著眼看著坐在椅子上的魏謙,心裡瀰漫著無法言說的委屈和痛苦——魏之遠有信心控制一切的來龍去脈,唯獨控制不了魏謙的心。
有時候做家長的人,如果面前的孩子一直態度強硬,他們可能還會理智地思考一下,但是一旦孩子避開他們的眼神,顯示出一點點退縮的意思,家長反而容易心頭火起。
魏之遠的沉默就這麼點燃了魏謙的怒火。
「你覺得自己很特立獨行是不是?你覺得自己情聖了,了不起是不是?」魏謙很少用這種口氣訓斥魏之遠,一股腦地爆發了出來,「我看你是找抽!」
魏謙斜斜地靠在椅子上,雙臂抱在胸前,方才被魏之遠整理過、格外整齊的衣服配著他格外不「整齊」的動作,顯出某種讓人怦然心動的獨特的氣質,魏之遠觸碰到他仰起的目光,他胸中的痛苦掙紮和慾望全都攪成了一團,變成一個一點就爆的火藥桶子,而不長的引線已經爆出了火花。
他的喉嚨忽然頓時幹澀起來。
盛怒之下的魏謙完全不知道,面前的似乎乖乖聽訓的寶貝弟弟正在默默地意淫自己,對項目那頭一團亂麻的焦慮和對魏之遠晦暗不明的未來的焦慮不分彼此地攪合在了一起,二者相互疊加,立刻相輔相成地發展壯大起來。
他毫不客氣地對著魏之遠劈頭蓋臉地發洩了出來:「什麼叫你會瘋?我看你已經瘋了!要死要活要瘋要傻的很光榮是吧?魏之遠,我他媽才剛覺得你懂事了一點,你能不能不要在我還沒來得及表揚你的時候,先一巴掌把我這一肚子話抽回去,啊?」
他發火的時候,眼睛格外的亮,五官比平時一片漠然的時候顯得更加生動,魏之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情人眼裡出西施,他甚至覺得,魏謙的眼睛裡就像跳動著兩團帶著魔咒的火,讓他寧可化成一團灰燼,也想撲到���中。
引線快要燒到頭了,他的呼吸無法抑制地粗重起來。
「你說你喜歡男的,改不了,行,只要你自己想好了,這我也捏著鼻子忍了。你是不是覺得我的縱容就是讓你無法無天地揮霍生命了?」魏謙一抬手,從書櫃裡抽出一本已經有些年頭的新華字典,重重地砸在了魏之遠身上,「你會不會說人話?不會說自己查字典好好學學去!」
字典正好砸中了魏之遠的胸口,魏謙下手沒輕沒重,魏之遠幾乎覺得自己有那麼幾秒是窒息的。
「轟隆」一聲。
蜿蜒的火星點燃了他心裡壓抑的黑箱,魏之遠自己也本以為那只是一簇燒過就散的煙火,然而他只來得眼前一黑,一時間神智全非,他心裡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燒成了一片火海,綿亙十萬裡扭曲的烈焰融入了他每一根血脈。
他胸中有心如深淵,第一次他以為要失去這個人的時候,通往深淵的門打開過一次,捲進了一條人命,而這是第二次。
魏之遠的耳畔終於只剩下那麼一個聲音:他是我的!是我的!
魏之遠突然一把抓住魏謙椅子兩邊的扶手,雙手爆出可怕的青筋——那是一個把魏謙困在了椅子裡的動作。
他的心跳如隆隆巨鼓,瞳孔劇烈地放大,額角和手心浸出細密的汗,死死地盯著他所渴望的那個人的臉、眼神、身體乃至一切。
魏之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事。
就在這時,外面的大門突然重重地響了一聲,宋小寶好幾斤重的書包大概是從她身上滑了下來,撞在了門上,隨後是她掏鑰匙開門的動靜,一串鑰匙冰冷的金屬碰撞的聲音稀裡嘩啦地打破了兩人之間行將窒息的氣氛。
魏之遠狠狠地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滿口的血腥味,撐在椅子把手上的手是麻木的。
小寶的大嗓門在外面響起來:「大哥!我看見你鞋啦,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魏之遠緩緩鬆開了手,這才感覺到大腦有些缺氧,而胸口在隱隱作痛,他臉色白了白,伸手按住被字典砸中的地方。
魏謙站起來走出去,魏之遠靠在他的書桌上,聽見客廳裡的交談聲。
魏謙:「剛到沒多久,你吃飯了嗎?」
小寶連抱怨再撒嬌地說:「我不吃,老師不讓我吃,快考試了,她還讓我減肥,餓死我啦。」
魏謙:「再減都沒人了,你們老師神經病啊?老不吃飯怎麼行,平時還要上課,你受得了嗎?」
小寶「嘿嘿」一笑,學舞蹈大量的肢體運動把她的身條拉了出來,細胳膊細腿顯得手長腳長,說不出的輕靈好看,唯有這嗓子笑法,依然把她回歸成了形象全無的傻妞一個:「受得了,我要是能通過專業考試,文化課過得去就行啦。說真的哥,做數學作業比空著肚子跑步痛苦多了。」
她說完,扔下書包,中氣十足地衝向宋老太的房間,嗷嗷叫喚著:「奶奶!俺胡漢三又回來啦!」
魏謙:「別蹦躂啦,小心樓下上來找你。」
宋小寶用行動充分詮釋了什麼叫做「弱智兒童歡樂多」,清脆地說:「來找啊來找啊,我給他們跳恰恰,哈哈哈哈哈!」
她一個人回來,整個家裡的噪音指數立刻指數冪上漲,到處都是她「哇啦哇啦」說笑的聲音,從誰誰誰今天摔了個大馬趴,到哪個老師把眉毛剃乾淨忘了畫——也不知道她哪那麼多感慨和樂子。
魏謙只覺得有五百隻大鴨子從他身邊列隊而過。
他揉了揉太陽穴,緩緩地吐出一口鬱結的氣。
魏之遠聽見門響,偏頭一看,魏謙走了進來。
魏謙回手關上了門,神色複雜地看了魏之遠一眼,終於還是嘆了口氣:「剛才砸哪了?過來我看看。」
魏之遠胸口上給砸青了一大片,中間隱隱帶著點淤血,看著怪嚇人的。
魏謙翻出跌打損傷的藥膏,彎下腰給他上了藥,已經平靜了下來的魏之遠慘遭了一份痛並快樂著的折磨。
上完藥,魏謙把藥膏盒子扔在他懷裡,低聲說:「氣死我了,滾回去自己反省。」
魏之遠就知道,這個事算揭過了。
接下來的好一段日子,魏謙都無暇他顧,他既沒有抽出時間去認識三胖介紹的女孩,也沒有時間煩惱魏之遠越長越歪的個性和已經正不過來了的性向。
C市項目的預售回款期開始了。
張總那不知哪裡來的盲目自信終於被慘淡的內部銷控表澆滅了,魏謙的預感成了真。
項目公司一般有自己的銷售團隊,怎麼賣,賣了多少,這些都是項目總管,打報告給雙方股東就好了,這次卻是老熊和張總兩大股東方的法人代表親自過去坐鎮銷售團隊了。
先是鋪天蓋地的廣告,然而沒用。C市的常住居民人口根本就沒有那麼多,完全消化不了這個體量,而度假療養別墅本身也是針對來此旅遊的外地遊客,但同類產品實在太多,競爭對手有的是,什麼「森林公園中的私人莊園」,「山居樓台隱居聖地」之類品類繁多,張總提的那個活像「臨終關懷老人館」一樣的療養概念根本沒有任何競爭力。
各家爭奇鬥豔一般,每家都有亮點,但是亮點多了就變成晃眼了——當地的別墅市場已經呈現了明顯的買方市場。【注】
說起來也是,出來旅個遊,看著地方好就在當地買個房子的燒包,全中國能有多少?
而這些燒包各自有家有業,當然不可能常住,弄個產權式酒店公寓每年臨幸一兩天,已經非常「傻多速」了,有多少人會花大價錢買一棟離群居索、進進出出都不方便的別墅的?
錢的問題還是小,難道找人打理不麻煩?
後來老熊他們也嘗試過在各自的老客戶群中搞「折價內部銷售」,依然以失敗告終。
這時,他們以前粗放式的撿著項目就幹,沒有品牌特色,甚至沒有固定產品的弊端凸顯了出來——這種超高端項目的客戶群體和以前做的城市住宅群甚至小規模的商業地產都產生了明顯的斷層。
簡而言之,就是老客戶裡根本沒幾個人買得起,別說購買,他們連關注都懶得關注。
中間有一段時間,他們幾乎放棄了「賣出去」的努力,想轉向「租賃」,租給某些旅遊機構或者酒店機構,改做別墅式度假酒店。
這個提案被雙方股東一致通過,然而且不說只租不售帶來的資金壓力,這一大片別墅區就連整租都租不出去。
只有幾家酒店管理公司表示過興趣,但是提出要不買也不租,只是替他們管理,而他們不但要承擔管理費用,每年這個別墅式度及酒店的盈虧風險還要自負。
至此,他們好像走到了一條絕路上。
然而這並不是最可怕的。
要知道,哪怕當年土地還便宜,整個項目做下來也要幾個億,其中大部分資金是借款。
「槓桿」【注】是資本密集型行業的雙刃劍,能乘風破浪,也能反咬一口。而借款是根據當年的用款還款計劃定的,眼下銷售回款沒有,去哪弄錢來還?
而借款合同的確沒有限定死,規定在一些情況發生的時候,可以拖延一年還款,但所有的條件,都建立在項目效益良好,拖延還款能帶來可以預期的、更大的收益的基礎上,他們沒有一條符合的。
臨近冬天,也代表著還款期限迫在眉睫。
一天冷似一天,上億的債務就好像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天比一天搖搖欲墜。
而別墅只賣出了兩套,其中一套還是老熊自己買的。
十二月初,老熊回來了,總部的人險些都認不出他來了,當年那條眼睛一條縫大的胖頭魚好像去抽過脂,瘦得臉型和輪廓都出來了,鬆弛的皮膚顯得他一下子像是老了十歲。
整個總部都是魏謙和三胖在坐鎮,兩人每天疲於奔命一樣地走訪債務人,掙紮著想為這件事找出轉機的餘地。
魏謙敲開老熊辦公室的門,雙眉之間快要擰出一條深溝了:「熊……」
老熊抬手打住他的話音。
他避開魏謙的目光,聲氣有些微弱地說:「先給我倒杯水。」
魏謙深吸一口氣,默不作聲地倒了杯涼水,「咣當」一聲放在了他面前,直接坐在了老熊的辦公桌上,沒好氣地說:「喝,嗆死你。」
老熊沒有做出任何回應,一口氣把水喝了個乾淨,然後一抹嘴:「召集大家,開個緊急會議。」
魏謙怒氣衝衝地出去了。
十分鐘之後,總部所有人,包括管理者和普通員工,全都聚集在了會議室裡,老熊一屁股坐在執行董事空了半年多的位置上,沉默得像一口啞口了的大鐘,只盯著自己的手發呆。
會議室裡鴉雀無聲,全都在等著這個精神和實際雙重領袖,對眼下的困境做出交代。
難熬的幾分鐘過去,老熊終於開了口:「整個項目,是我力排眾議,一定要推進的,現在這個情況,也是我一手造成的,我本人承擔全部的責任。」
魏謙覺得這個節奏不大對勁,剛要出聲,老熊卻彷彿感覺到了什麼,先抬起頭搶過話頭:「魏總你有意見一會再說,先等我宣佈完這個決定。」
魏謙往椅子背上靠了靠,手裡的筆轉了一圈,和三胖對視了一眼,心說這事恐怕要壞菜。
果然,老熊接著說了:「現在,關於這件事,我提出兩個解決問題的辦法,請大家——以及相關決策人員聽一聽,做個決斷。」
他深吸一口氣,站了起來。
「第一,從現在開始,我承擔所有的責任,我會以合理的價格收購諸位的股權,如果公司最終破產,有限責任人拍屁股走人,無限責任人如果被迫承擔連帶責任,我會給諸位發一份協議,你們都可以向我本人追償,十個工作日內,諸位就可以開始願意辭職辭職了。」
老熊話音剛落,地下都開始竊竊私語起來。
三胖終於忍不住也出聲了:「行了行了,都靜一靜——熊哥,你這是什麼餿主意?還沒破產呢先斷了後路?其他人沒有責任嗎?我覺得我就有責任,我們當初要是都鐵了心的不同意,你項目提案推得動嗎?」
老熊慘淡地笑了一下,輕輕地說:「你們都是被我綁上船的啊。」
魏謙:「行了你別扯淡了,說點有用的,破產前的事。」
老熊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舉起自己桌上執行董事的牌子:「第二計劃,就是我把位子讓出來,從現在開始,不對公司的決策有任何發言權,我只負責承擔最後的責任,魏總接替我成為這個執行董事。」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魏謙身上,魏謙的眼角「突突」地跳了起來。
老熊靜靜地轉向他:「魏總,你現在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了。」
作者有話要說:
【注】買方市場:簡而言之就是買的人少賣的人多,供過於求,市場由買方主導。
槓桿:財務槓桿能用很小的資金撬動很大的項目,簡單說就是借錢很多,如果盈利了,很小的資金能獲得極大的收益,但是虧損一樣。槓桿會成倍地放大投資者的損益。
第四十九章
後來魏謙回想起來,那一刻——老熊把他當眾點出來鞭屍的那一刻,他心裡真的就只有一個問題和兩個選擇:究竟是跟熊英俊這貨一刀兩斷好呢?還是跟他同歸於盡好呢?
可他很快就沒時間思考這麼哲學的問題了,老熊往旁邊撤了一步,把椅子往後拉了拉:「如果你同意,那你坐過來,現在開始,我不參與任何決策,你說了算,最後是死是活,責任我來擔,你要是不同意,咱們就繼續按著方案一來,我等著收屍。」
被「黃袍加身」的魏謙看著他,眼神從千言萬語中化為一句話:你怎麼就不去死一死呢?
老熊的目光落在魏謙身上,而後又避開了魏謙的目光。
事到如今,一切檢討和懺悔都到此為止了。
他知道這是一件顏面掃地的事,老熊捏著手裡那張會議桌上的名牌,心裡卻明鏡一樣地知道,這是他所能做到的,比較有尊嚴的退場了。
他看得清楚,魏謙突然被點名的時候,那一瞬間,眼神是慌亂的。
錯愕、難以置信與茫然交替著閃過,最後落在了回過神來的憤怒上。
但老熊知道,他一定會走過來。
魏謙就是這麼一個不見棺材不落淚的人,與他的年齡和閱歷無關,他已經習慣了背後無處可逃的日子,就算有一天世界末日了,眾人全部鳥獸散,他也一定是反應最慢的那一個。
只有這樣的人,能擔得起一個公司、乃至一個企業的脊樑。
片刻後,魏謙果然如他所料,低頭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站起來走了過來。
老熊把名牌遞給了他,魏謙遲疑了一下,接了過去,董事長秘書訓練有素,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這是怎麼個情況,就先動作麻利地換了杯水放在了魏謙面前。
水杯放在桌子上半晌,水面依然顫抖不止,不知道是不是端水姑娘的手在一直哆嗦的緣故。
木頭椅子一會沒人坐就會變得冰冷,魏謙從這種冰冷中感覺到那些直撲向掌舵人的狂風大浪,這讓他覺得透不過氣來。
在座的,除了幾個剛參加工作沒多久的小青年,大部分人都比他年長,而他們都在一言不發地看著他。這個世界上,所有人都會挑別人的刺,哪怕最細節的地方,也能有人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顯得自己很真知灼見地指摘一二。
但是大部分人真正坐在這個位置上的時候,也都會被這種極端的、暴露在風險中的畏懼感壓垮。
這麼說也許看起來很神奇,反正當時,就在魏謙坐上了老熊的椅子的一剎那,他心裡原本像其他人一樣的,對老熊的諸多怨憤就都煙消雲散了。
「我為什麼沒有阻止他?」魏謙捫心自問,「是出於對陳露的同情嗎?」
沒有人會允許老熊拿著幾個億的錢玩一場寄託感情的打水漂,他們最後一路沉默,最根本的原因,是包括他本人在內,沒有人在最開始決策的時候看出這個項目的風險點。沒人早早地預料到那一小片山坡,短短幾個月內就被瓜分成過剩的別墅市場,沒人在花團錦簇的項目建議書裡一針見血地看到它沒有一個準確實在的客戶群體。
市場變幻莫測,所有風和日麗的盡頭都有可能是一張猙獰的面孔,泰坦尼克號都撞上了冰山,每一天,都有無數的大小船隻在其中悄無聲息地消亡沉沒。
而這樣的險惡,普通員工乃至管理層都沒那麼容易感受到,因為它們全都在掌舵人的眼裡。
現在,是在他的眼裡。
魏謙沒有發表任何就職演說,他只是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潤了潤喉嚨,簡短地說:「別的不提了,先請熊總說一下項目部的銷售情況,然後預算部和投資部公佈一下資金缺口,聽完以後,想走人的可以提前散會,回去及時把辭職申請提交人事部門,想堅守的留下,我們討論下一個階段的工作重點——老熊,就從你開始吧。」
不過事實是,他雖然這麼說了,但是沒有一個人提前退場,工作不好找,只要還開得出工資一天,員工們就不會主動辭職,至於經理們……當初如果有一個人有「提前退場」這樣的決斷和真知灼見,或許他們也不會走到這一步。
最長的一個會開完了,魏謙和老熊是最後剩下的。
魏謙站起來在老熊面前站定,老熊閉上了眼。
「你閉眼幹什麼?」魏謙沒好氣地說,「你不會以為自己長成這幅熊樣,我也有胃口親得下去吧?」
老熊低聲說:「我還以為你會動手打我。」
魏謙往四周掃了一眼:「在這?那不能,我起碼也會等下班,等你走到沒人的地方,先給你套個麻袋再打。」
老熊低低地笑了出來:「真是個流氓。」
隨後,他重重地靠在椅子背上,把頭往後仰起,注視著頭頂的天花板。
好一會,老熊才囈語一樣地說:「我有時候奇怪,我還在這幹什麼呢?我難道不應該帶著陳露遠走高飛,周遊世界,或者陪她一起靜靜地等著最後一刻嗎?」
魏謙悄無聲息地在老熊旁邊坐下,面前是除了他們空無一人的會議室,透亮冰冷的石面長桌,表面上映出自己光怪陸離的影子,看起來好像是某種神秘寓言的開場白。
「可是我明明知道,到了這地步,見一面少一面了,我卻還是不想多見她。我半夜做夢都能夢見自己替她死了,醒過來卻不敢側頭去看她的臉,你說我是不是有病?」老熊下巴上露出了青青的胡茬,好像一萬年沒睡過覺一樣抬頭看著魏謙,目光中流露出一種灰燼般的、沉寂的坦然,他說,「謙兒,你還讓我去C市項目那邊吧,有任何需要我跑腿的,隨時待命。」
魏謙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他連戀愛都沒談過一場,怎麼知道人家夫妻又是怎麼回事���?
「行啊,隨便你吧。」魏謙說完,站起來走了。
也許有一天陳露死了,老熊就解脫了。
可是真有那麼一天,老熊還是老熊嗎?
歲月會把沙爍凝結成石頭,會把最早的、最青澀的愛情凝結成什麼呢?
魏謙突然有些後悔那天對魏之遠發火的事了。
魏謙藉著衛生間的水池洗了把臉,用最快的速度把後悔與疑惑全都丟在了一邊,他知道自己當務之急是有兩件事要做:怎麼穩住他的債權人,怎麼讓洽談延期的問題,以及怎麼去補上資金缺口,C市的項目究竟是想辦法盤活,還是想辦法撤退。
那段時間是怎麼過的,魏謙一直不想回頭看。
從前他一無所有的時候,在家裡跟宋老太為了百八十塊錢掐指頭算來算去,感受到的多半是生存的壓力,他的責任是一個家,是讓自己過得好一點,讓妹妹來要零用錢的時候,不至於因為沒有而臨時想什麼藉口躲出去。
現在,他算是這個城市裡的有產階級了,誰也不會再認為他是個窮人。儘管這年頭出去廣告牌子掉下來砸死仨人,有倆都是什麼總,但也沒人會否認他確實混得人模狗樣。
而他承受的壓力,也從一家老小,變成了全公司上下幾十、乃至上百個人下個月的工資和數億的債務。
三胖偷偷跟他說:「謙兒,我不瞞你說,我是真睡不著覺,天天晚上起床在屋裡瞎溜躂,我爸媽一開始還以為我是撒癔症呢,他們倆就快把我送精神病院了。我爸說讓我辭職別幹了,前兩年買了個小鋪面還租著給別人呢,拿回來自己開個火鍋店算了,只能混個溫飽就先混個溫飽,溫飽也挺好的。」
三胖說的是真話,他現在整天愁眉苦臉,連和心愛的女神談戀愛的沒精神了……更是忘了提醒魏謙,關於他們家小遠那一路狼狗望骨頭一樣覬覦的眼神的事。
魏謙評價他說:「瞧你這點出息。」
三胖一瞪眼:「難道你睡得著?我怎麼不相信?」
魏謙斜斜地看了他一眼:「你看我像睡不著覺的嗎?」
三胖一看,他精神果然是不錯,說不上容光煥發吧,起碼頭面都乾乾淨淨,臉色也不難看,眼睛裡沒有血絲,也沒有黑眼圈,說話的時候思路清晰,連驢脾氣和棺材臉都發揮正常,沒有任何異狀。
三胖就服了,心說人和人果然是有差別的。
以前魏謙考上重點高中的時候,他還覺得是這小子艱苦奮鬥熱愛學習,現在三胖發現,他和魏謙之間的差距果然如同天塹,不說別的,就他老人家這心理素質,活能趕上當年喪權辱國也吃得飽睡得著的慈禧太后,簡直沒治了。
慈禧太后已經作古多年,那賣國老娘們兒的精神世界至今早已經無從考證,魏謙不知道她是怎麼個情況,但他知道自己的精神世界是始終搖搖晃晃、臨到崩潰的。
「睡得著」根本是他吹牛糊弄……不,適當包裝穩定軍心的。
那年魏謙開始失眠,在這以前,他從沒想過這種毛病會落在自己身上,他曾經偏見地認為都是那些有錢有閒的大爺們,才會沒事捂個胸口失個眠什麼的。
前二十多年,他也確實是能隨時隨地倒頭就睡,現在,他終於不敢站著說話不腰疼了。
也不知道他這是算生理性的還是心因性的,魏謙一開頭是經常忙到後半夜,生活沒規律,過了一兩點也就不怎麼困了,快要破曉的時候才能眯上一會,久而久之,他就發現自己哪怕是按時躺下也睡不著了。
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像死狗,魏謙開始少量地服用安眠藥。
這件事本來一直是個秘密,直到被魏之遠發現。
那天魏謙出門去見了個諮詢公司的人,回來得挺早,魏之遠最近一直都在帶著自己的團隊對程式做最後的調試,每天都弄到很晚,回家一看魏謙的鞋在,臥室門關著,還以為他睡了。
由於第二天基本沒什麼活了,此時又正值寒假不用上課,魏之遠沒有很著急休息,他簡單洗漱後,就坐下來開始研究起下一步的計劃和大概思路。
臨近一兩點鐘的時候,魏之遠忽然聽見客廳裡有聲音,他一開始沒在意,後來覺得有些不對起來——那似乎是在翻找什麼的動靜。
魏謙的安眠藥吃完了,他一時忙忘了,沒想起來去買,到了半夜一如既往的睡不著,在床上痛苦地翻滾了一陣以後,他福至心靈地想出了一個餿主意——很多感冒藥裡有安眠成分,他決定臨時湊合一天,用感冒藥代替安眠藥。
是藥三分毒,魏謙心知肚明,他還知道,這玩意沒病找病地吃多了會傷害臟器和腦神經。
可失眠的痛苦放在一邊,這個不是不能忍,但魏謙第二天要去洽談債務延期問題,還有一場硬仗要打,這種時候怎麼能睡不著覺呢?
魏謙越想越焦慮,越焦慮越睡不著,到最後,他幾乎覺得哪怕是耗子藥能讓他躺下睡一宿,他也能面不改色地幹上一碗了。
魏之遠觀察了他一陣,奇怪地問:「你感冒了嗎?」
在他的印象裡,魏謙的體質不屬於那種容易感冒的——他要病就是大病,平時一般沒事。
魏謙嚇了一跳,手裡的感冒藥「啪嗒」一下掉回了抽屜裡,他回頭看了一眼魏之遠,怨念地想,這小子長大以後那黃鼠狼一樣走路悄無聲息的本事竟然沒有退步。
魏謙懶得和他解釋,只是搪塞了一句:「哦,有點。」
魏之遠才不相信,魏謙說話又沒有不正常的鼻音,看起來也不像發燒,而且以他哥的尿性,一點小災小病別說主動吃藥,他可能連察覺都察覺不到。
「有點?你就大半夜找感冒藥吃?」魏之遠走過去,皺著眉狐疑地打量著他拿過的藥,一目十行地掃過效果和副作用,突然抬起頭問,「哥,你不會是睡不著覺吧?」
魏謙面無表情地在心裡罵街:「怎麼這王八蛋連這都能看出來?」
同時,他淡定無比地衝魏之遠伸出手,仍用他那若無其事的語氣敷衍說:「嗯,有點——給我吧,你也早點休息。」
魏之遠一縮手:「感冒藥不能這麼吃。」
魏謙:「沒事,不經常。」
魏之遠匪夷所思地看著他:「你還想經常?你……唉,你等等。」
他從冰箱裡翻出一袋牛奶,倒進一個很小的鍋裡,放在火上煮,又在裡面加了一勺糖。
這東西喝完管飽不管用,魏謙早就試過,不過他也沒拒絕魏之遠的好意,只是在旁邊說:「放微波爐裡轉一圈不就得了?」
「那不一樣。」魏之遠說。
怎麼熱不是熱?魏謙沒想出來,不過喝起來好像是有些不一樣,他猜可能是因為魏之遠那一勺額外的糖的緣故。
喝完他就回屋了,打算等這小崽子睡著了再出來尋覓一圈。誰知剛躺下,魏之遠卻抱著被子跟進來了,魏謙扭開床頭燈,默默地看著魏之遠把被子扔在自己的床上,中間夾雜著某個重物——扒開一看,是一個卷在被子裡的特別厚的筆記本。
魏謙:「你幹嘛?」
魏之遠擠到他床上:「看著你睡。」
魏謙覺得自己雖然是睡不著,但是也不能說是特別清醒,一定要描述的話,就是他整個人的神經處於一個睡眠和清醒之間的麻木的狀態,他木然地企圖思索這是怎麼個情況,片刻後放棄了,問他的寶貝弟弟:「你是打算用這個把我打暈嗎?」
魏之遠說:「我有一個新的想法,可以給你講講,中間有很枯燥的演算法,看看能不能把你講睡著。」
他話沒說完,魏謙已經推開被子坐了起來。
「嗯,好,來吧,給我拿根筆。」
「……」魏之遠頓了頓,無奈地說,「就是想給你助眠,哥,你別總這麼嚴肅認真好不好?」
魏謙單手按了按有點酸脹的太陽穴,苦笑說:「這要是也能把我講睡著,那我不是每天開會不是都要睡好幾圈?」
魏之遠想了想,忽然把他的筆記本丟在一邊,然後笑了起來。
魏謙驚奇地發現,魏之遠的眼睛平時看起來一點也不彎,笑起來卻是正宗的笑眼,兩頭微翹,像一對漂亮的月牙。
「我明白了。」魏之遠說完,把床頭燈擰到最暗,讓燈下的一切只剩下一個影影綽綽的輪廓,然後他拉開窗簾,推開了窗戶,一大股寒氣立刻洶湧地向著溫暖的室內撲了進來。
魏謙立刻鑽進了被子:「你他媽開窗戶幹嘛?都把我徹底凍醒了,小遠同學,能勞駕您老人家移駕自己屋,別在這禍禍我了行嗎?」
魏之遠:「你看,下雪了。」
寒冬的窗戶上總凝結著冰花或者白霧,很難看清外面有什麼。
魏之遠一說,魏謙才看見漫天的鵝毛大雪,有幾片還隨著寒風飄進了屋,轉眼就化了。
魏之遠重新關上窗戶,卻把窗簾留了一條縫。
他把那一小塊的玻璃上的白氣擦乾淨,讓屋裡的人能看清外面窗檯上越壓越厚的雪。
然後把魏謙桌上的資料全部收拾乾淨扔到了桌子下面,把角落裡扔著的魏謙的一張畢業照拉過來擺在了正中間,又坐回床上,把枕頭和被子拉起來拍鬆軟,拉到魏謙的下巴上。
魏謙忍不住笑了笑:「你還挺會照顧人。」
魏之遠說:「等你老了,我還會這麼照顧你。」
魏謙沒能從中聽出他「白頭偕老」的隱喻:「等我老了,難道你會很年輕?你又不是我兒子。」
這一次,魏之遠沒有回答,他窸窸窣窣地在魏謙身邊躺下來,抬手關上燈,俯身輕輕地在魏謙耳邊說:「睡吧,等天氣好,被子要曬一曬了。」
魏謙的耳朵非常敏感,忍不住想躲開,可是魏之遠一觸即放,黑暗中只能看到他眼睛裡的光。
彎彎的笑眼,魏謙腦子裡突然閃現了那麼一副畫面,而後魏之遠在他耳邊的話好像生成了某種魔咒,他恍惚間就覺得被拍得鬆軟的被子裡有一股剛曬過的、陽光的香味。
人躺在床上,抬起的目光剛好能透過魏之遠留下的窗簾的縫隙看到那一小片被擦乾淨的窗戶,再透過窗戶看見漫天的大雪,裹在身上的被子於是顯得格外溫暖了。
室內外的溫差讓清透的玻璃很快又染上了朦朧的白霜,冰天雪地一點一點地被隔絕在窗外,很快看不清了,方才喝下的甜牛奶從胃裡氤氳到四肢百骸,發揮了微妙的安神作用。
小火上加熱出來的牛奶,和微波裡草草轉一圈出來的,確實是不一樣的。
身邊的人若有若無地發出一聲極舒服的喟嘆,朦朧間似乎有人抱住了他,但這並沒有觸動魏謙衰弱而敏感的神經,他睡著了。
關於他在外面遇到了什麼事,魏之遠沒聽他透露過隻言片語,他當然是關心的,但是克制住了自己,在這個時間和場合裡隻字未提、分毫不問——因為魏謙的焦慮並不會因為傾訴而減少一分。
魏之遠只是非常巧妙地搭配了視覺、聽覺、觸覺、味覺甚至是可以暗示出的錯覺,編了一個「家」給他。
不是一棟房子,甚至不是社會意義、倫理層面上的家,不是需要柴米油鹽醬醋茶、需要「當家」的家。
是眼睜睜地隔絕了寒風凜冽、暴雨瓢潑的地方。
是風雨兼程的旅人宛如歸宿的落腳點。
一夜好眠。
第二天,魏謙被自己那久做擺設的鬧鈴叫醒的時候,天光已經大亮。
客廳裡傳來宋老太拖拖踏踏地練習走路的聲音,魏之遠早早地出門查資料,小寶也去上課了。
魏謙匆忙地起床洗漱,餐廳裡放著烤好的麵包和煎得黃澄澄的荷包蛋,而頭天晚上他放在桌上的安眠藥藥瓶被魏之遠拿走扔了。
從那以後,魏謙再也沒有買過安眠藥,也再也沒有需要過。
第五十章
老熊是個非常超前的人,他喜歡自由民主有事好商量的氛圍。而隨著他這個創始人的公開讓位,魏謙卻成了整個公司的獨裁者,舊有的三會一層七嘴八舌的審批討論制度很快名存實亡。
用林清的話說,自從魏總變成魏董之後,他這個人的恐怖程度,也跟著鳥槍換炮地從「噴嚏大魔怪」水準升級到了「比克大魔王」,原本人性化、層級扁平的公司就像一片脆弱的肥皂泡,被他一巴掌就摧毀了。
魏謙接任不到一個禮拜,整個公司變成了一個機械運轉的集中營。
而在這樣如同納粹的重壓之下,工作效率竟然幾乎是以前的兩倍。
人事部門午休時間關起門來內部討論這個結果,林清總結了原因:是因為每次魏董冷冷地逼視著耽誤他事的人的時候,那目光都能讓人「兩股戰戰、幾欲先走」。
從魏謙辦公室接出來的內線人稱「午夜凶鈴」,電話接起來,那位一句沒頭沒尾、簡明扼要的「到我辦公室來」,更是恐怖如同「阿瓦達索命」。
要提交給債權人的材料被魏謙連續打回去要求重寫了二十多遍,只把投資、財務和預算部的三個部門經理寫得幾欲以頭搶地、殺身成仁。
他們要加班,行政和人事這些後勤部門就要協同,整個總部連前臺都只敢溜邊出門買飲料。
就這麼著,連軸轉了半個多月,沒日沒夜,平均每天工作時間超過十二個小時。
至於……週末?那是什麼?能吃嗎?
終於,最後一版在魏謙那得到了勉勉強強的認可。
「新上任的老闆是變態」這個認知,如同基石一樣地鑄造在了每一個員工心裡,然而奇怪的是,他們最後竟然都沒辭職。
危機降臨的時候,變態比寬厚的領導人管用得多。
一個多月後,魏謙帶著三胖和兩個部門經理輾轉了幾個債權人,經歷了數次談判。
結果是成功的,魏謙把還款期限拖了一年。
代價是他把目前手裡在建的項目公司股權,幾乎全部抵押了出去。
用三胖的話說就是:「這下可好了,咱們從死刑變成死緩了——哎,那不你們家小遠嗎?他怎麼到這來了?」
魏謙讓人把車停在公司寫字樓下,探出頭來問:「你怎麼來了?」
魏之遠從自行車上下來,把一個飯盒從車窗塞到他手裡:「我下個禮拜要跟一個老師去外地開個研討會,可能得週末才能回來了,每天做什麼,鐘點工阿姨那我都交代好了,她的工資和買菜錢我都付了,你有什麼要洗的衣服就放在門口的小簍裡,她會去拿。家裡平時的日用品我也都多買了一份備好了,奶奶平時吃的什麼藥,我按順序排好了,每種拿幾片我都寫好貼在藥瓶旁邊了,小寶要是不在家,你給她拿一下,一天三次。」
魏謙不易察覺地皺了皺眉,魏之遠交代的一大堆事雖然沒什麼需要他做的,但聽在耳朵裡真是覺得又瑣碎又麻煩。
「你要記得按時吃飯,」魏之遠說,「我買了一箱牛奶放在冰箱裡了,喝的時候熱一熱,別喝涼的。」
魏之遠囑咐完,才好像才想起有別人在場一樣,好像有點「不好意思」地衝其他人笑了一下:「哥,三哥,那我走了。」
說完,他就背著自己的單肩包,上了自行車,轉眼就消失在了街角。
兩個經理的表情就好像剛剛看見了拉登挖鼻孔一樣奇幻——儘管他們的變態老闆方才從頭到尾都沒說幾句話,但看起來卻是和顏悅色的。
魏先生和顏悅色是個什麼概念?
那就像侏儸紀和甜甜圈一樣,是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啊!
此時,唯有三胖談魚先生的表現是淡定……乃至嚴峻的。
他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感受到了某種兵臨城下的危機——魏謙他們家過日子什麼時候這麼囉嗦了?
魏謙以前的日子過得多隨意啊,想吃油條開窗戶沖樓下吼一嗓子,沒零錢先欠著,不想吃的時候隨便抓一把米,往鍋裡一扔就能煮出一鍋粥,隨便弄兩口鹹菜就吃了。還有他每天早晨騎自行車上學那會,都是隨手從宋老太鍋裡抓一根玉米,一手扶著車把一手拎著啃。雖說已經過去了幾年,可三胖還有種歷歷在目的錯覺。
三胖在辦公室時間長了,不自覺地會往縱深裡想。魏之遠給他的感覺就像一隻不動聲色的蜘蛛,潛移默化地在他家裡織造出了某種看不見也摸不著的秩序網。每個人都會下意識地習慣並且服從——包括魏謙這個外強中乾的一家之主。
三胖剛才分明看見魏謙皺眉了,以他們倆從小穿開襠褲的交情,三胖能從他的眼神裡讀出「啊?怎麼突然說要走,真麻煩」這樣的信息。
這要是在以前,別說弟弟出門一個禮拜,就是魏之遠出國去南極科考兩年都沒問題,誰愛去哪去哪,只要別死在外面不回來,魏謙多半還會鼓勵地給塞點錢——少一個在跟前礙眼的,他更消停。
變了,不知不覺就變了。
魏謙拎著飯盒下了車,三胖忙跟了上去,跟他一起上樓,他決定要摸清楚這件事是怎麼個意思。
三胖試探著問:「怎麼你成你們家甩手掌櫃了?」
魏謙嘆了口氣:「我這不是顧不上麼。」
三胖就半開玩笑地說:「你這不行啊皇上,權力都被架空了,內務府的門沖那邊開還記得嗎——你還知道你們家裡用什麼牌的衛生紙,小時工一小時工資多少錢嗎?」
魏謙:「……」
他真不知道。
從前宋老太當家那會,她因為不識字,很多事不懂也不會辦,還是需要魏謙留著心的。自從宋老太生病,好像在誰也沒注意的情況下,這些事就被魏之遠接過去了,魏謙好像再也沒走過心思。
三胖搖了搖頭:「完蛋了,萬歲爺,你就等著被逼宮篡位吧。」
魏謙一笑,沒往心裡去,以為他鬧著玩。
三胖就兜著圈子又說:「對了,我還想問呢,你家小遠都快大三了,在學校裡也沒給你找個弟妹回來?」
這孫子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魏謙當時臉色一變:「別提這事。」
三胖覷著週遭沒人,前腳後腳地跟進了魏謙的辦公室:「怎麼的?他找了個無鹽女還是河東獅?」
那就好了,只要是女的,活的,魏謙覺得自己都能喜聞樂見。
債務又拖了一年,魏謙覺得自己好不容易鬆了一口氣,還沒來得及喘上來,又被三胖給堵回去了,他一開始不想說,想隨意打個哈哈搪塞掉,就說:「人家每天忙著呢,上課下課的一大堆課外活動,還能偶爾拉個投資做個小玩意,賺點小錢。」
「哦,這事我知道,當年咱們像他那麼大的時候,不也是被老熊忽悠說什麼『勞動是過去,資本是現在,技術是未來』嗎,咱們當年就敢幹『現在』,人家有出息的現在就開始盯著『未來』了。」三胖說,「你出差不在家的時候,我看見過那幾個孩子一次,都帶著電腦,到你們家聚會,幾個小子,還有倆小姑娘,哎你別說,有個姑娘也不知道怎麼長的,確實挺有『未來味』,特別俊……」
魏謙食不下嚥地把魏之遠給他準備的飯盒放在一邊,拿著筷子當筆,在指間轉了一圈,終於忍不住沒精打埰地對三胖說了實話:「沒戲,那姑娘好成天仙也不管用。」
三胖預感到了這裡,魏謙的答案呼之慾出,他的眼皮一跳,有種烏鴉嘴成真的苦逼感。
果然,魏謙無力地說:「那混蛋東西跟我說他看上一個男的,我都跟他掰扯了好幾年了,死活掰不回來。」
三胖雖說是早料到了,但是親耳聽到,還是不知該用什麼表情才好,只好也擺出一張奇幻臉。
魏謙嘆了口氣,抬頭囑咐了三胖一句:「當你親兄弟才告訴你的,別給我出去亂說啊,對孩子不好。」
三胖看著魏謙,痛心疾首地發現,這毫無知覺的兄弟還在給人數錢呢。
他知道自己不能說破,一來魏謙不一定信,二來真說破了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只好雙手捧心做嬌弱狀,顫抖地問:「那……沒告訴你他看上誰了?」
魏謙翻了他一眼:「那誰知道——反正不是你,別緊張,你長得安全。」
三胖簡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呼天搶地說:「我的兄弟哎……」
魏謙還以為他在感嘆魏之遠,擺擺手說:「隨他去吧,我反正是管不了了。」
是啊,傻兄弟,到時候恐怕由不得你了——三胖用萬分糟心的表情看了魏謙一眼,默默站起來離開了魏謙的辦公室,總算是明白了當年他是怎麼把高燒當上火,把肺炎當感冒的,他從未像現在這樣痛恨魏謙的不拘小節。
三胖回去以後越想這事越不對勁,就像大多數直男一樣,魏之遠對魏謙單方面的那種扭曲的感情讓他渾身不舒服。
魏之遠是他看著長大的,從小「三哥」叫到大,三胖不想用惡意揣度他、評價他,更不想用「噁心」這個詞來形容,可讓他坦然接受,那也是萬萬不能的。
三胖覺得自己知道魏之遠是怎麼想的,魏之遠在用某種方式刷自己的存在感,照這樣下去,總有一天魏謙會離不開他。
由於小時候家庭的緣故,魏謙和女性交往本來就有些障礙,三胖不想看著魏之遠走入歧途,更不想看著他把他哥也牽扯進去。
這不行啊,再這麼下去就危險了,得想個什麼辦法,把這件事破壞了——三胖心裡暗暗地這麼想著。
且不論三胖是怎麼打算的,在魏謙用盡了全身解數暫時地解決了債務問題之後,他找到了盤活項目的一個轉機,帶來這個轉機的是一位有史以來最不著調的諮詢師。
大型的諮詢公司費用從百十來萬乃至上千萬不等,對於此時「錢就是一切」的魏謙而言,是昂貴得過分的,他只請得起一些本土的、相對比較小一些的諮詢公司,對方派了個人前來和他接洽。
來人名叫馬春明,和魏謙自己差不多大的年紀,還長著一張娃娃臉,一笑倆酒窩,那面相、衣著與談吐,都好像在用生命詮釋什麼叫做「嘴上沒毛,辦事不牢」,顯得格外不靠譜。
魏謙看著他那身邋裡邋遢、活像行為藝術一樣的舊西裝,只好先耐著性子試探地問:「請問您是學什麼專業出身的?」
諮詢師馬春明同志自豪地告訴他:「食品安全。」
魏謙:「……」
馬春明一見他的表情,自信心先遭到了打擊,他小心翼翼地打開面前的資料夾,小聲解釋說:「但是我覺得我的專業並不重要,我能在十天之內快速摸清一個行業,這才是客戶需要的素質。」
魏謙想了想,也有道理,他本人還是學生命科學出身的呢,現在也陰差陽錯地坐到了這個位置上,人家是靠這個吃飯的,多少應該有兩把刷子吧?
於是他保持著禮貌與溫和的態度,繼續問:「那我能請教一下,您上一單接的那種和自己所學專業無關的項目,是怎麼用十天摸清了整個行業的呢?」
馬春明沉思了片刻,用作檢討一樣的姿勢和語氣說:「這個……不瞞您說,這其實是我第一次接觸業務,我……我是剛從學校畢業的博士生,入職還不到半年。」
一個沒有人帶、沒有人教的食品安全博士,站在一個房地產老總面前,他和一個被丟在戈壁裡,剛學會走路的孩子有什麼區別?
魏謙甚至注意到對方拿著資料夾的手在簌簌發著抖。
什麼叫便宜沒好貨?
魏謙徹底失去了本來就不多的耐心,打算叫內線,把這位博士請出去。
誰知那馬春明這會機智了起來,一看他漠然的表情和抬手拿電話的動作,立刻就知道了自己即將被扔出去的命運,他急忙試圖挽救,以機關槍一樣的語速開口拚命為自己爭取著機會:「我我我真的可以在十天之內瞭解一個行業的,您聽聽我們的步驟!」
魏謙冷漠地說:「我不用聽了,我不想花錢請一個學食品的人來教我怎麼賣房子——博士也不行。」
他說完拿起電話,直撥給行政:「叫人過來一趟,幫我送送客人。」
馬春明緊張地直啃手指甲,眼睛眨得飛快,圓圓的臉使他看起來就像一隻抽了風的土撥鼠。
「您您您聽一聽!我馬上就說完——我們首先會研究整個這個行業是靠什麼生存,也就是大家賣的都是什麼。」土撥鼠飛快地說,迎著魏謙漠然的目光,額頭上很快浸出了一層虛汗,然而他毫無選擇,只有繼續說下去,以期待能有一點微末的希望打動面前這個年輕的掌舵人。
「研究完實際的價值以後,我們會研究這些價值的來源是什麼,也就是從開始『生產』開始,到徹底賣出去之間,哪些環節是輔助的,哪些環節是重點的,也就是創造價值的。」
這時,魏謙辦公室的門開了,行政辦公室的一個男員工先是訓練有素地和魏謙打了招呼,然後目光落在了快急哭了的諮詢師身上,客客氣氣地說:「是送這位客人出去嗎?」
馬春明沒想到自己這麼快就搞砸了,他頓時覺得人生都灰暗了起來,用一種悲憤莫名的表情注視著魏謙,蔫蔫地拿起自己的包,滿心絕望地想:世界上還有我這樣的廢物嗎?唸完了博士,竟然找不到一個對口的工作,好不容易輾轉進了一家「諮詢公司」,結果進去以後發現叫「騙子公司」還差不多,第一次做業務就被客戶鄙視得一塌糊塗……
馬春明覺得自己這樣的人活著還不去死,所以他決定離開這裡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找個地鐵站下去臥軌。
就在這時,魏謙突然開口說:「不,我讓你給客人倒杯水。他還要再坐一會。」
正在腦補自己是怎麼被飛馳的列車碾得血肉模糊,眼球掛在車窗上的馬春明呆住了。
直到那位工作人員給他倒了杯水,又默默地退出去。
魏謙雙手交叉放在桌子上:「你剛才說什麼?從項目開始到產品賣出過程中每一個環節的價值?講詳細一些。」
馬春明長出了口氣,擦了一把額前的汗:「就是先要搞清楚有哪些環節啊,前期都要做什麼,建設中的時候需要做什麼等等,每一步對項目能否成功的影響。」
魏謙突然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他找到自己錯在哪了。
最早和張總合作的時候,張總的價值在於人脈,他在當地非常有背景,能以質優價廉的條件拿到他們想要的地,這就是價值,體現在最終產品成本的大幅度減少上。
然而這次沒有,張總是個地頭蛇,他千里迢迢地跑到C市去爭取一塊土地,毫無根基,所以喪失了起碼的優勢。
他們取得土地使用權的拿地環節異常順暢,順暢到好像了理所當然那一樣。
可他們本該知道,前期拿地環節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增值環節,人脈或者規劃的優越性是增值的關鍵點,這些關鍵點完全沒有體現出來,政府就痛快地批了用地許可,那豈不是「李生大路無人摘,必苦」的結論?
心懷僥倖到底是不行的。
魏謙一瞬間想通了癥結所在,立刻電光石火地閃現了幾個解決方案的方向。
「馬春明是吧?」他抬起頭對惴惴不安的土撥鼠笑了一下,「我們誠邀您留下完成這項諮詢工作,過後如果可能,也歡迎你加入我們公司。」
第二天早晨,魏謙早早就去公司開會了,魏之遠收拾好了行李,和宋老太交代一聲,最後在家裡轉了一圈,確保自己沒有什麼遺漏,這才帶上門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這種蠶食鯨吞的策略怎麼樣,魏之遠決定要試探一下,自己在身邊的時候是不行的,偶爾遠離幾天,才能看出對方的丟盔卸甲情況,所以他才答應了老師的邀請。
這是一次進度測試。
魏之遠還不知道,自己未來一段時間的對手是三胖這個隱形破壞分子,他還在樂觀地估計,這麼下去,自己得手也就是一兩年的事。
他還以為自己還有大把的時間,可以徐徐圖之。
小寶假期短暫地住進了藝校宿舍,加訓,所以魏之遠一走,家裡就空了下來。
宋老太吃力地拄著枴杖,從房間裡挪動出來,在屋裡溜了兩圈,已經是大汗淋漓。
「我是個廢人了啊。」她想,低頭看著手裡的拐棍,「這東西拿起來就扔不掉了。」
她心情鬱鬱——最近一段時間,宋老太總是這樣,給她吃,她就吃,給她買東西,她就慣常訓斥別人不會過日子,她要麼顯得怒氣衝衝,要麼沒精打采,變得極其難以討好,誰都不知道怎麼讓她高興高興。
宋老太清楚地知道自己變傻了,她開始失去了對數字的敏銳,算不過賬來了,連錢財的概念也淡薄了起來。前面說的話,過兩分鐘就忘了,說完再過好半天才又會想起來,發覺自己說了惹人煩的車軲轆話。
宋老太堅強地活了下來,堅強地恢復良好,卻失去了快樂的能力。
而會說會笑的小寶一走,她就更孤獨了。
宋老太緩緩地挪動著枴杖,開門去了隔壁,她打算找麻子媽坐一坐,她現在說話含混,要說好幾遍別人才能理解,他們都忙,宋老太怕招人煩,於是也只有麻子媽有這個時間陪她聊天了。
等她進了麻子媽的家,宋老太發現麻子媽正盯著一張陳舊的、本市地圖發呆。
宋老太問:「她姨,你幹什麼呢?」
麻子媽轉過頭來,見了宋老太,卻並不慌張,她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被任何人看見都會大驚小怪,唯有這個老太太不會。
她們分享著同樣無能為力的生理感受,也有著同樣的痛苦和孤獨。
「大姐,」麻子媽壓低了聲音,帶著一點奇異的、好像知道自己即將去遊樂場的孩子那樣純粹而期盼的笑容,她對宋老太說,「我打算要走了。」
第五十一章
宋老太睜大了昏花的老眼看了麻子媽一會,而她連表達能力也受到了限制,明明有話想說,卻怎麼也理不清順序,只能任它們擁堵在僵硬的舌頭下面。
麻子媽平淡地解釋說:「您看,我父母早不在了,男人死了,現在連兒子也沒了,沒有親人了。我自己又是這個模樣,本來就沒什麼勁了,活著也是給人家當拖累,但是我以前總是想,我要是不活了,三兒和謙兒他們吃那麼多苦不就白費了嗎?所以一直不敢死,前兩天我大姑姐來了一趟,跟我說這房子值不少錢,這倒提醒我了,我這條老命還值一套房子錢呢,我要把房子留給那倆孩子。」
宋老太吃力地說:「你瞎想什麼呢?」
「我沒瞎想,我就是想挑個好地方,走了以後,讓別人找不著我。」麻子媽輕快地說。
似乎生命對她而言,已經成了一種痛苦的背負,這使得她奔赴死亡的過程格外輕快。
麻子媽說到這,轉頭問宋老太:「大姐,您跟我一起走嗎?」
宋老太連忙搖頭,含含糊糊地表達:「可不敢,在我們老家,誰家老人這樣,那讓人家怎麼戳你們家後輩兒孫的脊樑骨啊!」
她話說得急,麻子媽聽了好幾遍才明白,隨即,她笑了起來:「您想得太多了,我的老姐姐,咱們住的這地方,出來進去的,誰認識您是誰啊?樓上住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您認識嗎?誰戳得著誰的脊樑骨呢?」
宋老太反駁不出,她的伶牙俐齒被一場大病崩碎了,現在別人就是當面罵她,她都反應不過來該怎麼回話了,急得滿臉通紅。
麻子媽笑起來:「您慢慢說,不著急,咱們姐倆現在都是閒人。」
麻子媽雖然沒有直說,可這樣一走,不就是死嗎?
人怎麼可以尋死?那多……多丟人呢!
宋老太拚命地思考著該如何阻止她,努力讓自己劇烈起伏的呼吸漸漸放緩。
她現在的短期記憶差得要命,幾十年前的事卻反而像是河床下面的石頭,隨著水面漸漸乾涸而顯露出來。
宋老太一個字一個字艱難地往外蹦,試圖讓自己的咬字更清楚一點。
「我七八歲的時候,正趕上鬧日本兵,他們就在城西邊有個大本營,進進出出還有好多日本娘們兒,我三爺他們家就住在那邊,大人不敢走,小孩倒是沒人管,我爺就讓我去給他們送糧食。其實管也不怕,我媽生了五個閨女,那會都叫丫頭片子,丫頭片子不值錢,活一個死一個的,除了親娘,誰在乎呢?」宋老太看著麻子媽,殷殷地說,「當時我年紀小,也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日本兵會殺人,來回走了多少趟,可就真的沒碰上過什麼事,我爺都說我命大。」
麻子媽只是意味不明地笑了一下。
宋老太見無法打動她,只好繼續說:「後來三年自然災害,挨餓,沒吃的,大隊能分點糧食,可是家裡上有老下有小,也輪不到我們吃。寒冬臘月裡,我跟我嫂子拿著最後一塊鹹菜疙瘩兌涼水吃,我說等春天地裡野菜長出來就餓不死人了。我嫂子說:『嘿,你還想活到開春?我可不敢想那麼多。』結果怎麼樣?我們倆都活到開春了,還活成了兩隻七老八十的老王八。」
這一次,麻子媽連臉上的笑容都變得漠然起來,她渾濁的目光中似乎有一層膜,輕飄飄地把宋老太所有的話都隔絕在了耳朵外面。
宋老太費勁地探過身,抓住麻子媽僅剩的、變形的一隻手,用力晃了兩下:「活著吧,大妹妹,多難啊,活著吧!」
麻子媽沉默良久,終於還是搖了搖頭:「您甭說了,我都想好了,等我決定出去哪,研究出怎麼去,就找機會走。」
宋老太嘆了口氣,抹了一把眼睛,可是她眼睛太乾,已經不那麼容易哭出眼淚來了。
麻子媽問她:「這事,您會給我告訴別人嗎?」
宋老太沒來得及深究,就已經本能地搖了頭。
麻子媽臉上露出一個又像是如釋重負、又彷彿明白了什麼的表情,她下了斷言說:「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啊,總有一天,您也會跟我一樣的。」
後來宋老太拄著枴杖,拖著沉重的腳步,從麻子媽那離開了,她們倆誰也說服不了誰。
麻子媽弄得她心裡很不舒服,宋老太感覺臉上火辣辣的,也有點生氣,覺得麻子媽不是東西,辜負了三胖和魏謙他們早年的辛苦。
怎麼難、怎麼苦都不離不棄的那些情分,難道就只值幾間破房子嗎?
然而歸根到底,宋老太也承認,麻子媽從某種層面上來看是對的——她要麼辜負魏謙他們以前的辛苦,要麼繼續拖累他們。
要麼成全孩子們的良心,要麼成全自己的良心。
宋老太是怕死的,生命的路越是走到了盡頭,就越是恐懼死亡。
她好不容被搶救回來,好不容易恢復到如今的地步……可當她顫顫巍巍半晌,才努力地打開了家門的時候,心裡仍然在這樣萬分不容易裡,又一次對自己感慨:「廢物啊,活著是真沒勁。」
但她這種情緒持續的時間很短,因為這天晚上,宋小寶的集訓結束,回家了。
宋小寶不負責養家餬口,不負責安排家裡大小事宜,只負責一天到晚窮開心,她責任不大,做得也不錯——確實是每天都鬧鬧哄哄挺高興的。
小寶不嫌棄奶奶,奶奶說話慢也不要緊——反正全家上下,只要有她在,幾乎沒有別人發揮的餘地,她一個人能叨叨完全場。
魏謙推門進來,正好聽見她在那手舞足蹈地吹牛皮:「奶奶我告訴您說,等我將來混好了,沒準還去演電影呢!您沒看過電影吧……不對,跟電視不一樣,比電視螢幕大好多,有一面牆那麼大呢!」
魏謙就站在門口,情不自禁地笑了起來。
他想起來自己年少那會,總是嫌這小丫頭太聒噪,直到現在才發現,家裡有一個能聒噪的,那是福氣。
「哥!」宋小寶山呼海嘯地衝他撲過來,嘰嘰喳喳地說,「本少女瘦了沒有?漂亮了沒有?像一朵花嗎?」
魏謙表情是溫和的,話卻依然是毒辣的,他涼涼地說:「像,多好一朵狗尾巴花。」
小寶猴在他身上好一番撒嬌耍賴,魏謙好不容易才把她扒拉下來:「你二哥週末才回來,我過兩天也要出差,你自己一個人在家,照顧奶奶行嗎?」
宋小寶連忙立正:「放心吧,人民是你最大的後盾!」
魏謙在「人民」的後腦勺上拍了一巴掌:「去看看,家裡零錢夠用嗎?」
宋小寶顛顛地跑到平時放現金的櫃子裡看了一眼,回來報告說:「夠……哎,等等。」
她說完,又去宋老太房間裡把她平時要吃的藥拿出來查看了一番,掐著指頭算了算,回頭沖魏謙喊:「哥,奶奶藥快沒了,該買了,你再給我留點錢。」
眼看著宋小寶跑出去,宋老太忍不住緩緩地移動著步子,探出個頭去。
她就看見魏謙拿出錢夾,數了一打紅得刺眼的鈔票給小寶。
宋老太臉上打從小寶回來就沒落下過的笑容緩緩地消失了。
她想:「哎喲,怎麼,買一次藥要那麼多錢啊?這吃的都是金子嗎?」
魏謙果然隔天就要走了,臨走,他把自己家和總部都丟給了三胖照應。
三胖不知是哪根筋搭錯了,說著說著就故事重提,又要給魏謙說媒拉縴。
魏謙頓時一個頭變成兩個大:「三哥,你行行好吧,我他媽北都快找不著了,你還惦記著給我介紹姑娘?」
三胖煞有介事地診斷說:「找不著北了吧?感覺特別抓瞎吧?覺得人生充滿了壓力、毫無樂趣可言吧?你啊,這就是缺愛。」
魏謙面無表情地說:「我覺得我不太缺愛,我這毛病可能是缺錢引起的,你現在給我真金白銀地弄幾個億來,讓我當場以身相許都行。」
「滾一邊去,」三胖毛都炸起來了,「我們家女神光耀千古,就……就你這塊茅坑裡的臭石頭,倒貼都沒人要。」
魏謙聳聳肩:「行,沒人要就沒人要吧,那我走了。」
「回來。」三胖說著,從身上摸出上次他給魏謙看過的那個女孩的照片,硬是塞給他,「我上次跟你說過的,這姑娘叫馮寧,跟林清一屆的,研究生畢業以後留校了,現在一邊做行政工作一邊繼續往上念,一拿到博士立刻能轉正式的講師……」
魏謙快要哀嚎了:「饒了我吧,我真……」
三胖打斷他:「人家是高知,有才有貌的,介紹給你算便宜你丫了好嗎——我知道你現在顧不上,等擺平了項目那邊的事,回來見面認識認識,聽見沒有?好多人追呢,晚了就被人捷足先登了。」
魏謙敷衍:「擺平了再說。」
三胖那張萬年風和日麗的臉色突然變了,表情一沉,冷冷地問:「怎麼著,這麼好的姑娘還配不上你啦?你還整天人五人六地說你們家小遠,你自己呢?」
魏謙腳步一頓。
「三哥不會害你,我知道你不喜歡這類型的,但是過日子不單需要怦然心動,還得合適才能長久,一時倒是看對了眼,回家在一起天天沒事打架玩,那能行嗎?」三胖嘆了口氣,放緩了語氣,近乎是苦口婆心地說,「就你那臭脾氣,有幾個年輕姑娘能忍得了?你就得找個性格平和、肯包容別人的。見一面會怎麼樣?不行再找別的,會掉塊肉嗎?這麼大的一個爛攤子你都敢扛下來,見個女的不敢?」
就一次,魏謙終於鬆口了。
其實從內心來說,他自己都知道,他並不是對馮寧感興趣,純粹是被三胖那幾句話激的。
他好像僅僅是急於想要證明,自己是能給魏之遠做一個正面的榜樣的,他也是能做出成人式的、理智的選擇,而不是屈從於內心不該有的任性。
至於心裡隱約的彆扭,被魏謙毫無懸念地忽略不計了,他已經習慣忍耐各種壓力和不愉快,對婚姻生活並沒有太大的期盼與嚮往。
只是人就應該這樣。
而後魏謙帶著馬博士飛去了遙遠的C市。
在他剛離開的那幾天,魏之遠每天晨昏定省一樣地給他發短信,事無钜細,吃喝拉撒他什麼都要打聽,什麼都要管,連每天魏謙那邊的天氣預報都要給發一份提醒過來,煩得要死。
這麼過了一陣子,魏謙只要是聽見手機一響,都不用看,就知道十有八九又是他那倒楣弟弟。
後來有一天,不知道怎麼回事,魏之遠突然沒頭沒腦地發了條短信問:「她挺好的?」
魏謙沒看明白,以為是魏之遠發錯人了,他原本打算過一會問問,沒想到剛好手頭有點事,過一會就給忘了。
而後,魏之遠就突然了無音訊了。
魏謙一開始有點不適應,有種忽然被人忽視的不快。但他給家裡打電話報平安的時候沒聽出小寶又什麼異狀來,家裡一切都好,魏謙以己度人,估計魏之遠也是有什麼事太忙了,顧不上了,心裡彆扭的感覺持續了幾天,也就沒再往心裡去。
南方不像北方那樣,工程會受季節影響,魏謙到了以後,第二天就請來了一幫搞設計的,用了兩個禮拜的時間,合計出了一套改造的方案。
原來別墅區有兩個配套,一個是位於最北邊的醫院,一個是最南邊的會所。
北邊借助山間的溫泉,他們給改造成了一個融合女士美容服務的療養養生中心,南邊的會所則被改造成了一個私立學校。
為了這個學校,老熊又被派回去了,他在全國各地飛了一圈,幾乎發動了所有的人脈,這才挖來了一個著名的留學培訓機構,他們把人請到這裡,以免租金並且為教師提供食宿和定期療養作為條件,借助著那個留學培訓機構的品牌,包裝出了一個「私立國際學校」。
從外語培訓到留學仲介,一條龍服務,和學員簽訂保底合約,保證其申請到保底學校檔次以上的留學地點。
別墅區戶主免學費和服務費。
這一次鋪出去的廣告是以「私利國際學校」的名義,由留學培訓機構打出去的,很快覆蓋到了目標客戶群,活生生地把一片度假別墅變成了「學區房」,兩個月之內就幾乎收回了成本。
大半年之後,整個項目更是直接清盤,甚至遠超過了張總一開始預期的200%投資回報率。
當然,這些後續工作就是項目公司營銷團隊的事了,售樓處迎來第一波外地趕來看房子的客人的時候,魏謙就知道,他們這最艱難的一關過去了。
回去的半路上,馬春明屁股上長釘子一樣激動地問他:「那、那我這次的諮詢服務做的算成功嗎?算入門了嗎?魏董,你說過讓我來你這裡工作的事當真嗎?我可以……」
他側頭看了魏謙一眼,突然閉了嘴。
飛機還沒有離開跑道,而魏謙靠在椅子背上,居然已經睡著了。
當老闆也怪不容易的,馬春明心想。
顛簸過後,馬博士放下小桌板,拿出他的筆和本子,仔細認真地記載下了這一趟全部的工作心得。然後,他把本子翻到最後一頁,在空白頁上認認真真地畫了一隻正在往山上爬的小烏龜。
等魏謙中途被送餐的空姐叫醒的時候,馬博士本上已經有了一個加強連的小烏龜。
那熟悉的畫風,活靈活現的動作,讓魏謙經年過後一眼瞥見就認了出來,頓時,「馬春明」三個字變得熟悉起來,與他曾經用過的舊課本扉頁上的人名重合到了一起。
魏謙忍不住問:「你高中也是市三中學畢業的?」
馬博士連忙慌慌張張地合上本子,後悔自己一時得意忘形,竟然把最不靠譜的一面展示在了未來老闆面前。
魏謙忍不住失笑:「沒事,你畫吧,畫得挺好的。」
他沒想到,自己竟然就這麼邂逅了「神龜真人」,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他回想起當年拿著二手課本在兩廣打黑拳的事,在飛機引擎的隆隆聲中把放下來的遮光板撩開了一條縫,大片的雲層在機身下面,強烈的紫外線刺得人眼生疼。
魏謙胸中突然一片海闊天空。
……當然,如果他知道自己不在的這段日子,三胖背著他搞了什麼,以及他回去即將面對什麼,說不定就不會高興得這麼早了。
魏謙離開的第一天,三胖就潛進了他家,跟小寶說他有一份公司的資料要去魏謙屋裡拿。
小寶當然沒有絲毫懷疑,叼著蘋果走過,連看都沒看一眼。
三胖熟人作案,可謂是事半功倍,進了魏謙的房間後,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桌上原有的、陳舊的畢業照挪走了,換上了馮寧的照片放,還充滿暗示地在旁邊放了一個小禮物盒——明顯的女孩子氣的包裝盒裡裝著一個精緻的打火機。
魏之遠本來沒想到魏謙會突然決定去南方,不然他就不走了,一個禮拜後,他按時回家,雖說沒有實現觀測結果,有些遺憾,但他依然每天堅持騷擾魏謙一次,騷擾得不亦樂乎。
當中有一天,他似乎是終於把魏謙弄煩了,魏謙一個電話打回來,先簡要詢問了家裡的情況,而後開始訓斥魏之遠:「你還有完沒完了?電信剛在貴村開通業務,會玩手機了是吧?我這月通訊費比那邊談戀愛的二逼諮詢師還高!」
最後這幾句話罵得在魏之遠聽來動聽極了,挨訓挨得簡直心花怒放,可是這花骨朵還沒有完全打開,魏之遠就被另一個消息砸蒙了——三胖敲門,拎進了幾盒包裝精美的小點心,一進門遞給小寶說:「你哥是回不來了,便宜你們倆了,吃吧。」
小寶厚顏無恥地一邊扒拉包裝盒,一邊毫無誠意地客套說:「哎喲三哥,你來就來了,還拿什麼東西……下次多拿幾盒行嗎?」
「饞死你得了。」三胖笑嘻嘻地回她的話,卻有意無意地掃了魏之遠一眼,故意用曖昧的口氣說,「別瞎自作多情啊,這可不是給你買的,人家這是專門給你哥拿的。」
小寶必須保持體形,不敢多吃,只小心翼翼地掰了半塊解饞:「誰啊?誰給我哥買的?」
三胖對著站在她身後的魏之遠神秘一笑:「你們未來的嫂子。」
他滿意地看見,魏之遠的臉色驀地一變。
小寶呆了片刻,先是有點不適地皺了皺眉,然而她接受得飛快,很快又釋然,追著三胖問:「什麼時候的事?我哥怎麼沒說?她幹什麼的?脾氣好嗎?什麼樣啊?」
三胖哈哈一笑:「你三哥介紹的,能錯嗎?去你哥屋裡看看,肯定有照片。」
小寶立刻就去了,她很快找到了魏謙桌上馮寧的照片和那個禮盒,發現新大陸一樣地大驚小怪起來,還企圖拉著魏之遠一起觀賞。
「小寶,」這時魏之遠突然開口說,「奶奶好像在叫你。」
「哦,」宋小寶不疑有他,把剩下的點心一口塞進嘴裡,鼓著腮幫子掉頭跑了,「來啦!」
三胖覷著魏之遠陰沉的臉色,他從沒有見過魏之遠這樣,那種不加掩飾的陰冷讓三胖忍不住想起報復社會的變態殺人兇手,光是眼神就讓人不寒而慄。
魏謙是瞎吧?連這都看不出來——三胖心裡這樣感嘆著,預感著魏之遠要跟他當面撕破臉,藏在下面的話要坦誠相見了。
三胖裝作方才有所知覺的樣子,看著魏之遠的神色打趣說:「怎麼著?不樂意啦?」
魏之遠先是沒吭聲。
「唉,三哥知道,這就跟親爹找了後娘的感覺一樣,也就小寶那丫頭能這麼沒心沒肺。」三胖故作理解地拍了拍魏之遠僵硬的肩膀,裝模作樣地說,「可是你想想,你哥畢竟是你哥,連父母都跟不了兒女一輩子,別說是兄弟了,總有一天,你們都會各自成家,這是自然規律啊。」
三胖說完,抬頭觀察魏之遠的表情,然而在那年輕人的眼神裡打探不出一點端倪,裡面只是一片陰沉沉的黑,他終於忍不住脫口說:「你哥這輩子不容易,你……你……唉,少讓他操點心吧。」
魏之遠壓低了聲音,嘴唇幾乎不動地說:「三哥,你是知道了?」
三胖不知該怎麼回答,面對著這從小看著長大的孩子極致蒼白的臉,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魏之遠的嘴角動了動,似乎是極快地冷笑了一聲,而後他一聲不吭轉身走了。他最後的眼神讓三胖忍不住一陣心悸,忍不住想:這小子該不會給刺激大了,做出點什麼事吧?
作者有話要說:
註:雖然前因後果改得面目全非,不過此處引用真實商業案例改編
第五十二章
魏之遠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過來的,那段日子非要用一個詞來說,就是「暗無天日」。
最開始,他是憤怒。
對三胖,對那個不知名的陌生女孩,甚至是不明真相的小寶。
魏之遠覺得自己被整個世界孤立了,沒有人在意他挖空心思的努力。他從三胖的表情上看到無奈和迫於感情的寬容。
可他憑什麼需要被別人寬容?
他做錯任何事了嗎?
他就像一個身披風雪趕路的人,一路伸手不見五指,只有那一根燈塔用微弱而獨一無二的光引著他。
現在,他們連這一點僅有的東西也要奪取。
憤怒是一種不長久的情緒,就像一把沙子,要麼很快就會被風吹得煙消雲散,要麼沉澱成深深的、石頭一樣的怨恨。
再之後,魏之遠的情緒就滑向了後者。
怨恨像是一顆在他心裡埋了二十年的種子,埋得那麼深,那麼的如鯁在喉,稍加風雨就破土而出,長成連著血肉的參天大樹。
瘋狂的憎恨瀰漫在他心裡每一個角落——就像屍體,儘管再掩飾,也遮擋不住腐朽的氣味——即使魏之遠已經在極力不表現了,卻連一貫大大咧咧的小寶都察覺到了他的不對頭,每每跟他說話的時候聲氣都要低八度。
他的怨恨針對所有人,因此分攤到每個人頭上,也就顯得不那麼濃烈了,唯有魏謙。
魏之遠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他甚至自己都說不清楚,對大哥的感情濃鬱黏稠到了什麼樣的地步,乃至於現下幾乎有些愛憎不分起來。
愛之深,就恨不能食其骨、啖其肉、飲其血。
魏之遠的精神狀態處於某種極度麻木、也極度敏感的危險的狀態裡,醞釀著某種一觸即發的風暴。
就在這時,魏謙回來了。
魏謙從飛機上下來的時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在了機場打發馬春明給他買了一大杯濃茶,灌進去了,勉強提了提神,又趕到總部開會匯報近期工作要點。
等他筋疲力盡地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八點多了。
南方天熱,他裡面穿著單薄的襯衫,到了這邊才匆匆地裹上大衣,但北方的小寒風依然不停地往他的衣服裡灌,魏謙裹著一身的寒氣進屋,裸露在外面的皮膚凍得發白。
魏之遠聽見門響的那一刻,心臟就開始劇烈地跳動了起來。
他夢遊一樣地走了出來,感覺站在門口的大哥就像是活生生地撞在了他眼睛裡,生疼。
「你在家呢?凍死我了,」魏謙掃了他一眼,隨後頭也不抬地問,「有吃的嗎?」
魏之遠說不出話來,好一會,他才行屍走肉似的應了一聲,走進了廚房,拿了兩個雞蛋,開始切蔬菜丁,打算把剩下的一碗米飯炒了。
魏謙在外面說:「小遠,你甭弄那麼麻煩,有剩飯給我拿過來隨便吃兩口得了。」
魏之遠充耳不聞。
他好像非要做點什麼事,才能讓自己維持表面上的平靜。
魏謙以為他沒聽見,被屋裡的熱氣一蒸,全身的懶筋頓時開始往一塊糾結,他沒骨頭似的往沙發上一癱,行李箱丟在一邊,就打開了電視。
等魏之遠端著一碗炒飯出來的時候,魏謙已經靠在沙發上睡著了。
魏之遠的呼吸隨著腳步一起停住了。
手心的大碗開始發燙,然而他的雙手好像麻木了,絲毫也感覺不到。
魏謙的身體隨著沙發柔軟的坐墊縮到了一個小角落裡,架起來的二郎腿還沒來得及放下,一手虛虛地按在遙控器上,另一隻手委屈地橫在胸前,頭一側靠在沙發背上,下巴幾乎全縮進了衣領裡,他面無血色,乾裂的嘴唇上爆出細碎的幹皮和裂口,胸口的起伏都顯得那麼不明顯。
……像是死了。
魏之遠聽見自己的心臟重重地跳了一下。
他廣而不挑的閱讀中,曾經看過很多提到把活人做成標本的故事,以前只當是獵奇,從沒往心裡去過,而這一瞬,類似的念頭像是一道閃電,「嘩啦」一下打碎了他破破爛爛的精神世界。
如果讓那個人……再也不能說話,再也不能睜眼,再也看不到別人……
魏之遠覺得自己骨子裡一定就有某種屬於犯罪者的基因,他開始不受控制地往前走去,緩緩地靠近毫無知覺的魏謙,目光像是鬼迷心竅了一樣死死地盯在他身上。
耳背的宋老太已經睡了,而小寶還沒下晚自習。
近一點……再近一點。
近到能聽到魏謙細而平穩的呼吸聲,看見他一絲不動的眼睫。
就在這時,魏之遠心裡湧起毫無徵兆的悲傷,像是突然決堤的河,洶湧無情地衝散了他擁塞在五臟六腑中的冰冷的殺意,他聽見潮汐般轟然落下橫衝直撞的聲音,良久,又從中艱難地辨別出了自己壓到了水底的心音,那是簡而又簡的一句話……
他怎麼瘦了?
臆想的怨恨和活生生的人,將魏之遠心裡的愛和欲撕裂開了。
它們痛徹心扉,而後兩廂抵死糾纏,最後一起歸於近乎絕望的澄淨。
唯有刻骨銘心的感情能壓倒與生俱來的偏執,魏之遠知道,自己一輩子也不可能再動這樣的感情了。
他終於放下了端著的碗,蜷縮起被燙得發紅的指尖,輕輕地推了魏謙一把,彎下腰柔聲說:「哥,醒醒了。」
……醒醒了,我快要忍不下去了,求你看看我,我能為你粉身碎骨、魂飛魄散。
後來什麼都沒發生,魏謙被他叫醒以後,光速乾掉了一大碗炒飯,可能連嚼都沒顧上,就直接吞了,而後他晃晃悠悠地拽起行李箱回屋,不出意料地看見了三胖幹的好事——能自由出入他房間,還辦得出這種無聊事的人不作他想。
魏謙不喜歡揣度身邊的人,更懶得深思三胖這是什麼意思,只是感覺那胖子閒得蛋疼,自己罵了一句:「我操,死胖子。」
然後他就把包裝盒撕下來扔了,打火機看了一眼,也看不出值多少錢,隨手塞進了抽屜裡,最後把馮寧的照片扣過去,找了個犄角旮旯塞了起來。
在他眼裡,這只是三胖一個小小的惡作劇,小到連調劑生活都談不上,轉眼就忘了。
他丁點也沒有察覺到魏之遠心裡的一番天翻地覆。
那天是舊曆二月初一,似乎是應該快要開春了,可沒有春意,一整天都是陰沉沉的,似乎在憋著一場大雪,河水也沒有開化,春天在一片天寒地凍裡被遺忘了。
C市的項目危機正式解除,整個公司迎來了遲到的年會和格外豐厚的年終獎。
不知道是不是精神狀態太放鬆了,那天魏謙竟然起來晚了,三胖準備出發的時候跑來敲他的門,才硬是把他從床上挖起來。
魏謙兵荒馬亂地收拾乾淨自己,急急忙忙地出門了,自己丟三落四了什麼東西也沒注意到。
途中,三胖還在試探著問魏謙:「小遠跟你說什麼了沒有?」
「小遠?」魏謙愣了一下,「跟我說什麼?」
三胖眼珠轉了轉,忙打了個岔忽悠了過去,這段日子他精神也一直緊繃,唯恐魏之遠做出什麼不理智的事傷人傷己,然而魏之遠竟然好像變成了一顆啞炮,什麼都沒說,什麼都沒做。
三胖想:奇了怪了……別是憋著什麼大主意呢吧?
三胖:「哎,對了,晚上晚會,連慶功宴一起,你知道了吧?」
魏謙:「嗯。」
三胖:「大股東跟以前各個合作方的請柬都送到了,家屬也可以帶……哦,對了,我還叫了馮寧。」
魏謙翻了個白眼。
三胖立刻警告說:「你可是紅口白牙答應過了!」
魏謙只好擺擺手,隨他去了。
結果到了晚上慶功宴會的時候,張總又出來作妖,提議他們把C市那項目的大實景圖掛出來,大家好一起沾沾喜氣。
雖然張總這貨是把他們弄得如此灰頭土臉的罪魁禍首,不過面子畢竟還是要給的,魏謙讓人一找才發現,他早晨被三胖催得急,壓根忘了帶出來,只好臨時給家裡打電話,讓剛好在家的魏之遠給他送過來。
魏之遠到他們公司樓下的時候,董事長秘書正在等著他,忙迎上來親切地說:「你就是魏董的弟弟吧?他讓我在樓下接你一下。」
這位董事長秘書三十來歲,長相是純姑娘,性格卻能毫無過度地分裂出一個糙漢,剛春風和煦地和魏之遠說完話,轉眼接了個電話就開始瞪眼罵人:「你說你把演講稿放他桌上了?你指望魏董自己發現?你怎麼不指望哥倫布再他媽發現一次新大陸啊?就你們這幫小孩,辦事能不能仔細一點?我提醒你多少次了這個要你親自交到他手上,用你的嘴告訴他這個是晚宴開始前的開、場、白,不是什麼莫名其妙的合作方發來的賀電!你不告訴他還有這麼個東西存在,他敢直接上去鞠個躬告訴大家吃好喝好,你信不信?」
隨後,她意識到自己好像在人家弟弟面前抱怨了老闆,連忙沖魏之遠擠出了一個笑容,以其極快的變臉速度,用小碎步日本女人般微弱和緩的聲音說:「你還是學生吧?唉,我們這些人的工作就是替老闆注意這些他們無需注意的雞毛蒜皮,想起來還是上學比較有意思呢。」
魏之遠禮貌地衝她笑了一下,心裡卻著魔一樣地反覆回想起面前女人方才說過的話。
你指望他自己發現?
用你的嘴告訴他……
電梯很快到了,秘書小姐接過魏之遠帶來的東西,細心地給他安排了位置:「謝謝你啊,專門跑一趟,魏董讓你吃完飯坐他的車一起回去,有照顧不周的地方跟姐姐說。」
說完,她踩著高跟鞋,犯了狂犬病的炮仗一樣跑了。順著她的「發射軌道」,魏之遠抬起頭,就看見了他哥。
魏謙穿了正裝,一手插在兜裡,上衣衣擺被他的手腕折起一點,微微翹起的一側就露出若隱若現的腰身,脖子上的領帶還是當初魏之遠給他買的那條。他手裡拿著一張別人剛遞給他的紙——大概就是方才秘書小姐說的開場白。
他滿臉不耐煩,似乎想說什麼,一個禿頂老頭向他走過去,他只好短暫地收起自己的個人情緒,也露出一個熱情得恰到好處的笑容。
魏之遠不錯眼珠地盯著他,直到全場的燈都暗了下來。
他看著魏謙把那張愚蠢的紙隨手一折,塞進董事長秘書的杯子裡,空著手走上台,做了一個簡短又得體的開場。
大廳裡唯一一束光跟著的是他,所有人的目光跟著的也是他。
魏之遠不受控制地想起了更多的事——那十多年前用板磚拍死野狗的少年,被那封經年日久的「遺書」逗得前仰後合的大笑,那大步走過來抱起他、讓他鬆開手裡鐵管的懷抱,那染上時光般的跌打損傷藥膏味和煙味,那異地他鄉賓館深夜裡一身的傷痕……
冷漠的,堅定的,溫和的,焦慮的,憤怒的,無奈的……所有那人臉上出現的表情。
觥籌交錯的宴會開始,每個人都如釋重負般地輕鬆愉快。
魏之遠毫無食慾——他看見了那個照片上的女孩,她本人似乎比照片上更漂亮一點,站在三胖旁邊,羞澀地看了魏謙一眼,又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就是她吧?
以魏之遠的聰明,他後來冷靜下來,其實就已經猜到了他哥和這個女孩還沒有開始過,多半是三胖故意刺激他的……可是那又怎麼樣呢?
他們完全可以現在開始。
魏之遠沒吃東西,他只是空腹灌著酒,在酒精的味道中心神俱疲地想,我要放棄嗎?
在他的印象裡,凡是他想要的東西,還從沒有什麼是得不到的,而這樣的傲慢終於經歷了一次毀滅性的打擊。
魏謙不知是為了給三胖面子,還是出於本心,在馮寧面前表現得像個真正的青年才俊,三胖看著他們言笑晏晏,不動聲色地走開了,臉上是一塊石頭落了地的鬆快。
魏之遠閉上眼,心裡糾結起伏不休的天平終於往一邊偏去。
他想:好吧,我放棄了。
隨後,一整杯的烈酒被他一股腦地灌進喉嚨,火辣辣地一路燒進胃裡,舌尖上殘留的卻全是苦���。
直到宴會結束,魏謙才擺脫了其他人,在秘書的指點下找到了魏之遠。
魏之遠一身酒氣,眼神已經不對了。
魏謙只好架起他:「臭小子,還學會喝酒了,沒人管你了是吧?」
魏之遠癡癡地盯著他,一聲不吭,順從地順著大哥的手勁站起來。
魏謙一路把他扶到了自己辦公室,把魏之遠丟在椅子上,倒了杯涼茶給他:「醒醒酒再回家。」
說完,魏謙脫下西裝外套,準備一會出門換上大衣。
魏之遠輕輕地開口:「哥……」
魏謙拽鬆脖子上勒得他有點難受的領帶,隨口應了一聲:「嗯?」
「他就要屬於別人了,」魏之遠絕望地想,「我已經放棄了,他卻還從來不知道……」
秘書的話鬼使神差地又在耳畔響起。
用你的嘴告訴他……告訴他……
魏謙發覺他半晌沒出聲,還以為這醉貓已經睡著了。
他的領帶解了一半,幾根手指還在當中纏著,側過半個身似乎想要回頭看魏之遠一眼,就在這時,魏謙猝不及防地被一個人猛地撲得後退了幾步,直抵到牆上。
「哥……」
那人重重地壓在了他身上,又這樣囈語一般地叫了一聲,在魏謙還沒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的時候,他那還被鬆鬆垮垮的領帶纏著的領子突然被人粗暴的拽了過去,一個灼熱的吻堵住了他尚未開口的疑問。
孤注一擲般的激烈,轉眼就摧枯拉朽地席捲過每一個角落。
魏謙腦子裡一片空白。
直到這時,他才嗅到了對方身上的酒味,濃烈到無法言說。
就在這時,魏謙辦公室的門被人打開了,門響終於喚回了魏謙的神智,他一把推開魏之遠。
門口站著的是吃了一驚的老熊。
魏之遠踉蹌著往後倒去,後腰撞在魏謙的辦公桌上,桌上的文件搖搖晃晃地掉了下來,魏之遠爛泥一樣地滑了下去,他感覺自己下巴上挨了一拳,嘴唇被牙碰破了,血腥味沖鼻,滿眼的金星。
老熊很快反應了過來,迅捷地回身把門反鎖了,而後衝過去一把拽住魏謙又要落下去的拳頭。
「謙兒!」老熊用肩膀頂了魏謙一下,把他拖開了一段距離,衝著他的耳朵說,「別在這,行了!」
魏謙覺得自己的太陽穴帶起了眼角一陣沒完沒了的亂跳,站直了之後眼前幾乎一黑,臉色頓時煞白,魏之遠把他氣得胸口一陣陣地尖銳地刺痛。
老熊硬把他按在了椅子上,皺著眉看了魏之遠一眼,彎腰查看:「沒磕著後腦勺吧?還站得起來嗎?」
魏之遠拒絕了他伸過來想要扶他一把的手,搖搖晃晃地爬了起來,他的酒已經醒了,卻什麼也不願意想,什麼都不願意說,就這樣默不作聲地站在了一邊。
魏謙胸口堵著的一口氣好半晌才上來,他不想和老熊解釋這是怎麼一回事——連他自己都弄不清這是怎麼一回事,只好故作鎮定地說:「找我什麼事?」
老熊看了看這一地的混亂,嘆了口氣,彎腰撿起被魏之遠撞掉的文件,沉默了一會,輕聲說:「謙兒,我想走了。」
魏謙:「什麼?」
「我打算帶陳露走了。」老熊低聲說,「不幹了,我的股權會轉讓出來,你要是願意接,就接過去,不願意的話,我轉給協力廠商。」
魏謙深吸了一口氣:「你決定了?」
老熊:「嗯。」
魏謙長長地沉默了好一會,終於閉上眼睛,輕輕地揉了揉太陽穴:「好,我接。」
老熊衝他點點頭,不打算再逗留下去,轉身走了,臨出門的時候,他深深地看了一眼站在陰影裡的魏之遠,似有若無地嘆了口氣:「我給你們叫個司機。」
而這天晚上,似乎還不止這些鬧劇。
魏之遠走了以後,小寶回家了一趟,確定宋老太有吃的,又給她拿了藥,才匆匆要回學校上晚自習。
宋老太照常送她到門口,囑咐她路上慢點,就在這時,宋老太感覺到了自己胯下一片溫熱,她先開始沒反應過來。
小寶無意瞥見:「呀,奶奶,您褲子怎麼濕了?」
宋老太如遭雷擊一般地低下頭,她震驚且羞恥地發現,自己竟然失禁了。
小寶隨即明白過來,忙把書包丟在一邊,挽起袖子要幫她換褲子:「我先幫您……」
宋老太慌慌張張地後退一步。
「奶奶別動,我給您換褲子。」
「不用!」已經吐字不清的宋老太近乎是嘶吼著喝住了她。
小寶沒聽見過她發出這樣淒厲的聲音,一時愣在了原處。
宋老太哆哆嗦嗦地說:「你……你去……上學去吧,走,走你的。」
小寶:「奶奶……」
宋老太一手扶住牆,一手衝她揮舞起自己的枴杖:「走!快走!」
小寶遲疑了一下:「那您自己能行嗎?」
宋老太衝她咆哮:「走!」
小寶:「好好好,我馬上走,您……那什麼沒事啊,您慢點,晚上回來我給您洗褲子……啊啊啊,您別著急,我馬上走,馬上走。」
宋老太粗暴地趕走了小寶,覺得自己一根脊樑骨都被抽走了,她花了足足半個多鐘頭的時間,才吃力地換下了尿濕的褲子,換出了一身大汗。
她想在一片腥臊味中大哭一場,可眼淚已經乾了,她依然是一顆淚珠也哭不出來。
十年前,她從老家一路撿破爛來到這個城市,那時她是多麼的窮啊,多麼的體面啊。
她從未想到自己有一天會落到這樣的地步,宋老太幾乎覺得自己已經不算一個人了。
就在這時,家門被敲響了。
宋老太許久沒有反應,直到外面傳來麻子媽的聲音:「老姐姐,您睡了嗎?」
宋老太挪過去,給她開了門。
只見麻子媽坐著便捷式的輪椅,單臂還拎著一根拐,把自己打扮得容光煥發,除了一張地圖和一瓶礦泉水,她什麼也沒拿。
「老姐姐。」麻子媽說,「趁他們都不在,我就要走啦,再不走,天就要暖和了,我就得等到明年了。」
天暖和了,流浪的人就沒那麼好死了。
「我跟你告個別。」她說完,艱難地操縱著輪椅走向電梯。
就在這時,宋老太突然出聲叫住了她:「她姨!」
麻子媽回頭看著她。
宋老太嘴唇顫動良久:「我……我跟你,跟你一道。」
麻子媽好像早料到了,絲毫不吃驚地說:「你來吧。」
兩個女人就這樣,在一個行將落雪的寒夜裡,相攜著走出了所有人的視線之外,再也沒有出現過。
宋老太來自中秋,走去了早春,帶著她最後的尊嚴和體面。
「我好歹認識兩個字,寫了遺書,還留了一封信呢。」路上,麻子媽和宋老太這樣說。
宋老太問:「信上寫的什麼哪?」
「寫的是『我不是死了,只是走了』。」
並非死別,只是生離。
痛苦與幸福,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唯黃昏華美而無上。 ——海子。
|卷一|卷二|卷三 |
0 notes
Text
零の会
2020年6月6日 COVID19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評
オンライン句会
坊城俊樹出句

坊城俊樹出句
香水の独りの真夜をもてあます
他人事のやうな顔してサングラス
相模湾てふ塩水を泳ぐなり
胎の子に夏の沖てふ水遙か
小心で潔癖性でサングラス
角海老の裏よりぬつとサングラス
もう二度と愛せざる日の水着きて
騙すなら騙し通してサングラス
捨てられし夜を外さざるサングラス
夏風邪の大群衆とすれ違ふ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特選句 句評
色街に飼はれ緋鯉の水暗く 美紀
「暗く」は「昏く」が良いかもしれぬが、零の会らしいは緋鯉という生命と色街の女の命のぶつかり合いがもの凄い。季題の本情と女の本情の絡み合い。零の定番。
下闇を流るゝ水は星と遭ふ 順子
うまいなあ。やんなっちゃうなあ。「下闇」がもの凄い。「☆」が出て来る飛躍の世界。
噴水を昂りながら離れけり 伊豫
これもうまいなあ。やんなっちゃうなあ。「昂ぶり」ねえ、そうなんだろうねえ。私は唐変木なので分からない。女性の性の句だから佳人の作者だろう。違ったら面白いが。
水音を石柱に聴く夏館 眞理子
これもうまいなあ。やんなっちゃうなあ。石柱はこの館の池ノ辺に立つロココ式なんだろうか。丹下健三先生の作にもあったような。
父の恋滲んでをりしサングラス 順子
よくわからないのだが。「滲む」が。感覚的であろうが、遺品のレンズの表面にキズか曇りがあってそれを言うのか。写真の父上か。亡くなったお父上の若き日を忍んで。
元帥のポーズ決まりてサングラス 佑天
マッカーサーのこととは誰でもわかる。だから普遍性のある省略である。「ポーズ」も誰しもがあの写真を思い出す。
夏蝶のやはき香りとすれ違ふ 三郎
ものすごく良いでもないが。季題の本意だと「やはき」でもないが、逆説的に本意を覆しているのが面白い。「春蝶のもの凄き香とすれ違ふ」の如し。
万緑や石の狐の舌真赤 和子
季題が効いています。石から来て、急激に石の舌が真っ赤になるのも良い展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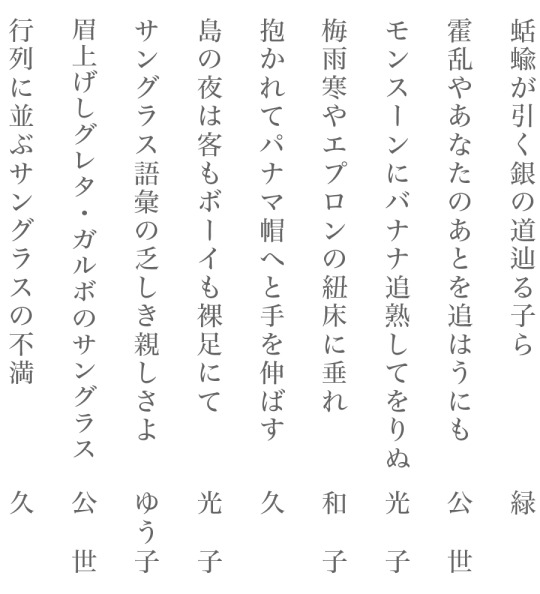
蛞蝓が引く銀の道辿る子ら 緑
よくこんな光景が出てきた。言われてみると私も同じことをしていた。現今の子もするのだろうか。郷愁また郷愁。
霍乱やあなたのあとを追はうにも 公世
「霍乱」かなるほど。この作者のこだわり方は凄まじい。季題の斡旋にも苦労したろうが、よく見つけた。日射病では物語として様にならぬ。
モンスーンにバナナ追熟してをりぬ 光子
なんとなく良い。「追熟」が良いのだろう。堅苦しいような、気象庁の長期的天気概況のような、歴史と地理の授業のような、東南アジアの社会ニュースのような。
梅雨寒やエプロンの紐床に垂れ 和子
梅雨の寒さと、この光景の接点がわからなくて印をつけてなかったのだが、よく見ると映画の一場面、特に日本映画の日常のアンニュイのようなものが見えてきた。地味だが。
抱かれてパナマ帽へと手を伸ばす 久
抱擁であろう。男女か。父と子か。どうも釈然としない。抱かれているのに、男のパナマ帽を脱がせる女性か。先にパナマ帽を取ってから抱擁するのが道理だが。嗚呼知りたい。
島の夜は客もボーイも裸足にて 光子
なんとなく良い。いかにも知っていたつもりだが、案外知らなかった事。裸足という季題に南国のアンニュイのようにものが足されて、良いんではないかい。
サングラス語彙の乏しき親しさよ ゆう子
なるほど。「語彙」ときたか。まあよくわかります。
眉上げしグレタ・ガルボのサングラス 公世
そう言えば、グレタの写真にサングラスの片方をズリ揚げたのがあったような。その写真は彼女の代表的なものか。「し」という助動詞の過去をあらわす部分を的確に取り入れたということに乾杯。
行列に並ぶサングラスの不満 久
なるほど。「不満」ときたか。全員そうだったら可笑しいですね。この列は、今回のコロナ騒動に関わることだろうか。海外でも日本でも、コロナ以降に行列を離れて並ぶ風習が。こんな句ならば街の風景と人々の惨状をコロナという言葉を使わないで諷詠できるのである。
▲問題句 句評
真つ白きあぢさゐだけが揺れてゐる 小鳥
なかなかいいのだが、類句か類想がある。そこいらの句会なら入選。
グラサンと言つたりもしたサングラス 荘吉
この俗っぽさは面白いが、いまさらグラサンの事を知らない人も居らず、だからユーモアでもない。サングラスの過去に拘るのもわかるがもっと飛躍を。
拍刻む昭和ロックや黴げむり ゆう子
これは名誉ある△です。唯我独尊句。「一拍」ずつ音を刻むのだろうが、ロックはビートと思うのですが。「黴げむり」は古きレコードのことか。昭和のロックは「頭脳警察」のことであろう。
軍楽隊トロンボーンはサングラス 荘吉
軍楽隊やジャズの古株となれば、トロンボーンはサングラスに決まっていると感じる。
サングラスはづさず隠れナルシスト 千種
面白い。ただし、サングラスをはずさないのは表ナルシストである。
大穴を狙う姐のサングラス 伊豫
面白い。実に面白いのだがなんか作りすぎじゃあないかい。太地喜和子か何かか。太地喜和子さんはうちの隣マンションに居ました。亡くなりましたが。「狙ふ」ですな。
入選句 句評
十薬に水の匂いの混ざりくる 慶月
上手い句だ。「匂い」は「匂ひ」。零の会だと、名詞や動詞の場合の活用は正確に。国語辞典と動詞や形容詞の場合は活用表を見て作るべし。
人間(じんかん)を見据えてをりぬサングラス 公世
これも格調高い良い句。「見据ゑ」だったら特選でしたのに。
カラフルなアイスクリームまでの列 久
いい句です。ただ、「カラフル」がアイスクリームに掛かるか、列のとりどりの洋服に掛かるかが少し迷う。後者かなと思うが、こういう並列の意味を醸す句はよくある。
星座の名ひとつも言えぬ端居かな 光子
「言えぬ」は「言へぬ」以下同文。
サングラスかけて少女に戻れれば 炳子
戻れないであろう。
入選句
水陰の灯心蜻蛉風立ちぬ 炳子
サングラスかけて少年は目敏し 悠紀子
サングラス浜の女になりきつて 秋尚
カレー屋のすぐに汗かく氷水 千種
長靴をふがふが踏んで水あそび 和子
深ぶかと女の祈りうすごろも 美智子
羅の母を鏡に見送りぬ 順子
水無月や津軽海峡黝き 佑天
片陰の姪は見知らぬ人とゐて 三郎
サングラス外しすとんと胸に差し 荘吉
水中花水差しやれば泡を生む 順子
日覆に赤い生き物売られけり 和子
風でなきものに蠛蠓揺らぐなり 千種
青梅や惑星のごと水に浮く 順子
竹落葉見えざる軸を旋回す 千種
口角の上がりて外すサングラス 小鳥
紫陽花や列車の音をとほく聴き 美紀
黴の書に詰まる想ひの往き来かな 梓渕
受話器から声を掻き消す日雷 清流
男独り仏を彫りて短夜を 炳子
皮肉屋のシャイな唇サングラス 千種
短夜や抱けばしゃべる人形と 炳子
サングラスと堕つる夕陽を見つめをり 眞理子
水馬覗き込む橋朽ちかけて ゆう子
駅からの海岸通りサングラス 要
短夜や蛾に二粒の黒眼 和子
妖精のかくるるおいど釣鐘草 眞理子
森深く獣も飛ぶか黒揚羽 千種
雑談の背中に揺らぐ水陽炎 三郎
噴水の風にながれてゆく港 伊豫
玉虫の星霜経たる今も美し 瑠璃
花橘残んの月を匂はしむ 炳子
昼前のバックシートに裸の子 久
緑蔭に謎の石組み団子虫 要
古池に水輪をつぐや若葉雨 光子
バザールに紛れて来るサングラス 順子
花魁の気位高し花菖蒲 要
タバスコとアイスコーヒー運ばれて 小鳥
水飴を手に緑蔭の紙芝居 瑠璃
サングラス後ろに掛けて粋がりて 慶月
紫陽花や小さき嘘をつかれゐて 美紀
蹲る猫の目蒼く枇杷熟るる 炳子
門扉より急ぐ白シャツの青年 小鳥
ねつとりと鳩歩くなり日の盛 和子
薔薇朱しその唇が毒を吐く 久
雲の上を軽鴨の辷りし水鏡 順子
一舟の水漬きて雷雨去りにけり 梓渕
夏蝶の想ひありしか子のそばに 三郎
軽薄を貫きとほすサングラス 要
自転車で夕立風と競ひたる 緑
新世界はじまつてをり揚花火 悠紀子
金魚売酔ひの名残の足さばき 悠紀子
なにもなき日なれど辻の立葵 順子
サングラス外し頷く男の子 伊豫
水槽の目高昨年より孤独 瑠璃
夏の燈に透けて動かぬ白蛾かな 和子
0 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