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展七人七色
Text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東京都文京区は雨が降っております。
昨日はテーブルウェア・フェスティバルの最終日が行われました。
最終日もいつもお世話に成っておりますお客様方にご来店を頂いたり、新規に知り合わさせて頂いたコーデネーターの方々にもアレコレと気に入って下さり、いつもの最終日より小忙しい一日でした。
展示会終了後、展示商品の箱詰め、展示在庫の段ボール箱詰め、什器の後片付け、車への積込みも無事に終え、一人での作業でしたので、何時頃まで掛かるやら不安でしたが、予定より早めに終えられました。
今回のテーブルウェア・フェスティバル、開催前からアレコレとお話も有りましたが、いつものお客様方や新規のお客様方、ギャラリーやショップや飲食店、その他の色々な皆様のおかげで、七日間良い展示会を終えられました。
期間中、川連の軽くて優しい手触りを、多くのお客様方に感じて頂け、嬉しいお言葉も頂き、本当に有難うございました。
そして今日はこれから、身支度を整えてから、秋田県湯沢市川連へ、車で帰省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皆様にとって今日も、良い一日と成ります様に。
https://jujiro.base.ec
#秋田県 #湯沢市 #川連漆器 #川連塗 #川連 #国指定伝統的工芸品 #伝統的工芸品 #伝統工芸 #秋田工芸 #秋田の物作り #秋田の物つくり #漆 #うるし #ウルシ #髹漆 #mieux #寿次郎 #テーブルウェアフェスティバル #ブースNo47秋田川連塗寿次郎 #12月5日から11日まで #プリズムホール #展示会最終日の様子 #展示会帰省日 #出張車移動 #車移動 #kawatsura #japanlaquer #JapanTraditionalCrafts #KawatsuraLacquerwareTraditionalCrafts #jujiro
10 notes
·
View notes
Text
youtube
鳳凰 龍 細密石彫刻製作 石基壇 聖徳太子殿 念佛宗仏教美術 The Prince Shotoku Hall The Buddhist Art of Nenbutsushu Stone carving
聖徳太子殿 The Prince Shotoku Hall
念仏宗無量寿寺(念佛宗) 総本山 佛教之王堂〜三国伝来の佛教美術 日本では類例を見ない四手先総詰組様式、および三手先腰組付縁の八角堂 It is a grand octagonal shrine with four-stepped intermediate bracket complexes under the eaves and three-stepped bracket complexes under the veranda, which is peerless in Japan.
概略 高さ17.2m(基壇、棟飾り込) 側通り柱間4.85m
輪島塗による高蒔絵、及び彫金が施された厨子に、中華人民共和国、工芸美術大師・佘國平佛師制作の「和国の教主」とうたわれる聖徳太子像がお祀りされている。
念佛宗(念仏宗)無量寿寺 聖徳太子殿 建築的特徴
他に類を見ない様式 四手先総詰組、三手先腰組付縁の八角堂は他に類を見ない。特に四手先総詰組は、日本建築史上初めての独自の変形組み手である。特殊な組み方をすることにより、組み手同士の立体的干渉を回避している。この念佛宗(念仏宗)ならではの、独創的な手法は、専門家をも捻らせている。日本の大工の始祖とも崇められる聖徳太子も、きっと納得されているに違いない。 天平の文化が華やかなりし頃、神社仏閣は、鮮やかに朱で彩られ、外国文化を吸収、醸成され、それはきらびやかなものであっ��。 そして今また千年の時を超え、念仏宗 佛教之王堂における聖徳太子殿は、天平時代の華やかさを凌ぐ存在感で、参詣者を迎える。 外装壁部には「天女」、阿件形の「鳳風」、衆生を導かんと雲を従えて天下る阿件の「龍」が、また蛙股部には「宝相華」が、胡粉の白一色に塗られた彫刻で荘厳されている。腰組部と階段脇の耳石にも阿件の精緻に「鳳風」が彫刻されている。 これら数多くの彫刻、彩色で彩られた御堂は、典雅な趣にみあふいざな満ち溢れ、訪れる者を夢の世界へと誘う。 桟唐戸は丹青技法による極彩色が施された「宝相華」や「転法輪」、「鳳凰」の彫刻で荘厳され、八方を守護している。 世界に誇る槙の日本庭園に囲まれた姿は、飛鳥・天平時代を偲ばせる典雅な趣に満ちている。 軒裏に扇垂木を用いており、内部は韓国人間国宝・李萬奉大僧正猊下、及び、直弟子洪昌源師制作の、韓国古来の伝統的丹青技法による彩色が施され、合計428点の彫刻が太子を賛嘆している。 念佛宗(念仏宗)無量寿寺 聖徳太子殿 建築的特徴 三国伝来の佛教文化 念佛宗(念仏宗)無量寿寺 佛教之王堂の聖徳太子殿は、かつて、聖徳太子が御堂にこもって、経典の解釈に没頭しておられる時、夢告(むこく)で教えを賜った(たまわった)との伝説から、法隆寺などでは平安時代より、「夢殿」(ゆめどの)とも呼ばれてきた。 ここ念佛宗(念仏宗)無量寿寺 佛教之王堂における聖徳太子殿は、日本の建築技術と韓国の丹青(たんせい)技法、そして中国の彫刻が見事に調和し、三国伝来の佛教文化の粋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例えば四手先総詰組様式及び三手先腰組付縁(こしぐみつきえん)は、他に比類なき日本建築の最高峰といえるもの。 また、内部に施された極彩色(ごくさいしき)は、韓国の丹青技法が日本で独自発展を遂げた平等院鳳凰堂の様式を踏襲したものであり、天井画写真下方の緑色部、「ぼかし」のような繧繝(うんげん)彩色や、全体的な白く縁どられた紋様等が特徴的である。 和国の教主 聖徳太子 念佛宗(念仏宗)無量寿寺 佛教之王堂 聖徳太子殿には、聖徳太子像をお祀りしている。天竺(インド)から唐土(中国)へ伝わった佛教の尊さを悟られ、神佛が習合する中、日本へ佛教を根付かせた「日本佛教の父」が聖徳太子。 「和を以て尊しとなす」 これは世界的に有名な聖徳太子『十七条憲法』の根幹(こんかん)をなす第一条の言葉。『十七条憲法』は、我が国最初の憲法であり、佛教精神を基(もとい)とした平和国家日本の建設に臨まれた聖徳太子の決意を表している。推古(すいこ)天皇即位の時、聖徳太子を摂政(せっしょう)とし、すべての政治を委ねられた。『日本書紀』には、その時、もろもろの豪族らは、君主と先祖の恩に報いるために競って佛をお祀りする場所を造ったとされ、以来、それが「寺」となった。つまり恩に報いるために寺が建てられ、佛教が興隆していった。 第二条に「篤く三宝を敬え。三宝とは佛・法・僧なり」そして「何れの世 何れの人か この法を 尊ばざる」として、どの時代、いかなる人であってもこの法を尊ぶべきことを明断しておられる。 そして佛教を基調とした国づくりをして、日本を統一国家に相応しい姿にされた。それによって寛容の心が根付き、民の争い事が減った。そして佛教伝来から僅か数十年で、当時の世界最新建築の佛教伽藍(ぶっきょうがらん)「四天王寺」「法隆寺」を建立した。聖徳太子が、「和国の教主」と呼ばれる所以。太子の願いは、大和の地に佛教を興隆させ、人々に平和をもたらすことでした。 丹生(たんせい)技法に彩られた堂内 青丹によし 奈良の都は 咲く花の 薫ふがごとく 今盛りなり 聖武天皇(しょうむてんのう)の御代、奈良で一世を風靡した丹生技法は、今、ここ社の地で大きく華開いている。 渡来して日本的発展を遂げた密度濃やかな繧繝(うんげん)彩色や、白縁模様で荘厳された極彩色の天井を、吉野檜の銘木に、拭き漆と熨斗(のし)模様を施した八角柱が八方から支える。 聖徳太子殿の「八角宮殿」 扉に描かれた阿吽の鳳凰は、聖天子(せいてんし)の出現を待ってこの世に現れ、飛天は、釈尊説法時に舞い降り、奉楽し、天華を散らし空中で舞う、とされている。 宮殿は、もともと、天竺(てんじく)における塔やその下の小室である「龕」(がん)を源流とし、後世、これが厨子(ずし)や仏壇に変化��た。 法隆寺玉虫厨子や橘夫人念持佛(たちばなぶにん)などは、その代表例。 念佛宗(念仏宗)無量寿寺 佛教之王堂 聖徳太子殿の「宝珠」 宝珠は、災いを除き、願いをかなえる力を持つとされ、聖徳太子殿の屋根に聳える宝珠は、聖徳太子の佛教興隆の成就を象徴しています。 この宝珠を護法神である、八頭の象が支えており、八方から佛敵より佛法を護り、宝珠の周りには、凡夫の煩悩を焼き尽くす火焔(かえん)が、勢いよく燃え盛っています。 聖徳太子殿の「輪島塗 高蒔絵」 日本の伝統技法の輪島塗りによる高蒔絵は、最高品質の漆を盛って、乾かないうちに松煙(しょうえん)を蒔きこみ、盛り上げ固めます。入手困難な「舟鼠(ふなねずみ)の蒔絵筆」を用い、輪島塗職人の二年間にわたる努力の末に完成しました。十枚の扉に浮かび上がる金色の『十七条憲法』の銘文は、職人会心の傑作です。 松竹梅と獅子 念佛宗(念仏宗)無量寿寺の宮殿下部には獅子が八方を護り、吉祥紋様の松竹梅が施されています。 風雪や厳寒に耐えて緑を保つ常磐木(ときわぎ)の「松」と「竹」、春、百花に先駆けて花開く「梅」を長寿・高潔・節操・清純などの象徴として「歳寒三友(さいかんさんゆう)」とも呼び、その吉祥紋様を背景に、獣類中、最も勇敢で高貴な、百獣の王の獅子が、宮殿を護っています。
2 notes
·
View notes
Text
【饼干cookie】khaji da/jaime Reyes
情人节看来只能发这个了,我没能写完
这篇是很久以前写的,除了ooc还有点幼稚
背景是毕业日的打工人jaime,两个小可爱的温馨日常
最新的一期看的,感叹万千,khaji da终于杀到人了。⊙ω⊙
我真的好爱他们两个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
埃尔帕索是个暖和的地方。
可惜在高中毕业之后,海梅就要去两个姨母那里打工了。离开埃尔帕索,说不定以后人们提到蓝甲虫时都不会再说他是他故乡的英雄了。这本就是有些伤感的事。
但是打工,海梅恨打工,餐饮服务业糟透了当一个超级英雄或许很难,但是那是件积极的事情,而打工,他宁愿和什么五维生物做交易靠亲吻某个超级反派来换取一个不用打工的生活。不用赚钱(被漂亮富婆包养!),或者非常有钱,在家每天悠闲的养着,没事出去救救人,拯救世界。
海梅在一堆盘子清洁剂产生的泡沫里走了神。五彩斑斓泡沫像是他的少年幻梦,暗含着他的青春活力,像棕榈城的阳光一样灿烂。
“ 我的超级英雄外甥还是连自己阿姨的忙都帮不上啊~”
泡沫破碎。
对于超英们来说,秘密身份应该是对家人坚决保密的事,但在海梅这里有点意外。他父母对他做超英没意见,而全家,就连七大姑八大姨几乎是个姓雷耶斯都知道他是蓝甲虫,会穿上蓝色的装甲张开甲虫翅膀在空中飞来飞去救人于水火之中。他开始担心有不省心的亲戚把这件事到处乱说。你懂的,小屁孩什么的。
他们会把他关在房间里供人参观,然后收门票
他从幻想中惊醒,卡基达在他的脑中发出一声咯咕。
“真是对不起姨妈,我又走神了,马上”
啊——————的餐馆!啊——寒酸的工作!海梅现在无比怀念当牙医的梦想,后悔自己怎么就没去上大学,去哥谭上大学也比刷盘子摔盘子好。
自从来到棕榈城,这里的一切都让人不适应,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孤独让海梅开始怀疑自己,在当了不少年的蓝甲虫后,他还是有些青涩,无论是懵懂的初恋还是打败致远的那段史诗,在平淡的英雄生活在时间的冲刷下都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每个成长的时期有每个时期需要解决的问题,他需要适应这样的生活,并做好长期打算。
获得力量,带着转变回归,但海梅不知道的是,他还有一份礼物。
【海梅。】
在又双叒叕把盘子掉到地上后,海梅被安排到餐厅的后门丢垃圾和扫地。漆黑的后巷里堆放着大大小小的黑色垃圾袋,在把它们都扔进箱子里时继续思考今后,但是他的脑子乱的像一段被扭起来的毛巾一样没办法再去想什么,迷茫和失败感还缭绕在心头。就在拿起扫把的时候卡基达忽然叫他名字,他差点没拿稳。
“怎么了?”海梅询问到,然后开始清理那些散乱的垃圾。
【记录你的工作效率呈下降趋势,根据你近期的激素活动水平,初步判断你正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你刚才造成非必要财产损失便是一个证明,根据列表查询结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会影响你的生活带来不好的影响和连锁效应。你似乎并不喜欢你的/工作/,它没有给你带来/积极的推进作用/】
海梅真的很纳闷卡基达为什么总喜欢把糟糕的情况复述一遍让它听起来更糟糕
“对,我一点都不喜欢”
【那你为什么还在继续,停止它】
海梅停下了,他有些无奈地回答
“我不能……这样的事情解释起来很麻烦,卡基,我不认为你能以好的方式理解它”他叹气
“我只能说,我不适应现在的环境,在埃尔帕索我们一直并肩作战的地方一切都是……舒适的。但是现在,布兰达和帕克在大学有自己要忙活的事情我们不能像以前一样关照彼此,这是个陌生的地方,而这么久了……我还没能有些归属感”
我还是感到很孤独”海梅把扫帚放下,他听到卡基发出细小的叽叽喳喳的声音,那是他在处理和思考的标志,海梅想他能理解这番话多少。
【你还有我】
圣甲虫有安慰自己的宿主的协议吗?海梅从未听和平使者提过类似的服务协议,他们本来的任务就是控制宿主然后作为渗透者服务致远。但不管怎么样,能听到他重点指出自己一直在陪伴这一点,真是令人感到安慰。
“……对伙计”
如果卡基达想要帮到海梅什么,他能为海梅做什么?
“我还有你……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互动或许情况就能好一些了”
【刚才我没能及时阻止那个财产损失,致歉】
“额不,没关系的卡基你……你怎么了?”
海梅敏锐地察觉到,卡基说出的话和最近发生的事情都有些问题。
【在上次对致远的抗争中,经过多面检查我的部分系统仍未完全修复】
很好,这下这里有两个状态不好的家伙了。
“你没事吧?”事情一下子严肃起来了,海梅还记得上次卡基达系统“故障”造成的后果。
【推算对今后的事件处理没有大碍,但需要10个地球日的时间修复】
“那就好,这两个月,我也没有什么英雄事业要做,除了去边际虫族那里帮帮忙以外”
“没什么好担心的卡基,我们在棕榈城现在有帮手了
他把最后的黑色大垃圾袋使劲扔进垃圾箱,午后的阳光已经蔓延至饭店后面的巷子里面。
“现在,我们回去休息一会好了,反正也没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了”
他走进休息室,也就是餐厅旁的一个小房车里
“我真是受够这件工作了”
【你可以辞职,停止它】
“对,但……”海梅叹气,然后把围裙松开,拿下来揉做一团扔出去,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把旁边的点菜板也扔了出去
舒展四肢,随意的岔开双腿,放松心身
“卡基,可以帮我拿一下我的饼干吗?”
一条小小的黑色触须从海梅背后伸出来一直伸到食品柜,用与外貌不符的力气拉开柜门,又从里面精准地掏出了那袋未开封的饼干
海梅拆开包装袋子,一用力,许多饼干渣掉在地上
“SHI#!”姨妈会杀了他的,海梅叫了一声,做了个弯腰动作,又躺了回去,算了一会再收拾。
他拿出一块饼干送进嘴里,这味道现在尝起来实在太棒了,他迫不及待地又拿出一块
就他在吃饼干的时候,他的甲虫搭档蠢蠢欲动
圣甲虫不明白,海梅为何在疲倦的时候喜欢进行进食这一行为,按逻辑来说,处在疲惫状态缺少能量的碳基生物应该保持静止或休眠状态虽说进食可以补充能量,但圣甲虫毕竟没有嘴巴,他不真正理解口腔纳入食物,咀嚼,分泌酶,舌头搅拌,牙齿粉碎,品尝,吞咽
所以那是他无法接通的感受了。卡基达有些烦躁,身为有机物来思考的那一部分的好奇心和观察欲望让他产生一些念头,让他想要成为海梅齿间碾碎的饼干,没有犹豫和仁慈地被挤压和摧毁。亲密接触那些他不能触的牙齿,每一处牙槽,每一点缝隙。
不可抗的程序将他的主观意志从这一危险的想法拉回。
运行。
首先,他不可能变成饼干。其次,如果真的发生【咀嚼】那么碎的应该是海梅的牙
他把注意力又放回到上升的激素,很明显,在吃零食时海梅的各指数是一种叫做【甜蜜】的味觉刺激的特征,卡基达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有助于日常生活,于是他希望海梅能多有这样的刺激,最好是……自己也能让他感到【甜蜜】吗?
当他的宿主感到愉悦时,他似乎也会有同样的反馈,或许是因为物理层面上他们的血肉相连吧。自发地取悦自己的宿主,而不是遵从程序设计,卡基达把这一点归咎于“故障”。
海梅吃完第二块,酥脆的饼干安慰了他被工作搞疲惫的身心,这让卡基达又想去体验一下【味觉】。
但在他这么做之前,他计算完了这盒饼干的热量。
一堂健康讲座即将开始——
但这次卡基达放弃了,据已知信息,甜味食物会促进多巴胺产生,有利于心情愉悦
算了,他开心就好。
一块又一块。
一块又一块……
【啧】
【停止它,全部食用这袋饼干不利于你的健康和正常消化你即将到来的晚餐】
“拜托卡基,再来一块”
【别吃了】
“最后一块”
【停止它】
“圣甲虫!”
【海梅.雷耶斯!】
一阵沉默,然后海梅开心的笑了起来,就像回到了从前,从和朋友开玩笑得到欢乐
卡基达不理解笑的机制,他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过的生活中快乐过,也不知道在人类之间笑声是会传染的
但他也咯咯笑了起来,就和海梅一样,因为他们很开心,显而易见
在朋友的笑声中,海梅感觉没那么孤独了,至少没先前那么孤独了。
在瞬间洋溢的幸福感中,充满蝉鸣凉爽热闹的夜又降临在棕榈市,这座城市正在点起新的微光,城市上空,一道蓝色流星划过
——————————————————
快去上大学啊jaime,加油哦⊙∀⊙!
我需要更多全宇宙第一可爱的圣甲虫宝宝和海梅·雷耶斯💙💙💙💙(*˘︶˘*).。。:*♡
希望你喜欢:D
#jaime reyes#khaji da#blue beetle#scarab love#khajai#khaime#khaji da×jaime Reyes#祝我产品情人节快乐(*๓´╰╯`๓)♡
3 notes
·
View notes
Text
【DC/Superbat/超蝙】Give me a hug before you fly 梦安眠于九霄 (Chapter 1)
纯爱,中间有刀,HE,慢更,预警有NC-17
吃了官方刀之后神智不清的产物,可能有狗血/双向暗恋/各种无厘头的幼稚玩意儿,是一个陷入情网的小镇男孩和自欺欺人实则一直在私心公用的笨蛋阔佬互相吸引、试探,然后经过一堆乱七八糟的乌龙和蓄谋策划之后终于亲上了的故事。(你闭嘴)
感谢阅读,希望你喜欢。
有私设,开头借鉴《正义联盟:末日》的某个片段。
——————正文分割线————————
Summary:克拉克不是一个容易感到孤单的人,但在遇见布鲁斯之后这种情况被改变了。而且被改变的不止这一样。
***
他鬼使神差地躲进树丛里,看着布鲁斯一瘸一拐地朝不远处停在阴影里的蝙蝠车走去,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布鲁斯走得很慢,这种缓慢里带着某种艰难的意味,以及逐渐超负荷的痛楚。克拉克默默看着那个黑色的身影朝安静停着的蝙蝠车的位置走去,感觉有一种沉重、莫名的东西压在背上,让他喘不过气来。
但他没动,还不是时候。谢天谢地,虽然作为一个记者的时候克拉克的跟踪技术很蹩脚,但作为一个氪星人,当他想悄无声息地窥伺一个受了伤、因为失血过多而头脑发晕、以及不知道多久没阖眼的普通人类的时候,他可以动用某些超能力来隐藏自己的行迹而不被对方发现,即使那个人是蝙蝠侠。
他就这样屏息凝神地隐藏在草丛里,一动不动,像一块石头。布鲁斯的背影在跳进蝙蝠车之前矮了矮,原地停顿了片刻。一瞬间克拉克以为他会就此昏迷,差点就要冲出去了。但随即那团黑漆漆的影子从地上轻轻跃起,准确地落进蝙蝠车的驾驶座里。克拉克听到一声隐忍的闷哼和轻微的嘶声,好一会儿,蝙蝠车顶上的车盖还没合拢,他能隐约看到两只尖耳朵小幅度地晃了晃。布鲁斯歪在椅背上,胸口急促起伏,他用深呼吸调整自己的状态,呼出长气的时候有些颤抖。
铅元素能够隔绝他的透视能力,却不能掩盖这些细小的声音,它们是只有像克拉克这种人才能捕捉到的、极其私人化的线索,暴露了布鲁斯令人担忧的糟糕状态。但克拉克还记着自己现在在做什么,他敢打赌,在他冲出去之前蝙蝠侠就会察觉到自己被人跟踪了,紧接着就是尴尬的抓包、审视、手足无措和沉默不语,或许他身上还会多几个等他回到家换衣服的时候才会发觉的微型蝙蝠监视器,再下一次,他获得类似这种机会的概率会更渺茫。想到这里,克拉克拽着自己披风的手默默攥紧了。
克拉克从前很讨厌偷偷摸摸地做什么事,客观上来说他也不擅长那样。从技术层面来讲,是因为他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毕竟你不能指望一对以经营玉米农场、赶集和蓄养牲畜为生的堪萨斯夫妇有培养出一个出色的情报特工之类的想法。倒不是说他对这种在大众眼中兼具危险和浪漫气息的特殊职业有什么偏见,克拉克只是无法想象怎么能有人做到在背着一身子弹、枪械和各种丁零当啷作响的金属小玩意,外加一身厚重的防弹背心的情况下还能悄无声息地到处乱窜(直到多年之后克拉克亲眼见到了那位声名远播的哥谭守护者。)——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连半夜偷偷到厨房里偷黄油面包吃都会被老妈发现!而且不止一次。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克拉克坚定地相信,那些能够背着一身装备、无声无息地走路的特工跟他一样会飞。
另一方面,堪萨斯的阳光和夜空都过于广袤,这里的雨水降落在松软肥沃的泥土里,它们滋养大地,润泽作物,而不是流进城市地下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变成滋生寄生虫、爬行者和病菌的一潭死水。日复一日地,堪萨斯的田垄养成了克拉克温厚不设防的性情和对善意的习以为常,一方面是因为迅速凸显的能力足以支撑他轻松越过那些在人类看来不可逾越的屏障(克拉克闭口不谈最初这种“轻松”是如何给他带来恐惧和孤僻的,而他又是如何克服它们的),另一方面是,在正义联盟成立——不,应该说是韦恩集团投资建成瞭望塔和JL地球基地之前——他从没想过自己也能像其他人那样正常地接受某种“训练”而不用担心对其他人(或建筑)造成灾难性的伤害。
但这种温厚不代表小克拉克是个不够聪明的孩子,阳光给他带来的不止是健壮的体魄和敏锐的感知,还有异乎寻常的敏感性格。无论如何他只是个孩子,为了得到同伴们的认可和赢得友情,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伪装和示弱。起初这像一个令人失笑的悖论:一个能够在短短几秒内穿越整个堪萨斯州的孩子,却追不上一颗被木棍击出的棒球。克拉克仰着脸,双眼盯着那颗在半空旋转的白色小球,他知道只要自己轻轻垫一垫脚,就可以用一只手准确地把它抓进掌心,但他没有那么做,克拉克装作焦急地看着它飞过自己的头顶,实则是在注意摔倒在草地上时不能用自己的手肘把草坪压出一个显眼的坑。
他轻轻扑倒在地上,双手捧着落下来的球,像一只笨拙的小狗那样打了个滚,听到不远处的队友纷纷欢呼起来。
“触地得分!”
场边的教练高声喊道。
克拉克浑身沾满草屑,趴在地上快乐地朝队友挥动手臂,队友们吹着口哨朝他飞奔过来。那一刻的快乐在阳光下闪耀,是如释重负的,也是无比真实的。
克拉克就是这么逐渐学会生活的。
再长大一些之后,克拉克逐渐了解到,他的能量来源于那颗温和耀眼的恒星的光辉而不是地球上的任何组成碳基生命的元素,这让他的自由限度超出了地球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宇宙,比如挣脱引力,冲破云层,从广袤的宇宙中毫无阻碍地俯瞰这颗美丽无方的蓝色星球。他第一次做到这件事的时候简直欢喜疯了,他张开手臂,绕着地球像一颗被引力抓住的流星一样飞了好几圈,连眉毛上都结了霜。冲进大气层的时候克拉克像一颗燃烧的小炮弹,身后带着一条发光的尾巴破开云海,那是克拉克第一次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试图通过大喊大叫来释放这种无可名状的激动,结果云里裹着的小冰粒被他呼出的暖气瞬间融化,连同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灰絮一起糊了他一脸。
克拉克选择让自己落进海里。那种感觉就像从一块极高的、无人能看到的跳板上起跳,整片天地间只有他一个人,他不必小心翼翼控制自己的力度,也不用动脑筋想该以怎样的姿态落进水里才最不引人注目,因为他知道无论速度多快、溅起的水花多高,他都不必担心自己伤害到任何人,那些被人指指点点、视为异类的噩梦随着呼呼吹过耳边的风被他远远地甩在身后,即便这时候有人抬头仰望天空,也只会错觉那是一架隐入云层的飞机或者别的什么。当克拉克从一片天空落进另一片更深更蓝的天空,浪花飞沫簇拥他的脸颊,触感温柔如同妈妈每晚睡前抚摸他额发的手。在大多数的日子里,克拉克肯特是一棵长在丘陵和田野里的不惹人注意的小树,但当他脱离日常生活的引力,飞上高空,年幼蓬勃的生命力得以以另一种姿态肆意舒展。
“克拉克!克拉克?你在哪里?”
“妈!”浮在红海上闭着眼睛傻笑的男孩一下子醒过来,下意识大叫着回应,周围原本慢悠悠游荡的热带鱼原本以为克拉克是一块被海水泡软的浮木,结果被后者激烈的一动吓得哧溜一下游走了。克拉克在原地扑腾,灌了好几口又咸又涩的海水才想起来自己现在在哪里——显然远在千里之外的妈妈是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
“糟了糟了糟了。”
手表不见了,失去了鞋袜的束缚的脚趾头惊慌又灵活地在海草和水流间蠕动,还有他的衬衫——!只剩下挂在脖子周围一圈的衣领,还有掖进裤腰里的一小截,湿哒哒地贴在身上。克拉克后知后觉,这才反应过来刚刚俯冲的时候,那些像没烧尽的灰絮一样塞了他一嘴的是什么东西,兴高采烈的小脸顿时像牙疼一样皱成一团。
“克、拉、克、肯、特——!”
玛莎女士中气十足的呼唤声在逐渐失去耐心,但如果让她看到一个浑身光溜溜、头发还乱得像鸡窝的克拉克肯特……克拉克不由得缩了缩脖子。他得用自己最快的速度赶回去,同时在心里祈祷能比妈妈早到家,好让他有时间从卧室的窗户溜进去起码穿件衣服。
(TBC)
5 notes
·
View notes
Text
旅遊/老蔣故居 奉化華麗轉身
周刊2108期 08/11出刊
立青 2024-08-11

從上海到奉化車程約二小時,途經「杭州灣跨海大橋」,橋長36公里為避免駕駛視覺疲勞,特將護欄分段漆成彩虹七色,起頭為紅色當看到紫色時表示快過完了,是個相當人性化的設計,前次來大橋中點「觀光塔」尚未完工,這次又因大霧還是沒能造訪,留到下次再來吧。
武嶺城門 氣派雄偉
奉化溪口是老總統的故鄉,是個山明水秀的寶地,先前已保留得不錯,近年來建設更是大有進步;兩岸雖仍在對峙,但對一代偉人的尊敬,卻是有目共睹的。進入溪口鎮迎面而來就是雄偉的城門,上書「武嶺」二字,就鄉鎮而言,有這般城門的實不多見。
00:00PreviousPlayNext
MuteFullscreen
Copy video url
Play / Pause
Mute / Unmute
Report a problem
Language
Share
Vidverto Player
ADVERTISEMENT


兩蔣故居 古色古香

「小洋房」是經國先生和方良女士的住所,一樓一底西式造型,客廳有鋼琴家具布置雅致,面對溪水的窗前立有「血債血還」的石碑,來紀念亡母。
蔣母墓道 國民史縮影

登妙高台 俯視全鎮

「千丈岩」距離不遠,然而時間不夠,決定日後再來遊覽。
彌勒寺 列四大聖山
「彌勒寺」就在路邊,規模弘偉金碧輝煌,由於彌勒佛在佛教傳說中是救世主,又圓寂於此,此間因而躍升為佛教四大聖山之一;石碑上刻有一聯:「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笑顏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如此豁達的精神,難怪成了信徒心中的佛。
不遠的山頭上建有巨型彌勒金像坐佛一座,俯視山下眾生,真是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的奇景。
春滿大地百花開,奉化的櫻花和玉蘭花還沒有凋謝,艷麗的桃花已蠢蠢欲動,無數的花苞聚在枝頭等待最佳時刻綻放。近年來奉化廣植桃花,試圖重現「桃花源」美麗田園景象,地方政府已訂定四月十五日為桃花節,並舉辦「奉化馬拉松運動大會」,可讓選手們在花香景美中爭取勝利。
「奉化博物館」位於文化中心西北角,依托原「熱電工廠」遺址而建相當環保,內設三個常設展廳和五個臨時展廳,走進大廳是一組竹節型巨浪藝術裝置,象徵奉化海進海退的演變和「良渚文化」人類文明的形成
0 notes
Text

我的女友蔡霞
第六章
蔡霞轻松地坐到租车的座位上,随手把公文包扔在车上。
“请到滑铁卢车站。”接着,他们就驶入下午的车流中,一路躲闪着骑自行车的邮差和那些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得头昏脑胀,打瞌睡的人。
“我到大象站下车,在那里停下,”格莱格.巴克斯特探身向前,对司机说道,他转过身对着蔡霞笑了笑,就像在会议上他给每一个人的那种笑,令人眼花撩乱,莫测高深。说道:“我们和好了?”
“说实在的,格莱格,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同意和你同坐这辆车的。如果我当时把车门关上,让你站在那里的话,你会觉得怎样?”
“热恋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再说,这也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蔡霞,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内行。”
“可很遗憾,你不是。”蔡霞补充道,“逻辑推理是一回事,内心的想法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总是反对我所说的一切?”
“我只是认为你的数据不对,仅此而已。”
“真是草包一个”,她推开他,改变了一下两大腿的姿势,这样,他的手就从她穿着黑色长统袜的大腿上滑了下来。这时,她内心深处的警铃响了起来,格莱格.巴克斯特会不会就是欧密茄陷阱的幕后人呢?毫无疑问,他正具备年青人所有的心理,而且据谣传,他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性爱好。但是,他如果真是欧密茄的话,他的行为又为什么如此粗野?如此毫不隐瞒?欧密茄的幕后人有足够的办法和智力进入她“安全”的计算机终端,不,不可能是巴克斯特。另一方面,几个月来,他一直全心全意地勾引她。这段时间,整个事件没有了线索,像机械规则一样,仅仅是一场闹剧罢了。
直到此时,她是如此确信这不再是一种游戏。
在大象地铁站外面的混凝土废墟上,她让巴克斯特下了车,并一直盯着他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售票厅里,不管他是不是欧密茄,反正他是个非常讨厌的家伙,要不是他在会议上提出反对,她恨可能已经把一切都做好了,他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呢?如此毫无理由地不合作呢?他明明知道,她的数据是正确的,如不是他动员会上其他人一起反对她的话,那天上午,她的计划早已通过了考查。每个人都会看到,她将实现她所说的一切。上帝啊!她已经在去年为他们赢得了百万大交易,他们还想要哪些更多的证明啊!
更糟的是,珍妮.罗伯逊特别的恶毒,很明显,珍妮憎恨蔡霞。理由不难想像,她比蔡霞年长十岁,但她的这一点点资历就像是用一根细线挂在空中一样不牢靠,她没有蔡霞能干,没有蔡霞那样有权威,也没有蔡霞聪明。她自己也很清楚这些。她觉得受到了威胁,无论蔡霞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些情况。事实上,自从蔡霞跨进格伦沃尔德和贝克公司首脑办公室的第一天起,珍妮.罗伯逊就一直在用她那微不足道的权力作努力,以求改变她的处境,然现实是,每况愈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初,正是珍妮把蔡霞从基层安排上来的,争辩说,电视交换式的通话将是工业发展的未来,这将给蔡霞更多的自由和机会,发挥她的才干,这真是说不清楚。毫无疑问,安排一个非常走红的顾问在她身边,珍妮是绝对不干的,这样的一个人加入她小小的圈子,只能对她不利,不行,她必须要蔡霞离开,最好是彻底离开她以前的工作场所。可好笑的是,她的这一安排,使蔡霞深深地扎了根。
当然,最重要的是,她首先要让蔡霞离开斯坦纳伯.迈尔斯,理由她自己最清楚:她已经迷上了这位上司,也不光是这理由,也不像是靠他的力量使她对蔡霞产生反感。
但是,她确实是翻脸不认人了。蔡霞回忆道,六个多月前的那个下午,她在格伦沃尔德和贝克公司的计算机房里工作到很晚,当时,她只开了一盏小小的台灯。所以,她想没有人会意识到她在那里,当她大约在七点四十五分钟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所有的办公室一片漆黑,只有走道的夜明灯还亮着,使得这地方好像是一个阴森可怕的地下室。她朝着电梯快步走过走廊,心想着不要被锁在里面,因为保全人员晚上八点要进行巡视。
她快到电梯门口时,听到一些声响从销售部主任的办公室里传来,她知道,主任西蒙正在苏格兰出差,而且看到主任的私人秘书在五点半的时候和其他人一起下班回家了,办公室里实在不该还有什么人。
她知道,应该叫来保全人员,找个什么人上来看看,里面的人到底在干什么,很有可能是工业间谍,或者纯粹是夜盗。再说,卷入不能摆脱的事情里去也是不明智的,但是,她也许应该先迅速地去看一看,以证实她猜想的事实是正确的,万一里面是二位工作得很晚的清洁工的话,那她就显得太可笑了。
她蹑手蹑脚地走近销售部经理办公室的门,门开了一条缝,透过一英寸的门缝,蔡霞能看到一缕光线从里面办公室射出来,外面秘书工作的办公室是空的。
小心翼翼地,她推开外间的门,仅仅容她侧身进去。在她的右边,西蒙私人办公室的门半开着。她屏住呼吸,提心吊胆,害怕破人抓住,声音是从里面传出来的。轻声耳语,病态式的笑声,混合着醉人的鸡尾酒。她想,她已听出了是谁的声音,可她怎么能够肯定呢?
她慢慢地靠近了门,紧贴着墙往里间瞧去,她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被人发现:因为里面的人的兴趣完全在对方身上,不会注意其他任何人。
珍妮.罗伯逊横躺在西蒙的办公桌上,她的裙子掀到了腰部,裸露的两条大腿在萤光灯下显得异常的苍白,她的脸向后倒仰着,长长的棕褐色头发散开着,几乎及地,如同一道光亮的帘幕,她的双眼紧闭着,嘴巴张着,一边吃吃地笑,一边喘着气。而此刻的斯坦纳伯.迈尔斯正在她的身体里使劲抽动。他的衣服仍然穿得很好,只是露出他的大公鸡和睾丸,这是位从裤子里掏出来为此刻的情妇服务的。他呻吟着插进她的肉体,对他周围一切完全志得一干二净了。
蔡霞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完全被吸引住了。她以前总是认为珍妮.罗伯逊对董事长的兴趣是出于对他的尊敬,甚至是崇拜。现在,她知道了珍妮的真实情感。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外面有着许多关于这位董事长性欲很强的谣言,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蔡霞想到了可怜、冷酷的玛莎.斯坦纳伯,迈尔斯。她幽默地想道玛莎很可能为了自己的方便,安排这次私通,二十年来,迈尔斯死沈的体重一直压在她身上让她吃不消。现在应该可以暂时休息、轻松一下了。
眼光所及的另外一件事扰乱了蔡霞的思绪:档案柜的门开着。珍妮在上面折腾的桌子上铺满了机密文件。斯坦纳伯.迈尔斯可能有权利接近这些文件,但珍妮是绝对不允许的。西蒙出差走了,可他怎么可能让这些文件,摊在办公室里让任何人都随便看?这样的事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再说,他那特别能干的秘书不会如此疏忽大意。蔡霞看着,想着,她不能,也不想弄懂。
直到几星期以后,西蒙被召到一个精致的会议室,被告知他已被调离该公司的时候,蔡霞才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天晚上,在办公室,西蒙已经被正式开除了。而珍妮和斯坦纳伯.迈尔斯正在他的墓地上作爱。这仅仅是不幸的开端,蔡霞沉思道,不仅珍妮和斯坦纳伯.迈尔斯有牵连,像格雷厄姆.埃德尔顿、乔恩.达西尔凡,塞迪,普拉丝,安.汉密顿这些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适合继续留在格伦沃尔德和贝克公司也将被清除出去,也因此而统统被牵连在一事件中。蔡霞开始担心,她是否将是下一个清理的对象。
出租车一路摇晃着,到了滑铁卢车站前面的广场。蔡霞下车付了钱,大步走上台阶。
“喂,亲爱的,像你这么一位如此性感的可爱女士,这么匆忙,在干什么呢?慢点走不行吗?”蔡霞回过头来,看到那出租车司机正朝着她在笑。他并不难看,挺年轻,皮肤呈好看的棕褐色,穿着无袖汗衫。
“你一定认为车子一路上颠簸得厉害,为什么不重新坐回来试试?这次,我一定让你坐得舒服。”非常诱人,但蔡霞不敢接受,对他的话充耳不闻,并加快了步伐,几乎是半跑着上了台阶,经过那些从车站里出来向下走的人,这些人一个个都带着掠夺性的笑容和一双双贪婪的手。这简直是离开了真实、明媚的太阳而回到了一个冷酷、黑暗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她几乎连自己也认不出来了。
她在干什么?她正在变成什么?回顾过去的几个星期,好像是做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梦,就像电影“黑暗”里的情况一样,她好像走进了一个黑暗的世界。在那里,她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行动来驱赶那些不能接受的性欲。
她关上火车车厢的门,坐了下来,这时,她又记起了那个无助的年轻人,双手被链子拴住,吊挂在空中,毫无生气。鞭子抽打在他身上,肉体上留下一道道红色的伤痕。为什么她要用鞭子抽打他?是什么强烈的冲动驱使她那样做的?这一幕充满了她的内心,使她的情欲像潮水一样涌了土来,势不可挡的欲望想要得到一种疼痛的快感和支配权。情欲,欧密茄已经表现出来,她原本不知道的学问,现在掌握了。
她发生了什么呢?欧密茄对她的灵魂和身体又做了些什么呢?单纯的性爱正演变成一个黑暗、又充满诱惑力的神秘痛苦世界。一种美妙的嗜好,很快就形成了习惯,而且不是那么容易被放弃。
“午安,麦克莱恩夫人。”上校摘帽致意,他一向如此,过分谦恭。他那水汪汪的蓝眼睛里闪烁的是会意的目光吗?蔡霞打消了这种猜疑的念头。自从她和William在果园里肆无忌惮做爱以来,她就一直担心,有人看到了他们。传闻像燎原的火一样蔓延得非常之快,早就有一些闲话和一些含糊的、暗示性的评论。它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什么含意。
“你早,上校,身体好吗?”“看到你,我的身体就更好了。蔡霞,近来很少见到你?”“噢,我一直在外面出差,”蔡霞慌忙地回答,“James也经常在外面,回头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几下,走进凉爽的门厅,唯一的声音是座钟的秒钟发出滴嗒滴嗒声,让人安心,晚上William要来陪她,免得她一个人孤独。
蔡霞踢掉鞋于,脱下衣服,走进浴室准备冲淋。冰冷的水像针一样刺激着她的神经末稍,清醒的神志只要她闪开,而她开始呻吟,非常轻,非常柔,不敢放纵。
蔡霞喜欢住在利特尔霍姆,可有时,好像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人人都想知道你的情况,而不像在那种城市,你只是其中一员,一个数字,而这里,有时你在令人恐慌的空间里事关重大。蔡霞又回想起那天在幽暗电梯厢里的无名人,当时在那儿,她最终成了激情的奴隶,不仅仅是其他人的,而且绝大部分是她自己的,没有意志,没有尊重,没有思想。
这是最大的空虚。
时下,空虚似乎很受欢迎,甚至恐惧,也没有关系,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听任摆布,投进有愿望、有激情的怀抱似乎是唯一有价值的取向。有时,思想就是痛苦,而痛苦是最快乐的肉体享受。
她穿好衣服,拿起信箱,给自己倒了一点喝的,走到外面的花园里。热浪向那坚固如墙的冰冷肌肤变来,片刻工夫,她被晒得头晕眼花。远处,果园最里面的那条小溪正吵闹地流过光滑的石头,树林以外,她只能看见迪恩纳.迈尔斯夫人瘦骨嶙峋的人形,她是教区委员,当地的作家,最爱管闲事。她假装把篮子浸在水里,知道要警惕任何丑闻和流言蜚语。唉,今天,她可要等一段时间。
蔡霞坐在日光床上,拆开信,除了一张煤气广告,没有什么奇异和恐怖的东西。她订购的二部书“法庭”、“快乐原则”寄来了,她把它们放在一边,就寝前阅读,或许,她和James能获得一些秘诀。
最后一个信封为A4型,棕褐色,没有邮戳,只有一个梅索特代码,显然是促销邮件,她拆都没拆,就想扔掉,突然,一个冲动,她把它撕开,抽出里面的东西。
这是偶像服装目录册,耀眼又光滑,封面上的妖女穿着黑色皮短裙,上衣开了二个孔,让乳房露在外面,僵硬的乳头,令人毛骨悚然,蔡霞突然注意到这女人染红的乳头用小小的银环穿刺而过,一根沉沉的银链把两个银环连结起来。
她翻过这一页,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简直难以想像它的存在。这是主人和雇工,女主人和奴隶的世界。这一页的对面,一个穿着紧身橡胶衣服,脚穿一双粗高跟皮靴的女人在拖曳一位不幸年轻男子,他只用了一个小小的皮袋子,套住阳具,自从她用厚画的黄铜钱绕在他细长的脖子上让他节制饮食以来,他的反抗完全没有用,这位女主人的表情,蔡霞以前从未见过:怪诞可笑中带有敌意和热诚。
翻过这一页,发现是裸体男女的照片,都用皮带约束着,男女主人都穿着皮装、橡胶、和PVC、戴着面罩,充满了险恶,皮靴、面罩和铠甲和她在花园舞会上穿的完全一样。她看着这些照片,欲望像潮水般涌来,渴望属于这个世界,那儿,劳役就是安全。当女主人或是雇工呢?想办法,一点都不要紧,只要重新划分就自由啦。
门铃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她看了一眼手表:三点半,她不希望有人来,昨晚一直工作到今天凌晨,上午参加会议,打算度过一个安静的下午,晚上要和William作爱。她不情愿地站起来,去开门。
后门外面,站着一个细长、穿着黑色皮装的摩托车骑士,他的脸完全被一个黑色头盔和面罩掩盖了,他带来一个盒子和书写板,当蔡霞为收到包里签字时,朝他的车瞥了一眼,吃惊地发现车子没有递送人公司名字,而且他把车停放在别墅那一边,在这与世隔绝的园子里,他好像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它。
她把书写板交还给这一言不发的递送人,收下包里,走去关门。但是骑车人走了过来,出人意料地一把抓住她,把她推进大厅。
他卡嗒一声关上身后的门,寂静的房子里,就他们二个人。
“你想干什么?”蔡霞想跑走,戴着皮手套的手抓着她的手臂,抓得不紧,也没有限制她,只是碰到她裸露的肌肤,这种碰触使她像触电一样,皮革和汗水的气味使她陶醉在突如其来的欲望中。
一个人藏在塑料玻璃面罩后面,一张脸和二只眼睛,那双眼睛是冷酷?还是善良?是机警?还是愚蠢?蔡霞不再想知道,面对恐惧、欲望和兴奋,她一言不发。
他的手开始给她脱衣服,蔡霞振奋得想大声喊叫,不过,也有一些害怕,害怕这位不说话的男人真的会伤害她,所以,她顺从地,几乎是麻木地答应他迫切的情欲,她好像毫无感觉。当她的身体,从上到下喷涌着未满足的性欲时,这外表就像在有些昏暗,神秘的沼泽呈沸腾的沼气在涌溢。
显然,她的裸体使他愉快,因为他的手从上到下抚摸着她的胴体,她心甘情愿与这柔软、生冷的皮革接触,她快乐地呻吟起来,乳头突了出来,在这种陌生的调情下,变得坚硬,呈玫瑰色。
在这位藏在皮革和塑料玻璃里的陌生的、机器人似的人身边,蔡霞赤身裸体,感到格外容易受伤,在这阴险的黑色衣服里真有一个男人吗?这没有睑面的罩里什么都没有吗?她是被一个美丽、淫荡的似人自动机勾引吗?
想到这里,蔡霞大腿分叉处变得潮湿、滑润,她的呼吸急促、浅短、在那些闪闪发亮的黑色臂铠里面,难道是金属爪子?而不是手指吗?想到皮革下面的金属骨骼,像一个奇怪的昆虫,或者像海洋深处的动物,她禁不住哆嗦起来,而金属爪子,在裸露的肌肤上慢慢懦动,又使她兴奋,使她着迷。
蔡霞伸手拉下骑车人皮裤的拉链,他没有阻止她。蔡霞的手伸到里面,在热乎乎的肌肤和温暖的皮革之间什么也没有。她的手紧紧抓住向上翘的阴茎,把它拉了出来,发现它正如所感觉得一样漂亮:平滑,粗长,带着丰满有光泽的龟头,她极想舐吃它,吮吸它,尝尝这生命的奶液。
可是,当她弯身去吮吸他时,骑车人把她推开,对她有别的办法。
骑车人打开后门,使厨房充满阳光,他似乎变得更不真实,皮衣服在突然射进来的光线下闪着光。他的阳具像雕刻的象牙紧贴着黑色的皮裤,这时,他一把抓住蔡霞的手腕,把她领到外面,走进无情的烈日。
“不,我不能,会有人看见。”她拼命挣扎,可是没有用,他根本不予理睬。
树林和灌木像一道屏障将小园和公路隔开来,也和花园的其他地方分开,平常,James在这儿用他购置的工具修理汽车,可眼下,全完了,一些专业性的活可以请人在自动系统上进行。蔡霞飞快环视周围。她没有发现的危险吗?那些树和灌木真能遮挡住她做的下流事不被村里人看见?奇怪的是,这一次,她想到的是名誉,而不是安全。她想起内心痛苦的迈尔斯夫人,时时警惕,把悬挂的篮子浸在水里。不管什么事,她肯定能发现,而且告诉给村里其他人。
但是她没有细想很长时间,骑车人对她有别的办法,他的哈雷.戴维森机车在下午的阳光下闪烁,蔡霞的手指摸过晒暖的座凳,机油的气味令她兴奋。
骑车人轻轻地把她推向车子,直到她的背贴着后车轮。起初,蔡霞不明白要她干什么,接着,就知道了。他抬起她的腰,把她的腿分开,让她跨骑在座凳上,背朝着把手,他又轻轻地把她的头放在油箱子上,用一根不长的绳子松松地把她的手腕系在把手上。
骑车人敏捷、有效地将阴茎插进她的里面,开始在阴道里插进,抽出,像极其润滑的圆筒的活塞上下活动。他的阴茎在柔软湿润的阴道里如丝般光滑,她的臀部对每一次冲刺作出相应的反应,他们有节奏的性交是那么的精确,令人陶醉。
现在,她也是机器的一部分,被人骑的机器,就像哈利.戴维森。她注视着天空,阳光擦得光亮的铬的反光,使她眯起了眼睛。
她控制不住,发出一声喊叫,这是如痴如醉的叫喊,蔡霞弓着背,更好地接受他汹涌的精液。
他静静地享受快感,只是轻微的擅抖泄露了他的快乐,在他身下,蔡霞躺在那儿呻吟,在忘我的境界里折腾,是她自己秘密欲望的受害者,心甘情愿的受害者。
接着,他帮她解开绳子,骑车走了,像幽灵一样消失在黄昏的天色里。
第二天上午,William开车把她送到机场,James因忙于同一位“重要的客户”洽谈,所以不能前来给出差的妻子送行。
“星期六我来接你,可爱的宝贝,祝你旅途愉快。”蔡霞还他一个纯真的吻,打开车门,她想把一切都告诉他,但最终还是没说,她微笑着下车,朝着领登机牌那边走去。
这次柏林之行是意料不到的优待还是该咒骂的麻烦事,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蔡霞本来就不想去。她需要弄清楚这件“欧密茄”事情,需要针对格伦沃尔德和贝克公司里的敌对行为做点什么,她不需要在国外待两天,还要尽力处理大量不必要的事件,如果格.巴克斯特不是如此难对付的话。
飞机降落在坦普尔霍夫机场,蔡霞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来到旅馆,一个四星级玻璃暖房和镀铬怪物。和赫尔.尼德梅耶的会见约在第二天上午,她可以逍遥度过这一天。
她应该努力劝说William一起来,至少,现在,不会感到如此孤独。柏林被认为是欧洲的游乐园,现在夜幕已经降临,蔡霞不希望体验太多的夜生活。也许,她可以去看一场电影,或去看戏。嘿,欢迎到富丽堂皇的旅馆来。
她孤独地吃完晚餐,看看杂志,她感到厌烦,一个单身女人去酒吧喝酒肯定不安全,当她房间的电话响起来时,她正打算不去,夜晚才刚刚开始。
“是麦克来恩。弗劳?”“我就是。”“有你一位客人,叫他去你的房间,好吗?”“我,行,没问题。”肯定是柏林方面的代理人,她心里想,斯坦纳伯,迈尔斯提到他可能要进行来往。
她把文件拿出来,自己顺便梳理一下,等了几分钟,听到有人敲门。“进来。”门开了,蔡霞突然惊慌地犹豫起来,当她返到窗口,朝下面的街看一眼时,看到了她害怕的东西。
一辆闪闪发亮的黑白哈雷.戴维森。
骑车人还像以前,不知姓名像机器人一样,模糊视线的面罩戴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人类表情的痕迹,他说话的声音依然平淡、冷漠。蔡霞看到震惊,心想在某种意义上,他走出电子操纵的。
“欧密茄召唤你。”
“你就是来告诉我这个,如果我不想去呢?我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接待处,到时会有六位体格魁伟的保安人员进来收拾你,难道我不会让人把你赶走?”
“因为你不敢让欧密茄不高兴,欧密茄的不愉快就是你的痛苦,蔡霞,他的快乐也是你的快乐,而且欧密茄有非常漂亮的礼物要送给你。”
“欧密茄非常慷慨大方。蔡霞,看看我给你带来的礼物。”
她朝床走进几步,向下看看盒子,她的心停止了几秒钟的跳动,吸了一口气,想起前一天信箱里收到的目录册里的照片,身穿皮革,戴着铁链、橡胶、闪光的PVC人像,那是她生活中看到过的最离奇的画像。
蔡霞双手颤抖,撕开盒子的外包装,里面是最优质的摩登、黑色皮装、散发着芬芳香味,她把衣服贴在脸上,呼吸这令人陶醉的香味。
“把它穿上,蔡霞,现在就穿上。欧密茄希望如此。”也许根本没想到要拒绝,蔡霞敏捷地解开衬衫钮扣,拉掉裙子、长统袜和奶罩,最后是衬裤,奇怪的是;在这位陌生人面前脱衣服,她是如此沉着,满不在乎,而这位陌生人就在前一天,在他的摩托车座位上还骑跨在她身上,蔡霞好像没有感觉到在一个男人脱衣服,绝对没有。现在,她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站在这微微发光的、黑色机器人面前。
她拣起这条连衫裤,拿近点查看,背后中央有一根拉链,似乎是唯一穿进去的通路,蔡霞把拉链向下拉开,脚伸进细长的裤腿,用细的拉链和带扣拉脚脖子收紧,再把衣服向上垃,接着手臂、胸脯套进去,背朝着这无名骑车人向上拉拉链的声音就像钥匙在小单室的门锁转动,也像母亲晚安的亲吻,因为这种束缚,限制也是她的安全。
“现在,戴上这个。”骑车人递给她一个更小的黑色皮面罩,意思是让她罩住整个头,她套在头上,向下拉拉链。一开始,冷冷地贴在脸上,不能呼吸,感到难以忍受的憋闷。只有眼睛、鼻子、嘴巴的洞孔使之坚持得住,按着,她开始体会到它的快乐,像这位戴着头盔的车手一样,她认为在自己无名的性爱世界里感到安全。
她走到穿衣镜面前,立刻被自己看到的样子吓呆了,不是蔡霞.麦克莱恩。不,再也不是,她不再是善良胸怀的爱笑的黑发女人。这个镜子里的人是可怕的动物,既被囚禁,也是监狱女看守,黑色的面罩,阴险邪恶,整个套在黑色皮革里的人,两只惊恐的绿眼睛四处张望。蔡霞突然兴奋地注意到细小的拉链颇有策略地移到胸前,拉链从肚脐向下开到两腿之间,不难想像,这很容易满足什么样的快乐,也许她想在旅馆房间里享受这游戏的快乐。
“现在该走了。”蔡霞转过身,心脏卜卜地跳。
“走?”
“欧密茄希望这样,蔡霞。”
“可是我穿成这个样子,不能去任何地方。”车手抓起细长的高跟皮靴和另一个头盔,递给她。
“把它们穿上。”颤抖着双手,蔡霞把正面头盔戴在头上,现在,这奇异的面罩被遮住了,她拼命把脚伸进窄紧的靴子,笨拙地摆弄侧面的搭扣,她足足高出六英寸,几乎不会走路,她真敢这副模样上街?
“跟我来。”蔡霞听见从头盔传来的机械声音,感到非常吃惊,原来是一个联络系统,欧密茄想到了一切。
让蔡霞苦恼的是,车手不领她走后面的楼梯,这可是通向大街的捷径,而是让她走在前面,经过会议室,楼梯间、进入旅馆主要的门厅。
感谢这头盔,蔡霞想。她的脸在面罩下发烫,所有的眼睛看着她,但起码,没有人知道她是谁,肯定没有人能猜到这位用拉链、扣、带装饰,穿着细高跟靴子,摇摇欲坠的皮装皇后正是几小时来办理住宿手续,衣着端庄的黑发女人。不过,在柏林,让人震惊的扮装并不少见。
他紧跟在她的后面,但不碰到她。然而,他的存在就是她周围的一切,迫使她向前迈步,它似乎在说,不要退缩,欧密茄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不要让他失望。她不习惯这么高的后跟,摔倒在楼梯上,他用戴着皮手套的手立即扶住她,避免了不幸,突然,她感到安全和自豪。
他们走出转门,来到外面的人行道,金色的晚霞透过模糊的面罩看起来阴森、怪诞。热浪钻进皮装,蔡霞的肌肤上渗出小小的汗珠。
车手扶着闪亮的摩托车,骑跨在上面,没有反冲式起动,只是碰一下按钮,引擎就轰鸣起来,这是电子点火,只适合欧密茄。面目不清的面罩向她转过头。
“上车。”蔡霞从来没有坐过摩托车,不知道怎样上车。她谨慎地把一条腿摆过座凳,脚尖摸到了一恻的搁脚板,高高坐在上面,觉得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一千一百西西的强劲马力,震动着她的身体,就像摇动一个碎布做的玩具娃娃。
这是性感的机械式人的声音,它好像不是从前面传来的,而是自己脑海里的声音,蔡霞犹豫着把手放在骑车人腰的两边。
“抓紧,不然你会掉下去。”她惊慌失措,皮革很光滑,很难抓得住,蔡霞最后把手钩住车手的皮带,但还是感到不安全,想下车。
可惜太迟了,只听到节汽阀的一声轰鸣,哈雷向前跳起,蔡霞被摔在靠背上,为安全起见,她紧紧抓住骑车人,靠着他坚硬的身体,就像在向后气流里一个无助的漂流物。
车子风她电掣驶过柏林的大街小巷,即便拐弯也不见速度慢下来,这种恐惧令人兴奋,她的心跳开始加速,她刚刚意识到回荡在脑海里的笑声是自己发出来的。
拉链无情地压在她的阴唇间,坚硬的金属线把它逗弄得生气勃勃;引擎的每一次震动,都被传送到蔡霞大腿之间的肌肤上,那跳动的阴部微妙地影响支配着她。
这时,耳边响起一阵嘘嘘声。
“可爱的小女人,欧密茄对你会满意的。”这是车手的声音。
刺耳的电子辟啦声压过了风的咆哮,把她拉回现实,她在干什么?她有怎样的感受?一个被皮革包起来,戴着面罩的孤独女人和一个从未见过他的脸的男人一起坐在车上穿过没有一个熟人的城市。这种恐惧激发起她的欲望,阴蒂配合着引擎有节奏的嗡嗡声在迫切跳动,温暖的大腿间充满生机。
尽管蔡霞以前从未到过柏林,不过还是能知道现在他们正走进以前的东部区,死气沉沉单调没特色的房屋拥挤在肮脏、窄街的迷宫里,房屋紧紧挨在一起,最深、最暗的角落似乎永远没有阳光照射进来。
他们颠簸着行驶过铺曙鹅卵石的街道,金属拉链更牢固地贴紧阴蒂,胸前的拉链也开始摩擦乳头。尽管她担心,可是乳头还是坚挺起来。
“快到了。蔡霞,希望你今晚大有作为,不要让我们失望,不要让欧密茄失望。”愤怒和恐惧使蔡霞大声喊叫起来,压倒了高涨的肉欲。
“可是谁?谁是欧密茄?”车手的头侧向她,可以肯定在黑暗的面罩下面,一张薄薄的、残忍的嘴巴在冷笑。
“欧密茄是欲望,蔡霞,欧密茄是你的性欲。”他突然关掉引擎,从坡上滑到下面,在蔡霞见到过的最低级、最华丽的夜总会外面停下来。用红、蓝广告霓虹灯表现一个裸体女人刺激性的姿势,入口处外面的黄色照片上,男人和女人用皮革和橡胶紧包着身子,肌肉发达的男人像刽子手似的,将肉欲怒发进那些裸体的“女奴隶”嘴里,威胁皮革皇后们。一个像雕像般庄严美丽的年青女子,硕大的乳房被紧包着身体的皮衣裹在里面,手里的鞭子正在惩罚跪在面前的裸体男子。蔡霞忍不住浑身哆嗦,意识到自己多少渴望见到这些可怕的女人。
“我们到了,蔡霞你喜欢吗?下来吧。”蔡霞缓慢地、犹豫着下了车,她不想走进这个俱乐部,决不行。她看了一下四周,寻找最佳的逃跑方式。摩托车?不行,太大了,她掌握不了。她还可以跑,但是这位高大、肌肉发达的车手肯定会追上来抓住她。她即使跑���,又能去哪里?如果回旅馆,欧密茄肯定会找到她。
欧密茄似乎无处不在。
“摘下头盔,把它给我。”她拿掉头盔,面罩显露在暗黑的夜色中,使她吃惊的是,没有一个行人扭过脸来看她,他们当然不会。离奇古怪在城镇这个肮脏下流的地方,是正常的流行。她这个样子离开这里,结果会怎样呢?
她跟着机车骑士穿过狭窄的人行道,每一步都是被动和不情愿。她不想去那儿,不愿穿过那积满污垢、饰有小珠的帘子,走进充满肉欲的社会底层,那噪音正从夜总会的地下室传进她的耳朵,她不能去。
然而她又想去,非常非常想去,她的整个身体在大声疾呼,希望她走过去,进入梦幻般的世界。
“跟我来!”她默默地、颤抖着,踩着高跟鞋穿过人行道,掀起珠帘。
0 notes
Text

我的女友蔡霞
第六章
蔡霞轻松地坐到租车的座位上,随手把公文包扔在车上。
“请到滑铁卢车站。”接着,他们就驶入下午的车流中,一路躲闪着���自行车的邮差和那些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得头昏脑胀,打瞌睡的人。
“我到大象站下车,在那里停下,”格莱格.巴克斯特探身向前,对司机说道,他转过身对着蔡霞笑了笑,就像在会议上他给每一个人的那种笑,令人眼花撩乱,莫测高深。说道:“我们和好了?”
“说实在的,格莱格,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同意和你同坐这辆车的。如果我当时把车门关上,让你站在那里的话,你会觉得怎样?”
“热恋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再说,这也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蔡霞,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内行。”
“可很遗憾,你不是。”蔡霞补充道,“逻辑推理是一回事,内心的想法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总是反对我所说的一切?”
“我只是认为你的数据不对,仅此而已。”
“真是草包一个”,她推开他,改变了一下两大腿的姿势,这样,他的手就从她穿着黑色长统袜的大腿上滑了下来。这时,她内心深处的警铃响了起来,格莱格.巴克斯特会不会就是欧密茄陷阱的幕后人呢?毫无疑问,他正具备年青人所有的心理,而且据谣传,他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性爱好。但是,他如果真是欧密茄的话,他的行为又为什么如此粗野?如此毫不隐瞒?欧密茄的幕后人有足够的办法和智力进入她“安全”的计算机终端,不,不可能是巴克斯特。另一方面,几个月来,他一直全心全意地勾引她。这段时间,整个事件没有了线索,像机械规则一样,仅仅是一场闹剧罢了。
直到此时,她是如此确信这不再是一种游戏。
在大象地铁站外面的混凝土废墟上,她让巴克斯特下了车,并一直盯着他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售票厅里,不管他是不是欧密茄,反正他是个非常讨厌的家伙,要不是他在会议上提出反对,她恨可能已经把一切都做好了,他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呢?如此毫无理由地不合作呢?他明明知道,她的数据是正确的,如不是他动员会上其他人一起反对她的话,那天上午,她的计划早已通过了考查。每个人都会看到,她将实现她所说的一切。上帝啊!她已经在去年为他们赢得了百万大交易,他们还想要哪些更多的证明啊!
更糟的是,珍妮.罗伯逊特别的恶毒,很明显,珍妮憎恨蔡霞。理由不难想像,她比蔡霞年长十岁,但她的这一点点资历就像是用一根细线挂在空中一样不牢靠,她没有蔡霞能干,没有蔡霞那样有权威,也没有蔡霞聪明。她自己也很清楚这些。她觉得受到了威胁,无论蔡霞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些情况。事实上,自从蔡霞跨进格伦沃尔德和贝克公司首脑办公室的第一天起,珍妮.罗伯逊就一直在用她那微不足道的权力作努力,以求改变她的处境,然现实是,每况愈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初,正是珍妮把蔡霞从基层安排上来的,争辩说,电视交换式的通话将是工业发展的未来,这将给蔡霞更多的自由和机会,发挥她的才干,这真是说不清楚。毫无疑问,安排一个非常走红的顾问在她身边,珍妮是绝对不干的,这样的一个人加入她小小的圈子,只能对她不利,不行,她必须要蔡霞离开,最好是彻底离开她以前的工作场所。可好笑的是,她的这一安排,使蔡霞深深地扎了根。
当然,最重要的是,她首先要让蔡霞离开斯坦纳伯.迈尔斯,理由她自己最清楚:她已经迷上了这位上司,也不光是这理由,也不像是靠他的力量使她对蔡霞产生反感。
但是,她确实是翻脸不认人了。蔡霞回忆道,六个多月前的那个下午,她在格伦沃尔德和贝克公司的计算机房里工作到很晚,当时,她只开了一盏小小的台灯。所以,她想没有人会意识到她在那里,当她大约在七点四十五分钟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所有的办公室一片漆黑,只有走道的夜明灯还亮着,使得这地方好像是一个阴森可怕的地下室。她朝着电梯快步走过走廊,心想着不要被锁在里面,因为保全人员晚上八点要进行巡视。
她快到电梯门口时,听到一些声响从销售部主任的办公室里传来,她知道,主任西蒙正在苏格兰出差,而且看到主任的私人秘书在五点半的时候和其他人一起下班回家了,办公室里实在不该还有什么人。
她知道,应该叫来保全人员,找个什么人上来看看,里面的人到底在干什么,很有可能是工业间谍,或者纯粹是夜盗。再说,卷入不能摆脱的事情里去也是不明智的,但是,她也许应该先迅速地去看一看,以证实她猜想的事实是正确的,万一里面是二位工作得很晚的清洁工的话,那她就显得太可笑了。
她蹑手蹑脚地走近销售部经理办公室的门,门开了一条缝,透过一英寸的门缝,蔡霞能看到一缕光线从里面办公室射出来,外面秘书工作的办公室是空的。
小心翼翼地,她推开外间的门,仅仅容她侧身进去。在她的右边,西蒙私人办公室的门半开着。她屏住呼吸,提心吊胆,害怕破人抓住,声音是从里面传出来的。轻声耳语,病态式的笑声,混合着醉人的鸡尾酒。她想,她已听出了是谁的声音,可她怎么能够肯定呢?
她慢慢地靠近了门,紧贴着墙往里间瞧去,她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被人发现:因为里面的人的兴趣完全在对方身上,不会注意其他任何人。
珍妮.罗伯逊横躺在西蒙的办公桌上,她的裙子掀到了腰部,裸露的两条大腿在萤光灯下显得异常的苍白,她的脸向后倒仰着,长长的棕褐色头发散开着,几乎及地,如同一道光亮的帘幕,她的双眼紧闭着,嘴巴张着,一边吃吃地笑,一边喘着气。而此刻的斯坦纳伯.迈尔斯正在她的身体里使劲抽动。他的衣服仍然穿得很好,只是露出他的大公鸡和睾丸,这是位从裤子里掏出来为此刻的情妇服务的。他呻吟着插进她的肉体,对他周围一切完全志得一干二净了。
蔡霞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完全被吸引住了。她以前总是认为珍妮.罗伯逊对董事长的兴趣是出于对他的尊敬,甚至是崇拜。现在,她知道了珍妮的真实情感。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外面有着许多关于这位董事长性欲很强的谣言,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蔡霞想到了可怜、冷酷的玛莎.斯坦纳伯,迈尔斯。她幽默地想道玛莎很可能为了自己的方便,安排这次私通,二十年来,迈尔斯死沈的体重一直压在她身上让她吃不消。现在应该可以暂时休息、轻松一下了。
眼光所及的另外一件事扰乱了蔡霞的思绪:档案柜的门开着。珍妮在上面折腾的桌子上铺满了机密文件。斯坦纳伯.迈尔斯可能有权利接近这些文件,但珍妮是绝对不允许的。西蒙出差走了,可他怎么可能让这些文件,摊在办公室里让任何人都随便看?这样的事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再说,他那特别能干的秘书不会如此疏忽大意。蔡霞看着,想着,她不能,也不想弄懂。
直到几星期以后,西蒙被召到一个精致的会议室,被告知他已被调离该公司的时候,蔡霞才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天晚上,在办公室,西蒙已经被正式开除了。而珍妮和斯坦纳伯.迈尔斯正在他的墓地上作爱。这仅仅是不幸的开端,蔡霞沉思道,不仅珍妮和斯坦纳伯.迈尔斯有牵连,像格雷厄姆.埃德尔顿、乔恩.达西尔凡,塞迪,普拉丝,安.汉密顿这些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适合继续留在格伦沃尔德和贝克公司也将被清除出去,也因此而统统被牵连在一事件中。蔡霞开始担心,她是否将是下一个清理的对象。
出租车一路摇晃着,到了滑铁卢车站前面的广场。蔡霞下车付了钱,大步走上台阶。
“喂,亲爱的,像你这么一位如此性感的可爱女士,这么匆忙,在干什么呢?慢点走不行吗?”蔡霞回过头来,看到那出租车司机正朝着她在笑。他并不难看,挺年轻,皮肤呈好看的棕褐色,穿着无袖汗衫。
“你一定认为车子一路上颠簸得厉害,为什么不重新坐回来试试?这次,我一定让你坐得舒服。”非常诱人,但蔡霞不敢接受,对他的话充耳不闻,并加快了步伐,几乎是半跑着上了台阶,经过那些从车站里出来向下走的人,这些人一个个都带着掠夺性的笑容和一双双贪婪的手。这简直是离开了真实、明媚的太阳而回到了一个冷酷、黑暗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她几乎连自己也认不出来了。
她在干什么?她正在变成什么?回顾过去的几个星期,好像是做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梦,就像电影“黑暗”里的情况一样,她好像走进了一个黑暗的世界。在那里,她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行动来驱赶那些不能接受的性欲。
她关上火车车厢的门,坐了下来,这时,她又记起了那个无助的年轻人,双手被链子拴住,吊挂在空中,毫无生气。鞭子抽打在他身上,肉体上留下一道道红色的伤痕。为什么她要用鞭子抽打他?是什么强烈的冲动驱使她那样做的?这一幕充满了她的内心,使她的情欲像潮水一样涌了土来,势不可挡的欲望想要得到一种疼痛的快感和支配权。情欲,欧密茄已经表现出来,她原本不知道的学问,现在掌握了。
她发生了什么呢?欧密茄对她的灵魂和身体又做了些什么呢?单纯的性爱正演变成一个黑暗、又充满诱惑力的神秘痛苦世界。一种美妙的嗜好,很快就形成了习惯,而且不是那么容易被放弃。
“午安,麦克莱恩夫人。”上校摘帽致意,他一向如此,过分谦恭。他那水汪汪的蓝眼睛里闪烁的是会意的目光吗?蔡霞打消了这种猜疑的念头。自从她和William在果园里肆无忌惮做爱以来,她就一直担心,有人看到了他们。传闻像燎原的火一样蔓延得非常之快,早就有一些闲话和一些含糊的、暗示性的评论。它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什么含意。
“你早,上校,身体好吗?”“看到你,我的身体就更好了。蔡霞,近来很少见到你?”“噢,我一直在外面出差,”蔡霞慌忙地回答,“James也经常在外面,回头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几下,走进凉爽的门厅,唯一的声音是座钟的秒钟发出滴嗒滴嗒声,让人安心,晚上William要来陪她,免得她一个人孤独。
蔡霞踢掉鞋于,脱下衣服,走进浴室准备冲淋。冰冷的水像针一样刺激着她的神经末稍,清醒的神志只要她闪开,而她开始呻吟,非常轻,非常柔,不敢放纵。
蔡霞喜欢住在利特尔霍姆,可有时,好像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人人都想知道你的情况,而不像在那种城市,你只是其中一员,一个数字,而这里,有时你在令人恐慌的空间里事关重大。蔡霞又回想起那天在幽暗电梯厢里的无名人,当时在那儿,她最终成了激情的奴隶,不仅仅是其他人的,而且绝大部分是她自己的,没有意志,没有尊重,没有思想。
这是最大的空虚。
时下,空虚似乎很受欢迎,甚至恐惧,也没有关系,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听任摆布,投进有愿望、有激情的怀抱似乎是唯一有价值的取向。有时,思想就是痛苦,而痛苦是最快乐的肉体享受。
她穿好衣服,拿起信箱,给自己倒了一点喝的,走到外面的花园里。热浪向那坚固如墙的冰冷肌肤变来,片刻工夫,她被晒得头晕眼花。远处,果园最里面的那条小溪正吵闹地流过光滑的石头,树林以外,她只能看见迪恩纳.迈尔斯夫人瘦骨嶙峋的人形,她是教区委员,当地的作家,最爱管闲事。她假装把篮子浸在水里,知道要警惕任何丑闻和流言蜚语。唉,今天,她可要等一段时间。
蔡霞坐在日光床上,拆开信,除了一张煤气广告,没有什么奇异和恐怖的东西。她订购的二部书“法庭”、“快乐原则”寄来了,她把它们放在一边,就寝前阅读,或许,她和James能获得一些秘诀。
最后一个信封为A4型,棕褐色,没有邮戳,只有一个梅索特代码,显然是促销邮件,她拆都没拆,就想扔掉,突然,一个冲动,她把它撕开,抽出里面的东西。
这是偶像服装目录册,耀眼又光滑,封面上的妖女穿着黑色皮短裙,上衣开了二个孔,让乳房露在外面,僵硬的乳头,令人毛骨悚然,蔡霞突然注意到这女人染红的乳头用小小的银环穿刺而过,一根沉沉的银链把两个银环连结起来。
她翻过这一页,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简直难以想像它的存在。这是主人和雇工,女主人和奴隶的世界。这一页的对面,一个穿着紧身橡胶衣服,脚穿一双粗高跟皮靴的女人在拖曳一位不幸年轻男子,他只用了一个小小的皮袋子,套住阳具,自从她用厚画的黄铜钱绕在他细长的脖子上让他节制饮食以来,他的反抗完全没有用,这位女主人的表情,蔡霞以前从未见过:怪诞可笑中带有敌意和热诚。
翻过这一页,发现是裸体男女的照片,都用皮带约束着,男女主人都穿着皮装、橡胶、和PVC、戴着面罩,充满了险恶,皮靴、面罩和铠甲和她在花园舞会上穿的完全一样。她看着这些照片,欲望像潮水般涌来,渴望属于这个世界,那儿,劳役就是安全。当女主人或是雇工呢?想办法,一点都不要紧,只要重新划分就自由啦。
门铃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她看了一眼手表:三点半,她不希望有人来,昨晚一直工作到今天凌晨,上午参加会议,打算度过一个安静的下午,晚上要和William作爱。她不情愿地站起来,去开门。
后门外面,站着一个细长、穿着黑色皮装的摩托车骑士,他的脸完全被一个黑色头盔和面罩掩盖了,他带来一个盒子和书写板,当蔡霞为收到包里签字时,朝他的车瞥了一眼,吃惊地发现车子没有递送人公司名字,而且他把车停放在别墅那一边,在这与世隔绝的园子里,他好像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它。
她把书写板交还给这一言不发的递送人,收下包里,走去关门。但是骑车人走了过来,出人意料地一把抓住她,把她推进大厅。
他卡嗒一声关上身后的门,寂静的房子里,就他们二个人。
“你想干什么?”蔡霞想跑走,戴着皮手套的手抓着她的手臂,抓得不紧,也没���限制她,只是碰到她裸露的肌肤,这种碰触使她像触电一样,皮革和汗水的气味使她陶醉在突如其来的欲望中。
一个人藏在塑料玻璃面罩后面,一张脸和二只眼睛,那双眼睛是冷酷?还是善良?是机警?还是愚蠢?蔡霞不再想知道,面对恐惧、欲望和兴奋,她一言不发。
他的手开始给她脱衣服,蔡霞振奋得想大声喊叫,不过,也有一些害怕,害怕这位不说话的男人真的会伤害她,所以,她顺从地,几乎是麻木地答应他迫切的情欲,她好像毫无感觉。当她的身体,从上到下喷涌着未满足的性欲时,这外表就像在有些昏暗,神秘的沼泽呈沸腾的沼气在涌溢。
显然,她的裸体使他愉快,因为他的手从上到下抚摸着她的胴体,她心甘情愿与这柔软、生冷的皮革接触,她快乐地呻吟起来,乳头突了出来,在这种陌生的调情下,变得坚硬,呈玫瑰色。
在这位藏在皮革和塑料玻璃里的陌生的、机器人似的人身边,蔡霞赤身裸体,感到格外容易受伤,在这阴险的黑色衣服里真有一个男人吗?这没有睑面的罩里什么都没有吗?她是被一个美丽、淫荡的似人自动机勾引吗?
想到这里,蔡霞大腿分叉处变得潮湿、滑润,她的呼吸急促、浅短、在那些闪闪发亮的黑色臂铠里面,难道是金属爪子?而不是手指吗?想到皮革下面的金属骨骼,像一个奇怪的昆虫,或者像海洋深处的动物,她禁不住哆嗦起来,而金属爪子,在裸露的肌肤上慢慢懦动,又使她兴奋,使她着迷。
蔡霞伸手拉下骑车人皮裤的拉链,他没有阻止她。蔡霞的手伸到里面,在热乎乎的肌肤和温暖的皮革之间什么也没有。她的手紧紧抓住向上翘的阴茎,把它拉了出来,发现它正如所感觉得一样漂亮:平滑,粗长,带着丰满有光泽的龟头,她极想舐吃它,吮吸它,尝尝这生命的奶液。
可是,当她弯身去吮吸他时,骑车人把她推开,对她有别的办法。
骑车人打开后门,使厨房充满阳光,他似乎变得更不真实,皮衣服在突然射进来的光线下闪着光。他的阳具像雕刻的象牙紧贴着黑色的皮裤,这时,他一把抓住蔡霞的手腕,把她领到外面,走进无情的烈日。
“不,我不能,会有人看见。”她拼命挣扎,可是没有用,他根本不予理睬。
树林和灌木像一道屏障将小园和公路隔开来,也和花园的其他地方分开,平常,James在这儿用他购置的工具修理汽车,可眼下,全完了,一些专���性的活可以请人在自动系统上进行。蔡霞飞快环视周围。她没有发现的危险吗?那些树和灌木真能遮挡住她做的下流事不被村里人看见?奇怪的是,这一次,她想到的是名誉,而不是安全。她想起内心痛苦的迈尔斯夫人,时时警惕,把悬挂的篮子浸在水里。不管什么事,她肯定能发现,而且告诉给村里其他人。
但是她没有细想很长时间,骑车人对她有别的办法,他的哈雷.戴维森机车在下午的阳光下闪烁,蔡霞的手指摸过晒暖的座凳,机油的气味令她兴奋。
骑车人轻轻地把她推向车子,直到她的背贴着后车轮。起初,蔡霞不明白要她干什么,接着,就知道了。他抬起她的腰,把她的腿分开,让她跨骑在座凳上,背朝着把手,他又轻轻地把她的头放在油箱子上,用一根不长的绳子松松地把她的手腕系在把手上。
骑车人敏捷、有效地将阴茎插进她的里面,开始在阴道里插进,抽出,像极其润滑的圆筒的活塞上下活动。他的阴茎在柔软湿润的阴道里如丝般光滑,她的臀部对每一次冲刺作出相应的反应,他们有节奏的性交是那么的精确,令人陶醉。
现在,她也是机器的一部分,被人骑的机器,就像哈利.戴维森。她注视着天空,阳光擦得光亮的铬的反光,使她眯起了眼睛。
她控制不住,发出一声喊叫,这是如痴如醉的叫喊,蔡霞弓着背,更好地接受他汹涌的精液。
他静静地享受快感,只是轻微的擅抖泄露了他的快乐,在他身下,蔡霞躺在那儿呻吟,在忘我的境界里折腾,是她自己秘密欲望的受害者,心甘情愿的受害者。
接着,他帮她解开绳子,骑车走了,像幽灵一样消失在黄昏的天色里。
第二天上午,William开车把她送到机场,James因忙于同一位“重要的客户”洽谈,所以不能前来给出差的妻子送行。
“星期六我来接你,可爱的宝贝,祝你旅途愉快。”蔡霞还他一个纯真的吻,打开车门,她想把一切都告诉他,但最终还是没说,她微笑着下车,朝着领登机牌那边走去。
这次柏林之行是意料不到的优待还是该咒骂的麻烦事,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蔡霞本来就不想去。她需要弄清楚这件“欧密茄”事情,需要针对格伦沃尔德和贝克公司里的敌对行为做点什么,她不需要在国外待两天,还要尽力处理大量不必要的事件,如果格.巴克斯特不是如此难对付的话。
飞机降落在坦普尔霍夫机场,蔡霞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来到旅馆,一个四星级玻璃暖房和镀铬怪物。和赫尔.尼德梅耶的会见约在第二天上午,她可以逍遥度过这一天。
她应该努力劝说William一起来,至少,现在,不会感到如此孤独。柏林被认为是欧洲的游乐园,现在夜幕已经降临,蔡霞不希望体验太多的夜生活。也许,她可以去看一场电影,或去看戏。嘿,欢迎到富丽堂皇的旅馆来。
她孤独地吃完晚餐,看看杂志,她感到厌烦,一个单身女人去酒吧喝酒肯定不安全,当她房间的电话响起来时,她正打算不去,夜晚才刚刚开始。
“是麦克来恩。弗劳?”“我就是。”“有你一位客人,叫他去你的房间,好吗?”“我,行,没问题。”肯定是柏林方面的代理人,她心里想,斯坦纳伯,迈尔斯提到他可能要进行来往。
她把文件拿出来,自己顺便梳理一下,等了几分钟,听到有人敲门。“进来。”门开了,蔡霞突然惊慌地犹豫起来,当她返到窗口,朝下面的街看一眼时,看到了她害怕的东西。
一辆闪闪发亮的黑白哈雷.戴维森。
骑车人还像以前,不知姓名像机器人一样,模糊视线的面罩戴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人类表情的痕迹,他说话的声音依然平淡、冷漠。蔡霞看到震惊,心想在某种意义上,他走出电子操纵的。
“欧密茄召唤你。”
“你就是来告诉我这个,如果我不想去呢?我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接待处,到时会有六位体格魁伟的保安人员进来收拾你,难道我不会让人把你赶走?”
“因为你不敢让欧密茄不高兴,欧密茄的不愉快就是你的痛苦,蔡霞,他的快乐也是你的快乐,而且欧密茄有非常漂亮的礼物要送给你。”
“欧密茄非常慷慨大方。蔡霞,看看我给你带来的礼物。”
她朝床走进几步,向下看看盒子,她的心停止了几秒钟的跳动,吸了一口气,想起前一天信箱里收到的目录册里的照片,身穿皮革,戴着铁链、橡胶、闪光的PVC人像,那是她生活中看到过的最离奇的画像。
蔡霞双手颤抖,撕开盒子的外包装,里面是最优质的摩登、黑色皮装、散发着芬芳香味,她把衣服贴在脸上,呼吸这令人陶醉的香味。
“把它穿上,蔡霞,现在就穿上。欧密茄希望如此。”也许根本没想到要拒绝,蔡霞敏捷地解开衬衫钮扣,拉掉裙子、长统袜和奶罩,最后是衬裤,奇怪的是;在这位陌生人面前脱衣服,她是如此沉着,满不在乎,而这位陌生人就在前一天,在他的摩托车座位上还骑跨在她身上,蔡霞好像没有感觉到在一个男人脱衣服,绝对没有。现在,她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站在这微微发光的、黑色机器人面前。
她拣起这条连衫裤,拿近点查看,背后中央有一根拉链,似乎是唯一穿进去的通路,蔡霞把拉链向下拉开,脚伸进细长的裤腿,用细的拉链和带扣拉脚脖子收紧,再把衣服向上垃,接着手臂、胸脯套进去,背朝着这无名骑车人向上拉拉链的声音就像钥匙在小单室的门锁转动,也像母亲晚安的亲吻,因为这种束缚,限制也是她的安全。
“现在,戴上这个。”骑车人递给她一个更小的黑色皮面罩,意思是让她罩住整个头,她套在头上,向下拉拉链。一开始,冷冷地贴在脸上,不能呼吸,感到难以忍受的憋闷。只有眼睛、鼻子、嘴巴的洞孔使之坚持得住,按着,她开始体会到它的快乐,像这位戴着头盔的车手一样,她认为在自己无名的性爱世界里感到安全。
她走到穿衣镜面前,立刻被自己看到的样子吓呆了,不是蔡霞.麦克莱恩。不,再也不是,她不再是善良胸怀的爱笑的黑发女人。这个镜子里的人是可怕的动物,既被囚禁,也是监狱女看守,黑色的面罩,阴险邪恶,整个套在黑色皮革里的人,两只惊恐的绿眼睛四处张望。蔡霞突然兴奋地注意到细小的拉链颇有策略地移到胸前,拉链从肚脐向下开到两腿之间,不难想像,这很容易满足什么样的快乐,也许她想在旅馆房间里享受这游戏的快乐。
“现在该走了。”蔡霞转过身,心脏卜卜地跳。
“走?”
“欧密茄希望这样,蔡霞。”
“可是我穿成这个样子,不能去任何地方。”车手抓起细长的高跟皮靴和另一个头盔,递给她。
“把它们穿上。”颤抖着双手,蔡霞把正面头盔戴在头上,现在,这奇异的面罩被遮住了,她拼命把脚伸进窄紧的靴子,笨拙地摆弄侧面的搭扣,她足足高出六英寸,几乎不会走路,她真敢这副模样上街?
“跟我来。”蔡霞听见从头盔传来的机械声音,感到非常吃惊,原来是一个联络系统,欧密茄想到了一切。
让蔡霞苦恼的是,车手不领她走后面的楼梯,这可是通向大街的捷径,而是让她走在前面,经过会议室,楼梯间、进入旅馆主要的门厅。
感谢这头盔,蔡霞想。她的脸在面罩下发烫,所有的眼睛看着她,但起码,没有人知道她是谁,肯定没有人能猜到这位用拉链、扣、带装饰,穿着细高跟靴子,摇摇欲坠的皮装皇后正是几小时来办理住宿手续,衣着端庄的黑发女人。不过,在柏林,让人震惊的扮装并不少见。
他紧跟在她的后面,但不碰到她。然而,他的存在就是她周围的一切,迫使她向前迈步,它似乎在说,不要退缩,欧密茄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不要让他失望。她不习惯这么高的后跟,摔倒在楼梯上,他用戴着皮手套的手立即扶住她,避免了不幸,突然,她感到安全和自豪。
他们走出转门,来到外面的人行道,金色的晚霞透过模糊的面罩看起来阴森、怪诞。热浪钻进皮装,蔡霞的肌肤上渗出小小的汗珠。
车手扶着闪亮的摩托车,骑跨在上面,没有反冲式起动,只是碰一下按钮,引擎就轰鸣起来,这是电子点火,只适合欧密茄。面目不清的面罩向她转过头。
“上车。”蔡霞从来没有坐过摩托车,不知道怎样上车。她谨慎地把一条腿摆过座凳,脚尖摸到了一恻的搁脚板,高高坐在上面,觉得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一千一百西西的强劲马力,震动着她的身体,就像摇动一个碎布做的玩具娃娃。
这是性感的机械式人的声音,它好像不是从前面传来的,而是自己脑海里的声音,蔡霞犹豫着把手放在骑车人腰的两边。
“抓紧,不然你会掉下去。”她惊慌失措,皮革很光滑,很难抓得住,蔡霞最后把手钩住车手的皮带,但还是感到不安全,想下车。
可惜太迟了,只听到节汽阀的一声轰鸣,哈雷向前跳起,蔡霞被摔在靠背上,为安全起见,她紧紧抓住骑车人,靠着他坚硬的身体,就像在向后气流里一个无助的漂流物。
车子风她电掣驶过柏林的大街小巷,即便拐弯也不见速度慢下来,这种恐惧令人兴奋,她的心跳开始加速,她刚刚意识到回荡在脑海里的笑声是自己发出来的。
拉链无情地压在她的阴唇间,坚硬的金属线把它逗弄得生气勃勃;引擎的每一次震动,都被传送到蔡霞大腿之间的肌肤上,那跳动的阴部微妙地影响支配着她。
这时,耳边响起一阵嘘嘘声。
“可爱的小女人,欧密茄对你会满意的。”这是车手的声音。
刺耳的电子辟啦声压过了风的咆哮,把她拉回现实,她在干什么?她有怎样的感受?一个被皮革包起来,戴着面罩的孤独女人和一个从未见过他的脸的男人一起坐在车上穿过没有一个熟人的城市。这种恐惧激发起她的欲望,阴蒂配合着引擎有节奏的嗡嗡声在迫切跳动,温暖的大腿间充满生机。
尽管蔡霞以前从未到过柏林,不过还是能知道现在他们正走进以前的东部区,死气沉沉单调没特色的房屋拥挤在肮脏、窄街的迷宫里,房屋紧紧挨在一起,最深、最暗的角落似乎永远没有阳光照射进来。
他们颠簸着行驶过铺曙鹅卵石的街道,金属拉链更牢固地贴紧阴蒂,胸前的拉链也开始摩擦乳头。尽管她担心,可是乳头还是坚挺起来。
“快到了。蔡霞,希望你今晚大有作为,不要让我们失望,不要让欧密茄失望。”愤怒和恐惧使蔡霞大声喊叫起来,压倒了高涨的肉欲。
“可是谁?谁是欧密茄?”车手的头侧向她,可以肯定在黑暗的面罩下面,一张薄薄的、残忍的嘴巴在冷笑。
“欧密茄是欲望,蔡霞,欧密茄是你的性欲。”他突然关掉引擎,从坡上滑到下面,在蔡霞见到过的最低级、最华丽的夜总会外面停下来。用红、蓝广告霓虹灯表现一个裸体女人刺激性的姿势,入口处外面的黄色照片上,男人和女人用皮革和橡胶紧包着身子,肌肉发达的男人像刽子手似的,将肉欲怒发进那些裸体的“女奴隶”嘴里,威胁皮革皇后们。一个像雕像般庄严美丽的年青女子,硕大的乳房被紧包着身体的皮衣���在里面,手里的鞭子正在惩罚跪在面前的裸体男子。蔡霞忍不住浑身哆嗦,意识到自己多少渴望见到这些可怕的女人。
“我们到了,蔡霞你喜欢吗?下来吧。”蔡霞缓慢地、犹豫着下了车,她不想走进这个俱乐部,决不行。她看了一下四周,寻找最佳的逃跑方式。摩托车?不行,太大了,她掌握不了。她还可以跑,但是这位高大、肌肉发达的车手肯定会追上来抓住她。她即使跑掉,又能去哪里?如果回旅馆,欧密茄肯定会找到她。
欧密茄似乎无处不在。
“摘下头盔,把它给我。”她拿掉头盔,面罩显露在暗黑的夜色中,使她吃惊的是,没有一个行人扭过脸来看她,他们当然不会。离奇古怪在城镇这个肮脏下流的地方,是正常的流行。她这个样子离开这里,结果会怎样呢?
她跟着机车骑士穿过狭窄的人行道,每一步都是被动和不情愿。她不想去那儿,不愿穿过那积满污垢、饰有小珠的帘子,走进充满肉欲的社会底层,那噪音正从夜总会的地下室传进她的耳朵,她不能去。
然而她又想去,非常非常想去,她的整个身体在大声疾呼,希望她走过去,进入梦幻般的世界。
“跟我来!”她默默地、颤抖着,踩着高跟鞋穿过人行道,掀起珠帘。
1 note
·
View note
Text

我的女友蔡霞
第六章
蔡霞轻松地坐到租车的座位上,随手把公文包扔在车上。
“请到滑铁卢车站。”接着,他们就驶入下午的车流中,一路躲闪着骑自行车的邮差和那些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得头昏脑胀,打瞌睡的人。
“我到大象站下车,在那里停下,”格莱格.巴克斯特探身向前,对司机说道,他转过身对着蔡霞笑了笑,就像在会议上他给每一个人的那种笑,令人眼花撩乱,莫测高深。说道:“我们和好了?”
“说实在的,格莱格,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同意和你同坐这辆车的。如果我当时把车门关上,让你站在那里的话,你会觉得怎样?”
“热恋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再说,这也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蔡霞,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内行。”
“可很遗憾,你不是。”蔡霞补充道,“逻辑推理是一回事,内心的想法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总是反对我所说的一切?”
“我只是认为你的数据不对,仅此而已。”
“真是草包一个”,她推开他,改变了一下两大腿的姿势,这样,他的手就从她穿着黑色长统袜的大腿上滑了下来。这时,她内心深处的警铃响了起来,格莱格.巴克斯特会不会就是欧密茄陷阱的幕后人呢?毫无疑问,他正具备年青人所有的心理,而且据谣传,他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性爱好。但是,他如果真是欧密茄的话,他的行为又为什么如此粗野?如此毫不隐瞒?欧密茄的幕后人有足够的办法和智力进入她“安全”的计算机终端,不,不可能是巴克斯特。另一方面,几个月来,他一直全心全意地勾引她。这段时间,整个事件没有了线索,像机械规则一样,仅仅是一场闹剧罢了。
直到此时,她是如此确信这不再是一种游戏。
在大象地铁站外面的混凝土废墟上,她让巴克斯特下了车,并一直盯着他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售票厅里,不管他是不是欧密茄,反正他是个非常讨厌的家伙,要不是他在会议上提出反对,她恨可能已经把一切都做好了,他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呢?如此毫无理由地不合作呢?他明明知道,她的数据是正确的,如不是他动员会上其他人一起反对她的话,那天上午,她的计划早已通过了考查。每个人都会看到,她将实现她所说的一切。上帝啊!她已经在去年为他们赢得了百万大交易,他们还想要哪些更多的证明啊!
更糟的是,珍妮.罗伯逊特别的恶毒,很明显,珍妮憎恨蔡霞。理由不难想像,她比蔡霞年长十岁,但她的这一点点资历就像是用一根细线挂在空中一样不牢靠,她没有蔡霞能干,没有蔡霞那样有权威,也没有蔡霞聪明。她自己也很清楚这些。她觉得受到了威胁,无论蔡霞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些情况。事实上,自从蔡霞跨进格伦沃尔德和贝克公司首脑办公室的第一天起,珍妮.罗伯逊就一直在用她那微不足道的权力作努力,以求改变她的处境,然现实是,每况愈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初,正是珍妮把蔡霞从基层安排上来的,争辩说,电视交换式的通话将是工业发展的未来,这将给蔡霞更多的自由和机会,发挥她的才干,这真是说不清楚。毫无疑问,安排一个非常走红的顾问在她身边,珍妮是绝对不干的,这样的一个人加入她小小的圈子,只能对她不利,不行,她必须要蔡霞离开,最好是彻底离开她以前的工作场所。可好笑的是,她的这一安排,使蔡霞深深地扎了根。
当然,最重要的是,她首先要让蔡霞离开斯坦纳伯.迈尔斯,理由她自己最清楚:她已经迷上了这位上司,也不光是这理由,也不像是靠他的力量使她对蔡霞产生反感。
但是,她确实是翻脸不认人了。蔡霞回忆道,六个多月前的那个下午,她在格伦沃尔德和贝克公司的计算机房里工作到很晚,当时,她只开了一盏小小的台灯。所以,她想没有人会意识到她在那里,当她大约在七点四十五分钟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所有的办公室一片漆黑,只有走道的夜明灯还亮着,使得这地方好像是一个阴森可怕的地下室。她朝着电梯快步走过走廊,心想着不要被锁在里面,因为保全人员晚上八点要进行巡视。
她快到电梯门口时,听到一些声响从销售部主任的办公室里传来,她知道,主任西蒙正在苏格兰出差,而且看到主任的私人秘书在五点半的时候和其他人一起下班回家了,办公室里实在不该还有什么人。
她知道,应该叫来保全人员,找个什么人上来看看,里面的人到底在干什么,很有可能是工业间谍,或者纯粹是夜盗。再说,卷入不能摆脱的事情里去也是不明智的,但是,她也许应该先迅速地去看一看,以证实她猜想的事实是正确的,万一里面是二位工作得很晚的清洁工的话,那她就显得太可笑了。
她蹑手蹑脚地走近销售部经理办公室的门,门开了一条缝,透过一英寸的门缝,蔡霞能看到一缕光线从里面办公室射出来,外面秘书工作的办公室是空的。
小心翼翼地,她推开外间的门,仅仅容她侧身进去。在她的右边,西蒙私人办公室的门半开着。她屏住呼吸,提心吊胆,害怕破人抓住,声音是从里面传出来的。轻声耳语,病态式的笑声,混合着醉人的鸡尾酒。她想,她已听出了是谁的声音,可她怎么能够肯定呢?
她慢慢地靠近了门,紧贴着墙往里间瞧去,她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被人发现:因为里面的人的兴趣完全在对方身上,不会注意其他任何人。
珍妮.罗伯逊横躺在西蒙的办公桌上,她的裙子掀到了腰部,裸露的两条大腿在萤光灯下显得异常的苍白,她的脸向后倒仰着,长长的棕褐色头发散开着,几乎及地,如同一道光亮的帘幕,她的双眼紧闭着,嘴巴张着,一边吃吃地笑,一边喘着气。而此刻的斯坦纳伯.迈尔斯正在她的身体里使劲抽动。他的衣服仍然穿得很好,只是露出他的大公鸡和睾丸,这是位从裤子里掏出来为此刻的情妇服务的。他呻吟着插进她的肉体,对他周围一切完全志得一干二净了。
蔡霞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完全被吸引住了。她以前总是认为珍妮.罗伯逊对董事长的兴趣是出于对他的尊敬,甚至是崇拜。现在,她知道了珍妮的真实情感。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外面有着许多关于这位董事长性欲很强的谣言,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蔡霞想到了可怜、冷酷的玛莎.斯坦纳伯,迈尔斯。她幽默地想道玛莎很可能为了自己的方便,安排这次私通,二十年来,迈尔斯死沈的体重一直压在她身上让她吃不消。现在应该可以暂时休息、轻松一下了。
眼光所及的另外一件事扰乱了蔡霞的思绪:档案柜的门开着。珍妮在上面折腾的桌子上铺满了机密文件。斯坦纳伯.迈尔斯可能有权利接近这些文件,但珍妮是绝对不允许的。西蒙出差走了,可他怎么可能让这些文件,摊在办公室里让任何人都随便看?这样的事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再说,他那特别能干的秘书不会如此疏忽大意。蔡霞看着,想着,她不能,也不想弄懂。
直到几星期以后,西蒙被召到一个精致的会议室,被告知他已被调离该公司的时候,蔡霞才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天晚上,在办公室,西蒙已经被正式开除了。而珍妮和斯坦纳伯.迈尔斯正在他的墓地上作爱。这仅仅是不幸的开端,蔡霞沉思道,不仅珍妮和斯坦纳伯.迈尔斯有牵连,像格雷厄姆.埃德尔顿、乔恩.达西尔凡,塞迪,普拉丝,安.汉密顿这些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适合继续留在格伦沃尔德和贝克公司也将被清除出去,也因此而统统被牵连在一事件中。蔡霞开始担心,她是否将是下一个清理的对象。
出租车一路摇晃着,到了滑铁卢车站前面的广场。蔡霞下车付了钱,大步走上台阶。
“喂,亲爱的,像你这么一位如此性感的可爱女士,这么匆忙,在干什么呢?慢点走不行吗?”蔡霞回过头来,看到那出租车司机正朝着她在笑。他并不难看,挺年轻,皮肤呈好看的棕褐色,穿着无袖汗衫。
“你一定认为车子一路上颠簸得厉害,为什么不重新坐回来试试?这次,我一定让你坐得舒服。”非常诱人,但蔡霞不敢接受,对他的话充耳不闻,并加快了步伐,几乎是半跑着上了台阶,经过那些从车站里出来向下走的人,这些人一个个都带着掠夺性的笑容和一双双贪婪的手。这简��是离开了真实、明媚的太阳而回到了一个冷酷、黑暗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她几乎连自己也认不出来了。
她在干什么?她正在变成什么?回顾过去的几个星期,好像是做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梦,就像电影“黑暗”里的情况一样,她好像走进了一个黑暗的世界。在那里,她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行动来驱赶那些不能接受的性欲。
她关上火车车厢的门,坐了下来,这时,她又记起了那个无助的年轻人,双手被链子拴住,吊挂在空中,毫无生气。鞭子抽打在他身上,肉体上留下一道道红色的伤痕。为什么她要用鞭子抽打他?是什么强烈的冲动驱使她那样做的?这一幕充满了她的内心,使她的情欲像潮水一样涌了土来,势不可挡的欲望想要得到一种疼痛的快感和支配权。情欲,欧密茄已经表现出来,���原本不知道的学问,现在掌握了。
她发生了什么呢?欧密茄对她的灵魂和身体又做了些什么呢?单纯的性爱正演变成一个黑暗、又充满诱惑力的神秘痛苦世界。一种美妙的嗜好,很快就形成了习惯,而且不是那么容易被放弃。
“午安,麦克莱恩夫人。”上校摘帽致意,他一向如此,过分谦恭。他那水汪汪的蓝眼睛里闪烁的是会意的目光吗?蔡霞打消了这种猜疑的念头。自从她和William在果园里肆无忌惮做爱以来,她就一直担心,有人看到了他们。传闻像燎原的火一样蔓延得非常之快,早就有一些闲话和一些含糊的、暗示性的评论。它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什么含意。
“你早,上校,身体好吗?”“看到你,我的身体就更好了。蔡霞,近来很少见到你?”“噢,我一直在外面出差,”蔡霞慌忙地回答,“James也经常在外面,回头见。”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几下,走进凉爽的门厅,唯一的声音是座钟的秒钟发出滴嗒滴嗒声,让人安心,晚上William要来陪她,免得她一个人孤独。
蔡霞踢掉鞋于,脱下衣服,走进浴室准备冲淋。冰冷的水像针一样刺激着她的神经末稍,清醒的神志只要她闪开,而她开始呻吟,非常轻,非常柔,不敢放纵。
蔡霞喜欢住在利特尔霍姆,可有时,好像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人人都想知道你的情况,而不像在那种城市,你只是其中一员,一个数字,而这里,有时你在令人恐慌的空间里事关重大。蔡霞又回想起那天在幽暗电梯厢里的无名人,当时在那儿,她最终成了激情的奴隶,不仅仅是其他人的,而且绝大部分是她自己的,没有意志,没有尊重,没有思想。
这是最大的空虚。
时下,空虚似乎很受欢迎,甚至恐惧,也没有关系,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听任摆布,投进有愿望、有激情的怀抱似乎是唯一有价值的取向。有时,思想就是痛苦,而痛苦是最快乐的肉体享受。
她穿好衣服,拿起信箱,给自己倒了一点喝的,走到外面的花园里。热浪向那坚固如墙的冰冷肌肤变来,片刻工夫,她被晒得头晕眼花。远处,果园最里面的那条小溪正吵闹地流过光滑的石头,树林以外,她只能看见迪恩纳.迈尔斯夫人瘦骨嶙峋的人形,她是教区委员,当地的作家,最爱管闲事。她假装把篮子浸在水里,知道要警惕任何丑闻和流言蜚语。唉,今天,她可要等一段时间。
蔡霞坐在日光床上,拆开信,除了一张煤气广告,没有什么奇异和恐怖的东西。她订购的二部书“法庭”、“快乐原则”寄来了,她把它们放在一边,就寝前阅读,或许,她和James能获得一些秘诀。
最后一个信封为A4型,棕褐色,没有邮戳,只有一个梅索特代码,显然是促销邮件,她拆都没拆,就想扔掉,突然,一个冲动,她把它撕开,抽出里面的东西。
这是偶像服装目录册,耀眼又光滑,封面上的妖女穿着黑色皮短裙,上衣开了二个孔,让乳房露在外面,僵硬的乳头,令人毛骨悚然,蔡霞突然注意到这女人染红的乳头用小小的银环穿刺而过,一根沉沉的银链把两个银环连结起来。
她翻过这一页,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简直难以想像它的存在。这是主人和雇工,女主人和奴隶的世界。这一页的对面,一个穿着紧身橡胶衣服,脚穿一双粗高跟皮靴的女人在拖曳一位不幸年轻男子,他只用了一个小小的皮袋子,套住阳具,自从她用厚画的黄铜钱绕在他细长的脖子上让他节制饮食以来,他的反抗完全没有用,这位女主人的表情,蔡霞以前从未见过:怪诞可笑中带有敌意和热诚。
翻过这一页,发现是裸体男女的照片,都用皮带约束着,男女主人都穿着皮装、橡胶、和PVC、戴着面罩,充满了险恶,皮靴、面罩和铠甲和她在花园舞会上穿的完全一样。她看着这些照片,欲望像潮水般涌来,渴望属于这个世界,那儿,劳役就是安全。当女主人或是雇工呢?想办法,一点都不要紧,只要重新划分就自由啦。
门铃的声音把她拉回现实,她看了一眼手表:三点半,她不希望有人来,昨晚一直工作到今天凌晨,上午参加会议,打算度过一个安静的下午,晚上要和William作爱。她不情愿地站起来,去开门。
后门外面,站着一个细长、穿着黑色皮装的摩托车骑士,他的脸完全被一个黑色头盔和面罩掩盖了,他带来一个盒子和书写板,当蔡霞为收到包里签字时,朝他的车瞥了一眼,吃惊地发现车子没有递送人公司名字,而且他把车停放在别墅那一边,在这与世隔绝的园子里,他好像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它。
她把书写板交还给这一言不发的递送人,收下包里,走去关门。但是骑车人走了过来,出人意料地一把抓住她,把她推进大厅。
他卡嗒一声关上身后的门,寂静的房子里,就他们二个人。
“你想干什么?”蔡霞想跑走,戴着皮手套的手抓着她的手臂,抓得不紧,也没有限制她,只是碰到她裸露的肌肤,这种碰触使她像触电一样,皮革和汗水的气味使她陶醉在突如其来的欲望中。
一个人藏在塑料玻璃面罩后面,一张脸和二只眼睛,那双眼睛是冷酷?还是善良?是机警?还是愚蠢?蔡霞不再想知道,面对恐惧、欲望和兴奋,她一言不发。
他的手开始给她脱衣服,蔡霞振奋得想大声喊叫,不过,也有一些害怕,害怕这位不说话的男人真的会伤害她,所以,她顺从地,几乎是麻木地答应他迫切的情欲,她好像毫无感觉。当她的身体,从上到下喷涌着未满足的性欲时,这外表就像在有些昏暗,神秘的沼泽呈沸腾的沼气在涌溢。
显然,她的裸体使他愉快,因为他的手从上到下抚摸着她的胴体,她心甘情愿与这柔软、生冷的皮革接触,她快乐地呻吟起来,乳头突了出来,在这种陌生的调情下,变得坚硬,呈玫瑰色。
在这位藏在皮革和塑料玻璃里的陌生的、机器人似的人身边,蔡霞赤身裸体,感到格外容易受伤,在这阴险的黑色衣服里真有一个男人吗?这没有睑面的罩里什么都没有吗?她是被一个美丽、淫荡的似人自动机勾引吗?
想到这里,蔡霞大腿分叉处变得潮湿、滑润,她的呼吸急促、浅短、在那些闪闪发亮的黑色臂铠里面,难道是金属爪子?而不是手指吗?想到皮革下面的金属骨骼,像一个奇怪的昆虫,或者像海洋深处的动物,她禁不住哆嗦起来,而金属爪子,在裸露的肌肤上慢慢懦动,又使她兴奋,使她着迷。
蔡霞伸手拉下骑车人皮裤的拉链,他没有阻止她。蔡霞的手伸到里面,在热乎乎的肌肤和温暖的皮革之间什么也没有。她的手紧紧抓住向上翘的阴茎,把它拉了出来,发现它正如所感觉得一样漂亮:平滑,粗长,带着丰满有光泽的龟头,她极想舐吃它,吮吸它,尝尝这生命的奶液。
可是,当她弯身去吮吸他时,骑车人把她推开,对她有别的办法。
骑车人打开后门,使厨房充满阳光,他似乎变得更不真实,皮衣服在突然射进来的光线下闪着光。他的阳具像雕刻的象牙紧贴着黑色的皮裤,这时,他一把抓住蔡霞的手腕,把她领到外面,走进无情的烈日。
“不,我不能,会有人看见。”她拼命挣扎,可是没有用,他根本不予理睬。
树林和灌木像一道屏障将小园和公路隔开来,也和花园的其他地方分开,平常,James在这儿用他购置的工具修理汽车,可眼下,全完了,一些专业性的活可以请人在自动系统上进行。蔡霞飞快环视周围。她没有发现的危险吗?那些树和灌木真能遮挡住她做的下流事不被村里人看见?奇怪的是,这一次,她想到的是名誉,而不是安全。她想起内心痛苦的迈尔斯夫人,时时警惕,把悬挂的篮子浸在水里。不管什么事,她肯定能发现,而且告诉给村里其他人。
但是她没有细想很长时间,骑车人对她有别的办法,他的哈雷.戴维森机车在下午的阳光下闪烁,蔡霞的手指摸过晒暖的座凳,机油的气味令她兴奋。
骑车人轻轻地把她推向车子,直到她的背贴着后车轮。起初,蔡霞不明白要她干什么,接着,就知道了。他抬起她的腰,把她的腿分开,让她跨骑在座凳上,背朝着把手,他又轻轻地把她的头放在油箱子上,用一根不长的绳子松松地把她的手腕系在把手上。
骑车人敏捷、有效地将阴茎插进她的里面,开始在阴道里插进,抽出,像极其润滑的圆筒的活塞上下活动。他的阴茎在柔软湿润的阴道里如丝般光滑,她的臀部对每一次冲刺作出相应的反应,他们有节奏的性交是那么的精确,令人陶醉。
现在,她也是机器的一部分,被人骑的机器,就像哈利.戴维森。她注视着天空,阳光擦得光亮的铬的反光,使她眯起了眼睛。
她控制不住,发出一声喊叫,这是如痴如醉的叫喊,蔡霞弓着背,更好地接受他汹涌的精液。
他静静地享受快感,只是轻微的擅抖泄露了他的快乐,在他身下,蔡霞躺在那儿呻吟,在忘我的境界里折腾,是她自己秘密欲望的受害者,心甘情愿的受害者。
接着,他帮她解开绳子,骑车走了,像幽灵一样消失在黄昏的天色里。
第二天上午,William开车把她送到机场,James因忙于同一位“重要的客户”洽谈,所以不能前来给出差的妻子送行。
“星期六我来接你,可爱的宝贝,祝你旅途愉快。”蔡霞还他一个纯真的吻,打开车门,她想把一切都告诉他,但最终还是没说,她微笑着下车,朝着领登机牌那边走去。
这次柏林之行是意料不到的优待还是该咒骂的麻烦事,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蔡霞本来就不想去。她需要弄清楚这件“欧密茄”事情,需要针对格伦沃尔德和贝克公司里的敌对行为做点什么,她不需要在国外待两天,还要尽力处理大量不必要的事件,如果格.巴克斯特不是如此难对付的话。
飞机降落在坦普尔霍夫机场,蔡霞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来到旅馆,一个四星级玻璃暖房和镀铬怪物。和赫尔.尼德梅耶的会见约在第二天上午,她可以逍遥度过这一天。
她应该努力劝说William一起来,至少,现在,不会感到如此孤独。柏林被认为是欧洲的游乐园,现在夜幕已经降临,蔡霞不希望体验太多的夜生活。也许,她可以去看一场电影,或去看戏。嘿,欢迎到富丽堂皇的旅馆来。
她孤独地吃完晚餐,看看杂志,她感到厌烦,一个单身女人去酒吧喝酒肯定不安全,当她房间的电话响起来时,她正打算不去,夜晚才刚刚开始。
“是麦克来恩。弗劳?”“我就是。”“有你一位客人,叫他去你的房间,好吗?”“我,行,没问题。”肯定是柏林方面的代理人,她心里想,斯坦纳伯,迈尔斯提到他可能要进行来往。
她把文件拿出来,自己顺便梳理一下,等了几分钟,听到有人敲门。“进来。”门开了,蔡霞突然惊慌地犹豫起来,当她返到窗口,朝下面的街看一眼时,看到了她害怕的东西。
一辆闪闪发亮的黑白哈雷.戴维森。
骑车人还像以前,不知姓名像机器人一样,模糊视线的面罩戴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人类表情的痕迹,他说话的声音依然平淡、冷漠。蔡霞看到震惊,心想在某种意义上,他走出电子操纵的。
“欧密茄召唤你。”
“你就是来告诉我这个,如果我不想去呢?我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接待处,到时会有六位体格魁伟的保安人员进来收拾你,难道我不会让人把你赶走?”
“因为你不敢让欧密茄不高兴,欧密茄的不愉快就是你的痛苦,蔡霞,他的快乐也是你的快乐,而且欧密茄有非常漂亮的礼物要送给你。”
“欧密茄非常慷慨大方。蔡霞,看看我给你带来的礼物。”
她朝床走进几步,向下看看盒子,她的心停止了几秒钟的跳动,吸了一口气,想起前一天信箱里收到的目录册里的照片,身穿皮革,戴着铁链、橡胶、闪光的PVC人像,那是她生活中看到过的最离奇的画像。
蔡霞双手颤抖,撕开盒子的外包装,里面是最优质的摩登、黑色皮装、散发着芬芳香味,她把衣服贴在脸上,呼吸这令人陶醉的香味。
“把它穿上,蔡霞,现在就穿上。欧密茄希望如此。”也许根本没想到要拒绝,蔡霞敏捷地解开衬衫钮扣,拉掉裙子、长统袜和奶罩,最后是衬裤,奇怪的是;在这位陌生人面前脱衣服,她是如此沉着,满不在乎,而这位陌生人就在前一天,在他的摩托车座位上还骑跨在她身上,蔡霞好像没有感觉到在一个男人脱衣服,绝对没有。现在,她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站在这微微发光的、黑色机器人面前。
她拣起这条连衫裤,拿近点查看,背后中央有一根拉链,似乎是唯一穿进去的通路,蔡霞把拉链向下拉开,脚伸进细长的裤腿,用细的拉链和带扣拉脚脖子收紧,再把衣服向上垃,接着手臂、胸脯套进去,背朝着这无名骑车人向上拉拉链的声音就像钥匙在小单室的门锁转动,也像母亲晚安的亲吻,因为这���束缚,限制也是她的安全。
“现在,戴上这个。”骑车人递给她一个更小的黑色皮面罩,意思是让她罩住整个头,她套在头上,向下拉拉链。一开始,冷冷地贴在脸上,不能呼吸,感到难以忍受的憋闷。只有眼睛、鼻子、嘴巴的洞孔使之坚持得住,按着,她开始体会到它的快乐,像这位戴着头盔的车手一样,她认为在自己无名的性爱世界里感到安全。
她走到穿衣镜面前,立刻被自己看到的样子吓呆了,不是蔡霞.麦克莱恩。不,再也不是,她不再是善良胸怀的爱笑的黑发女人。这个镜子里的人是可怕的动物,既被囚禁,也是监狱女看守,黑色的面罩,阴险邪恶,整个套在黑色皮革里的人,两只惊恐的绿眼睛四处张望。蔡霞突然兴奋地注意到细小的拉链颇有策略地移到胸前,拉链从肚脐向下开到两腿之间,不难想像,这很容易满足什么样的快乐,也许她想在旅馆房间里享受这游戏的快乐。
“现在该走了。”蔡霞转过身,心脏卜卜地跳。
“走?”
“欧密茄希望这样,蔡霞。”
“可是我穿成这个样子,不能去任何地方。”车手抓起细长的高跟皮靴和另一个头盔,递给她。
“把它们穿上。”颤抖着双手,蔡霞把正面头盔戴在头上,现在,这奇异的面罩被遮住了,她拼命把脚伸进窄紧的靴子,笨拙地摆弄侧面的搭扣,她足足高出六英寸,几乎不会走路,她真敢这副模样上街?
“跟我来。”蔡霞听见从头盔传来的机械声音,感到非常吃惊,原来是一个联络系统,欧密茄想到了一切。
让蔡霞苦恼的是,车手不领她走后面的楼梯,这可是通向大街的捷径,而是让她走在前面,经过会议室,楼梯间、进入旅馆主要的门厅。
感谢这头盔,蔡霞想。她的脸在面罩下发烫,所有的眼睛看着她,但起码,没有人知道她是谁,肯定没有人能猜到这位用拉链、扣、带装饰,穿着细高跟靴子,摇摇欲坠的皮装皇后正是几小时来办理住宿手续,衣着端庄的黑发女人。不过,在柏林,让人震惊的扮装并不少见。
他紧跟在她的后面,但不碰到她。然而,他的存在就是她周围的一切,迫使她向前迈步,它似乎在说,不要退缩,欧密茄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不要让他失望。她不习惯这么高的后跟,摔倒在楼梯上,他用戴着皮手套的手立即扶住她,避免了不幸,突然,她感到安全和自豪。
他们走出转门,来到外面的人行道,金色的晚霞透过模糊的面罩看起来阴森、怪诞。热浪钻进皮装,蔡霞的肌肤上渗出小小的汗珠。
车手扶着闪亮的摩托车,骑跨在上面,没有反冲式起动,只是碰一下按钮,引擎就轰鸣起来,这是电子点火,只适合欧密茄。面目不清的面罩向她转过头。
“上车。”蔡霞从来没有坐过摩托车,不知道怎样上车。她谨慎地把一条腿摆过座凳,脚尖摸到了一恻的搁脚板,高高坐在上面,觉得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一千一百西西的强劲马力,震动着她的身体,就像摇动一个碎布做的玩具娃娃。
这是性感的机械式人的声音,它好像不是从前面传来的,而是自己脑海里的声音,蔡霞犹豫着把手放在骑车人腰的两边。
“抓紧,不然你会掉下去。”她惊慌失措,皮革很光滑,很难抓得住,蔡霞最后把手钩住车手的皮带,但还是感到不安全,想下车。
可惜太迟了,只听到节汽阀的一声轰鸣,哈雷向前跳起,蔡霞被摔在靠背上,为安全起见,她紧紧抓住骑车人,靠着他坚硬的身体,就像在向后气流里一个无助的漂流物。
车子风她电掣驶过柏林的大街小巷,即便拐弯也不见速度慢下来,这种恐惧令人兴奋,她的心跳开始加速,她刚刚意识到回荡在脑海里的笑声是自己发出来的。
拉链无情地压在她的阴唇间,坚硬的金属线把它逗弄得生气勃勃;引擎的每一次震动,都被传送到蔡霞大腿之间的肌肤上,那跳动的阴部微妙地影响支配着她。
这时,耳边响起一阵嘘嘘声。
“可爱的小女人,欧密茄对你会满意的。”这是车手的声音。
刺耳的电子辟啦声压过了风的咆哮,把她拉回现实,她在干什么?她有怎样的感受?一个被皮革包起来,戴着面罩的孤独女人和一个从未见过他的脸的男人一起坐在车上穿过没有一个熟人的城市。这种恐惧激发起她的欲望,阴蒂配合着引擎有节奏的嗡嗡声在迫切跳动,温暖的大腿间充满生机。
尽管蔡霞以前从未到过柏林,不过还是能知道现在他们正走进以前的东部区,死气沉沉单调没特色的房屋拥挤在肮脏、窄街的迷宫里,房屋紧紧挨在一起,最深、最暗的角落似乎永远没有阳光照射进来。
他们颠簸着行驶过铺曙鹅卵石的街道,金属拉链更牢固地贴紧阴蒂,胸前的拉链也开始摩擦乳头。尽管她担心,可是乳头还是坚挺起来。
“快到了。蔡霞,希望你今晚大有作为,不要让我们失望,不要让欧密茄失望。”愤怒和恐惧使蔡霞大声喊叫起来,压倒了高涨的肉欲。
“可是谁?谁是欧密茄?”车手的头侧向她,可以肯定在黑暗的面罩下面,一张薄薄的、残忍的嘴巴在冷笑。
“欧密茄是欲望,蔡霞,欧密茄是你的性欲。”他突然关掉引擎,从坡上滑到下面,在蔡霞见到过的最低级、最华丽的夜总会外面停下来。用红、蓝广告霓虹灯表现一个裸体女人刺激性的姿势,入口处外面的黄色照片上,男人和女人用皮革和橡胶紧包着身子,肌肉发达的男人像刽子手似的,将肉欲怒发进那些裸体的“女奴隶”嘴里,威胁皮革皇后们。一个像雕像般庄严美丽的年青女子,硕大的乳房被紧包着身体的皮衣裹在里面,手里的鞭子正在惩罚跪在面前的裸体男子。蔡霞忍不住浑身哆嗦,意识到自己多少渴望见到这些可怕的女人。
“我们到了,蔡霞你喜欢吗?下来吧。”蔡霞缓慢地、犹豫着下了车,她不想走进这个俱乐部,决不行。她看了一下四周,寻找最佳的逃跑方式。摩托车?不行,太大了,她掌握不了。她还可以跑,但是这位高大、肌肉发达的车手肯定会追上来抓住她。她即使跑掉,又能去哪里?如果回旅馆,欧密茄肯定会找到她。
欧密茄似乎无处不在。
“摘下头盔,把它给我。”她拿掉头盔,面罩显露在暗黑的夜色中,使她吃惊的是,没有一个行人扭过脸来看她,他们当然不会。离奇古怪在城镇这个肮脏下流的地方,是正常的流行。她这个样子离开这里,结果会怎样呢?
她跟着机车骑士穿过狭窄的人行道,每一步都是被动和不情愿。她不想去那儿,不愿穿过那积满污垢、饰有小珠的帘子,走进充满肉欲的社会底层,那噪音正从夜总会的地下室传进她的耳朵,她不能去。
然而她又想去,非常非常想去,她的整个身体在大声疾呼,希望她走过去,进入梦幻般的世界。
“跟我来!”她默默地、颤抖着,踩着高跟鞋穿过人行道,掀起珠帘。
0 notes
Text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总是不尽人意?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米迷离?为什么我们永远得不到一刻灵魂上的安宁?为什么,上帝,我在这里向您询问:为什么如此多年以来,我们的青春 我们的生活,我们经历的一切都不可避免,恐怖和恶心,为什么我们的美好总像烧毁的电影,我们只能坐在灰烬旁看着这不可复原的消亡,为什么我们不得以幸福,却生活在一个需要爱,青春,温情和慰藉的世界里?”
夏日伊始,他位于阁楼的屋子闷热潮湿,夜里蚊虫四起,他难于安心入睡,整夜整夜的开始失眠,蚊虫扇动翅膀的细小声音环绕在屋子之中,他能跟随忽大忽小的声响才揣测二者之间的间距:一直以来,它们的族群都带着极强的报复性的生活在夏季,死了就活,活了就死。碾碎在洁白餐桌上的尸首透露着湿哒哒的恶心,在黏答答的桌布上干成他身上的一颗痣。困倦之间,他蜷缩起来的脚趾能想起来许多话语,放在他的耳蜗里发酵,他母亲在楼下的厨房里絮絮叨叨地抱怨,水声混杂着陶瓷碗和塑料筷子的相撞,他总是因为这些声音想起车祸、故意伤人和铅黄电影里的坠楼场景。而母亲洗的筷子上总是留有洗洁精的苦味,像砒霜,捞出来的米饭和发霉了一样,他选用勺子吃饭,坦然的接受母亲因他不使用筷子的讥讽,从他的成绩到他的中文,他的懒惰到他的叛逆,就像一把时刻哀怨的牛排刀放在沥水台上,干掉的水渍成了白色的污垢,就像父亲身上的白斑滋生、酗酒和漠视,电视就像许多年前的一样,总是反复播放他们热恋时最爱的瞬间,伊莲罗莱斯的那首我的名字伊莲(Je m'appelle Hélène)。当初在巴黎的花神咖啡馆下,他们互相热恋着彼此,父亲说我的伊莲,母亲回答我是你的伊莲。他们爱的好像都是伊莲而不是彼此,只是当初接吻结婚再做爱,剩下一团丑的皱巴巴的肉在病床上。长期的睡眠不足使他忧郁狂躁,昏昏欲睡的同时却保持高度的清醒,他总是睁眼看着自己的屋子,想到当初母亲生下自己时的幻想,一团红的像猪肉的胎儿从刀口里被取出来,丑陋、肮脏,浑身血污,在病床的嚎啕大哭是对母亲持续而长久的折磨,她狂躁,暴怒,脱发而心怀怨恨,对他说:如果当初没有生下你就好了!她后来好像也明白自己爱着的伊莲是她的青春,她的懵懂,她的美貌,她不再是丈夫的那个伊莲了,那个伊莲在marin的出生证明里死掉了,marin的出生证明就是她的死亡通知单,她打开的灶火台就是火葬场的火焰。
他们爱上的青春都是伊莲的幻影,伊莲的想象。他们真的爱对方吗?
想到这里,marin起身,赤脚踩在咯吱咯吱的地板上,将轻薄的床垫从床架上撤下,搬到白色油漆铁窗下,夜晚有风吹过、砰砰地砸在窗上,鸽子飞过橘色路灯是的背影也会鬼魅般浮现,嗖的一声从空气中迷失,在他闭这的眼皮下投下一颗小而盲的黑点。他翻身面对墙壁,身上披着湿乎乎的床单,马卡龙色系、浅色的苹果绿,平铺时透蓝,若有似乎若隐若现的在某些时刻中流进他的视网膜里,饱和度极低,像他手机里那些视频里加上的灰色滤镜。有时候,他感觉自己的生活中也充满这悲情剧的基调,要不然怎么能解释他在学校里历经的压力和煎熬,痛苦和折磨呢?他母亲为她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但没有温情所在,她用东亚式的母亲威慑着她儿子的生活,就像一座山正在缓慢以母亲的名字讲他一点点活埋。越是长大,marin越是感觉无法呼吸,难以和母亲面对面的诉说母子之间的爱意,而是沉默和对峙,她辱骂他为傻逼和脑残,他愤怒的反抗她为婊子和贱人,就像任何大街上粗俗的少年少女一样,她给了她的儿子一巴掌,清脆的像折断的芹菜根。不知为何,在那天之后,他卖掉了小时候祖母送的俄罗斯套娃和意大利手工香薰,从面包店的柜台里偷了十欧元凑齐了三十块夹在书页里,又顺走母亲外套里的硬币和父亲叠在床头柜的零钱,断断续续的凑出了五十元。这是他青春的售价。
marin还记得那是星期二,清晨七点,空气中弥漫着冷漠的湿气,门口���街景一直延续到无法目睹到的彼端,轻盈的薄雾在头顶上盘旋,许多次,他站在雾里伸出手看自己的五根手指在雾气中,即使那朦胧的纱网没有遮住任何一块肌肤,但他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从小指骨开始的消亡,慢吞吞的吃下了他的双手,到那时,他就没有办法说任何的话了:他的唇舌已经退化,此刻他脸上的只不过是装饰和象征。他用双手说话,但伴随时间和他的成长的迷途,他已经失去了使用双手创造某种美好事物的能力,连诉说的欲望都跟随一同湮灭了。小指骨几乎是他的奢求:约定与宣誓的力量,不过现在他并不觉得可惜,只因他没有那可以约定的人。往常一样,他收拾书包,去弗朗索瓦杜邦前吃早餐,看巧克力麦片在牛奶碗里被泡的发涨发皱的模样,像揉一把纸巾浸在里面,刺激胃病发作,母亲迷糊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她说:“快点去学校。不许迟到”。她一直是这样,自从他六年级在考试中迟到后被拒绝补考,他列出来的成绩单里头一回出现一个数字0之后,她再没允许marin迟到过,许多次,她走进他的房间,毫不留情的推搡他的身体,因为marin锁上门,第二天,她蹲在地板上,用螺丝刀将门锁拧了下来,她总感觉自己就是真理:你是我的儿子,你为什么对我锁门。门锁孤零零的躺在餐桌上,散发铁锈的铜黄味
那天开始,他就没有自由可言了。早上,母亲的目光阴冷潮湿,蛇。中午,他在母亲的手边吃饭,夜晚,母亲在监视器里,无所不在。他想要呼吸。夜里,母亲的气息宛若死尸,他无数次隔着一面墙,听到因鼻塞而困难的呼吸,他像颗缩在母亲鼻腔里的豌豆。
他坐在椅子上,吃那碗冷的发腥的早餐,昏暗的白炽灯使他看不清周边,只有他身体的阴影在絮乱中被模糊边缘,舒展在瓷质桌面上,低瓦数的冷白灯成为他头疼病灶的又一病因,他目眩:看到大理石台面上的条纹在重合中蹂躏在一团,钻进他脑子里,抽的发疼,想象寄生虫在大脑中蠕动,用他母亲尖锐的嗓音说话,他干呕、咳嗽,舌根处仿佛有锯子在摩擦,咽下不治之症,吃下的麦片在食道里栖息,久久不愿被胃酸溶解,铁勺子在瓷碗里砰砰作响,干呕后再也难以进食,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进食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排��,有时候他想在床上一死了之。不是那种割腕或者上吊的死,他小时候割腕,用刀片在腿上割口子,母亲发现给他一巴掌,说你想死就去跳楼,用别的方法死,为什么要自残?你觉得自残很值得炫耀吗,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我对你做错了什么,你要自残给我看?他边哭边给她磕头,感觉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像不孝,像出轨,像遗精,他喊妈妈,妈妈,妈妈,你原谅我,你不爱我,我要爱你,你为什么不对我温柔!王秀兰过来给他送创可贴,她大一岁,成绩好,自信,在家成为一个好女儿,不多说话。她说马霖,不要自残,你懂吗,爸爸妈妈眼里自残是神经病,是精神病,你长大会被送进精神病院里的,他抽抽搭搭的说,眼眶发肿发红,眼球的血丝遍布,像水晶球摔碎的裂缝,我恨妈妈,她说没有我就好了,她可以离婚,她可以回国,她可以做自己,可我从来没有想被她生出来过。王秀兰没说话,给他递纸巾,看手机,看聊天记录,她说痛苦是没有办法的,长大了就好了。对,长大就好了,现在也不遗精了,他偶尔晨勃,用茶包泡茶,突发奇想的加奶,没自残过,只是偶尔争吵过后躺在床上,楼下是母亲发泄式的碰撞声,盘子、碗、杯子和塑料筷,他想,如果能一下子烂成一团血肉,消失,变成数据库,他想要消失,想要一个有爱的世界,想要有个人能承担他的痛苦,而不是像泡久了的麦片,皱巴巴的被抿烂。marin在作文里写我想要变得无所不能,或者强大,我想要慰藉自己,我要英雄出现。
我想要一切都不曾发生。
弗朗索瓦杜邦是公立学校,不用学费,原本母亲不会同意让他去公立学校,因为里面有小偷、骗子、瘾君子和小混混,没有学习的氛围,只有青少年性爱,短视频流行,脏话和性早熟。但2004年,图书馆被改名,成为学校,王秀兰的母亲和sabina说,即使是公立学校,但好在教师资源还行,以前是图书馆,现在还有一间房间专门用来放书,离家近,放学就能回家帮忙。母亲还不满意,就问王秀兰,弗朗索瓦杜邦怎么样,她坐在沙发里,几乎快要缩起来成一个圆,她说还可以,不错,挺好的,我觉得可以。于是第二天,母亲敲定他的初中和王秀兰一起。放学后,他们相约在公园,王秀兰说也许你还会坐我坐过的位置,初一的時候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半年我換到了靠墻的位置。他说真的吗,挺好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过来的。王秀兰看着他,很久后,像是艰难的思考,说就那样,活过来就过来了,我没记下来什么。marin看着她,身边有人在放流行音乐,雷鬼音乐,看见臀部和松垮的裤子,恶心,恶心的肉欲,恶心的青少年,恶心的青春期,他看见王秀兰的脸颊在她回答之后短暂的陷入了扭曲,像是融水的浴球,缓慢而不容抗拒的溶解成粉末,被吞入残忍的下水道,那时候,他第一次感觉自己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过过来该怎么过去,青春是否就是如此痛苦的。他在一瞬间甚至有点恨王秀兰,他恨她的温驯,她的麻木,她的家庭,她的中文,她用来成为炫耀资本的一切,如果她能拯救他就好了,就像姐姐,像真正的妈妈,像老师一样引领他,他学不会的语法置换,空出来的请假条签名,他纰漏的试卷上缠绵悱恻的错误选项,他的青春一直在茫然,无措的感觉自己是个纯真的婴儿,一切都还未分明的世代,却要这样学会啃食一切的苦难,他看见王秀兰没有联网和流量的手机,反复的浏览寥寥无几的对话框,翻来覆去,突然心中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幻觉,其实他们是一样的。
王秀兰没有朋友,她妈妈爱她的轮廓和安静,却不爱她的本性,她阴暗冷酷的本性,想sabina一样,她是另一种自己。
他们用十块钱买了火车票,接踵摩肩,打开的感应门像两瓣肉,adrien伸出手,在玻璃镜面上粘上一枚指印,在光晕和太阳下的幻影里,marin可以清晰的看到adrien的指纹,犹如一朵从内而外的左螺旋生长的海螺纹,一个小混乱的漩涡,凝在水雾上。adrien穿着低跟的皮鞋,装模作样又自大,响声在无人的楼梯口里幽怨的响了又响,他感觉adrien在催促他,但又似乎不是。向下的通道很神秘,恶心,散发着腥辣的汗味和遗留的速食垃圾,marin收回卡,夹在手机壳里,仅剩的钱在一张薄而扁平的卡纸下显得可怜兮兮,这是他青春在面粉、酵母、蔓越莓和燃烧的碳火里的青春,价值五十块,现在已经几乎见底,他纠结于活下去的难题,哪怕现在的肚子里还揣着未消化的披萨和可乐,但是已经开始害怕起穷困潦倒后发生的饥饿和羞辱,
他们没有假面,这是一个令人痛苦难耐的世界,他们抽烟,喝酒,去酒吧前坐着度过一个个难眠的下午,夜里坐在车里入梦。尽管失眠和噩梦接踵而至,但他们任然不习惯在白天入睡。adrien身上总有挥之不去的柑橘香味,混杂着他的愁绪,他的孤独,他童年中一个人坐在落地长廊里,顺着被柱子隔开的一道道伤口的漩涡里流浪的午后,阳光穿过黑夜,穿过树冠,穿过那些仿造希腊的罗马柱,穿过他树荫下废弃的秋千和被摧毁的沙堡。然后读书,弹琴,他看令人哀嚎的痛苦之书,邪典,教义,折磨和伤害,收购铅黄电影,着魔,在午夜的屋栋中回荡 那些哀嚎和撕裂肉体的声音,就像他给自己做解剖手术时掉的眼泪。marin问你从不在意噪音和投诉吗,adrien说他从不在意,屋子很空,夜晚到来,光会暗淡下去,灯会熄灭,空气会慢慢变冷,感官的一切都会逐步消失在黑夜的面纱之下,有的时候他都感觉自己已经死了,因为感觉不到体温和思想,察觉不到记忆和主义,死亡并不像老师和书里写的一样,死亡不像是埃贡席勒的作画,也不像是萨拉凯恩的戏剧,死亡就像做抽血手术和变成不同的树那样,首先一股强烈细小的剧痛在身体上某个地方出现,然后感受着某种事物慢慢跟随着时间被抽离的麻木感,近乎酷刑的漫长持续在每个夜晚,有好几次,他因为无法忍受胃溃疡和胃下坠的痛觉而呕吐,现在他的食道被胃酸上涌侵蚀而导致受损,很长时间里要禁食和休养。但事实是:他和marin二人共享一包烟,喝酒,吃橄榄,睡觉时永远侧躺,毫不在意他的身体。感受疼痛使他察觉生命存在,感受欲望也能察觉生命存在,施展暴力可以、自我伤害也可以,
adrien看着他,平静地问道:告诉我,就现在。
marin看见他绿色的眼睛,绿色,生命的颜色,鲜活的颜色,嫉妒与砷的颜色,死水、绿藻、宝石、霉菌的颜色,他想起梦中那个对他笑的金发男孩,和adrien使用同一个名字的那个男孩,坐在公园长椅下,手指拂过手中的传教单,字母缓慢地的浮现,说:上帝愿我们的幸福不朽……那时候,他感觉自己被爱情的烈焰燃烧住了手臂,否则怎么能解释他不由自主环住双臂的动作?那种感觉就像是火灾事故被烧死的可怜人,被火焰舔舐全身时不由得痉挛和颤栗,蜷缩着赴汤蹈火,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变成梦中那个美丽、可爱的少女,和他轮廓相似而命运大庭相径的女孩,嫉妒之火在腹腔中莽撞地燃烧,连带着愤怒和仇恨:他冥冥之中感觉二人相似,在五官的浮现和习性之上,但生活却不遂他所希望的。不幸和屈辱一直贯彻在他的生活里,他感觉是某种书写痛苦的书,越是想要幸福就越不如愿,
他们脱下衣服,坦诚的相见。这时候marin才直观的认识到普通人和模特的差距不仅仅在于相机和妆容,adrien偏瘦,甚至抵达可以被称之为消瘦的地步,相片里那些看似剪裁合体的衣服实际要比标准尺码还小,他在十二岁就开始绝食和减脂,父亲不在意他的身体,也许是他不在意,也许是adrien不在意,adrien摇摇头,说感觉自己身体里有一个黑洞,永远无法被填满,他是个孩子的时候不克制食欲,母亲的爱养育他的胃部,时常觉得不够满足,自natalie阿姨去世之后,他的母亲开始着手给他制作营养餐,他不再能像以前一样贪吃,开始减食,但自从母亲失踪之后,他就对吃食没有太大的欲望,除了面包、贝果和蝴蝶酥,他说我的食欲养育了那个漆黑的洞,它吞掉了他爱着人,他不想消失,也不想孤独,所以他不再满足欲望,而是克制,久而久之,他能塞下比自己尺寸还小一个码的衣服,肋骨和锁骨贴在肉下,咯吱咯吱的响。
marin贴着adrien,感觉自己在和一团骨头拥抱,硌的发慌,在光晕里像两句剥开肉的骨架在接踵中相撞,肋骨发出发怵的声响,胸膛贴着骨架,心脏在里面悦动的旋律:狂躁,激昂,甚至是暴力疯狂的,他像看伊恩麦克尤恩书里的一样,从后背和大腿附近徘徊,adrien的低语渗人的响起,他在说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的低声呢喃着,这时候,marin感觉他怀里的好像是一具尸体,幽灵,美丽的尸体,美丽的幽灵,他紧张的双手触碰到某个部位,adrien瘦骨嶙峋的脊椎从头至尾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栗,痛苦的喘息、惊悚的粗喘,marin想,如果自己是个女孩的话,月经血会像草莓果酱,动脉栓,夏日,孤零零的花盆,她不会那么痛苦的,她和妈妈都是女人,女人是不会吃掉女人的,她可以和adrien谈恋爱,可以在花园里幽会,她会觉得一切柔情都是温柔的,可他是个男孩,至少现在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为男人,也许在结束之后,那种毫无意义的凄凉的交配结束了,他就可以说自己是个男人了,学校里的孩子们都以自己有过性经验而侃侃而聊,很快,他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了。他还是听见他在哭,呼吸中弥漫着酸味,marin想adrien的肌肤细腻的像凝胶,双手在他的身体上的时候,和他自己不一样,他们是不一样的,marin迷迷糊糊的想。adrien不需要揉面、切菜、抗面粉和货物,他只需要读书,狂躁,穿上衣服就好,所以他的手细腻纤细修长,所有美好的对手的记忆,都可以存在在他的手上,可他用这种手去慰藉他的身体,他的嘴唇,他的胸腔,他衍死的锁骨。adrien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他疯狂的亲吻,偏执的撕咬,他用黏腻的语调说着混乱的话,说着俄语
marin在黑暗中伸出双手,此刻,他的手在黑夜中散发着幽幽的光晕,完整的在漆黑的背影中翻来覆去,窗外有车驶过的噪音,橘黄色的路灯在窗口邪恶地想象窗帘里的世界。他问adrien:在我没有见过你的时间里,你都存在在哪儿?
adrien似乎翻了个身,细细碎碎的声音响起。许久后,他轻诺着,说他哪儿都没去。
marin说不,你怎么可能哪儿都没去,我见过很多次你死在我的浴缸里。
adrien沉默着。marin呼唤着他。
adrien说:许多次,你已经将我杀害,可我仍然在拨打你的电话,你的母亲接过我的话,我邀请你过来将我杀死,你觉得这是舞会,可你却把妈妈杀了。
marin说:你不是萨宾娜吗?
sabina说:不,我永远不是。我是adrien。marin若有所思,翻个身,看见adrien脸上发黑的血管,犹如藤蔓与奸污的蕨类河床在他脸上发霉,他害怕的闭上了眼睛,因为adrien在熟睡,他一直安静的睡去了。而sabina的身影在走廊的对角线边上踌躇着,有好几次,他可以承认他看见妈妈的幽灵,阴冷的在他鞋子上走着。他有点害怕,热的痛觉发冷,在他脖子上蜗居着,他又要像孩子一样哭了。他还是没有长大。他就这样一直惶恐不安的想着,
有人怀疑他们吸毒吸爽了,这不是什么意外问题,好多青少年都会陷入这种困境,做爱,吸毒,然后发疯般尖叫。但他们很安静,很平静,看着形形色色的鞋子和脚印,一言不发,恍若陷入了这个世界虚假的购物袋里,捆在一团不透风的袋子里,一切事物与他们在没有实感关系。然后他们被分开,陷入两个不同却性质相似的牢笼,女警官坐在对面和marin说话。她以前在西班牙进修,说话时会带着西语不于发育的介词和语调,显得她诡谲的流露出一丝恐怖的陌生,她说的法语不再是他青春期前听到的,父亲扁桃体发炎而粗糙的愤怒,母亲中文语调的法语和尖酸的道理,一切都变得陌生不可知了。南美,有时候,年轻人就在酒吧门口的椅子上抽麻,那些神志不清的笑声混杂着叫骂和推搡的笑声,混乱的像南美人的家族血统列表单,她和那些人做朋友,知道他们在房间里的衣柜里种麻株,泥土滚出来,落在地板上。法国每年都要青少年在离家出走,有人想自杀,有人因为受不了家庭,有人因为被折磨,你是那一类?她用那双看起来并不能存在在世界上的青绿色眼睛凝视铁栏杆后的他,她用那种朋友式的妈妈的语气说:说吧,dupain,你说吧,这没有问题,你很好,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marin缩在拘留室的角落,想象女警官是否有一头棕色或橘色的长发,不知道是他多日的失眠和精神错乱导致的还是他们在逃亡的途中,真的意外吸食了那些罪恶的果子,总之世界变成了梵高的星月夜,女警官的话语语序变得乱七八糟的,词藻变成卡片游戏,他用脑子经量处理里面的母子裙带关系,他轻飘飘地回女警官的话:在某些时候,他好像没有那么安静,有点可恶,混球,我怀疑他有精神疾病,狂躁?神经质?(他神经质的冷笑了一声)不过总体还是好的,我们聊戈达尔,我没看过,他看了全部,有时候他说话都带着里面无形的诗意,我是说那种神经兮兮的说话方式,我们没能聊下去,我有点后悔了,但哲学课课题还没开始吧?王秀兰没说过,哦,她说以后她要学福柯!……我想他还是挺好的,就是有点暴力?不应该,他有自闭症吧,我不清楚,他疯了,我也差不多,你能给我妈妈打电话吗,让奶奶来吧,我对不起她。
他不敢说是因为还没有建立起对母亲的说辞,他逃跑时根本没想那么多,他偷窃的钱,他丢在街边垃圾桶的课本和作业纸,他掰断的电话卡和那天早上对她说的婊子和贱人,他本意不是好的,但也没有坏到哪里去,他想做个好孩子,想要躺在她的身边哭泣,或者说他的暗恋史,
他们蹲在当初第一次搭话的河的旁边,adrien握住marin垂在一旁的手,轻飘飘的提议到:我们再逃一次吧。
他想起伊恩麦克尤恩的那篇小说的题目《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第一句是“从夏日伊始……”。他们之间所有的疯狂都开始在夏日,他怀念着对方身体上细小的绒毛在肌肤相触中毛绒绒的躁动,羞涩和目眩在呼吸中蔓延,想起接吻,想起那首我的名字是伊莲,他们把车厢里所有的花束和树叶都丢在路边,丢掉手机和定位器,攥着剩余的钱重新离开了巴黎这条象征着青少年爱情懵懂和成长残酷的街道,夏日伊始的时代已经过去,象征着青春已经过去了一个短暂中的宝贵,但此刻,他们都感觉自己愈发的幼稚,想到戈达尔的狂人皮埃尔,想到费迪南和玛丽安所在夜幕的车座里,他们听见收音机谈起越战的时候,死亡是一个轻飘飘冷嗖嗖的数字,对人们来说什么都不是,是虚无,是结束的一段音频,是空荡荡的袖管,梦组成了我们,我们组成了梦,生命是要死的迪斯科舞厅,摇摇晃晃的跳着舞,青苹果的青涩在唇舌之中复苏,爱——浅薄又羞耻的语言,在肉欲间蔓延。marin把手放在adrien腿上,梦呓般。当adrien说着“这一天”的时候,我甚至能想象到他脸上倦怠又忧郁的神情,爱是神秘的毒药,但我想知道他说这话时候的心情和动作,而不是他一张脸上露出的妊娠纹般漆黑的树纹,他亲吻我,说着爱的时候轻松的就好像像是在吐血,生病就是这样的,吐血和不悯,轻轻松松的说出来,亲吻,离开,牙齿间小小的哀伤,今天是个很好的日子,我们没有钱去加油,今天是个很好的日子,河对岸有一家酒厅,我们没有钱,也许会被杀,会被打,但我不知道了一切,是否要去乞讨,还是回去,他无知的活着,adrien,他,对,那个孩子,我把手放在他的腿上,他就会露出一张近乎于空白和悲恸之中的神情,不说话,也不哭泣,掏出手表,换来几百块,我们继续流浪,我们杀掉了屋子里的老鼠,已经没有恐怖阴森的食物存在我们所在的小屋子里,但老鼠的尸体和紫色胎膜里的幼鼠却一直呆在我们的脑海中,无法褪去的一层精神科确诊病例。
他们想要成为风,风是真正孤独的旅人,是乡愁,是塔可夫斯基,是桑葚,是被苔丝吃掉的玫瑰花,没有落脚点,永远屹立在虚无和绝望的欲望上的灵魂,多好啊,永垂不朽,然后死掉,自由是一场痛苦的凌迟,顺着摇下的车窗流进来,歪歪扭扭的上路,他们��着高速公路一路向西,弃车,消失在伊莲丢失的日记本里。
希瑟尔和“我”说我们下午先去清理房间,然后去远行,沿着河道远行。“我”把手放在她温热的肚子上,说好。
希瑟尔和“我”都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和“希瑟尔却一无所知,在马路旁坐着,孤立无援。”
0 notes
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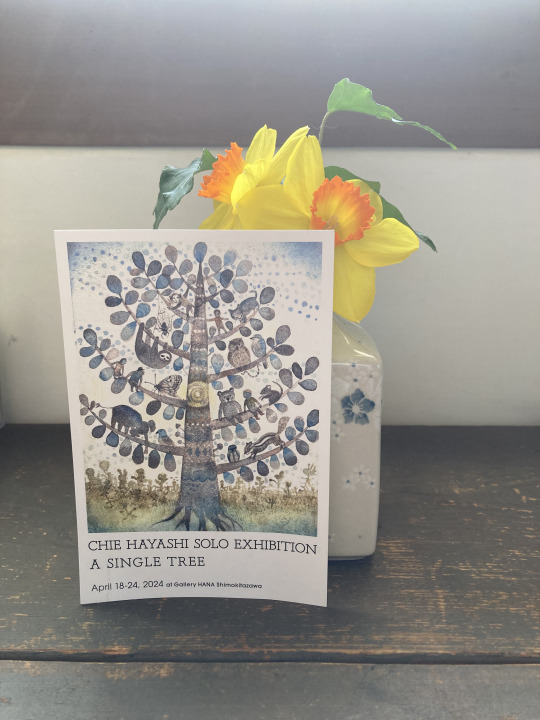



【開催中日記】
安曇野個展、速くも、
明日4/22月で終わりです。
ちなみに
今回の展覧会タイトルは
"雨の樹" という店名をうけて、
��た、会期中の七��二候
"虹始見 にじはじめてあらわる"
からつけました。
作品世界とも絡んでくれたかな
と思っていますがどうかな…
———————————————————
戸次祥子展「葉影の虹」
4/12〜22(水曜休)
11:00~17:00
於:雨の樹
長野県安曇野市穂高有明9929
(google map あり)
tel. 0263-31-6678
mail [email protected]
———————————————————
空間のことや余談など:
(写真3、4)
居心地の良い喫茶スペースは、紙に注文を書いてカウンターに出す→出来たら呼んでくれる方式。とってもおいしい珈琲をいただけました。廊下には、本のたくさん詰まった本棚や、造り付けの瀟洒なカップ棚もあります。
全て、木工の井崎正治さんによる空間。やさしいクリーム色の漆喰壁ですが、床や天井など、絶妙に配されたダークトーンが空間を引き締めていて、私の作品も引き立てられました。今回は、壁じゅう目一杯に作品を陳列くださっていたけれど(数点はずして頂いたほど;)、逆にうんと少ない作品数で、しつらい的な展示にしても、良さそうな場所だと思いました。
(写真5、6、7)
この感じだともうコラージュだけでも私は充分な感じでしたが、木口木版も色々並んでいます。初期、過渡期のものも。
(写真8)
雨の樹店主 岡本由紀子さんは、「あづみのチロル」「安曇野スタイル」といった、アート・クラフト作家の拠点やネットワークを長く運営してこられた方です。そのお人柄を慕って来られている感じのお客さん多数。ここに至るまでの想いを書き留めた手製本が。一冊購入。
(写真9、10、11)
さまざまな一期一会や再会あり。
隣町で山羊追いをしてから来てくれた千絵さん(下北沢で個展中)。
穂高駅から徒歩で来られた川岸さん(六月に雨の樹で個展)。
小学五年生くらいの男の子から突然紙と鉛筆を渡されて、
「食べ物を一つ、リアルに描く。よーいドン!」
…負けた気がする。
私は皿に盛っただけのカレーを描いた。
(写真12)
玄関も良い。
靴を脱いで、柔らかなスリッパに履き替えます。
・
穀雨に入った。
雨の日の雨の樹も良さそうですね。
0 notes
Text
春夏秋冬
H:南宋無門慧開禪師的一首詩「好時節」: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春夏秋冬四季,在我們平常人心中是無感的,除了農人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我們只知道寒冷冬天過後,春天覺得暖和,百花也開了。夏天來熱呼乎,秋天有點涼,落葉也多了。冬天來了又冷。其他無言。詩人作家寫四季,詩情畫意隨筆來,美美的意境詠嘆,無聊就念念解心煩。20240420W6
網路資料
正月期間,今天就介紹南宋無門慧開禪師的一首詩,它告訴我們甚麼是「好時節」: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春花秋月,夏風冬雪,一年四季都可以是好時節,但最讓你能夠感到好時節的,不是外在的春夏秋冬,而是「若無閒事在心頭」,也就是說,心中沒有掛慮,沒有恐懼,那麼任何時候都是好時節。2021年3月1日
荀子王制:
聖主1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春
作者:朱自清
1933年7月
姊妹計劃: 數據項
 參閱維基百科中的:春季 閲文言維基大典文
盼望着,盼望着,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
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欣欣然張開了眼。山朗潤起來了,水長起來了,太陽的臉紅起來了。
小草偷偷地從土裏鑽出來,嫩嫩的,綠綠的。園子裏,田野裏,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坐着,躺着,打兩個滾,踢幾腳球,賽幾䠀跑,捉幾回迷藏。風輕悄悄的,草軟綿綿的。
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䠀兒。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裏帶着甜味;閉了眼,樹上髣髴已經滿是桃兒、杏兒、梨兒!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着,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野花遍地是:雜樣兒,有名字的,沒名字的,散在草叢裏,像眼睛,像星星,還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楊柳風」,不錯的,像母親的手撫摸着你。風裏帶來些新翻的泥土的氣息,混着青草味,還有各種花的香,都在微微潤溼的空氣裏醞釀。鳥兒將窠巢安在繁花嫩葉當中,高興起來了,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唱出宛轉的曲子,與輕風流水應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這時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
雨是最尋常的,一下就是三兩天。可別惱。看,像牛毛,像花針,像細絲,密密地斜織着,人家屋頂上全籠着一層薄煙。樹葉子卻綠得發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時候,上燈了,一點點黃暈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靜而和平的夜。鄉下去,小路上,石橋邊,撐起傘慢慢走着的人;還有地裏工作的農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們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裏靜默着。
天上風箏漸漸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裏鄉下,家家戶戶,老老小小,他們也趕䠀兒似的,一個個都出來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擻抖擻精神,各做各的一份兒事去。「一年之計在於春」,剛起頭兒,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剛落地的娃娃,從頭到腳都是新的,它生長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壯的青年,有鐵一般的胳膊和腰腳,他領着我們上前去。
說夢
作者:朱自清
1925年10月
姊妹计划: 数据项
偽《列子》里有一段夢話,說得甚好: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不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复役人。……尹氏心營世事,慮鐘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仆:趨走作役,無不為也; 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
此文原意是要說出“苦逸之复,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這其間大有玄味,我是領略不著的;我只是斷章取義地賞識這件故事的自身,所以才老遠地引了來。我只覺得夢不是一件坏東西。即真如這件故事所說,也還是很有意思的。因為人生有限,我們若能夜夜有這樣清楚的夢,則過了一日,足抵兩日,過了五十歲,足抵一百歲;如此便宜的事,真是落得的。至于夢中的“苦樂”,則照我素人的見解,畢竟是“夢中的”苦樂,不必斤斤計較的。若必欲斤斤計較,我要大膽地說一句:他和那些在牆上貼紅紙條儿,寫著“夜夢不祥,書破大吉”的,同樣地不懂得夢!
但庄子說道,“至人無夢。”偽《列子》里也說道,“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張湛注曰,“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可知我們這几位先哲不甚以做夢為然,至少也總以為夢是不大高明的東西。但孔子就与他們不同,他深以“不复夢見周公”為憾;他自然是愛做夢的,至少也是不反對做夢的。——殆所謂時乎做夢則做夢者歟?我覺得“至人”,“真人”,畢竟沒有我們的份儿,我們大可不必妄想;只看“乃當不眠”一個條件,你我能做到么?唉,你若主張或實行“八小時睡眠”,就別想做“至人”,“真人”了!但是,也不用擔心,還有為我們掮木梢的:我們知道,愚人也無夢!他們是一枕黑甜,哼呵到曉,一些儿夢的影子也找不著的!我們徼幸還會做几個夢,雖因此失了“至人”,“真人”的資格,卻也因此而得免于愚人,未嘗不是運气。至于“至人”,“真人”之無夢和愚人之無夢,究竟有何分別?卻是一個難題。我想偷懶,還是摭拾上文說過的話來答吧:“真人……乃當不眠,……”而愚人是“一枕黑甜,哼呵到曉”的!再加一句,此即孔子所謂“上智与下愚不移”也。說到孔子,孔子不反對做夢,難道也做不了“至人”,“真人”?我說,“唯唯,否否!”孔子是“圣人”,自有他的特殊的地位,用不著再來爭“至人”,“真人”的名號了。但得知道,做夢而能夢周公,才能成其所以為圣人;我們也還是夠不上格儿的。
我們終于只能做第二流人物。但這中間也還有個高低。高的如我的���友P君:他夢見花,夢見詩,夢見綺麗的衣裳,……真可算得有夢皆甜了。低的如我:我在江南時,本忝在愚人之列,照例是漆黑一團地睡到天光;不過得聲明,哼呵是沒有的。北來以后,不知怎樣,陡然聰明起來,夜夜有夢,而且不一其夢。但我究竟是新升格的,夢盡管做,卻做不著一個清清楚楚的夢!成夜地亂夢顛倒,醒來不知所云,恍然若失。最難堪的是每早將醒未醒之際,殘夢依人,膩膩不去;忽然雙眼一睜,如墜深谷,万象寂然——只有一角日光在牆上痴痴地等著!我此時決不起來,必凝神細想,欲追回夢中滋味于万一;但照例是想不出,只惘惘然茫茫然似乎怀念著些什么而已。雖然如此,有一點是知道的:夢中的天地是自由的,任你徜徉,任你翱翔;一睜眼卻就給密密的麻繩綁上了,就大大地不同了!我現在确乎有些精神恍惚,這里所寫的就夠教你知道。但我不因此詛咒夢;我只怪我做夢的藝術不佳,做不著清楚的夢。若做著清楚的夢,若夜夜做著清楚的夢,我想精神恍惚也無妨的。照現在這樣一大串儿糊里糊涂的夢,直是要將這個“我”化成漆黑一團,卻有些儿不便。是的,我得學些本事,今夜做他几個好好的夢。我是徹頭徹尾贊美夢的,因為我是素人,而且將永遠是素人。
(原載1925年10月《清華周刊》第24卷第8號)
揚州的夏日
揚州從隋煬帝以來,是詩人文士所稱道的地方;稱道的多了,稱道得久了,一般人便也隨聲附和起來。直到現在,你若向人提起揚州這個名字,他會點頭或搖頭說:“好地方!好地方!”特別是沒去過揚州而念過些唐詩的人,在他心里,揚州真像蜃樓海市一般美麗;他若念過《揚州畫舫錄》一類書,那更了不得了。但在一個久住揚州像我的人,他卻沒有那么多美麗的幻想,他的憎惡也許掩住了他的愛好;他也許离開了三四年并不去想它。若是想呢,——你說他想什么?女人;不錯,這似乎也有名,但怕不是現在的女人吧?——他也只會想著揚州的夏日,雖然与女人仍然不無關系的。
北方和南方一個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無水而南方有。誠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決了堤防,但這并不能算是有水;北平的三海和頤和園雖然有點儿水,但太平衍了,一覽而盡,船又那么笨頭笨腦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揚州的夏日,好處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稱為“瘦西湖”,這個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以行,“雅得這樣俗”,老實說,我是不喜歡的。下船的地方便是護城河,曼衍開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這是你們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還有許多杈杈椏椏的支流。這條河其實也沒有頂大的好處,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靜,和別處不同。
沿河最著名的風景是小金山,法海寺,五亭橋;最遠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們是知道的,小金山卻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錯——可是我還不曾有過那樣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個塔,和北海的一樣,据說是乾隆皇帝下江南,鹽商們連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這個塔;但還有一樁,你們猜不著,是紅燒豬頭。夏天吃紅燒豬頭,在理論上也許不甚相宜;可是在實際上,揮汗吃著,倒也不坏的。五亭橋如名字所示,是五個亭子的橋。橋是拱形,中一亭最高,兩邊四亭,參差相稱;最宜遠看,或看影子,也好。橋洞頗多,乘小船穿來穿去,另有風味。平山堂在蜀岡上。登堂可見江南諸山淡淡的輪廓;“山色有無中”一句話,我看是恰到好處,并不算錯。這里游人較少,閒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閒寂胜。從天宁門或北門下船。蜿蜒的城牆,在水里倒映著蒼黝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撐過去,岸上的喧扰像沒有似的。
船有三种:大船專供宴游之用,可以挾妓或打牌。小時候常跟了父親去,在船里听著謀得利洋行的唱片。現在這樣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划子”,真像一瓣西瓜,由一個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撐著。乘的人多了,便可雇兩只,前后用小凳子跨著:這也可算得“方舟”了。后來又有一种“洋划”,比大船小,比“小划子”大,上支布篷,可以遮日遮雨。“洋划”漸漸地多,大船漸漸地少,然而“小划子”總是有人要的。這不獨因為价錢最賤,也因為它的伶俐。一個人坐在船中,讓一個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撐著,簡直是一首唐詩,或一幅山水畫。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撐船,也非“小划子”不行。“小划子”雖然便宜,卻也有些分別。譬如說,你們也可想到的,女人撐船總要貴些;姑娘撐的自然更要貴囉。這些撐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說過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們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說以亂頭粗服,風趣天然為胜;中年而有風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場作戲,或尚不傷廉惠;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覺意味索然了。
北門外一帶,叫做下街,“茶館”最多,往往一面臨河。船行過時,茶客与乘客可以隨便招呼說話。船上人若高興時,也可以向茶館中要一壺茶,或一兩种“小籠點心”,在河中喝著,吃著,談著。回來時再將茶壺和所謂小籠,連价款一并交給茶館中人。撐船的都与茶館相熟,他們不怕你白吃。揚州的小籠點心實在不錯:我离開揚州,也走過七八處大大小小的地方,還沒有吃過那樣���的點心;這其實是值得惦記的。茶館的地方大致總好,名字也頗有好的。如香影廊,綠楊村,紅葉山庄,都是到現在還記得的。綠楊村的幌子,挂在綠楊樹上,隨風飄展,使人想起“綠楊城郭是揚州”的名句。里面還有小池,叢竹,茅亭,景物最幽。這一帶的茶館布置都歷落有致,迥非上海,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樓可比。
“下河”總是下午。傍晚回來,在暮靄朦朧中上了岸,將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搖著扇子;這樣進了北門或天宁門走回家中。這時候可以念“又得浮生半日閒”那一句詩了。
(原載1929年12月11日《白華旬刊》第4期)
夏日田間即景(近沙士頓)
作者:徐志摩 1922年寫於1922年2月,原載於1922年3月14日《時事新報·學燈》,並未錄入徐志摩在世時出版的4本詩集中。
版本信息
姊妹计划: 数据项
柳林青青,
南風薰薰,
幻成奇峰瑤島,
一天的黃雲白雲,
那邊麥浪中間,
有農婦笑語殷殷。
笑語殷殷——
問後園豌豆肥否,
問楊梅可有鳥來偷;
好幾天不下雨了,
玫瑰花還未曾紅透;
梅夫人今天進城去,
且看她有新聞無有。
笑語殷殷——
「我們家的如今好了,
已經照常上工去,
不再整天的無聊,
不再逞酒使氣,
回家來有說有笑,
疼他兒女——愛他妻;
呀!真巧!你看那邊,
蓬著頭,走來的,笑嘻嘻,
可不是他,(哈哈!)滿身是泥!」
南風熏熏,
草木青青,
滿地和暖的陽光,
滿天的白雲黃雲,
那邊麥浪中間,
有農夫農婦,笑語殷殷。
想飛
作者:徐志摩 1925年收錄於散文集《自剖》
姊妹计划: 数据项
假如這時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牆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簷下偎著一個戴黑帽兒的巡警,半攏著睡眼,看棉團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著玩……假如這夜是一個深極了的啊,不是壁上掛鐘的時針指示給我們看的深夜,這深就比是一個山洞的深,一個往下鑽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這樣一個深夜,它那無底的陰森捻起我遍體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篩的雪,篩淡了遠近間揚動的市謠;篩泯了在泥道上掙扎的車輪;篩滅了 腦殼中不妥協的潛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靜。那在樹蔭濃密處躲著的夜鷹,輕易不敢在天光還在照亮時出來睜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裡有一點子黑的。正衝著太陽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著眼、對著那兩株樹縫裡瞧,黑的,有排子來大,不,有桃子來大──嘿,又移著往西了!
我們吃了中飯出來到海邊去。(這是英國康槐爾極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勖麗麗的叫聲從我們的腳底下勻勻的往上顫,齊著腰,到了肩高,過了頭頂,高入了雲,高出了雲。
啊!你能不能把一種急震的樂音想像成一陣光明的細雨,從藍天裡衝著這平鋪著青綠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點都是跳舞的小腳,安琪兒的。雲雀們也吃過了飯,離開了它們卑微的地巢飛往高處做工去。上帝給它們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著,這兒一隻,那邊又起了兩!一起就衝著天頂飛,小翅膀活動的多快活,圓圓的,不躊躇的飛,──它們就認識青天。一起就開口唱,小嗓子活動的多快活,一顆顆小精圓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們讚美的是青天。瞧著,這飛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頂著無底的天頂細細的搖,──這全看不見了,影子都沒了!但這光明的細雨還是不住的下著……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背負蒼天,而莫之夭閼者;」那不容易見著。我們鎮上東關廂外有一座黃泥山,山頂上有一座七層的塔,塔尖頂著天。塔院裡常常打鐘,鐘聲響動時,那在太陽西曬的時候多,一枝艷艷的大紅花貼在西山的鬢邊回照著塔山上的雲彩,──鐘聲響動時,繞著塔頂尖,摩著塔頂天,穿著塔頂雲,有一隻兩隻,有時三隻四隻有時五隻六隻蜷著爪往地面瞧的「餓老鷹」,撐開了它們灰蒼蒼的大翅膀沒掛戀似的在盤旋,在半空中浮著,在晚風中泅著,彷彿是按著塔院鐘的波蕩來練習圓舞似的。那是我做孩子時的「大鵬」?
有時好天抬頭不見一瓣雲的時候聽著貌憂憂的叫聲,我們就知道那是寶塔上的餓老鷹尋食吃來了,這一想像半天裡禿頂圓睛的英雄,我們背上的小翅膀骨上就彷彿豁出了一銼銼鐵刷似的羽毛,搖起來呼呼聲的,只一擺就衝出了書房門,鑽入了玳瑁鑲邊的白雲裡玩兒去,誰耐煩站在先生書桌前晃著身子背早上上的多難背的書!
啊!飛!不是那在樹枝上矮矮的跳著麻雀兒的飛;不是那湊天黑從堂匾後背衝出來趕蚊子吃的蝙蝠的飛;也不是那軟尾巴軟嗓於做集在堂簷上的燕子的飛。要飛就得滿天飛,風攔不住雲擋不住的飛,一翅膀就跳過一座山頭,影子下來遮得陰二+畝稻田的飛,要天晚飛倦了就來繞著那塔頂尖順著風向打圓圈做夢……聽說餓老鷹會抓小雞!
飛。人們原來都是會飛的。天使們有翅膀,會飛,我們初來時也有翅膀,會飛。我們最初來就是飛了來的,有的做完了事還是飛了去,他們是可羨慕的。但大多數人是忘了飛的,有的翅膀上掉毛不長再也飛不起來,有的翅膀叫膠水給膠住了,融拉不開,有的羽毛叫人給修短了像鴿子似的只會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對翅膀上當鋪去典錢使過了期再也贖不回……真的,我們一過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飛的本領。
但沒了翅膀或是翅膀壞了不能用是一件可怕的事。因為你再也飛不回去,你蹲在地上呆望著飛不上去的天,看旁人有福氣的一程一程的在青雲裡逍遙,那多可憐。而且翅膀又不比是你腳上的鞋,穿爛了可以再問媽要一雙去,翅膀可不成,折了一根毛就是一根,沒法給補的。還有,單顧著你翅膀也還不定規到時候能飛,你這身子要是不謹慎養太肥了,翅膀力量小也再也拖不起,也是一樣難不是?
一對小翅膀馱不起一個胖肚子,那情形多可笑!到時候你聽人家高聲的招呼說,朋友,回去罷,趁這天還有紫色的光,你聽他們的翅膀在半空中沙沙的搖響,朵朵的春雲跳過來擁著他們的肩背,望著最光明的來處翩翩的,冉冉的,輕煙似的化出了你的視域,像雲雀似的只留下一瀉光明的驟雨──「 Thou art unseen,ut yet I hear the shrill delight.」──那你,獨自在泥塗裡淹著,夠多難受,夠多懊惱,夠多寒傖!趁早留神你的翅膀,朋友。
是人沒有不想飛的。老是在這地面上爬著夠多厭煩,不說別的。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到雲端裡去,到雲端裡去!那個心裡不成天千百遍的這麼想?飛上天空去浮著,看地球這彈丸在太空裡滾著,從陸地看到海、從海再看回陸地。凌空去看一個明白──這本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權威,做人的交代。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動,就擲了它,可能的話,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
人類初發明用石器的時候,已經想長翅膀,想飛,原人洞壁上畫的四不像,它的背上掮著翅膀;拿著弓箭趕野獸的,他那肩背上也給安了翅膀。小愛神是有一對粉嫩的肉翅的。挨開拉斯(Icarus)是人類飛行史裡第一個英雄,第一次犧牲。安琪兒(那是理想化的人)第一個標記是幫助他們飛行的翅膀。那也有沿革──你看西洋書上的表現。最初像一對小精緻的令旗,蝴蝶似的粘在安琪兒們的背上,像真的,不靈動的。漸漸的翅膀長大了,地位安準了,毛羽豐滿了。畫圖上的天使們長上了真的可能的翅膀。人類初次實現了翅膀的觀念,徹悟了飛行的意義。挨開拉斯閃不死的靈魂,回來投生又投生。
人類最大的使命,是製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飛!理想的極度,想像的止境,從人到神!詩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盤旋的。飛:超脫一切,籠蓋一切,掃蕩一切,吞吐一切。你上那邊山峰頂上試去,要是度不到這邊山峰上,你就得這萬丈的深淵裡去找你的葬身地!
[這人形的鳥會有一天試他第一次的飛行給這世界驚駭,使所有的著作讚美,給他所從來的棲息處永久的光榮]啊!達文西!
但是飛?自從挨開拉斯以來,人類的工作是製造翅膀,還是束縛翅膀?這翅膀,承上了文明的重量,還能飛嗎?都是飛了來的,還都能飛了回去嗎?鉗住了,烙住了,壓住了,──這人形的鳥會有試他第一次飛行的一天嗎?……
同時天上那一點子黑的已經迫近在我的頭頂,形成了一架鳥形的機器,忽的機沿一側,一球光直往下注,硼的一聲炸響,──炸碎了我在飛行中的幻想,青天裡平添了幾堆破碎的浮雲。
(一九二五年十月六月)
故都的秋(郁達夫)
秋天,無論在什么地方的秋天,總是好的;可是啊,北國的秋,卻特別地來得清,來得靜,來得悲涼。我的不遠千里,要從杭州赶上青島,更要從青島赶上北平來的理由,也不過想飽嘗一嘗這“秋”,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當然也是有的;但草木雕得慢,空气來得潤,天的顏色顯得淡,并且又時常多雨而少風;一個人夾在蘇州上海杭州,或廈門香港廣州的市民中間,渾渾沌沌地過去,只能感到一點點清涼,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態,總看不飽,嘗不透,賞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開,半醉的狀態,在領略秋的過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國之秋,已將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總要想起陶然亭的蘆花,釣魚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鐘聲。在北平即使不出門去罷,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來住著,早晨起來,泡一碗濃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綠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馴鴿的飛聲。從槐樹葉底,朝東細數著一絲一絲漏下來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靜對著象喇叭似的牽牛花(朝榮)的藍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夠感覺到十分的秋意。說到了牽牛花,我以為以藍色或白色者為佳,紫黑色次之,淡紅色最下。最好,還要在牽牛花底,教長著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細且長的秋草,使作陪襯。
北國的槐樹,也是一种能使人聯想起秋來的點綴。象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來,會舖得滿地。腳踏上去,聲音也沒有,气味也沒有,只能感出一點點极微細极柔軟的触覺。掃街的在樹影下一陣掃后,灰土上留下來的一條條掃帚的絲紋,看起來既覺得細膩,又覺得清閒,潛意識下并且還覺得有點儿落寞,古人所說的梧桐一葉而天下知秋的遙想,大約也就在這些深沈的地方。
秋蟬的衰弱的殘聲,更是北國的特產;因為北平處處全長著樹,屋子又低,所以無論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見它們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這秋蟬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樣,簡直象是家家戶戶都養在家里的家虫。
還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象樣。
在灰沈沈的天底下,忽而來一陣涼風,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來了。一層雨過,云漸漸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陽又露出臉來了;著著很厚的青布單衣或夾襖曲都市閒人,咬著煙管,在雨后的斜橋影里,上橋頭樹底下去一立,遇見熟人,便會用了緩慢悠閒的聲調,微歎著互答著的說:
“唉,天可真涼了─—”(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長。)
“可不是么?一層秋雨一層涼了!”
北方人念陣字,總老象是層字,平平仄仄起來,這念錯的歧韻,倒來得正好。
北方的果樹,到秋來,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棗子樹;屋角,牆頭,茅房邊上,灶房門口,它都會一株株地長大起來。象橄欖又象鴿蛋似的這棗子顆儿,在小橢圓形的細葉中間,顯出淡綠微黃的顏色的時候,正是秋的全盛時期;等棗樹葉落,棗子紅完,西北風就要起來了,北方便是塵沙灰土的世界,只有這棗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國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沒有的GoldenDays。
有些批評家說,中國的文人學士,尤其是詩人,都帶著很濃厚的頹廢色彩,所以中國的詩文里,頌贊秋的文字特別的多。但外國的詩人,又何嘗不然?我雖則外國詩文念得不多,也不想開出賬來,做一篇秋的詩歌散文鈔,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詩人的集子,或各國的詩文的An-thology來,總能夠看到許多關���秋的歌頌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詩人的長篇田園詩或四季詩里,也總以關于秋的部分。寫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見有感覺的動物,有情趣的人類,對于秋,總是一樣的能特別引起深沈,幽遠,嚴厲,蕭索的感触來的。不單是詩人,就是被關閉在牢獄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會感到一种不能自己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嘗有國別,更何嘗有人种階級的區別呢?不過在中國,文字里有一個“秋士”的成語,讀本里又有著很普遍的歐陽子的《秋聲》与蘇東坡的《赤壁賦》等,就覺得中國的文人,与秋的關系特別深了。可是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國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
南國之秋,當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橋的明月,錢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涼霧,荔枝灣的殘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濃,回味不永。比起北國的秋來,正象是黃酒之与白干,稀飯之与饃饃,鱸魚之与大蟹,黃犬之与駱駝。
秋天,這北國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話,我愿把壽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換得一個三分之一的零頭。
一九三四年八月,在北平
冬天(朱自清)
說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鍋”(鋁鍋)白煮豆腐,熱騰騰的。水滾著,像好些魚眼睛,一小塊一小塊豆腐養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鍋在“洋爐子”(煤油不打气爐)上,和爐子都熏得烏黑烏黑,越顯出豆腐的白。這是晚上,屋子老了,雖點著“洋燈”,也還是陰暗。圍著桌子坐的是父親跟我們哥儿三個。“洋爐子”太高了,父親得常常站起來,微微地仰著臉,覷著眼睛,從氤氳的熱气里伸進筷子,夾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們的醬油碟里。我們有時也自己動手,但爐子實在太高了,總還是坐享其成的多。這并不是吃飯,只是玩儿。父親說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們都喜歡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著那鍋,等著那熱气,等著熱气里從父親筷子上掉下來的豆腐。
又是冬天,記得是陰歷十一月十六晚上,跟S君P君在西湖里坐小划子。S君剛到杭州教書,事先來信說:“我們要游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在想起來還像照在身上。本來前一晚是“月當頭”;也許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別吧。那時九點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們一只划子。有點風,月光照著軟軟的水波;當間那一溜儿反光,像新砑的銀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爾有一兩星燈火。S君口占兩句詩道:“數星燈火認漁村,淡墨輕描遠黛痕。”我們都不大說話,只有均勻的槳聲。我漸漸地快睡著了。P君“喂”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見他在微笑。船夫問要不要上淨寺去;是阿彌陀佛生日,那邊蠻熱鬧的。到了寺里,殿上燈燭輝煌,滿是佛婆念佛的聲音,好像醒了一場夢。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S君還常常通著信,P君听說轉變了好几次,前年是在一個特稅局里收特稅了,以后便沒有消息。
在台州過了一個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個山城,可以說在一個大谷里。只有一條二里長的大街。別的路上白天簡直不大見人;晚上一片漆黑。偶爾人家窗戶里透出一點燈光,還有走路的拿著的火把;但那是少极了。我們住在山腳下。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風聲,跟天上一只兩只的鳥影。夏末到那里,春初便走,卻好像老在過著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我們住在樓上,書房臨著大路;路上有人說話,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見。但因為走路的人太少了,間或有點說話的聲音,听起來還只當遠風送來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們是外路人,除上學校去之外,常只在家里坐著。妻也慣了那寂寞,只和我們爺儿們守著。外邊雖老是冬天,家里卻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來的時候,樓下廚房的大方窗開著,并排地挨著她們母子三個;三張臉都帶著天真微笑地向著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們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們四人。那時是民國十年,妻剛從家里出來,滿自在。現在她死了快四年了,我卻還老記著她那微笑的影子。
無論怎么冷,大風大雪,想到這些,我心上總是溫暖的。
(原載1933年12月1日《中學生》第40號)
白馬湖之冬
夏丏尊
在我過去四十餘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嘗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馬湖的時候了。十年以來,白馬湖已成了一個小村落。當我移居的時候,還是一片荒野,春暉中學的新建築巍然矗立於湖的那一面,湖的這一面的山腳下是小小的幾間新平屋,住著我和劉君心如兩家。此外兩、三里內沒有人煙。一家人於陰曆十一月下旬從熱鬧的杭州移居於這荒涼的山野,宛如投身於極帶中。
那裡的風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響,好像虎吼。屋宇雖係新建,構造卻極粗率,風從門窗隙縫中來,分外尖削。把門縫窗隙厚厚地用紙糊了,椽縫中卻仍有透入。風颳得厲害的時候,天未夜就把大門關上,全家吃畢夜飯即睡入被窩裡,靜聽寒風的怒號,湖水的洴湃。靠山的小後軒,算是我的書齋,在全屋子中是風最少的一間,我常把頭上的羅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油燈下工作至深夜,松濤如吼,霜月當窗,饑鼠吱吱在承塵上奔竄。我於這種時候,深感到蕭瑟的詩趣,常獨自撥劃著爐火,不肯就睡,把自己擬諸山水畫中的人物,作種種幽邈的遐想。
現在白馬湖到處都是樹木了,當時尚一株樹都未種,月亮與太陽卻是整個兒的,從山上起直要照到山下為止。在太陽好的時候,祇要不颳風,那真和暖得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庭間曝日,甚至於喫午飯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飯一樣。日光曬到那裡,就把椅凳移到那裡。忽然寒風來了,祇好逃難似地各自帶了椅凳逃入室中,急急把門關上。在平常的日子,風來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時候,半夜即息。至於大風寒,那是整日夜狂吼,要二、三日才止的。最嚴寒的幾天,泥地看去慘白如水門汀,山色凍得發紫而黯,湖波泛著深藍色。
下雪原是我所不憎厭的。下雪的日子,室內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燈。遠山積雪,足供半個月的觀看,舉頭即可從窗中望見。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下雪不過一、二次,我在那裡所日常領略的冬的情味,幾乎都從風來。白馬湖的所以多風,可以說是有著地理上的原因的,那裡環湖原都是山,而北首卻有一個半里闊的空隙,好似故意張了袋口歡迎風來的樣子。白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風景地相差不遠;唯有風卻與別的地方不同。風的多和大,凡是到過那裡的人都知道的。風在冬季的感覺中,自古占著重要的因素,而白馬湖的風尤其特別。
現在,一家僦居上海多日了,偶然於夜深人靜聽到風聲的時候,大家就要提起白馬湖來,說「白馬湖不知今夜又颳得怎樣厲害哩!」
0 notes
Text
山樱之落 贰 东山道与北陆道之行 5
伊万的预料没错,由于摄入了过多的脂肪加之牠吃下了远超平日食量的食物——这就是自己动手烤制食物的坏处,每次伊万这样做时,牠总会不知不觉吃得过多——几小时后牠的确感到了反胃。已经在喝那种伊万讨厌的、用开水冲泡绿色的茶叶粉末的、名为抹茶的樱和菊建议伊万喝些抹茶,不过伊万不认为自己应该在已经感到反胃的前提下挑战自我喝下些瞧上去像是用长了绿霉的面粉制作的东西,故牠采纳了樱、菊的第二个建议,吃些当季的、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水果。
“这是从伊万君下午瞧见的那些种在西对庭院里的蜜柑树上摘下来的。”樱捧着茶杯说,坐在她身侧的菊正握着一种用竹子制作的、形状如倒过来的伞菌的器具将开水与茶粉搅匀。
下午时在菊的带领下——樱再次缺席,显然是为了完成某些伊万不知具体内容的政务——伊万参观了整个三嘉原御所,御所的面积比牠在山路上看见得更大些,与习惯将建筑修作相连的整体的欧美房屋不同,日式建筑喜欢将房屋修作分离的个体,并用走廊将其中一些房屋连接起来。据菊介绍,西对是御所里专门修给客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菊也告诉伊万若牠不喜欢西对,那么牠也可选择除去母屋外的任何一处空余的房间。不过伊万看不出牠有什么理由不喜欢西对,那是栋背对母屋、形如颠倒倾斜的英文字母L的房屋,较长的部分是给身份尊贵的客人居住,较短的部分则属于客人的仆从。进入房屋的那条走廊能瞧见母屋后的、御所里最大的庭院,房屋另一侧则是个较小的单独的庭院,院中种植着好几个结满了果实的橘树,面向小庭院的推拉门中下段的、原本由数层纸构成的部分被替换成了玻璃,而窗户则完全是由木框与玻璃制作的,如此呆在房间里时,不需推开门与窗户也能望见小庭院里的由橘树、枫树、灌木以及石头组成的景致。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无论是窗户的高度还是推拉门玻璃的部分都遵从了日本人跪坐的习惯,故坐在椅子上的伊万必须得弯腰才能看见跪坐的日本人看见的景色。
“在俄罗斯,我们把蜜柑唤作мандарин уншиу,”伊万一面剥开蜜柑皮一面说,“翻译成日语就是‘来自萨摩的橘子’。通常我们把这种树种植在室内充作观赏植物,因种植在室外的蜜柑到了秋季就会被冻死。”牠将一瓣蜜柑塞入嘴中,因溢满口腔的微酸味而忍不住皱眉眯眼,“喔,这可比我在国内吃到的更酸些,但也更新鲜。”
“更酸吗?”樱问,“我还以为种植在室内的蜜柑会因营养、日晒不足而口感更差。”
“食用的蜜柑都种植在高加索地区,那里位于俄罗斯最南部,西方临黑海,东方临里海,南部与奥斯曼帝国接壤。”伊万介绍说,“不过由于高加索地区距离莫斯科较为遥远,每次运送到莫斯科的蜜柑总是不太新鲜,一部分蜜柑也会被制作成果酱罐头运送至莫斯科贩卖。”牠又往嘴里塞了一瓣蜜柑,“过去我能吃到的刚采摘下来的水果都是浆果,从七月至九月,几乎每日都有居住在近郊的老嬷嬷们带着装在玻璃罐里的浆果进城里贩卖,她们采摘的皆是野生的浆果,商店里贩卖的则是种植园里人工种植的浆果。而面包店、餐厅也会在收获浆果的时节推出季节性的食品,例如用浆果制作的各类糕点和甜点,路上还会出现一种贩卖冰冻或冰镇酸奶油、牛奶、浆果的混合物的小贩。”
“听上去很不错。”菊搅匀了茶粉,又给伊万倒了杯冲泡好的绿茶叶,“日本的人们倒没有将水果制作成果酱的习惯,气候炎热时吃的消暑食物也是放进井底冰镇的西瓜,或水羊羹、水馒头、葛饼等由米与砂糖制作的菓子。”
“你们想试试果酱吗?”伊万将最后一瓣蜜柑塞入嘴里,“有砂糖的话,我就能用这些蜜柑制作橘子果酱,”牠瞥了眼自己面前那杯散发出微苦气味的绿茶叶开水汤——牠拒绝把这种略苦涩的、不美味的水称为茶——“还能用果酱冲泡俄式茶。上次去那家不太正宗的俄式餐厅时你俩的饮料皆点的咖啡,我一直想向你们介绍俄式茶。”
翌日伊万醒来时仍感到昨晚吃下的食物尚未完全消化,牠侧躺在布团上透过障子上的那排玻璃——昨晚闲聊时樱、菊告诉牠这种推拉门被称为障子[1],而中下部分镶嵌有玻璃的则被称为雪见障子,是为了冬日时人们能呆在温暖的屋子里赏庭院中的雪景所用,房间内那些由纸和木框所制的、表面绘有植物与动物的风景画的推拉门则被称为襖[2]——盯着庭院中的蜜柑树发了好一会儿呆才起床。
伊万本想着也许今日牠就能制作橘子果酱,因牠想着在动身去犬舞见县以及周围地区寻找日本的民俗怪谈前将橘子果酱制作好以便于携带在路上食用,毕竟考虑到日本的货运发展程度、人民的富裕程度以及日本人的饮食习惯,牠已经预感到未来旅途中的餐饮不会让牠满意。‘也许我还能制作些别的、易于保存和携带的食物。’伊万想,其实假如时间充足的话,牠很愿意制作些烟熏肉,牠和牠的姐妹、弟弟夏季回领地时从当地的农民那儿学会了好几种腌制肉类的方法。来到日本后伊万曾为拯救自己的味觉以及维持足够的肉类摄入量而尝试过制作烟熏肉,可惜土田太太家的庭院太小,东京的气候也不够干燥、凉爽,悬挂在屋檐下的烟熏肉一部分被鸟、老鼠以及人——牠猜是那些偷偷躲街角窥视牠的日本男孩们干的,不过牠并不打算为几块烟熏肉报警——偷走吃掉,剩下的那部分则很快长出了各种颜色的霉斑。
然而吃过早饭——伊万颇惊讶得发现早餐中有一道肉菜,看来的确如樱昨日介绍的那样,此地的人们饮食中肉类占有较大的比重——菊却问伊万是否要跟随牠与樱一同去犬舞见神社。
“后日我将在神社里举行为皇室以及日本祈福的仪式。”樱解释道,“今日得去检查与仪式有关的器物是否被准备好,为了避免后日的仪式出错我也会与巫女们进行排练。假如伊万君对犬舞见神社以及钤姬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我们一同前往神社。”樱顿了顿,又提议道:“伊万君不是喜欢日本的民俗怪谈吗?后日的祈福仪式也算日本民俗的一种,伊万君不介意的话后日可以来旁观祈福仪式。”
“好啊。”伊万答应了樱的邀请,并有意用开玩笑的语气说:“说起来你们这里有笔记本与钢笔、或任何非毛笔的便于写字的笔吗?我想由于地震,我找回我的行李、尤其是那个记录了我收集的日本的民俗怪谈的笔记本的几率小到接近零。”
像是听出了伊万语气下对房东及她的女儿的担忧,菊安慰道:“也许土田太太与她的女儿不会有事的,伊万君不是购买了西式的桌椅吗?如果她们在地震时躲在了西式四脚桌下,那么桌椅就能帮她们抵挡砸下来的屋瓦与房梁。”
如菊听出了伊万藏在打趣之中的担忧,伊万也听出了菊为了安慰牠而有意忽略了日本政府因各种因素救援不及时而导致躲在木桌下的土田太太及她的女儿死于脱水、无法及时离开废墟的土田太太如地震当日他们三人在路上遇见的那些困于火灾的人们那样死于吸入有毒气体等可能性,“也许吧。”伊万附和道,暗自祈祷土田太太和她的女儿拥有在地震中幸存的好运气。
尽管犬舞见神社就位于三嘉原御所对面的那座山上,但有违于伊万以为的他们将步行前往的预想,樱依旧命仆从牵来了马。考虑到这两日见到的马匹数量、马的状态以及饲养马的成本,伊万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樱、菊的家族的财富水平。
与通往三嘉原御所的、压实了土面的山道不同,通往犬舞见神社道路是由或大或小的石块组成的、随地势而变换坡度的石制阶梯,石梯两旁则摆放着用另一种石材制作的落地灯具。伊万本以为他们会下马步行,可樱、菊丝毫不曾停顿,径自握着缰绳操控马走上石阶,进在坡度较为陡峭的地段放慢速度并侧头看向伊万仿佛在观察牠是否需要帮助。伊万的确不曾有过在此类地形骑马的经历,所幸牠的友人所提供的马温顺、易于操控且显然拥有在此类地形中行走的经验,不需牠作出额外的指挥,牠所骑的那匹马便自行跟着樱骑着的头马轻易度过了山路中最为陡峭的部分。
在通过最后一道被樱、菊称为鸟居的、涂抹有红漆的木柱建筑结构后,出现于伊万视野里的是一条比山道更宽阔些的石板路与伫立在石板路中间的、不知为何穿着衣服的、巨大的犬形石雕,石板路的尽头有着一前一后两座样式与牠在东京见到的神社相近的房屋,另一些较小的房屋则分布于石板路两侧。而建筑群的左侧有着一片伊万不知是否该唤其为庭院的区域,那里有着仅供一、两人并行的石板路,植物间摆放着零星的用于装饰的石头,植物栽种的位置以及植物种类明显经过了人工规划,但就植物的外形与生长状态来看,似乎又并未受到太多人为干涉,且与伊万游览过的日式庭院不同,那片区域不曾被矮墙包围,或准确来说,整个神社外围都不曾修建矮墙,导致神社与山林的界限较为模糊。
神社里的人不算多,除去穿着白衣红裤——伊万记得那套服装应该有着专门的称呼,但他忘记是什么了——的巫女们以外还有昨日伊万在三嘉原御所里瞥见过的佣人。
“由哥哥向伊万君介绍神社吧,”他们下马后樱说,“我得去为明日的祈福仪式做准备。”
待樱离开,菊一面带领伊万向神社内部走去一面说:“其实这里的建筑及建筑的功能与伊万君在东京拜访过的神社大致相同,最大的区别大约在于建筑风格以及犬舞见神——”当牠俩路过一座位于石板路旁的、内部放置着装有清水的石制水缸与长柄竹勺的凉亭时,伊万忍不住打断菊的介绍问:“我们不需要如拜访东京的神社那样洗手吗?我记得洗手是日本拜访神社的必须得做的一个环节。”
菊愣了愣,似乎为伊万的问题感到惊讶。“嗯,严格来说,那并非是进入神社的环节,而是祭拜神明的环节。”菊解释说,“今日伊万君并非来祭拜钤姬而仅仅是来游览神社的,不是么?而且钤姬,或者说犬舞见神社对这些用以表达对神明尊敬的行为不是特别在意。我不知别的地区的手水舍最初是为了什么目的而修建,犬舞见神社的手水舍出现的原因是为了便于外出归家的钤姬饮水,毕竟钤姬是犬,未使用人类形态时无法使用需要双手的井,而宏姬又认为仅为了饮水就得下山去藏田川太过不方便,所以才命人引来山泉水修建了手水舍,或按照那时的称呼,是犬飲。”菊顿了顿,微笑着说:“虽然对钤姬而言,化作犬形时只需一纵跃就能自神社前去藏田川边,但面对喜爱的对象,人们总忍不住替对方做些什么并让对方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吧。”
菊转步来到手水舍旁,大约是瞧出伊万对此话题感兴趣而打算进行更多的介绍。“不过如我提到过的那样,钤姬大部分时间都与宏姬住在三嘉原御所里,甚少返回神社,所以根据家史记载,犬飲很快变成了外出归来的巫女以及前来拜访神社的人们洗手洗脚的场所。”预料到伊万的不解,菊不等伊万询问就解释说:“那时人们普遍穿着草鞋,行走在土路上时下雨容易溅到泥浆,天晴则容易沾上尘土,所以即便仅在村庄内与村庄附近行走,人们的腿脚上也时常被尘土弄脏。而到了夏天,年龄幼小、容易跌进井中且受限于身高、力量而无法转动连轴把手的孩子们也会将水果洗干净后放进犬飲中冰镇再食用。”
“这倒是非常的——”伊万思索着能描述牠感受的形容词,几秒后牠放弃了并说:“——具有实用性。”
“是的。”菊肯定道,“到了交通变得更为便利、犬舞见与外界有了更多往来的镰仓时代,犬飲才受外来者的影响更名为手水舍,不过至今犬舞见神社的手水舍仍保留着诸多实用功能,例如夏季炎热时氏子们会坐在石沿上将脚伸进石缸外围的水池里纳凉,导致极少数拜访神社的外来者总是惊讶于此地的人们对神明不尊敬的态度。”
伊万必须承认牠也感到挺惊讶的,因牠完全无法想象夏季时拜访教堂的人们为了消除燥热感而脱掉鞋并将双脚伸进教堂前的装饰喷泉里,同时经过了菊的解说,牠明白了为何犬舞见神社里的手水舍修建得比牠在东京神社瞧见的手水舍更大,外围的水池边缘更高更宽。
菊向着手水舍前方的建筑走去,在路过对面的建筑时说:“那里是巫女的住所和社务所。由于犬舞见的人们至今仍实行的是妻问婚,所以与日本其它地区不同,犬舞见神社并不承办神道婚仪式。”伊万随着菊的介绍看向面朝石板路的、类似柜台的建筑,柜台后方的墙壁上悬挂着一些用绳子串连在一起的尖牙,那应该就是牠前日在藏田川町祭拜钤姬的人们手上瞧见过的御守,尖牙项链一旁也有着菊提到过的那种布制的、小方块状的御守。
“你们这里没有悬挂祈祷用的小木牌的大木牌吗?”伊万问菊道,抬手比划出三角形屋顶的手势,“就是东京神社里那种顶部有着屋顶的木牌。”
“伊万君说的是絵馬掛け吗?如我之前介绍的,钤姬不是那种需要依靠实现人们的愿望来获取信徒的神明,犬舞见的人们也没有向钤姬许愿的习惯,所以神社里不出售绘马,也没设置悬挂绘马的木牌。”菊说着神色里透出几分苦恼,“不过外来者有时会将项链、手链形态的御守当作此地特产的、形状特殊的绘马,许愿后将其挂在神社周围的树上或神社前那座钤姬的石雕上。也因此,巫女们隔一段时间就会向本田家家主提议禁止外来者拜访犬舞见神社。”
“听上去这里的巫女讨厌做额外的工作。”
“倒不是额外的工作惹恼了巫女,事实上,氏子和村里的孩子们通常将搜寻并清理被外来者错当绘马挂在树上或其它地方的御守当作一种考验眼力的游戏。惹恼巫女的是外来者总是无视她们的‘这是御守而非绘马,犬舞见神社不出售绘马’的解说以及‘请勿将御守悬挂在树枝或其它任何地方’的警告。”菊叹息着说,“这里是神乐殿。”牠在一座面朝石板路的部分是高至人腰的未修建障子的木台、后半部分是典型的日式房屋的建筑旁停下,“这里是举行神乐祭以及另一些小型祭祀、仪式的地方,例如丧葬或庆祝幼儿年满特定岁数的仪式。”
“年满特定岁数的节日?是那个——”伊万在脑中翻找土田太太告诉牠的节日名称,却发现自己根本记不起具体的名字,“——与数字有关的节日吗?就是那个会带小孩子去神社并给孩子吃糖的节日?”牠不确定地说,“我还特意去买过那种长条状的糖,它的味道倒不如它的外表那么精致。”
“伊万君说的是七五三[3]吧。我虽不曾吃过那种名为千岁饴的糖果,但我知道通常这种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食物都着重于将外观塑造得符合其象征的意义,而非着重于味道。”菊停顿一瞬,补充道:“或至少就我所知,犬舞见以外的地方是这样。不过犬舞见没有庆祝七五三的习惯,我们也不喜欢用虚岁来计算人的年龄。伊万君知道什么是虚岁吗?”见伊万摇头,菊便解释说:“简单来说,就是将刚出生的婴儿的年龄计为一岁而非零岁,因此虚岁的年龄通常比真实年龄大上一至两岁。”
菊带着伊万向神乐殿后方绕去,伊万瞧见时有抱着些牠不知名称的、大约是祭祀上将会使用的器物的巫女或仆从在神社各建筑间行走。“犬舞见只使用实际的岁数来计算人们的年龄。”菊继续介绍,“在孩子年满五岁的夏日,我们会统一举行庆祝他们活至五岁的、希望他们能健康成长的仪式。而犬舞见的女孩比男孩多一个节日,当女孩年满十三岁后我们会于秋季举行仪式庆祝她们的身体开启第二轮成长,仪式中她们会佩戴由一种名为くさぎ的、具有特殊香气的野草以及一种名为か的、亮红色的野果制作的饰品,仪式后还会吃下加有くさぎ的汁水、由か装饰的和果子,因此这一节日被命名为かくさぎ节。写作汉字的话则是菓芸节。”
伊万跟着菊走进那片人工规划过却又肆意生长的区域,“伊万君,瞧,这就是芸草。”菊指向石板小径旁一簇簇茂密的、高及牠大腿的灌木说,随后牠弯腰掐下一小截顶端较嫩的枝叶递给伊万,“伊万君不介意的话可以嗅一嗅芸草的气味。”
伊万接过芸草依言将其抬至鼻前,如菊描述的那样,这种植物的确有着一股独特的、牠从未在其它植物中嗅到过的气味,牠甚至无法以诸如甜、苦等词来形容钻进牠鼻腔里的气味,牠只知道那股气味能被称为好闻,嗅起来使牠心情愉悦。
“其实最初犬舞见虽有庆祝女孩初潮的习惯,可并未形成统一的节日,而是在每个女孩儿来初潮后由她的家人自行庆祝。不过自某代本田家家主在她的女儿来初潮后举行了较为隆重的庆祝仪式后,逐渐那个时日就变成了固定的节日。说起来,若菓芸节时我们恰巧留在犬舞见的话,伊万君就能旁观菓芸节的仪式了呐,那时不止是犬舞见之里的女孩儿,整个犬舞见县的女孩儿都会来到神社参加仪式。”
伊万留意到菊所说的“整个犬舞见县”,牠一边与菊沿着石板小径朝神社中最大、最精致的两栋建筑走去,一边好奇地问:“你们的领地里还有别的村落吗?我只听你们提起过这里和藏田川町。”
“还有位于被群山包围的湿原内的多鹤野村,位于藏田川支流的立石川沿岸的立石村等。虽然犬舞见县较日本其它县而言面积要小上不少,但犬舞见依旧被划分成了县啊。”菊说,牠带着伊万回到石板路上并停在石板路尽头,靠近后伊万才发现面前的建筑与东京神社所见的建筑在风格与构造上有着不少区别,例如面前这栋在伊万的印象中用于供信徒向神明礼拜的、等同于教堂中的十字架与耶稣圣像的建筑前方未摆放保存信徒们许愿时扔下的硬币的木箱。当然,在菊数次提及后,伊万不需询问也能推测出,犬舞见神社不在此处摆放保存许愿硬币的木箱的原因是钤姬不会也不需要实现人们的愿望,但既然如此,为何此建筑的屋檐下、房门前——伊万不知该如何描述那一��域,牠猜那一区域在建筑学中有着特殊的名称——依旧悬挂着巨大的铃铛与粗壮的、或是直直垂至地面或是横向系在房梁上的草绳呢?
“我已经能猜出你们这儿不放置那个用来储存许愿硬币的木箱的原因,可我印象中巨大的铃铛与垂地的草绳都是供信徒许愿后摇晃的,你们保留铃铛和草绳的原因是什么?”伊万问。
“为了与神明保持联系。”菊回答,“本坪铃、即这种巨大的铃铛在日本的宗教中有着神明能听见其响声的传说,日本其它地区的信徒在许愿、往赛钱箱内扔硬币后摇晃铃绪——铃绪是垂至地面的、供人们摇晃的草绳——的原因是因人们相信他们的愿望能随着铃声一同传至神明耳中。钤姬虽不会实现人们的愿望,但此地的人们仍有希望让钤姬知晓的事以及想要传达给钤姬的话语,因此神社里悬挂着本坪铃与铃绪。只是与其它地区不同,在犬舞见,仅有巫女拥有摇响本坪铃的权力,据说其他人摇响本坪铃后会遭遇不幸的事,本田家家史中也记载着几件不知真假的、外来者无视巫女警告偷偷摇响这里的本坪铃后因意外受伤乃至死亡的故事。”
伊万好奇那些故事的内容,但牠决定之后再详细询问菊,因根据过去的经验,若牠此刻就询问菊那些故事,那么最终话题会偏离向牠俩都无法预测的方向,以至于也许傍晚来临他俩都依旧站在原地闲聊。
“而且,与其说犬舞见神社保留本坪铃、铃绪,倒不如说赛钱箱并非是神道教、即日本本土宗教出产的器物,而是佛教传至日本后,神道教吸纳了一些佛教的传统。”菊继续介绍道,“至于横向系在房梁上的草绳的名字是注连绳,用以区分人居住的人间以及神明居住的神界,也就是说,注连绳之后的地方、即拜殿内部是属于钤姬的神域。”菊说着向拜殿——伊万猜菊口中的拜殿指的是面前这栋建筑,日本建筑的专属名称多到牠几乎感到恼怒,不过相对的,东正教教堂也有着许多关于建筑结构以及建筑本身的术语,所以牠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后方的那座被一圈木栅栏圈起来的建筑走去。“那里就是本殿了。本殿是神社中最为重要的建筑,其内供奉着被视作神明象征物的物品,通常是按照传说中神明外表雕刻的石雕,极少数情况中被供奉的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器物,例如分别被供奉于伊势神宫、热田神宫与皇居内的三神器八咫镜、草薙剑与八尺琼勾玉。”
菊停在拜殿与本殿之间的石板路上,伊万发现与牠原以为的不同,围绕本殿的那圈木栅栏没有被封死,而是建造了如牧圈门那样的可开关的栅栏门.“我们这儿的神社也属极少数情况之一,象征着钤姬的石雕就是伊万君在神社入口处见到的那座石雕,那也是整个犬舞见唯一一座钤姬石雕,据称是宏姬仿照钤姬犬形的外表雕刻而成。而本殿里被此地的人们供奉的是一个ちん。”
“ちん?”伊万用疑问的语气重复念出又一个牠听不懂的词。
“即陣。”菊说着在空气中写下陣字,“传说这个阵ふうい[4]——”牠停顿一瞬,“我是说,这个阵、即一种刻画在地面上的图案构成了一道门,而那道门将一些糟糕的事物,例如疫病、自然灾害、厄运等阻挡在另一个世界中,以让这个世界的人们拥有健康的身体、安稳的生活等。钤姬守护此地、守护整个日本的职能也因此而来。不过如我提到过的那样,最初本殿是供钤姬居住的房屋,这也是本殿不仅是建筑风格、连修建方式都与日本其它神社的本殿有区别的原因,因宏姬在修建本殿时考虑到钤姬拥有人与巨犬两种形态,故本殿不但修建得比通常应有的更加高与宽,本殿的门也选择了能用犬鼻顶开的双开铰链门而非推拉滑门。”
伊万抬头望向本殿的门,“���如本殿的门是按照钤姬作为犬的尺���修建的,那么她的体型比我想象得更为巨大,我还以为钤姬的体格与方才见到的那座石雕的大小是相同的。”
“关于钤姬的体格究竟有多么巨大有着不同的说法,在某些传言中,钤姬身形巨大如一座山,曾有过路人以为自己瞧见了一座突兀出现于绿色的群山中的雪山,结果定眼一看才发现那是蹲坐在地上的白色巨犬。而本地人相信钤姬犬形的体格比本殿更小些。至于在本田家家史中,据记载钤姬化作犬形时其实能随着她的意愿改变体格的大小,例如宏姬初次见到钤姬时,钤姬的犬形就是普通人类的大小,导致宏姬差点儿误以为自己遇见了一名披着狼皮却又在狼皮之上穿了层衣服的奇怪的人,而在日常生活中,钤姬倾向于化作比神社前石雕更大些的尺寸,那样她既能快速奔行于山林间,又能不受阻碍得出入本殿、三嘉原御所的母屋等建筑。”
伊万不知道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否算是对神明不尊敬,但依照菊的描述,钤姬听起来真的很像一只活泼的、喜爱四处跑动的狗,或至少,菊的描述让牠想起了奥尔加养过的那只名为波莉娅的西西伯利亚莱卡犬。
“钤姬死后,本殿就从钤姬的住所变成了供奉阵的殿,而宏姬悲痛于钤姬的死亡,颁布了禁止人们拜访、进入本殿的命令,除去她以及她的女儿錆姬能随意出入外,就只有巫女们能进入本殿以清理、维护这栋建筑,连尚未成为巫女的氏子也是没有进出本殿的资格的。”
“那么看来我是没有参观本殿的运气了。”伊万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是的,很抱歉,伊万君。”菊向伊万投来一个歉意的眼神,“其实里面也没什么好看了。就是空旷的、没有任何家具甚至没有铺畳的殿,与失去襖的间隔、能站在门边望见房间另一端的母屋相似,且由于门窗未更换成用玻璃代替和纸的新式障子,内部的光线远比母屋昏暗。”
“我猜宗教建筑都是这样。”伊万耸耸肩说,“为了营造出神秘感以让人们因未知而产生恐惧、尊敬,大部分宗教建筑都存在只允许极少数特定人员进入的区域。东正教教堂里就存在一个名为алтарь的、通常只允许最高等级的神职人员进入的非公共区域。”牠回想了一下与樱、菊一同游览过的尼古拉堂[5]的内部结构,“你还记得我们游览过的位于千代田区的那座东正教教堂吗?教堂最内部不是有面挂满了基督、圣母以及历代沙皇的油画的墙吗?墙后的空间就是алтарь。某年夏天回到领地中后,我和奥利娅曾趁着领地里教堂的神父不注意而偷偷溜进去过,结果失望的发现那只是个没有窗户的、弥漫着陈旧气味的房间,房间中间有一张其上摆放着黄金烛台以及另一些黄金饰物的桌子。说起来,明日的祭祀会在本殿举行吗?”
“不会。”菊摇摇头说,“只有新春祭祀会在本殿举行,而即便是新春祭祀,被允许进入本殿的也仅有樱、我和部分巫女。明日的祭祀仍是在神乐殿举行。”
伊万回想起菊方才说的神乐殿是举行一些“小型祭祀、仪式的地方”,深感自己的友人最不日本人的地方就是对待日本皇室的态度,牠打量着本殿,在抬头观察本殿的屋顶与木柱之间那些层层重叠的、形状特殊的木制结构时余光瞥见了位于本殿斜后方的建筑。
“那里是什么地方?”伊万以眼神示意着那栋大半部分被茂密的枝叶遮挡住的、瞧上去体积比神乐殿更小些的、所处水平位置比本殿更高但屋顶却比本殿更低的建筑。
“啊,那是——”菊刚开口就停了下来,牠微皱着眉露出思索的表情,“那是……该怎么说呢?那其实是本田家家主的住宅,没有特定的名称。”菊说着又止住话音且眉头皱得更深,正当伊万打算说“假如不便向我解释的话你什么都不必说”时,菊叹息一声并说:“得从头说起才能向伊万君介绍清楚。伊万君已经知道了作为本田家初代家主的宏姬是飞鸟时代推古天皇时期臣籍降下被赐姓本田的内亲王。”菊应是接收到了伊万神色里的疑惑,立即解释道:“内亲王是日本皇室女性的一种封号,等同于英语中的princess。飞鸟时代乃至其后的直到武家政权崛起的数百年中,日本的王权与神权是结为一体的,即日本皇室皆是神明的后代,而作为神明后代的他们天然拥有统治日本的权力。”
“这倒是与基督文明有着很大的不同,”伊万沉思道,“笃信基督的西欧、中欧、南欧地区很长一段时间中王权都不得不服从于神权。至于俄罗斯,因被蒙古入侵后古罗斯分裂成诸多小公国,且那些小公国一部分被金帐汗、波兰统治,一部分维持了独立,同时它们又相互征战,故莫斯科公国出现前有关俄罗斯的记载都混乱、模糊且难以考究。但根据流传下的书面资料来看,无论是信仰古斯拉夫教的时期还是罗斯受洗[6]后改为信仰东正教的时期,在俄罗斯境内,面对王权,神权从未拥有过压倒性的优势。”
“我想日本与西方在神权、王权方面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倾向于将其分离,而我们则将其融合。这也是即便明治天皇让我继承本田家爵位却依旧无法改变本田家的继承法则的原因,不仅是自宏姬开始的历代本田家家主的性别令此地的人们习惯并仅接受女性作为他们的统治者,将神权与王权融合的风俗也让人们天然偏向选择能与神明沟通的女性而非缺乏这种天赋的男性。虽然法律上樱没有继承爵位,不拥有统治犬舞见县这一自治区的权力,但在犬舞见县的人们眼中,樱从阿母那里继承了统领犬舞见所有巫女的、守护那道将厄运抵挡在另一个世界中的门的神职,因此拥有神职的樱才是此地真正的主人。”菊说着似被什么有趣的东西逗笑了,“当年确定本田子爵的继承人选后,尽管本田家以及家臣们在天皇的命令下引来一段较为混乱的、犹豫是否该用武力表示抗议的时期,但藩民们反而保持着混合了漠不关心和平静的心态,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天皇赐下的子爵之位还是版籍奉还后裕福国更名为犬舞见县、实施府县制后欲派人担任犬舞见县的县令等——顺带一提,明治天皇虽数次派人,可那些人皆在前来犬舞见途中患了重病而丧失了行动能力——都是外来者的玩意儿,而外来者的胡闹无法影响他们的生活。”
伊万纠正了自己几分钟前的想法,牠发现不止是自己的两名友人,受友人统治的本地人对日本皇室也持有与友人们相同的、不那么日本人的态度,
“拥有神职的、必须主持各类较为重要的祭祀的本田家家主在特定时期,例如祭祀时长为数日的新春祭时都非常忙碌,所以为了节省时间,她们会暂时居住在那座屋子里而非在三嘉原御所与犬舞见神社间往返并将时间浪费在山路上。不过那栋房屋最初却不是为了便于本田家家主主持祭祀而修建。”菊说着沿着一条通向山林的、终点应是那栋房屋的小径走去,“据家史记载,那栋屋子是宏姬在钤姬死后修建的,且直到宏姬逝世前,尤其是将政务交给她的女儿錆姬后,大部分时间她都居住于那处而非三嘉原御所。”
因菊行在伊万之前,伊万无法观察菊的表情,只能听见菊以一种音调无起伏但显然与平静有区别的语气说:“无法忍受看见喜爱之人的居所,即便那只是名义上的,也无法继续留在与喜爱之人度过了大部分时光的地方,可又情不自禁想要离喜爱之人的象征物更近些。我猜宏姬就是抱着如此矛盾的心态做出了封闭本殿、搬离三嘉原御所定居此处的决定吧。”
[1]障子
[2]襖
[3]七五三
[4]即ふういん,日语‘封印’一词的读音
[5]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собор (Токио)
[6]罗斯受洗
0 notes
Text
司馬中原
H:有很多作家,一輩子未曾買過其著作,中學卻讀過其作品,久久不能忘。司馬中原即是一例,作家於2024年1月4日往生,享耆壽90歲。20240105W5
網路報導:
2024年1月4日 週四 下午3:41國寶級鬼故事作家司馬中原(本名吳延玫)今天20240104傳出病逝,享耆壽90歲,五兒子吳融昊接受媒體訪問時證實此事。
司馬中原本名為吳延玫,1933年生於南京,1949年隨國軍來台。他在15歲從軍,並未受過完整正規學校教育,全靠自學與自修成為作家。在軍中歷任教官、訓練官、參謀、新聞官,1962年以中尉軍階退役後,就以寫作為志業。
維基百科介紹:
司馬中原,本名吳延玫,生於江蘇淮陰,之後原籍登記為南京,臺灣國寶級鬼故事作家、恐怖小說作家、繪本作家,有「鬼故事大師」之稱。 維基百科
出生資訊: 1933 年 2 月 2 日(90歲),中國南京市
著作: 荒原, 靈異, 遇邪記, 刀兵塚, 青春行, 中國吸血殭屍, 寄望昇歌, 六角井夜譚, 精神之劍, 寒食雨, …
本名: 吳延玫
中學國文
火鷓鴣鳥 司馬中原
火鷓鴣鳥的衣裳是用春天黃昏的雲剪裁的,深深淺淺的紫紅色,帶著一層層的斑紋。牠的形狀像鴿樓上飼養的鴿子,只是比家鴿小一些,看樣子,遠比家鴿精靈。牠的喙子泛著帶紫的亮紅色,眼也是,爪也是。有人管牠叫野鴿子,而我們做孩子的,都管牠叫七姑姑。
七姑姑,這名字是由牠的叫聲來的。
在春天,滿眼的柔綠鋪著地,也洗亮了天,群樹的綠蔭是一片油漆未乾的畫。這裡那裡,分不清有多少種鳥雀在喧噪,在歌唱,在嘲嘲喳喳地私語;其中只有一種鳥的聲音是最特出的,那就是火鷓鴣。牠的鳴聲並不嘹亮,卻是出乎意外地徐緩低沉,總是那麼迷離,那麼柔軟,彷彿多飲了春光,發為醺鳴,你分不清牠們究竟是唱出了快樂,還是唱出了哀愁?
一聲遞一聲的,七—姑—居,苦……,七—姑—姑—,苦……。那是牠們世代相傳,一成不變的調子,從古遠的日子起始,就這麼永生永世地唱下去,彷彿也有些歡樂,也帶些哀愁;正像那一野春天給人的感受一樣。
多霧的春晨,東天剛泛一些兒白,那樣的鳴聲便或高或低、或遠或近地流過來,透過蒼黃的紙窗,流進每一家低矮的茅舍,滴進人初醒的矇矓意識中,化成一股煙霧;或是如雲如絮地托起人的殘夢,在一片迷離幻境中蕩漾飄遊。你不知那聲音是來自地下,還是來自天上?
傳說火鷓鴣是一種心慈的鳥,在古老的年代裡,眼見著一個人稱七姑姑的老婆婆,孤苦無依,病死在頹圮的茅屋裡,就覺得世上缺少愛心和同情。牠們飛出巢,到處唱著「七姑姑—苦」,藉以告訴人們去埋葬那位老婆婆。牠們這樣一代一代地啼過幾千幾百年,日後還會這樣啼下去的。很傻的鳥兒,可不是?但當我初聽這傳說時,我曾經為那把無人收葬的白骨哭泣過,因而我知道火鷓鴣的兩眼為何總是紅紅的。初聽火鷓鴣的啼叫,原來在心裡多了一股軟甜甜的感覺;聽了這傳說之後,便覺得有些沉沉的愁了。
無力去收葬千百年前的骸骨,總該抓把糧食撒在林邊,餵一餵這些癡心的啼鳥罷!在鄉野的鳥的世界裡,火鷓鴣是最得人關注的,因為人人在做孩子的當口,都聽過那段故事。
也許從那事發生後,火鷓鴣就不再像馴鴿似地信靠人類了;只要有一個人影兒落在牠們的眼裡,牠們就展翅飛遁到遠處去,驚疑懼怯,不敢落下來就食。
我曾匿伏在林裡,看見牠們落在撒糧地方,輕靈地掀尾跳動著,或是緩緩地踱步,一隻、兩隻……,無論幾隻聚在一起,牠們都是相親,和睦的,不像麻雀那樣吱喳地爭吵,烏鴉那樣粗野地張口啄架。牠們是天上落下來的,一朵一朵小小的祥雲。

0 notes
Text
初見美國
藝文上下古今
立青
2023-12-25
在八○年代飛到了華府,抱著朝聖的心情,先後參觀了國會大廈、白宮、林肯紀念堂、傑佛遜紀念堂和太空科學館,再到阿靈頓陣亡將士紀念碑致意,一股腦地將對美國的民主、自由、科技和英勇的象徵性景點,一一走了一遍,完成多年來對美國的嚮往。
好友張大哥並不住在華府,而是附近馬里蘭州的一個小鎮,大約半小時的車程,一路大樹成林綠草青青,一排排的平房座落在白漆圍籬內,顯得格外安寧。晚餐是當地的特色「海鮮吃到飽」,聰明的老中自備醬油、麻油、醋等調料,雖然是大排長龍,但可讓我大飽口福。
次日的購物又讓我大開眼界,兩層的大樓堆滿各式百貨,應有盡有,我也如願地買到了一頂西部牛仔帽,又是圓了一件美國夢。美國的公路超寬,汽車是台灣的半價,當時汽油每加侖不到一美元,真是開車的天堂。
此行計畫是拜訪中西部的工廠,路程不算近,三個人的機票、酒店、落地後的交通所費不貲,盤算後決定驅車前往。我特高興,一路有機會開車,又可以看到和經歷到我心裡希求的目標。先到「汽車協會」去索取免費的地圖,以了解最近最方便的路徑以及沿途的狀況。資料顯示是約十二小時七百哩的行程,吃過晚飯出發到目的地,正好是早晨上班時間。
離開繁榮的馬里蘭州,進入維吉尼亞州,走沒多時樓房和住家就稀落得多,取而代之的是寬廣的草地和頗具規模的莊園,維多利亞式的建築非常雅緻,瞬間將我帶入電影「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場景,幾隻雪白肥胖的綿羊點綴在翠綠的草園上,真美!
不多時天色已暗,感覺上地勢漸高,路標顯示已進入西維吉尼亞州,印象中是個礦區,電影「礦工的女兒」(Coal Miner's Daughter)和歌曲「鄉村路帶我回家」(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都有相當細膩的描述。公路往來都是雙車道,中間是寬闊的分隔草地,路上沒有其他車輛,只有我們一輛車摸黑前駛,顯得如此的孤單。
突然間前方警車燈火大亮,在黑夜中非常突兀,嚇得我立刻踩住煞車以為超速被逮。霎那間只見一片黃影在眼前閃過,張大哥說:是鹿!若被撞到就是車毀人亡。慢速駛過警車,揮手致意感謝,前後不到三分鐘,卻歷經生死,不勝感慨。
公路邊除了餐飲和加油站,就沒有任何商店,餐飲業不外漢堡、熱狗和披薩,飲料只有咖啡和汽水。加油站除了加油,還有維修和雜貨買賣,物價比較貴,號稱「公路強盜」,兩者都提供最重要的服務:廁所。想要住宿和吃頓大餐,就必須駛出公路,進入市區的商業街道才有。
踏入肯塔基州已近拂曉,天光微亮金色的朝陽,照在薄霧的廣袤草原,景色怡人,抬頭望見公路的招牌「藍色茵草公園公路」就已說明一切。路邊白色的欄柵裡,已都是大大小小各色的馬匹,悠然自得好不令人羨慕。附近的「德比賽馬場」是世界級的賽馬場,可惜時序不對,只能空手而歸。
到達鮑靈格林(Bowling Green)已超過十二小時,因有時差追回一小時,符合計畫皆大歡喜,到早餐店用餐,漱洗整裝出發,準時到達目的地。該工廠生產跑車,外殼是玻璃纖維製成的,不會生鏽,適合熱帶多雨地區,工廠之附責裝配,零件製造還要到田納西州的納許維爾機械工廠去參觀。
雖然隔了一個州���實際距離只要半小時。到了工廠見到主管,���談甚歡。完成階段性任務後,一想這不是「鄉村音樂之都」嗎?沒錯!滿街都是唱片製作相關的店面,到處都能聽到鄉村音樂,大家都興奮極了。時間正好是下班的快樂時光,衝進一家現場樂隊表演的酒吧,叫了啤酒聽著音樂,這種忙中偷閒的公差真是爽歪歪。
回到鮑靈格林想找家「肯德基炸雞」並不容易,也許本地人已經吃膩了。在肯州大學附近找到「金龍飯店」中國菜,門口安置了一尊關公像很有特色,老爸掌廚、老媽櫃檯、兩個小孩跑堂,樓下開店樓上住家其樂融融,典型第一代移民生活的寫照。我們分別點了牛肉、雞肉和蝦,端上來全都一個樣,張大哥說,在中西部能吃到醬油就不錯了。
約八點鐘打道回府,原路向東直行,到十二點錯過加油站路口,不想回頭繼續向前。四十分鐘後,油箱已漸到底,警告聲咚咚不停,緊張流汗之際,總算看到油站招牌。轉進後一片漆黑,停到加油機旁大燈直射,忽在暗處屋內聽到擴音機有人說話:「全部下車站著別動,派一人過來,十點以後只收現金,我有獵槍對著你們!」張大哥以三倍價錢裝滿油箱後,快速逃離,總算見識到誰才是公路強盜。
一身冷汗過後,大家發現肚子其餓無比,加油站的販賣機只有汽水和糖果棒不管用,一路下山真是飢寒交迫。絕望中在漆黑的夜裡,一道光芒紅底金色拱橋的燈光,表示麥當勞在此,二話不說立刻衝入,漢堡、薯條、蘋果派加上熱咖啡,吃到嘴裡千金不換,這美國國民餐點,卻有救命之功。
回家的路是下坡,行雲流水般地飛馳,沖散了清晨的薄霧,遠方地平線升起一到破曉的金光,又是美好一天的開始。路邊的建築物逐漸增加,顯示將進入市區,我卻陷入沉思,這即將結束奇妙而刺激的旅程,讓我確定是否留在美國繼續發展的最大動力。
0 notes
Text
各地句会報
花鳥誌 令和5年11月号

坊城俊樹選
栗林圭魚選 岡田順子選
………………………………………………………………
令和5年8月3日
うづら三日の月花鳥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思ひ出はねぶた祭りの鈴の音 由季子
居合はずも気配感じて墓参り さとみ
小さき手の祈る姿や原爆忌 都
新刊にしをりはさみし今朝の秋 同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5年8月5日
零の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夏蝶の影夏蝶の見当たらず 和子
夏帽を墓誌にぱさりと一礼す 小鳥
炎帝の甘い息なり草いきれ 和子
ビルとなく夏草となく墓となく 千種
墓参直方体の石たちへ 緋路
刻む名のなき墓石の灼けてあり 和子
十字架の寝墓を埋めし夏の草 美紀
空蟬を俯きにして走り根に 要
炎天にかつて士族は墓じまひ いづみ
岡田順子選 特選句
睡蓮の影睡蓮の葉に揺るる 緋路
利通の墓へ鋼の夏日かな 俊樹
墓参直方体の石たちへ 緋路
葬列の中のたじろぐ黒日傘 三郎
あふひ句碑墓域にありて百日紅 佑天
奔放で供花ともならず猫じやらし 荘吉
青山の水に肥りし金魚かな 美紀
夏草に陋屋のごと耶蘇眠る はるか
立ち枯れの草より薄き八月の蝶 和子
イザベラの墓へ絵日傘高く上げ 小鳥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5年8月5日
色鳥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金灯籠灯の曼陀羅をよへほ節 美穂
盆灯籠十万億土超ゆ君へ 久美子
流燈の火の川となり闇に浮く 孝子
流灯の破線となりて彼の世へと 睦子
行く夏や波に消えゆく砂の山 修二
家紋古る釣灯籠に代々の火を 久美子
黒髪に戴く山鹿灯籠かな たかし
シヤンデリア墜ちてはじまる夏舞台 睦子
縁日やうすものの母追ひ越さず かおり
ダリア立つ背に御仏のおはす如 勝利
炎帝を睨み返せし不動尊 かおり
戦争を知る人とゐて沙羅の花 朝子
恋に堕つ日々はまぼろし星月夜 美穂
風天忌しがらみ捨てて西東 修二
思ひの外長く連れ添ひ夕端居 光子
あの雲の八月六日兄の背に 朝子
河童忌やセピア色なる供華の水 睦子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5年8月7日
花鳥さざれ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九頭竜に天蓋として秋の空 かづを
饒舌を寡黙にしたる猛暑かな 同
老い包む羅にある粋を着て 同
絽の喪服広げて暫し母偲ぶ 笑
海上を照らし消えゆく花火舟 同
羅に心の綾は隠し得ず 雪
絽の美人正面見すゑ瞬かず 泰俊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5年8月8日
さくら花鳥会
岡田順子選 特選句
鳳仙花記念写真のまた増えて 裕子
秋薔薇キリスト葬は花のみに 令子
図書館の絵本を借りて秋の朝 実加
秋初め装丁だけで選ぶ本 登美子
褪せ果つるトーテムポール夏の月 同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5年8月8日
萩花鳥会
広島の原爆殘害眼前に 祐子
盆提灯座敷一変かの浄土 健雄
ひぐらしがよう帰ったと里日暮れ 俊文
七夕や家族揃うてバーベキュー ゆかり
庭野菜取りたて供ふ盆支度 恒雄
ひと日生く古稀の我また花木槿 美惠子
………………………………………………………………
令和5年8月9日
鳥取花鳥会
岡田順子選 特選句
化粧水嫁にねだりて生身魂 すみ子
立葵老女の夢は咲きのぼる 悦子
棚経を待つ朝よりの野良着脱ぎ 美智子
水脈長く長くや土用蜆舟 都
縁台の仰臥は浮遊天の川 宇太郎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5年8月12日
枡形句会
栗林圭魚選 特選句
烈日の寺の甍や蟬時雨 亜栄子
白粉のゆふぐれ匂ふ句碑明かり 文英
達者なる日を百歳の生身魂 同
好物に笑顔は童生身魂 恭子
小湾の潮香満ち足る島の秋 多美女
ビートルズ聴きつうたたね生身魂 亜栄子
草々に水やり終へて今朝の秋 恭子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5年8月14日
なかみち句会
栗林圭魚選 特選句
打水に乾きし土の匂ひして 迪子
蜩の声に憶ふは奥貴船 貴薫
新涼や虚子文学碑なぞり読む 怜
蜩や今日の仕舞ひにジャズを聴く 貴薫
新涼の風運び来る水の音 三無
蜩の声に包まれ森深き 秋尚
新涼の風運びゆくミサの鐘 怜
直したる服受け取りて涼新 貴薫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5年8月14日
武生花鳥俳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耳に残る脱穀の音終戦日 昭子
大都市の火の海と化し終戦日 みす枝
薄れゆく記憶手繰りし原爆忌 英美子
俗論をまた聞かさるる残暑かな 昭子
喜んで逃げる爺婆水鉄砲 みす枝
しみじみと肩甲骨や更衣 昭子
夫の船べりを掴みて鮑海女 同
桐一葉風の意のまま落ちにけり 英美子
どの墓も供華新しき盆の寺 信子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5年8月16日
伊藤柏翠記念館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火取蟲てふに一夜を果つ定め 雪
考へず居れば済むこと髪洗ふ 同
花火果て破に残りし余熱かな 真喜栄
漆黒の闇に銀漢ふりかぶり 同
百日紅又百日紅てふ団地 清女
それとなく秋を呼びゐる風の音 かづを
九頭竜の闇を沈めてゐる銀河 同
ゴジラ似の雲立ち上がる原爆忌 嘉和
地獄より来る祖もありぬ盂蘭盆会 世詩明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5年8月16日
福井花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啼く声の細くとぎれし法師蟬 啓子
足さばき揃ひよせ来る盆踊り 笑子
灯籠に女心の一句添へ 希子
流灯の仏慮の風に促され 同
球児等もスタンド席も灼けてゐし 和子
地図上に台風の道あるらしく 同
盆の月古城の上にまかり出る 隆司
吟行も供養の一つ盂蘭盆会 泰俊
故郷の色町とほる墓参 同
表情のはみ出してゐるサングラス 雪
頷いてばかりも居れず生身魂 同
月夜の踊り雨夜の踊り見しと文 同
何となく日向水ある日向かな 同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5年8月16日
鯖江花鳥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蝿叩きにも自らなる居場所 雪
頷いて居れば安泰生身魂 同
火を恋ひし火蛾の果てとはこんなもの 同
狙ひたる金魚に又も逃られし 同
音もなく傷も付けずに流れ星 みす枝
蜩の声が声呼び森震ふ 同
偕老に二本つましく牽牛花 一涓
来世又君に逢むと墓参 世詩明
夏まつり村の掟は捨て難し 同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令和5年8月18日
さきたま花鳥句会
鳳仙花迷路のごとき蔵の街 月惑
天高し殿堂入りの行進曲 八草
夕まずめ途切れ途切れに法師蟬 裕章
あの人に会ひたくなりし天の川 紀花
座の窪きまり南瓜のおほらかに 孝江
朝の厨一分間の終戦日 ふゆ子
夜咄やはたと団扇の風止まる とし江
炎暑寺水鉢かつぐ鬼を吸え 康子
一夜あけ光の洗ふ野分後 恵美子
尺玉の花火の弾け音弾け みのり
強風に七夕飾りもつれけり 彩香
………………………………………………………………
令和5年8月20日
風月句会
坊城俊樹選 特選句
裏返り空を見詰むる秋の蟬 秋尚
校庭の空を奪ひし秋茜 経彦
大空に機関車の缶灼けゐたり 幸風
菩提樹を絡めとりたる葡萄葛 同
なびき癖各々違へねこじやらし 秋尚
山城の搦め手いづこ野路の秋 眞理子
一葉落ち青空丸く生まれたる 三無
栗林圭魚選 特選句
TARO展残暑を赤く塗り潰す 千種
おしろいの紅固く閉ぢしまま 秋尚
横山に行合の空今朝の秋 幸風
校庭の空を奪ひし秋茜 経彦
水被り残暑の石の獣めく 千種
たくさんの水飲み干して夏果てり 久
わが息の荒さをしづめ秋の蟬 千種
秋の蟬力惜しまず昼を裂き 三無
噴水の歪みもとより秋暑し 千種
妣の声聞きに葉月の恐山 経彦
(順不同特選句のみ掲載)
………………………………………………………………
0 notes
Text
金門823砲戰
轟雷計畫/八二三砲戰局的8吋屨帶式自走榴彈砲/自枋寮登陸/進駐高雄棒球場/送到金門的料羅灣/王道夷,江崇武,周孝煌三位艇長/
陳定宇,海軍小艇隊,預官27期,逢金門823砲戰前夕,寫于紐約,70歲紀念!
民國47年9月17日漆黑的深夜,三艘噸位僅約280噸的"合"字号戰車登陸艇(LCU),在澎湖外海強勁的東北季風吹颳下,海面一片波濤洶湧,但三艘艇慢速有序的進入美國海軍的兩棲登陸船塢艦山貓号( LSD Catamount ), 這是一艘總排水近萬噸的運載登陸艦艇的母艦,此刻,這艘母艦的任務是要將這三艘艇運送到金門的料羅灣。這項任務是攸關金門全島近十萬軍兵的生死,乃至於中華民國存亡的重任!因為三艘艇上所裝載的是能扭轉八二三砲戰局的8吋屨帶式自走榴彈砲。
自從中共在8月23日傍晚發動全方位對金門及附屬離島發動砲擊開始,金門守軍就被全面壓制,從美國已解祕的第二次台海危機資料顯示,砲戰開始的兩週內( 8/23-9/5日 ),中共打了127,973發砲彈,而我方總反擊量僅27,381發,而且有4天居然一發都未反擊。在這種劣勢下,國防部長俞大維強烈要求美方批准他多年以來申請的8吋自走式榴彈砲,美方本無意因重型武器支援台灣而破壞兩岸均勢,但兩位美軍顧問在砲戰發起時的犧牲及輿論態勢的發展,美方不得不同意立即將六門編配於美軍駐琉球的陸戰隊的8吋砲,借給台灣。
這六門巨砲,由美艦運送自枋寮登陸,直接進駐高雄棒球場,我方被選入操控這些巨砲的是第八軍團砲兵607 已兵營第一連,因為該營是當年全陸軍砲兵首屆金像獎射擊比賽冠軍,同時,因為是屨帶式自走砲,許多裝甲部隊技術士官加入,經過美軍一絲不苟的要求下,砲兵連苦練戰技僅一週就完成換裝訓練,能熟练地操作巨砲,而整個運動場被履帶車,縱橫奔走,蹂躪至慘不忍睹。與此同時,海軍與第七艦隊立即著手此一將這些巨砲由小艇乘大艦的計劃,獲得第七艦隊司令畢克莱( Wallace M. Beakley)中將的同意,黎玉璽指派登陸艦隊司令林溥負責計劃執行,經兩晝夜,"轟雷計畫"完成。接著就是"合"字号戰車登陸艇隊和美方船塢艦(LSD)的裝載訓練,特別是夜晚在燈火管制下進出母艦,以及在母艦航行中進出船塢,狹窄的船尾塢門,海上的強風和湧浪考驗艇上每一官兵的技術,體力。另外,搶灘,退灘,裝載,下載,編隊都要在最短時間,訓練完成。
先總統蔣公完全瞭解這一計畫的成敗攸關台灣存亡,從《黎玉璽回憶錄》上,寫著蔣公從計畫著手硏究到第一次執行完成,全期十六天,各項細節詳細垂問,各種操演如重砲裝卸操作及搶灘演習,他都親臨灘頭。他在十二日一個夜晚,到灘頭觀看並召見三位艇長,給這些約二十二歲中尉們莫大的鼓勵,王道夷艇長說:只要我人不死,船不沉,我一定達我任務!
美軍為確保任務的保祕性,特別安排將一艘與LSD17山貓号的同型艦LSD22 Fort Marion,改漆舷号為LSD17,當山貓号從馬公航向金門時,假的山貓号回馬公,而誤導中共情報人員。
十八日的晚間,船塢艦山貓号抵達料羅灣外十二海浬的水域,開始浮水作業,三艘合字号,合昇、合永、合川,出了母艦後,全速衝向灘頭,此刻,艇内的砲兵也發動屨帶式自走砲,裝彈藥和器材的兩輛卡車也啓動引擎,就等船衝到灘頭,艇的大門一開,將砲車駛向安置好的砲位。
中共的砲火完全覆蓋着衝向灘頭的最後航程,雖然,海軍已安排許多漁船,携帶大片的鋁板成為雷達的目標,減少三艘艇被砲火命中的危險,但滿天飛來的砲彈呼嘯,猛烈無比。船身隨震波搖滾不止,熾烈的砲火籠罩在船的四周,更要命的是,濃煙、火光、水柱遮掩了灘頭的白色登陸誌和兩側雷區的紅色燈標,合永艇艇長江崇武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他從望遠鏡中在煙塵濛濛的海岸際看到一盞白燈及兩盞相距很近的紅燈,也只是一瞥而已,在一陣爆炸後就熄滅無踪,只剩一盞紅燈,驚的他一身冷汗,他立刻向左修正航向,憑藉剛才看到的大概白燈位置衝去,當船躍過第一道白色激浪時,江崇武知道上了灘頭,立刻下令拋後錨,當錨鋼索放到350 呎時,船身猛然一挫,船己穩穩地搶上灘頭。船艏的登陸跳板也立即平搭在海灘上,而此時,猛烈的砲火也達到了最高潮,船四周似乎都是不停息的水柱。、
8吋砲組的指揮官從砲車上露出身子,江艇長給他一個前行手勢,砲車隨即響起一陣引擎的怒吼,這座龐然大物的砲車,昂著粗重砲管,像一隻無畏的怪獸,屨帶輾過甲板擦迸出火花,從船艏躍向灘頭,緊隨其後的彈藥車,裝甲人員及器材車,如一條鋼鐵火龍,衝向火海,無畏無懼,視死如歸!
王道夷、江崇武、周孝煌三位艇長都完成任務,拉起錨索,退出灘頭,順利回到母艦。據金防部的灘頭落彈量報告:登陸的八号灘頭,共落下二千發,誤差為5%,至於海上及空中爆作則無法計算!整個轟雷計畫共完成四次運載登陸,十二門巨砲運抵金門(有一次砲車觸雷屨帶損毀),九月二十六日下午16:30所有巨砲首次射擊,50餘發炮弹,每一發重達180 磅的威力,造成中共陣地及民用設施極大的破壞。
今天逢八二三紀念日,記下一些關於這場戰役的讀書心得,特別是王道夷艇長,他是我在服海軍預官役時的海灘總隊上校總隊長,儀表出眾,可惜是限官班而非官校畢業,昇遷機會有限,不過他因運砲任務成功,得了七等雲麾勳章也不容易!
陳定宇,海軍小艇隊,預官27期,逢金門823砲戰前夕,寫于紐約,70歲紀念!
0 notes